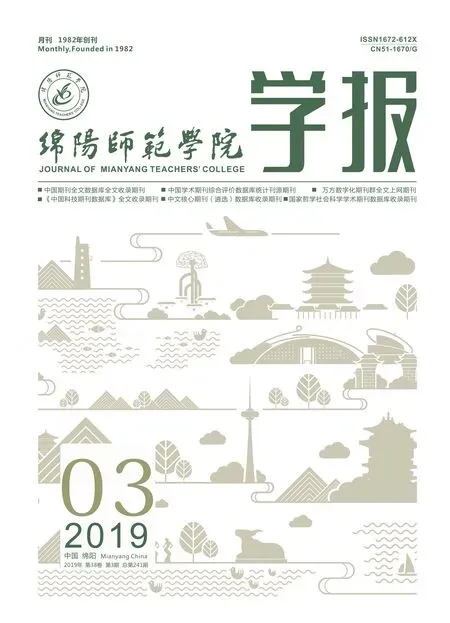對伊格爾頓《理論之后》的理論反思
劉 琴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南充 637000)
2003年,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一書問世,這本薄薄的小書開篇第一章便宣告“文化理論的黃金時期早已消失”,以一個撥開重重迷霧,登高望遠的勝利者姿態睥睨當下的文化現狀。這一審判官式的宣言在知識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使“任何在20世紀末文化戰爭的學術前沿參與論爭的人都會豎起耳朵”[1],也是到目前為止,伊格爾頓的“學術生涯中引發最多爭議的一本”[2]246。那么,此書到底在哪些方面刺激著當代人文學者的神經?又為何會成為“引發最多爭議的一本”?
在《理論之后》(After Theory)[3]的前言部分,特里·伊格爾頓說:“此書主要為對文化理論現狀感興趣的學生和一般讀者而作,但我希望對這一領域的專家們也會有用,其重要原因是它駁斥了我所認為現今正統的文化理論。我認為:正統的文化理論沒有致力于解決那些足夠敏銳的問題,以適應我們政治局勢的要求。我將努力闡述其原因并提出補救措施。”這幾行簡短的文字可謂是對此書宗旨的明確闡述,簡潔的文字卻包蘊著大量信息,如什么是“現今正統的文化理論”?正統的文化理論沒有致力于哪些“足夠敏銳的問題”?文化理論要適應什么“政治局勢的要求”?
要弄清什么是“現今正統的文化理論”,就必須對“文化”和“理論”兩個詞加以界定。在《文化的觀念》(The Idea of Culture)[4]一書中,伊格爾頓寫道:“英語中,culture這個詞的原始意義就是耕作(husbandry),或者對自然生長實施管理”,“‘文化’最先表示一種完全物質的過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過來用于精神生活。于是,這個詞在其語義的演變中表明了人類自身從農村存在向城市存在、從農牧業向畢加索(Picasso)、從耕作土地到分裂原子的歷史性的轉移。用馬克思的說法,文化這個詞語使得基礎與上層建筑在一個單一的概念之中得到了同一”[5]1-2。“文化”最先只表示一種物質的過程,而后才指涉精神生活。“文化”一詞的含義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而變化,人們的文化觀念也隨著社會生活的改變而改變。“到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也逐漸意味著電影、形象、時尚、生活方式、促銷、廣告和通訊傳媒”[6]26,“愉悅、欲望、藝術、語言、傳媒、軀體、性別、族群,所有這些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文化”[6]39,“文化”在伊格爾頓這里,涵蓋了從陽春白雪的高雅藝術到庸俗膚淺的社會生活。“文化”成為一個籠統的包含一切人類精神活動及其活動產品的萬能詞。
“‘理論’是一個松散的和包羅萬象的術語,通常用來指受結構主義,特別是后結構主義的影響而產生的論述人文學科的學術話語”[1]54,而伊格爾頓所說的“理論之后”的“理論”應該被理解成帶引號的和以大寫字母“T”開頭的“理論”,也就是理論的“理論”,即以“文化”和“文化理論”自身為批判對象。弄清“文化”及“理論”的概念之后,“理論之后”的意旨也就不難理解了。它并不是“理論”之終結,也不是“反理論”,而是對“理論”的反思,“是對理論再次進行富有雄心的思考,以便它有能力再度理解宏大敘述”[2]247。那么,理論到底需要反思什么?
伊格爾頓認為,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式。那批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偉大理論家,如威廉斯、克里斯蒂娃、德里達、杰姆遜、賽義德、拉康、列維·施特勞斯、阿爾都塞、巴特、福柯等相繼過世后,新的一代理論家還未能拿出可與前輩們比肩的理論作品,因此,文化理論陷入了青黃不接的處境。然而,我們處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下金錢至上的商品化時代,我們需要對理論進行反思,反思當前的社會制度,反思人類文明的根基,反思存在的價值,反思真理、德性等一系列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命題。
值得欣慰的是,現今的文化理論取得了一定的歷史性進展,如對性、大眾文化、后殖民理論、女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新主題的研究。伊格爾頓指出“在一批略顯狂野的學者身上,對法國哲學的興趣已經讓位于對法式接吻的迷戀。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遠遠要比中東政治來得更令人著迷”[6]4,“西格蒙·弗洛伊德認為,要不是有了他所謂的現實原則,我們就會整天躺在家里,雖然感到有點丟人,但仍干著銷魂的勾當”[6]7,“文化理論現今的表現就像一位獨身的中年教授,不經意間與性邂逅,正在狂熱地彌補已逝的青春韶華”[6]6。這些語言雖然有些夸大其詞,但的確針砭時弊。對“性”文化的研究,確立了性欲作為人類文化基石之一的學術性地位。文化理論的另一歷史性進展就是確立了大眾文化值得研究。傳統文化理論一直以來對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視而不見,但如今研究對象已從晦澀難懂的理論和深不可測的文學作品轉向到瑣碎的日常生活,因為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就是文化本身。除了“性”和大眾文化,文化研究最熱門的就是所謂的后殖民研究。“后殖民理論首先發軔于第三世界國家獨立自主失敗之后,它標志著第三世界革命紀元的終結,以及我們現在所知的全球化的晨曦。”[6]10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研究中心從革命轉到民族和階級再轉到了種族,而種族主要是文化事務,注意力也就從政治挪到了文化,畢竟文化是“保持激進政治生機勃勃的一種方式,也就是用其他方式來繼續進行激進的政治。”[6]45,于是“文化政治學”就此誕生。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把現代性、民族國家、知識生產和歐美的文化霸權都同時納入自己的批評視野,從而開拓了文化研究的新階段。
文化理論雖然取得了上述成績,但仍舊沒有關注到那些“足夠敏銳的問題”。讓伊格爾頓憂心忡忡的是,“人文科學已經喪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在自詡不受權勢的玷污。它如還想繼續生存,停下腳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擔當的責任(assumption)就至關重要。正是這種批評性的自我反省,我們稱之為理論”[6]27。文化應該擔當怎樣的責任?伊格爾頓指出,文學藝術講的是價值的語言,而非價格的語言;藝術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做一個獨特的個體。在市儈實用主義、工具理性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提醒我們作為“人”的存在。人文學科或“文化”,是敏感地顯示現代性整體危機的所在,它涉及禮儀、社群、想象力的創造、精神價值、道德品質以及生活經驗的肌理,所有這些都陷入了冷漠無情的工業資本主義重圍之中。理論仍舊沒有關注到那些“足夠敏銳的問題”,例如對真理、德行和客觀性的思索;對現今建立在人類剝奪的非存在之上的政治秩序的質疑;對革命、基礎和基要主義者的思考;對死亡、邪惡和非存在的探索。所有這些都是事關人類生存最具普遍性和終極性的問題,但理論沒有履行它的義務,反思成為它的當務之急。
理論沒有解決它本應解決的許多根本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理論無用。這是可笑的市儈實用主義,或清教徒式的信念:即任何無用的、不會馬上產生現金價值的東西都是一種罪惡的放縱。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反對理論”的理論成了激進思潮中引人注目的趨勢。理查德·羅蒂和斯坦利·費什認為,理論的作用不過是為人們的生活方式提供各種理由,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理論不僅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且也不可能、不需要為生活方式提供解釋,我們需要的僅僅是照自己所做的去做。哈羅德·布魯姆認為,將文學“理論化”的企圖忽視了文學是不可呈現的這個關鍵問題,如果你在閱讀的時候不能認出它,那么就沒有人能夠在幫助你了解它或者更好地愛上它。蘇珊·桑塔格認為,解釋不過是心靈的有意識的舉動,它所說明的是解釋的某種編碼、某些“規則”;解釋破壞了由各種感性內容構成的藝術和藝術作品,它把藝術變成了可供使用的文章和各種范疇的內心規劃的安排。在闡釋學中,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藝術的情欲,而不是概念化的解釋。總之,反對理論的理論把理論的抽象和概念化看作是生活世界、藝術世界、不可為理性把握之物的對立面。理論是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和藝術世界的牢籠。理論的危機正讓文藝學研究經受新一輪的話語洗禮,也預示了當下文藝學研究正經歷某種動蕩,甚至是大的轉折。但當前文藝學研究中對理論危機的解讀和應答也是非常含糊的,各種闡釋間隔和縫隙也暴露了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是對“理論盛宴”的額手相慶,還是對“理論危機”的悲觀消沉,都體現了理論知識生產與價值更替變幻多端的格局,同時也反映了我們理論研究中的一種尷尬處境。
冷戰結束后,全球化進程在思想文化領域似乎并沒有帶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恰恰相反,在意識形態領域,在批判和想像力方面,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種單一化和保守傾向,是實證主義和經驗論。反理論的思維一方面似乎是延續一種“終結者”的思維方式,從“上帝已死”“作者已死”“哲學的終結”“歷史的終結”到最近的“理論已死”,眼下的全球化進程的時代一方面缺乏理論激情、理論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顯地需要理論。理論是否“已死”?理論又能“何為”?是否20世紀理論運動自身也形成了一種體制化、經院哲學化、官僚化傾向,迫使新一代尋找新的理論生長點?
在今天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完全拒斥理論的學術路徑是很難想象的,因為理論已然滲入了各個學科和研究領域,即便口頭上反理論的人,其實也不得不接受許多“理論”帶來的學術前提和思想前提。用理論來反“理論”,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在理查德·羅蒂和斯坦利·費什這類反理論者看來,文化批判徹頭徹尾就是一場鬧劇,因為文化之間根本不存在評判的理性基礎。要發動文化批判,我們必須要站在我們所處文化之外的那個不可能的阿基米德點上。對批判者而言,要抓住自己的頭發跳出自己的文化顯然是十分荒唐的。更何況盡管文化無所不在,但它卻并非形塑我們生活最重要的東西。”[7]126“你不能用理論來證實自己生活方式的正確,因為理論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文化并沒有任何理論基礎。文化就是文化。”[6]53-54正如伊格爾頓在《批評家的任務》里所說:“我經常指出一個令人覺得諷刺的現象,即理論家剛一宣布歷史終結,歷史就立刻以‘反恐戰爭’的復仇形式歸來,宣揚歷史終結的理論家被弄了個措手不及……宣告歷史終結實際上再次激勵了歷史,這在歷史上有過先例:黑格爾宣告歷史終結,受到了克爾愷郭爾、馬克思等人尖銳的反駁。又正如藝術先鋒派,以試圖關閉歷史之門的行為打開了歷史之門。”[2]246因此,“理論之后”并非“理論之死”,更不是“反理論”,而是對既有的理論進行解構與反思,并鳳凰涅槃般重生。
那“理論之后”理論到底該何去何從?是向舊的形式妥協,新瓶裝舊酒還是徹底打破老套的思維框架,對理論進行重塑?很明顯,在一個不斷變更得更膚淺的時代,文化理論必須發明全新的寫作方式以適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宏大敘事以及隨之而來的破壞性反應席卷全球的政治局勢。
為探究理論重生之路,我們先來看看理論自身的限度。
其一,激進的文化理論一味地艱深晦澀,這不符合文化理論民主的本質。在《批評家的任務》一書中,伊格爾頓說:“激進知識分子有責任深入更廣泛的選民,或者,至少要讓支持自己的選民可以理解自己……我相信文學理論是一種真正的民主活動。”[2]178有人認為:“伊格爾頓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寫作《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一書,從1983年出版截止目前共發行了三次,已售出了約一百萬冊。”[2]176由此可見,市場需要這樣的“大眾化理論”。事實上,有很多并未上過大學或并非文學類專業的文學愛好者渴望了解這一領域發生的事情,但精英化的高深理論往往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這不利于理論的傳播及推廣。故而理論需要重塑的方向之一便是去“貴族化”和“精英化”,盡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話語方式言說,以挽救伊格爾頓所說的文化“帶有貴族氣息,而且高傲得讓人無法接受”[6]81的理論悲愴。其二,文化與權利和政治的關系曖昧不清。文化挑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同時又陷入冷漠無情的工業資本主義的重圍之中,從而不得不臣服于這一野蠻的秩序。在一個科學與商業主導的世界,從事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被排擠到邊緣。就像文化一樣,他們既處在社會之內,又處在社會之外。文化本應該是權力的對立面。在愈發功利性的社會生活中,“文化提醒我們有些東西沒有價格,卻有價值”,“隨著人類生活越來越受到操縱、越來越量化,藝術的目的就是要堅持成為獨特個體的權利”,“隨著藝術變得越來越可有可無,文化反而能夠將自身的非必要性變成德性”,“只要矢志不渝,文化就能夠起到對政治批判的作用”,“如果人類價值的脆弱的城堡被權利與政治攻入,很難想象人們還能撤退到哪里”[6]94-95。在這個個體變得越來越渺小的社會里,文化成為人類精神家園的最后堡壘。面對權利與政治的強勢進攻,理論要做的就是拼死抵抗。其三,理論未能解決事關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對道德和形而上學感到羞愧,對愛、生物學、宗教和革命感到尷尬,對邪惡表示沉默,對死亡與苦難諱莫如深,對本質、普遍性與基礎性獨斷專行,對真理、客觀性和大公無私識見淺薄。”[6]98因此,在《理論之后》的后四章中,伊格爾頓對這些論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試圖通過不同的角度來處理這些根本問題,以補救理論目前的缺陷。
厘清了文化理論存在的問題后,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的后半部分指明了理論重塑的方向,即為理論尋求倫理學基礎。
《理論之后》的后半部分回到了伊格爾頓在1965年出版的《新左派教會》里討論的范圍,即為真理、德性、客觀性、道德、革命、死亡、邪惡、愛等倫理學范疇辯護。很明顯,伊格爾頓用以補救理論缺陷的武器就是被人們日漸遺忘的倫理學。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開篇里說,倫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至善的學問”,并認為倫理學是政治學的分支。因為要成為善人,就必須有個良好的社會。在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被壓迫、被剝削的社會環境下,善良是一種道德的奢侈品。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機制,沒有人能夠做到“至善”。馬克思繼承的正是這樣的道德思想,他認為道德探索必須檢驗組成特定行為或特定生活方式的所有因素,而不僅僅是個人行為或個人的生活方式。馬克思說“道德就是意識形態”[6]138。因此,道德不是個人事務而是政治事務。伊格爾頓之所以花大量篇幅論證道德是政治事務而非個人事務,是因為文化理論家們“把道德當作令人尷尬之事來躲避”[6]135,并將道德歸于個人問題。他們也就順理成章地消解了復雜的政治難題,如恐怖襲擊,我們只需要解釋恐怖分子是沒有道德的壞蛋就可以了。這也是為何伊格爾頓以倫理學作為文化理論的基石。在當前反絕對真理、反統一道德、反本質、反價值的后現代主義時代,倫理學告訴我們什么是真理、本性、道德、德性以及它們的重要性。
同時,伊格爾頓寄希望于倫理與政治的聯姻,以期創建一個可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這里就回到了前面所說的“宏大敘事”,即馬克思主義——“利奧塔徳摒棄他所認為的宏大敘事時,首次使用宏大敘事這個術語來表示馬克思主義”[6]38。亞里士多德認為追隨有德性的生活是我們人類所應有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就是我們促成互相的自我實現。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的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即促成你的自我實現,我才能取得我的自我實現。這樣的政治形式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而能否過上有德性的生活,取決于倫理教育;能否實現社會主義,則取決于政治。因此,只有倫理和政治聯姻,我們才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過上有德性的生活。
理論自身的限度即是它未來要努力的方向。然而,在這樣一個探討價格而非價值、崇尚物質而非道德的平庸市儈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真理”“德性”“客觀性”似乎都變得輕飄飄而不切實際。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是否還能潔身自好,堅守人類最后的精神家園?這是每一個知識分子需要思考的問題。讓文化堅守住人類最后的精神家園是每一個知識分子要為之付出努力的使命,而理論則是我們用以捍衛它的最好的武器。理論自身的職責便是要保持自身對歷史矛盾以及時代問題的敏感性。在分析和闡釋過程中,它需要對自身的話語運作和形式構造進行批判性反思,并以“追求真理”為其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