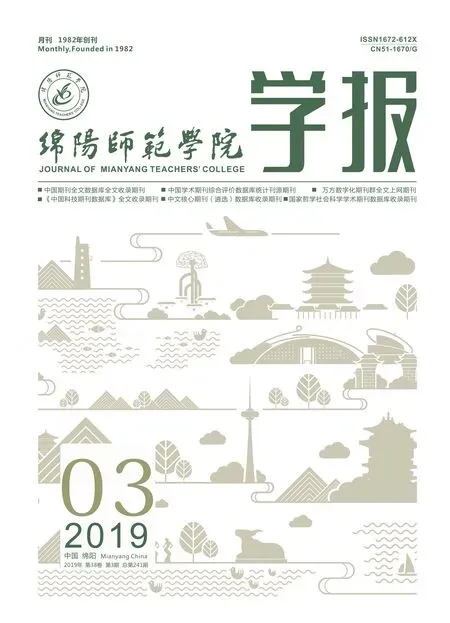孤獨的異鄉者
——讀王安憶的《紅豆生南國》
陳佩娟
(陜西理工大學, 陜西漢中 723000)
《紅豆生南國》是王安憶2017年出版的中篇小說集,其中包括《鄉關處處》《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三篇。作者用三篇小說給我們講述了生活在不同城市的移民者的故事。在繁華的城市,那些外來者們用他們的勤勞與和智慧在城市努力生活。盡管城市人來人往,但對這些外來者來講,他們在身份和情感上都很難融入進去,他們依然處于孤獨之中。王安憶通過對三個身份不同、客居他鄉的異鄉者的書寫,表現出那些定居于城市的人們對故鄉深厚的情感,同時也反映出人口流動過程中存在的文化沖突。人們在陌生的城市謀生,要盡快融入城市,但對以前的生活方式和語言習慣又有所保留,這就形成了城市里的老鄉群。人們喜歡和與自己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這也是一種留戀故土、緬懷故鄉的無奈之舉。他們期待重歸故里,但現實的生活卻無法滿足他們的愿望,這也就造成了現在大多數城市移民的精神孤獨。此外,作者也寫出了那些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者們對身份和血脈的焦慮。作者通過對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移民者們的書寫,反映出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人情、人性和城市異鄉者的鄉土情感。
一、王安憶的城市視角
保姆月娥、編輯“他”和商人陳玉潔,他們三人有著不同的特點:月娥淳樸、勤勞;“他”深沉、寬厚;陳玉潔優雅、端莊。同時她們又有相同點,那就是積極、善良。作為城市移民者,他們承受著生活的孤獨,面對著許多困難,經歷了各種變故,獨自在陌生的城市生活。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當中,那些看起來波瀾不驚的生活也會讓人感覺到疼痛、感傷或開心、激動。城市的生活節奏飛快,人們都專注于自己的事情,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同自己無關的人來往,因此這些城市移民者很少被關注。許多城市移民都面臨著去與留的艱難抉擇,也有許多城市居民不再選擇留在原來的城市,就如同陳玉潔這樣的老上海人,他們會移居國外或者其他城市,成為海外移民者。
小說中的主人公們因為各種原因離開了原來的家鄉,到異地謀生。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被生活逼迫而選擇離鄉,在異鄉的他們,并沒有在孤獨和失落中失去自我,失去對人生的追求。《紅豆生南國》中的“他”小時候家境貧苦,被賣給了阿姆。年幼的他跟著阿姆來到陌生的香港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不順利。結婚后婆媳關系常使他夾在當中受氣,經常陷入兩難的境地,最后他離婚了,孩子也跟著妻子離開。在生意上投資失敗,落入人生的低谷,但是他并沒有因此墮落。雖然養母阿姆脾氣暴躁,早年也因為“他”給家庭帶來的沉重負擔而粗魯地折磨過他,但他依然感念阿姆的養育之恩,一直尊重她,照顧她,為她養老送終。離婚之后雖然他變成了孤獨的留守者,但是面對女同事的示愛,他為了她的未來考慮,拒絕了。事業失敗后他沉著面對,接受命運和現實的安排,重新找到工作,開始一段新的生活。《鄉關處處》中,五十多歲的月娥到上海做保姆,盡管她對城市的新鮮事物很好奇,但她并沒有刻意去打聽,本本分分做自己的工作。被雇主誤解時,她極力反駁,不因為自己的農村身份而忍氣吞聲。她盡心盡力照顧每一位雇主,省吃儉用存下每一筆工資,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給家庭減輕負擔。《向西,向西,向南》中陳玉潔離開家鄉,只身到美國生活,期間她發現丈夫出軌了,女兒也因學業離開她,原本和睦的家庭被摧毀,面對變故,她并沒有怨恨,而是勇敢面對未來的生活,和好友徐美棠一起經營餐廳。盡管生活中總有些瑣碎的事來得猝不及防,他們始終在積極應對,頑強地與生活抗爭,克服自己內心的疲憊與恐懼,堅持自己對生活最初的目標和向往。事實上很多人會在成長的道路上慢慢消沉,而他們在異鄉,想方設法相互支持,在陌生的城市開始新的生活。
王安憶對于城市移民題材的關注與她的經歷有關。“童年時期隨父母到上海生活,初到上海時難以融入這個新的環境,家庭的原因更讓她與她的保姆感情深厚,她對上海市民階級的認識是通過保姆實現的。”[1]拉康談到:人的發展過程中需要他人的介入,人只有在他人的形象中才能了解自己。王安憶也是從自己與保姆們的交往中意識到自己和這些外來人之間有著共同的身份和處境,對城市移民者的書寫不僅僅是記錄城市移民群體,而是對自身處境的書寫。陌生環境中語言不通,再加上母親嚴格的家教,讓王安憶感到自己不屬于這個城市。她極力想要排解這種孤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這也讓她有了更大的興趣去觀察社會底層移民者們的生活狀態。共同的身份認同,使她在情感上對城市移民群體有更深刻的體會。對于這些城市移民者來說,城市的繁華能給自己帶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必定是艱苦的,除了工作帶來的身體上的疲憊,更大的痛苦來源于精神層面。對新城市的陌生感,讓人難以融入這種環境。事業的失敗和困難、家人的離散和矛盾,都會成為城市移民者們的生活障礙。
二、城市移民的鄉土情感
作者早期的城市移民題材作品多是寫女孩子們渴望城市生活,為立足城市奮力拼搏。比如《富萍》中的富萍,從農村到上海后眼界更開闊了,認識到命運應掌握在自己手中,對家人安排的婚姻表示不滿,選擇出走,與居住在上海棚戶區的殘疾青年結合。《妙妙》中的妙妙,雖然生活在小鎮,可心氣很高,她對美好生活的認識都來自電影里描述的大城市生活。她的穿著打扮和思想行為也緊跟城市的潮流,因此她成為了小鎮上的異類。在先前的作品中,作者更多的是寫年輕的農村女孩子對現實不滿,向往和迷戀城市生活,展現出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年輕人迫切想要實現自己理想的狀況。《紅豆生南國》這部小說集的故事與之前作品有所不同,這些移民者的生活中少了浮躁和沖動,更多地展示了理智、溫和的一面,對于故鄉不是像妙妙那樣想要逃離,而是充滿對家人的思念和對故鄉的懷念。三十多年來的快速發展,農村也逐漸擺脫了貧困落后的面貌,人們不再刻意改變自己的農村身份。就像月娥這樣的打工者們都認識到,城市只是他們謀生的地方,而不是最終的歸宿地,所以對于城市生活也就不會太癡迷。另外,人到中年,脾氣也越來越溫和,考慮問題也會更周到,在處理問題時會冷靜思考,作者在寫作中也體現出這一點,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具親和力。
小說中的主人公盡管以前的生活狀況多有不同,他們在城市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生活。從作品中可以看出,月娥從農村到城市是為了掙錢,減輕兒子的負擔;阿姆帶著“他”定居香港也是因為去菲律賓尋夫無果,家鄉回不去,半途定居香港;陳玉潔到美國一開始是打算看望女兒,后來決定買房,尋找商機。他們不再強烈要求擁有城市人的身份,更多的是為了到城市工作,改善經濟條件。現代社會許多人的追求也是如此。在經濟大發展的環境下,現實生活相比理想是大家更迫切的需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離開家鄉,外出謀生。農村人往城市移,城市人向外國移,這也是不可阻擋的社會發展趨勢。相比農村,城市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工資水平也較高。雖然他們在城市面臨許多困難,做的工作也是最累、最辛苦的,但為了能給后代提供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給他們一個好的經濟條件,改變家族和后代命運,他們選擇在城市掙錢,努力讓后代離開農村。對于許多有一定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的城市人,也更愿意移民國外,投資經商或者在國外找一份工作,或者讓子女在國外接受教育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各國的交流合作加速了各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交通和通訊技術的不斷革新也拉近了各國之間的距離,進一步加快了人口的流動。作者的書寫就是表達在這樣的社會發展中,普通人的生活變化和他們對于鄉土、血緣的感受,對于喧囂的陌生城市生活的理解。
在一個新的群體里,移民們還是希望能夠離自己原有的生活更近一點,希望在新的城市重新建立起一種鄉土情感,所以他們的交際圈子也基本限定在同鄉人之間[2]88-94。月娥從農村到了上海,與他的同鄉們擠在一起合租房子,一是為了節省房租,二是因為跟同鄉們在一起讓她有親切感。在外地,同鄉人就是希望,是支撐著她繼續留在城市的精神力量。她們那些同鄉相約一起去跳廣場舞,去逛動物園,她們之間是原有的地緣關系群體的轉移,其內部關系還是維持原狀。月娥與上海的各個東家們之間是新形成的地緣關系,因為她插入到了另一個群體當中去了。同樣的,《向西,向西,向南》中,在陳玉潔、徐美棠還有餐廳的華裔女人和福建男人以及那個香港的富二代之間形成的交流關系,也算是一種地緣關系。“他”在香港的生活圈子很小,婚前與阿姆在一起生活,有幾個同學關系較好,成家后以家庭為中心,離婚后獨居,常來往的朋友也就是同一個單位的同事們。他們都是在外漂泊的人,對于故鄉的依賴和鄉土文化的懷念之情很深,但是她們又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處境。月娥是地道的農民,最終想要回到故鄉。對于“他”和陳玉潔來說,原來的故鄉已經沒有他們生存的空間,雖然在城市有了安身之處,但又不能完全接受和認同現在的新家。他們是無根的人,所以在異鄉的這些漂泊者就更需要同鄉之間的團聚,彼此給予精神上的安慰。
三、城市移民的艱難抉擇
對于移居他鄉的游子,故鄉濃濃的血緣親情是他們終身的牽掛,異鄉同根同源的深厚友情是他們生活的依靠[2]45-50。在《紅豆生南國》中,“他”多年以后回到故鄉與親人相認,照顧生母的晚年生活,血緣關系就是維系他和家族的紐帶,生母給了他生命。他相信父母是因為貧窮才將他賣給阿姆,在他的心中,親情無價,承載著親情的故鄉才是他一直思念的真正歸宿。《向西,向西,向南》中,陳玉潔和徐美棠在國外都習慣和華人相聚共事。《鄉關處處》中,月娥除了工作需要,基本上都是和自己的同鄉姐妹們在一起。他們離開原來的圈子,到一個陌生的城市環境中,以前的所有感情和人脈都被切斷,開始一個人的生活,孤獨也隨之而來,對家鄉和原來的生活更加思念。因此,新的人情關系的建立就非常重要,這是移民者們在以后長期的異鄉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情感需求。作者從知識分子的視角來審視這一現象,隨著移民者離開故鄉,他們的鄉土情感斷裂,通過原來的文化形態、生活方式、語言習慣等形式保留,形成一種較為本土的文化圈,在城市讓這種鄉土情感又繼續生長,以此來緩解他們對親情和鄉土的思念之情[3]。王安憶在童年時期看到其他小朋友能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去走親戚,但自己卻只有“同志”家可以走動。因此她在情感上也期待血緣親情和鄉土人情的建立,在寫作中表現出對傳統的家族、血緣和鄉情的關注,同時也體現出對城市移民的情感關照。
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使得人們有了一定的條件去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發展空間。許多人將留在城市定為自己的終身目標,但是又有許多人始終無法融入進去,這當中除了經濟原因,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文化與血緣。移民者身居城市,卻又不真正屬于城市,在城市中他們的血緣關系和家族體系喪失[4]。就如《紅豆生南國》中的“他”,在香港生活多年以后,有了三個孩子,當他再回到故鄉,對生母盡贍養義務,此時他與生母之間并沒有什么感情,只是因為血緣的連結。在香港,他的家族只限于他與兒子兩代人。這也像現在的許多城市移民一樣,血緣關系只是維持在一代人或者兩代人之間,有家而沒有族,血緣的聯系只是在小的家庭內。第一代的城市移民者們還會逢年過節就不遠萬里奔赴家鄉,與家人團聚,但是他們的后代是在城市生活和接受教育的,對于鄉土的情感基本不存在,這也就對鄉土血緣的延續造成了威脅。后代在城市講當地的語言,遵循城市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城市的人際關系,在未來他們不會再回到農村。現在的許多農村年輕人外出工作,老年人留守在家,這一代的老人去世后,年輕一代基本上也不會再返鄉,這也正是現在的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作者通過對移民者的城市生活描寫,反映出隨著人口遷移,原來的血緣和家族關系正在逐漸消失。
作品中還揭示了移民者對另一種環境和文化接受的問題。陳玉潔多年前在柏林出差半個月,使她倍感無聊。在國外吃中餐,住中國旅館,逛中國人的書店,交中國朋友,她并不覺得自己要融入到外國人的圈子中去,她聽著歌劇會睡著,逛街也感到無聊,簡直是一種折磨,她在異鄉尋找家鄉味道時遇到了多年后成為了她好友的徐美棠。美棠也有著同樣的感受,她無法融入外國人的圈子。到歐洲三十多年,受了很多苦,最終也安定了下來,但是她一直在華人的圈子中生存。多年以后,她依然會認為外國人的生活方式很奇怪,即使常年在國外生活,也忘不了那一口家鄉話。作為跨文化的移民,尤其是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人,在內心還是很難完全接受另一種文化。徐美棠與陳玉潔最后的友情與相伴,除了她們彼此在最需要幫助和依靠的時候給予對方安慰和鼓勵,還有就是她們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認同。
第一篇《鄉關處處》中,月娥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城市移民,在農村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她,性格里有著農村人的淳樸真誠、吃苦耐勞,但又對城市的新事物有點膽怯和疑惑。她所見到的城市人的生活與她想象的并不同,在傳統習慣和道德要求下生活的她對城市人的生活無法理解。初到城市,見到了許多她先前沒有見過的“奇葩”生活。比如,第一家的雇主,全家人冬夏都住酒店;一家子都不工作,靠著和父親差不多年紀的“女婿”養活;女人炒股,大房子炒成了小房子,小房子最后也被炒沒;爺爺的兒女賣掉了老房子,把爺爺送到了養老院……作者通過月娥這個農村婦女的眼光來審視現代的城市生活,讓人物形象更具體,故事更生活化,可讀性更強。用低于作者視角的錯位敘述方式,反映了在城市生活中出現的許多與傳統道德觀念相違背的現象。月娥覺得這種過日子的方式就是瞎折騰,這也體現了作者對現在城市文化發展中一些現象的諷刺。
作者對于故鄉、家族、血緣的書寫,以及這部作品中人物對故鄉和家族的情感表達,引發讀者對中國傳統的家族文化在現在社會經濟發展和世界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不斷萎縮現象的思考。月娥對上海的雇主們生活狀態的感受,也是作者對城市人的生活被物質充斥、人情味逐漸缺失現象的批判。人們對物質的追求和期望越來越高,忙碌的工作讓情感需求和精神生活被逐漸遺忘。與此相反,小說中移民們用積極向上、樂觀豁達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努力工作,更珍惜親情、友情,懂得感恩。兩種生活形成一種對比,更凸顯了作者對過分追求物質生活、違背親情倫理的價值觀的批判,對積極向上、踏實勤奮、不忘初心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的肯定。
四、結語
《紅豆生南國》這部小說描寫移民者的生活狀態,揭示了移民在異鄉的真實生活。在真實生活中,文化、血緣、生活習慣等因素給移民生活帶來深刻影響,生活壓力和離鄉之后的心理壓力也給他們造成困擾,這都是當下應該重視的社會問題,因此關注移民者的生活狀態是必要的。作者在敘述故事時更注重體現人們的生活觀,這些移民不管身處怎樣的困境,他們都是理智地面對。文化尋根意識促使作者通過小說人物來展現血緣親情和鄉土文化的力量,對當今社會上存在的消極墮落的文化表示批判。通過文字極強的表現力,可以準確地表明人物的情感和行為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給讀者創造一個自由發揮想象的空間。作者用豐富的語言、獨特的視角和細膩的情感講述了城市移民的生活狀態,反映出文化和鄉土情感是影響城市移民群體生活的重要因素,對現在城市移民的文化根基和鄉土血緣關系提出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