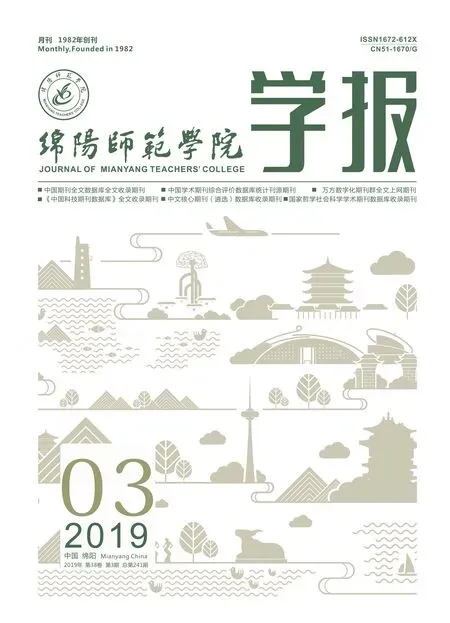論魯迅小說的“民間書寫”特質
洪 蕊
(安徽大學文學院,安徽合肥 230039)
前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陳思和先生在《民間的浮沉——對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和《民間的還原——文革后文學史某種走向的解釋》中對“民間”做出系統闡述。其中談到:民間是與國家相對的一個概念,民間文化形態是指在國家權力中心控制范圍的邊緣區域形成的文化空間。[1]“民間文化”指中國下層百姓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的、與上層社會主流文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一整套關于天與人、人與人、人與自我及生與死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比起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或大傳統來,它一直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屬于“小傳統”范疇,基本上主要處于自生自滅、“無所為而為”的狀態[2]。
魯迅十分關注國民的未來,小到衣食住行、風俗民情,大到國民性,綜合起來就是“人”的命題。要挖掘當時中國軟弱無能的癥結還在于“人”,這個“人”是抽象性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概稱,這個絕大多數就是普通民眾,也就是當時占主要比例的底層人民。所以魯迅的小說寫的大部分都是底層人民與他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民間文化貫穿于其中。
在魯迅的小說中,雖然沒有直接出現“民間文化”這樣的術語,但他的小說深刻體現了民間的種種文化形態,有積極健康的民俗文化,也有愚昧害人的鬼文化。我們可以從《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中看到,魯迅的民間書寫是圍繞著社會底層人物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展開的,并常將中國的民間文化與國民性進行融合性描寫,從而展現出更為深刻且震撼人心的民間世界。
目前,對于魯迅小說民間書寫方面的研究,基本都是關于民俗性思考、地域文化特色等局部性的研究,并沒有綜述性的概括。本文通過分析魯迅小說中關于民間書寫的幾個最突出的特質,對魯迅小說的民間書寫特質進行概括性表述。
一、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魯迅的小說中有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這些地域文化特色是民間文化精華的匯集與體現。魯迅對民間文化的書寫又與自身經歷緊密相關,而這就涉及到魯迅故鄉紹興的民間文化,也就是越地文化,包括貫穿魯迅小說的越地精神、極具特色的紹興土語、充滿民間特色的起名方式和極具民間屬性的事物等等。這是魯迅小說民間書寫的第一個特質。
(一)越地精神
紹興地處越地,錢塘江以東是越地,越先民記錄:“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獸以給食。”越地地勢崎嶇,到處是山,臨江倚海,這種惡劣的自然特征形成越人剛強、不屈的風骨;而大禹、勾踐的精神也在越地代代相傳,形成越人堅韌不拔、剛強抗爭的精神。越地自然環境惡劣,人們的反抗意識也就越強,對于公平、正義有著強烈追求;且越地有著前后貫通的異端思想傳統,從王充、嵇康到王陽明、黃宗羲,再到魯迅的老師章太炎。魯迅生活在這里,自然深受這種意識影響[3]45-50。
這些精神由民間代代相傳,常常在魯迅的小說中體現出。比如《狂人日記》中,“狂人”認為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質是“吃人”,周圍全是被封建宗法浸毒的魔鬼。再比如《鑄劍》中,不惜喪命也要向楚王復仇的眉間尺。
魯迅從小喜歡紹興目連戲,目連戲講的是目連救母的故事,源于印度佛教傳說,后來傳入中國并與越地民間文化融合,目連成為不畏艱險求佛祖幫其救母的形象。魯迅欣賞其中傳達的抗爭、復仇、張揚、狂放的精神,并且非常喜歡“無常”和“女吊”這兩個鬼形象[4]。他們形象上雖然是鬼,卻有著對于正義、人性、公平的強烈意識,相比較當時所謂的“正人君子”更有人情味,他們與魯迅的抗爭、復仇精神契合,魯迅還為此還寫過《無常》和《女吊》兩篇文章。
魯迅小說滲透的越地精神最突出的就是不屈、懷疑、復仇,這些是民間精神的一種典型,是民間文化的精華部分,體現出魯迅對于民間文化美好成分的認同和推崇。
(二)紹興土語
魯迅小說中的語言很有特點。他能夠用非常簡潔凝練的語言概括事物或事件,這與其對紹興土語和白話文的靈活運用有很密切的關系。
在《狂人日記》中,寫到狂人吃兄長給自己的魚時是這樣描寫的:“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兜肚連腸”這個詞是紹興土語,可以從中感受到狂人對于當時整個社會“吃人”本質的察覺和厭惡。再比如“醬”字在紹興土語中的意思是“悶熱的環境下人與人緊緊挨在一起”。這個字在《高老夫子》和《逃名》中出現多次,而這一個“醬”字就能將環境的惡劣、心境的煩悶充分烘托出[5]78。
這些土語是民間文化的組成部分,極具地方特色和民間文化色彩。魯迅能靈活地應用它們,并將它們融入白話文中,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是對民間文化的一種傳播和認同。
(三)起名特色
在紹興,民間盛行給人用體重、歲數、外貌特征、紹興日常生活中常見之物來起名,比如魯迅就有綽號“胡羊尾巴”。
在魯迅的小說中,有大量這類取名現象。有以體重命名的,在《風波》中,有“九斤老太”“六斤”“七斤嫂”之類;有以歲數命名的,在《離婚》中,有“八三”(將父親和爺爺的年齡相加),在《社戲》中,有“六一公公”;有以外貌特征來命名的,在《藥》中有“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紅眼睛阿義”,《明天》里有“藍皮阿五”“紅鼻子老拱”;還有內含暗示的名字,如《藥》里的“華大媽”“華老栓”“華小栓”和“夏瑜”,他們的姓氏合在一起是“華夏”。
這些民間盛行的起名方式被魯迅運用到小說中,不僅體現了魯迅小說的民間書寫特質,也幫助魯迅用更隱晦而巧妙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時政現象的態度和觀點,比如《藥》中指向“華夏”的“華老栓”(代表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和“夏瑜”(代表革命者),這兩類人相遇往往是雞同鴨講,相互不理解,革命結果也總是失敗的悲劇。
(四)紹興事物
在魯迅的小說中經常會出現S城、趙莊、未莊、魯鎮、酒店、茶館、羅漢豆(茴香豆)、黃酒、烏氈帽之類的事物,而這些正是民間所特有的東西。
在《孤獨者》《在酒樓上》中,S城就是以紹興為原型而構建的,在《故鄉》《祝福》《社戲》中,趙莊、未莊、魯鎮又是以魯迅外婆家鄉為原型的。魯迅以它們為人物活動的場所,寫下一系列底層人物的普遍物質與精神狀態。
酒店和茶館在魯迅的小說中出現的頻率很高。比如在《孔乙己》中:“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柜臺,柜里面預備著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孔乙己》故事的主要發生場所就是咸亨酒樓,而這個酒樓的設置原型其實就是紹興各處常見的酒店,曲尺柜臺,板桌長凳,都是民間酒樓所特有的。
魯迅小說中故事發生場所也是按照紹興民間特點來設計的,比如《在酒樓上》中:“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
《孔乙己》中好幾處點到一種食物:羅漢豆(茴香豆)。“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羅漢豆浸鹽再溫水煮熟,是紹興一帶常用的做法,這種事物本身就極具民間特質。在《阿Q正傳》中,“阿Q正沒有現錢,便用一頂烏氈帽做抵押……”;在《故鄉》中,“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這是少年閏土的形象,烏氈帽象征的是民眾,是民間書寫的一種具化形象。
這些典型的民間事物貫穿在魯迅小說中,成為典型環境的一部分,使魯迅小說充滿民間書寫的特質,成為魯迅小說中民間事物的代表性象征。
(五)祭祀婚喪
在魯迅的小說中,常常會出現祭祀和婚喪的民俗形式,這些是民間文化的一種重要構成。比如在《祝福》中,就說到年底的祭祀事宜,包括掃塵、洗地、宰鵝、殺雞和徹夜煮福禮。還有《孤獨者》中,魏連殳回去參加祖母葬禮,葬禮儀式是先跪拜、哭、亡者入棺,再是跪拜、哭、給棺材釘棺蓋,且女人們都要念念有詞。
魯迅在小說中經常穿插紹興的祭祀婚喪習俗,他在描述這些尋常民俗時,通過巧妙使用詞組的組合特點、修飾語的色彩含義,將故事中主人公矛盾、壓抑的精神狀態表現出,而這種矛盾、壓抑的精神狀態正是底層民眾普遍的精神狀態。這種方式是民間書寫特質的一種深刻體現。
二、陌生化的敘述視角
魯迅的小說很多都是以個人經歷為素材,塑造了以魯鎮和魯鎮百姓為原型的民間世界。但魯迅離開故鄉后,人生的大部分時段都是漂泊在外,對于鄉土生活已經有了一定的隔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魯迅便采取陌生化的敘述手法,有意對鄉土農村的景物和人情風貌進行簡約化處理,讓自己以一個離別故鄉多年的游子身份闖入鄉土的民間生活,用陌生的眼光觀察周圍的人與事,用陌生的口吻敘述鄉土世界中的民間生活。這是魯迅小說民間書寫的第二個特質。
(一)隔膜感
魯迅故意拉開自己和故鄉的距離,使隔膜感始終卡在自己與純粹的鄉土世界之間,這種看不見卻又一直存在的一層障礙成為魯迅筆下鄉土世界的一個特色。比如在《故鄉》中,“我”來到闊別二十年的故鄉后,感慨自己所看到的故鄉是蕭索、荒蕪的,色彩是蒼黃、單調的,完全沒有朝氣,并不是自己記憶中故鄉的模樣,并感到悲涼和失望。這種情緒是充滿隔膜感的,不是“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思念,而是一種物是人非的失望情緒,他描繪的故鄉沒有確切的真實感,但寥寥幾筆卻淋漓盡致地勾勒出一個闊別二十年的故鄉形象,讓人印象深刻。
(二)對鄉土世界的批判與懷念
魯迅常常會以知識分子批判啟蒙[6]的立場對民間鄉土進行建構,以局外人闖入的方式重塑小說敘述視角。魯迅在陌生的俯視打量中,揭示了一個漂泊在外多年的知識分子陌生化視角下的鄉土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有民間固有的愚昧、麻木、冷漠和封建落后的一面,對此,魯迅以五四影響下的新思想對陳舊的鄉土民眾的物質和精神世界進行描寫和批判。比如《故鄉》中,原本是“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變成庸俗不堪像圓規似的女人,她兩手打在髀間,沒有系裙,張著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里細腳伶仃的圓規;在《風波》中,七斤的辮子不符合當權者的規定,七斤嫂為此惶恐不已,而旁觀者又是一副無知、自保、安于現狀的態度,心里算計著自己抵不住張翼德,覺得七斤就要沒有性命了,想發表些議論卻什么都說不出來,亂嚷了一會就回家睡覺去了,其中魯迅還用了“蚊子”“嗡嗡”“赤膊身子”這些貶義色彩的詞匯讓讀者對這些村民的無知愚昧感到厭惡惡心,而這些描述展現的就是當時民眾普遍的奴性心理;在《孤獨者》中,魏連殳回到故鄉后,魯迅以全知敘述者的身份將村里人無知又好奇的心理和神態描述得淋漓盡致。
同時,魯迅筆下的鄉土世界也有民間特有的質樸、勤勞、詩意的一面。比如《故鄉》中關于少年閏土的回憶,充滿美好和淡淡的夢幻感,深藍天空中的圓月,海邊的沙地和碧綠的西瓜,戴項圈的少年和刺向猹的鋼叉,這些描寫是魯迅陌生化視角下的鄉土世界中美好的部分。
(三)批判中的自我懷疑
“我”總是在高空中以啟蒙者的視角打量民間世界的愚昧之處,但又常常在揭露舊生活的丑陋中透出對自己的否定和懷疑。在《故鄉》中,“我”躺在船上,遠離老屋和故鄉的山水,產生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閏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里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么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遠罷了。”以及在《祝福》中,祥林嫂問了“我”關于地獄的問題,而我卻支支吾吾無法回答,最后逃也似的離開了。這些都體現出作者對于理想社會的不信任和迷茫。
因為童年故鄉留給自己的美好回憶,魯迅對故鄉民間文化中積極健康的因素有著發自內心深處的共鳴;但民間文化又有太多愚昧、麻木、冷漠、封建的成分,使魯迅對民間又持整體批判的態度;加上五四所指向的新世界并不清晰,使他在對舊世界進行批判的同時,又對自己在理性上跟隨五四啟蒙思想所追求的新世界產生懷疑。所以在魯迅以“我”的視角所構建的民間世界中,“我”始終是介于局外和局內的身份,并以陌生化的視角去觀察民間的世界。魯迅一直刻意拉開自己與故鄉民間的距離,不斷加重對故鄉的人與物的隔膜感,保持著一個獨立于民間和五四啟蒙之外的客觀身份。
三、對民間文化中鬼文化的突出
在魯迅的小說中,對鬼文化的突出描寫是魯迅小說民間書寫的第三個特質。民間文化中的鬼文化成分或以顯性材料出現在魯迅的小說中,或作為隱性的主旨貫穿于魯迅的創作中。
(一)魯迅小說中鬼文化的分析
鬼文化本身含雜了很多毒素:統治者為控制人民思想所宣傳的變質的小乘佛教,民眾長久以來被壓榨而產生的對現實的絕望、麻木的悲觀思想,落后的封建生產力下民間文化中的粗鄙成分。這種文化讓像祥林嫂之類的底層人民被封建迷信吞噬,讓民眾變得愚昧、麻木、冷漠。
在《華蓋集》中,魯迅說:“華夏大概并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我裝作無所聞見模樣,以圖欺騙自己,總算已從地獄中出離。”[7]178魯迅清醒地認識到民間文化充塞著“故鬼、新鬼、游魂”這些鬼文化,也深知民眾受這些粗鄙的鬼文化毒害至深,但面對這樣龐大又根深蒂固的社會現象,魯迅感到無可奈何。在魯迅的小說中,《祝福》里祥林嫂是受鬼文化荼毒最典型的代表。“頭發全白,臉上瘦削不堪,眼珠間或一輪”的祥林嫂,一方面在活人的世界里受迫害,一方面又擔憂死后面對兩任丈夫會遭受悲慘對待,她在喪子和被社會遺棄的境遇下變得不人不鬼。魯迅就是通過勾勒這類人物,從而達到批判當時民間文化中使民眾變得殘酷冷漠、愚昧不堪的鬼文化的目的。
鬼文化中也有“無常”“女吊”這種象征公平、正義的形象,魯迅對此形象持欣賞和認同的態度。不過這種正面的形象在鬼文化中是少見的,所以魯迅對于鬼文化主要還是批判態度。他把這種抽象的批判具化為一個個生動的故事,祥林嫂的悲劇就是由這種以糟粕為主的鬼文化導致的。
(二)魯迅對鬼文化的批判
魯迅對于禍害民眾的落后封建鬼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他談道:“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8]98
他認為錯誤的鬼神信仰使民眾變得安分守己,沉默冷漠,愚昧麻木。他曾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中說:“在中國的天地間,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艱難極了。”魯迅對這種鬼文化的厭惡在其作品《祝福》中有深刻的反映。
《祝福》中,祥林嫂死了丈夫,又被婆婆賣給另一家做老婆,孩子被狼叼走,她不僅沒有得到真正的同情,反而被當做不潔、有罪的人。在這種情況下,“鬼文化”起作用了,別人讓她到土地廟捐一條門檻當做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自己一世罪名,免得死了受苦[9]24-30。這種建議是迷信落后“鬼文化”的表現,是極其愚昧害人的,結果祥林嫂死前還沉浸在自己死后會不會被兩個丈夫搶的陰影里。祥林嫂在受盡人為施加的苦難后,沒有人真正為她著想難過,看客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有罪”,她變成寡婦是她的罪,她被別人搶親是她的錯,她成天念叨她的“阿毛”太煩了……祥林嫂沒有精神寄托和救贖的方式,封建毒蝕下的鬼文化成為她唯一的稻草。
魯迅發現了中國人普遍的“精神疾病”,而民間文化中的“鬼”文化是催促精神死亡的要素,所以魯迅強調要打鬼,要去除民間文化里的“毒氣”“鬼氣”[10],這正來自他對中國歷史和國民性的深刻認識。
四、對民間文化的雙重態度
在魯迅的思想文化世界里,常常發生極其強烈的沖突和悖論。
在五四時期啟蒙主義風潮的影響下,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整體態度是否定的。比如魯迅從小非常反感《二十四孝圖》中對于封建孝道的鼓吹,他認為“臥冰求鯉”“老萊娛親”“郭巨埋兒”這些是違背人性的,是殘酷自私、無視孩童性命的荒唐矯情的典范。這種意識一直影響著魯迅,表現在后來對“貓”的仇視,強烈的復仇意識,剛直的個性,犀利批判的筆鋒。他的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都鮮明地體現出他的思想,這種關注“人”的態度讓他在現實生活中成為一個戰斗者,在故鄉尋根中發掘自己的精神家園,并對現實進行巧妙的諷喻和猛烈的批判。
但仔細閱讀其小說,我們會發現魯迅對于某些民間文化形態又有著很強的認同感,比如對于“無常”“女吊”等形象的贊賞態度。
在上層文化對民間文化的腐蝕問題上,魯迅持毫不留情的批判態度;但對于鄉村人物的傳統民間文化,魯迅卻持批判兼溫情的雙重態度。綜合來說,一方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另一方面卻又欣賞其中的活潑與底蘊,這是魯迅小說民間書寫的第四個特質。為何魯迅小說中對于民間文化的態度這樣復雜?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要從多方面去研究思考。
(一)對民間文化否定態度的形成原因
首先民間文化的創造和傳播者主要是底層人民大眾,這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低級、封建、落后的因素。魯迅清楚地看到這一客觀事實,看到民間文化中被上層文化浸染的違背人性、殘酷自私的成分,也看到民間文化中被鬼文化侵蝕的愚昧、麻木、冷漠的成分。他意識到,正是這些毒素,使國民劣根性不斷加重,而這種劣根性又貫穿在日常生活中,導致種種人間悲劇。魯迅將民間文化中的卑劣成分導致的悲劇演繹成一個個故事,展現在其小說中,比如《故鄉》是鬼文化侵蝕下的悲劇,《阿Q正傳》是國民劣根性導致的悲劇,《孔乙己》是上層文化毒蝕下的悲劇。
其次,在五四啟蒙思想的影響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化持一種對立的狀態,魯迅作為五四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對民間文化也持大體上否定的態度。而且魯迅經歷了家庭“由盛到衰”的巨大變故,他體會了小康家庭瞬間墜入困頓的落差,各種陰毒的傳言和本家親戚的欺辱,這讓魯迅體察到民間文化的主體——底層人民大眾在思想上的冷漠和自私。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過:“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11]178魯迅的家庭變故讓他在先天上擁有對人性丑陋處更敏銳的洞察力,讓他對于改造民間文化有更強烈的欲望。魯迅奔赴南京上學,再到日本留學,在新的思想文明沖擊下,他發現民族文化中有兩種不同的文化:一是傳統上層文化,這是被統治者操縱的文化。在《拿來主義》里,魯迅表示:“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著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著他們滅亡。”[12]40這種文化是魯迅堅決抵制打擊的文化;一種是下層文化,也就是民間文化。在魯迅看來,中國傳統民間文化有著不可小覷的作用,但含有的精華與糟粕不等,需要用“拿來主義”,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利成分,整合傳統民間文化,剔除糟粕并取其精華,形成有利于改造國民性的新文化。
(二)對民間文化肯定態度的形成原因
首先,魯迅故鄉的民俗和童年的記憶讓他對民間文化有著濃厚的感情,其后的漂泊經歷更加重他對童年的追憶,這就使他在對故鄉民間文化的描寫中時常透出溫情。魯迅出生在浙江紹興,紹興地處歷史上的越地,這里“春祭三江,秋祭五湖”,“信鬼神、好淫祀”,是一個非常具有民間文化特色的鄉鎮。魯迅不到一歲的時候,家人把他帶到長慶寺拜和尚為師,原因是根據當地習俗,要放養孩子,才能躲開鬼神的殺害。之后,魯迅的童年回憶里有給自己講神話故事的祖母和長媽媽,和小伙伴們一起看社戲的愉快經歷,還有和閏土刺猹捕鳥的游戲體驗;同時,他的童年又貫穿了父親對自己關于圣賢經傳學習的嚴格要求,以及因為回答不好所受的嚴厲懲罰。毫無生命力的傳統上層文化讓他產生厭惡情緒,民間文化中質樸、勤勞、詩意的美好部分讓魯迅產生認同感。在《故鄉》中,當魯迅回憶到童年玩伴時是一幅充滿詩意的場面,有一些頗具詩意的意象,如“深藍的天空”“金黃的圓月”“海邊的沙地”,“碧綠的西瓜”“戴項圈的少年”“刺向猹的鋼叉”。這種美好的場面在魯迅文章中很少出現,一般都是在他回憶到故鄉童年時才會有的。
其次,魯迅從小受傳統文化教育熏陶,嗜讀像《明季稗史匯編》之類的各種野史雜說,又喜好描摹《山海經》中的各種畫樣。這些讓他對中國民間文化有著深入的了解,并感受到民間文化巨大的活力。我們可以從他的小說創作中找到許多以民間傳說、民間流傳的神話為原型的作品:《補天》里對女媧補天的重塑,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鑄劍》中將越地特有的復仇精神表現得激越悲壯;《奔月》中將英雄后羿塑造成悲劇人物,寫的是英雄的悲哀。在《故事新編》中,魯迅將自己對民間文化的深入了解,緊密結合當時的社會問題,反映出更深刻的思想內涵。
此外,五四時期的民間文化熱對魯迅也有一定影響,這使魯迅更加重視民間文化。在《談胡俗》里記錄了魯迅對于民間文化的觀點:“清末革命運動的勃興,其目標全在政治,注意禮俗方面者絕少,唯章太炎先生可說是唯一的人。太炎先生于民國二年秋入北京,便為袁世凱所羈留,前后幽居龍泉寺及錢糧胡同者四年。對于北方習俗深致笑罵,可以考見其意見之一斑。”[13]105章太炎先生在禮俗方面的博學和深刻見解讓魯迅佩服,也使魯迅更加重視民間文化內容的廣闊性與復雜性。
結語
綜上,我們可以對魯迅小說的“民間書寫”特質進行界定:它圍繞著底層民眾,貫穿了大量極具鄉土特色的人情事物;以知識分子陌生化的眼光去勾勒鄉土世界,以五四影響下的新思想對陳舊的鄉土民眾的物質和精神世界進行描寫和批判;對民間文化中的鬼文化有很突出的描寫,或隱性或顯性。顯性的是寫小說人物相信鬼文化而導致悲劇性結局,如《藥》,隱性的是小說人物在落后鬼文化的籠罩下的悲劇人生,如《祝福》;體現的是魯迅對民間文化的雙重態度,一方面不斷以陌生化的眼光去打量民間世界并批判其中的荒唐、無知和冷漠,另一方面又不斷質疑五四所指向的新世界并質疑自己的批判者身份,且加之童年在鄉土民間的美好回憶,使魯迅在小說中對民間文化表現出來的態度總是矛盾而又復雜,讓人難以琢磨。
我們通過分析魯迅小說的“民間書寫”特質,可以發現更多真實、本土的民間文化,也能發現一個有過切實民間體驗、后又漂泊他鄉的知識分子視角下的民間世界的獨特性,體會那個時代國民性之所以有許多卑劣成分的深層原因,感受到作為后人眼中的“偉人”魯迅的矛盾、迷茫和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