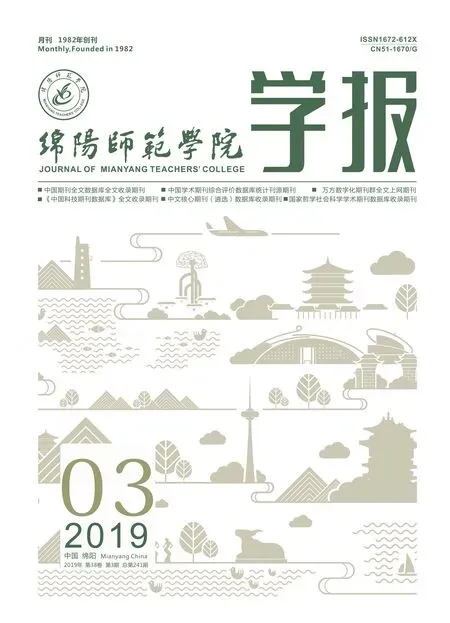《孔子詩論》論析
楊鐵梅
(運城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山西運城 044000)
《孔子詩論》,即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殘存1 006字。從學術界所取的名稱來看,《孔子詩論》是儒家孔門對《詩經》的品讀論詩成果,它對《詩經》的注解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孔門的詩學思想以及先秦詩學。《孔子詩論》是先秦詩學發展之下的產物,充分體現了先秦詩學的特點與思想內涵,這為深入研究先秦詩學理論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我們以《孔子詩論》為切入點,對其思想內涵以及所體現的先秦詩學思想進行解讀,以此來更深入地理解孔門和先秦詩學的理論特色,具有非常重要而又現實的研究意義。
一
對于《孔子詩論》,首先最直接的問題就是作者問題。目前,學術界對此意見紛呈,學者們暢所欲言,發表了各自的看法,因此《孔子詩論》的作者問題,目前尚無完全的定論。從大體來說,學術界對《孔子詩論》的作者問題有以下幾種意見。馬承源明確認為,《孔子詩論》的作者就是孔子本人[1]1-10,朱淵清在認定字形的基礎上認為《孔子詩論》的作者也是孔子[2]403-404,裘錫圭亦持此論[3]6。李學勤通過大量戰國簡文的考辨認為,《孔子詩論》的作者是子夏而非孔子本人,它不像《論語》一樣記載孔子言行,而是孔子弟子所為[4]52。范毓周亦認為,《孔子詩論》的作者是子夏,因為子夏傳《詩》在孔子弟子中最為有名,漢代傳《詩》者皆以子夏為宗師[5]。彭林則認為,《孔子詩論》中有部分言辭的確為孔子所說,但還有一部分則不可論定為孔子所言,《孔子詩論》是一個“以部分代整體”“以偏概全”的標題[6]。高華平認為,從與《孔子詩論》同時出土的《子羔篇》來看,從后代《孔子家語》《毛詩序》中與子羔論《詩》的材料來看,《孔子詩論》的作者應當是子羔[7]。葛立斌認為,從斷字、孔子曰的稱呼方法、文章結構、解詩方法及其詩學思想分析來看,《孔子詩論》從總體而言應當屬于戰國中前期的作品[8]。另外,曹建國認為,《孔子詩論》多言情性、身心等,而孔子弟子子游尚禮、貴情,所以其作者很有可能是子游[9]34。
雖然學者們的意見紛繁多樣,但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除了葛立斌的意見之外,其他學者們的看法都肯定,《孔子詩論》是先秦時期的產物;第二,不容否定的是,無論是不是孔子本人所著,《孔子詩論》都與孔子有著相當大的、甚至是直接的關系。無論是孔子本人所言,還是孔子的弟子根據孔子言論所言,甚或是孔子的弟子在孔子的影響下所發言論,我們都可以看成是孔門言論。所以,我們從整體上來說《孔子詩論》是儒家孔門的詩論,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孔子的觀點。
二
“性”字在我國出現得非常早,《尚書·召誥》中就有“節性”的說法。這些“性”在文中往往僅是指生命中所蘊含的欲望,并沒有哲學上的相關意義。《論語》中對性的記載也是吉光片羽,只在《論語·陽貨》提及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詩論》與《論語》不同,高舉“性情”大旗,歌頌詩歌的“性情”價值,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在這里,《孔子詩論》可以看作是思孟學派的“性情說”的前驅。《孔子詩論》第16簡“吾以《葛覃》得是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第20簡“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第24簡“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中反復強調了“民性固然”,這恐怕是有意而為之的[10]。這里出現的“民性”,是與《性情論》中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性”是一樣的。在對《詩經》的解讀中,孔子認為這些性情是人們的本原,是天生存在的。“情”與“性”是密不可分的,“情”也是人性的一種本能,是“性”的一種直觀表現。《孔子詩論》體現了鮮明的“情本”主義,對“情”的詮釋是《孔子詩論》的一大特色,如第16簡的“《燕燕》之情,以其獨也”,第18簡“《杕杜》,則情喜其至也”,第22簡“《宛丘》曰:‘洵有情,而無望’。吾善之”。《孔子詩論》中,除了多個簡出現了“情”字以外,還有許多表達情感的詞匯,如第18簡中“因《木瓜》之報,以喻其怨者也”的“怨”,第21簡中“《猗嗟》,吾喜之”中的“喜”等,這些涉及情感的詞匯據統計達到60次之多,這使得《孔子詩論》有著濃郁的情感色彩,豐富了蘊意。
《詩經》的產生與禮、樂是緊密相連的,故而《孔子詩論》也很重視對禮、樂的思想表達。《孔子詩論》是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下產生的,它意圖對《詩經》進行闡述,使禮與樂統一來重新塑造禮樂的功能。《孔子詩論》追求“禮”與“情”的和諧統一,將“情”納入到“禮”中,充分展現了在“情”的基礎上“重禮”的思想內涵。例如,第10簡中“《關雎》以色喻于禮”,第11簡中“《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第12簡中的“好反納于禮,不亦能改乎”,以及第14簡中“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愿;以鐘鼓之樂”等等。這一系列的描述展現了“情”需要“禮”的約束,即使君子好色也需要遵從禮制。再如第13簡“《漢廣》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就是遵循禮儀而不做浪蕩之舉的最佳證明[11]。對于“禮”的思想闡述,在《孔子詩論》中還表現為對先王的贊美與敬畏之情,如第5簡中“《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為其本;秉文之德,以為其蘗”,第21簡“《文王》吾美之”,這都是表達對文王的歌頌和崇敬,也是“禮”的表現之一。“禮”與“樂”是相聯系的,對于“樂”來說,它是伴隨著禮的存在而存在。《孔子詩論》在其開篇就明確指出了“詩無隱志,樂無隱情,文無隱意”。《孔子詩論》認為詩、樂、禮是一體的,在第3簡中曰“《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這是對《邦風》的音樂功能進行了評論。《孔子詩論》第14簡亦可以見出,其對于《關雎》可見“樂”所呈現的好色之愿的愉悅之情。
詩歌在中國往往是文學、歷史、政治等傳承的載體,具有較為明顯的記錄功能。詩歌在春秋時期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味,充當了捍衛王權的工具。《詩經》中的許多詩歌都表達了對王權的歌頌,《孔子詩論》的王權觀非常明顯,只歌頌圣主不批駁昏君。《孔子詩論》第6簡中說:“《烈文》曰:‘亡競維人,丕顯維德。嗚呼!前王不忘。’吾悅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貴且顯矣!頌。”此簡可以見出孔子的觀點,他認為品德高潔的賢者能永垂千古,最重要的在于以圣賢的“前王”為榜樣。《孔子詩論》對文王和武王進行了頌揚[12],大力推崇周文王之德行。這在第5簡、21簡、22簡中都有明確的體現。《孔子詩論》大力頌揚圣主賢君,對于昏君卻并未直接批判,而是采用諷諫的手法希望他們能夠成為一代明君,例如第8簡說:“《十月》,善諞言;《雨無正》、《節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惡,少有危焉。《小弁》、《巧言》,則言讒人之害也。”此簡認為昏君不“明”并非自身的原因,而在于受到了小人讒言的影響[13]。《孔子詩論》所展現的王權觀揭橥了其濃厚的尊王思想,表現了孔子對周朝禮樂制度的尊崇,這也與《論語》中孔子一生“復禮正樂”是相呼應的。
三
《孔子詩論》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表現在文學上。《孔子詩論》的開篇就寫道:“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這是《孔子詩論》明確表達了詩在“志”上的作用。“詩亡離志”與“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相協調。“詩言志”是中國詩歌的傳統,孔子在《論語》中就多次提到的詩言志的特點。在先秦思維里“詩言志”是一個公論,叔向就在襄公二十七年時指出“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具有典型先秦詩學特點的《左傳》通過“感發意志”等方式來對自己的志向進行表達。尤其是在群雄逐鹿的春秋戰國時期,更希望能一展鴻鵠之志,而“詩”就成為了重要的傳承載體。對于孔子來說,處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他只有從事政治活動,一生致力于“復禮正樂”,傳播自己的思想,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大同”理想。這是孔子的畢生所愿。《孔子詩論》正是借以對《詩經》中的有關“禮”的闡述來表現“志”,詩論中對于先王功德的贊頌又何以不是其“志”的表現形式?我們是否可以說,正是“志”,才是孔子“禮”的情感抒發。
《孔子詩論》最為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對“情感”的討論與表達。先秦時期對于情感不大推崇,“樂亡隱情”是人們情感表達的最常用的方式。“禮”與“樂”密不可分,“禮樂”與“情”密不可分,這點可以從《語叢》《性自命出》等簡看出[14]。漢代以后“人情”觀點更加有逐漸消失的傾向。《孔子詩論》正是通過“禮”為人情所出,“樂”為人情所表,點明了先秦詩學中“情感”的思想。例如,第1簡“樂亡離情”,是《詩論》的開宗之處;第3簡“其言文,其聲善”能夠反映出詩樂相通的思想。《詩序》是孔子之前就存在,經孔子整理而傳下來的。《孔子詩論》中的詩論觀點能夠反映出與《詩序》在《詩經》中的重要作用,《孔子詩論》雖未直接言明,但蘊含著《詩序》具有表現創作動機、解說詩意的思想。文學與人性相通,孔子將詩與修養相聯系,用詩歌來顯示人格塑造,體現出“人本思想”。從前面對《孔子詩論》中的性、情思想內涵的分析來看,《孔子詩論》蘊含了豐富的情感表達,所涉及到的情感也是多方面的,有涉及到男女情愛的,也有涉及到兄弟之情的,例如在第10簡曰:“《關雎》之媐、《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報、《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重而皆賢於其初者也’”這里涉及到了戀愛、祝福、相思以及送別等題材內容,均用一個字對作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點明了每首詩的主旨情感。《孔子詩論》還往往喜歡用言簡意賅的詞匯直接表達了自己的讀詩感受,例如第21簡說:“《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鳲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它直接用“善”“喜”“信”“美”來直觀地表達對作品的情感,是孔子主體對《詩經》閱讀的情感活動,呈現出了明顯的“以情論詩”的特色。
《孔子詩論》第三簡中對《邦風》評論說:“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物是德、禮的外在表征,這里的“文”指的是邦風之詩的所包含的豐富多彩的物類,“善”指的是邦風內所匯聚的象征著禮、德、仁、政內涵的“五色比象”。該簡對邦風的社會功能進行了強調,給予了邦風極高的藝術評價,以觀“人俗”,傳承“善”,具有明顯的教育指向功能。《禮記·經解》曾記載了孔子這樣的一番話:“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禮記》產生之前,《詩經》的詩教觀念就已經成型并廣泛傳播于個諸侯國家,先秦典籍中很多關于詩的議論就是很好的證明。可以說《孔子詩論》與“性情論”一樣,最終的目的在于教化。《孔子詩論》雖然沒有明顯的、直觀的教化,但是它采用了一種“迂回”的方式來實現詩教功能的實現。例如,第6簡和第8簡通過先揚后抑與諷諫的手法相結合的方式來勸諫君主勿信小人,效仿先賢,樹文王之德美,成賢明之君主。再如,第24簡對《甘棠》有云“悅其人,必好其所為”,將知恩圖報認為是人的本性,也在引導人們樹立德行。另外,《孔子詩論》對涉及到《關雎》的鑒賞指出了要克己奉禮,在人性的情之所至也需要遵循禮制。第27簡中“《蟋蟀》,知難”引導人們的反思,不要虛度光陰,要努力提高自身品德的修養。從以上的種種來看,《孔子詩論》并未嚴格意義上遵循詩教,而是與“禮”融合在一起來進行傳教。
四
將《孔子詩論》與其他的先秦詩學如《毛詩序》《荀子》等相比較而言,其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從《詩經》的內容與情感出發,而不是以史來論《詩》。縱觀《孔子詩論》,我們可以看到所涉及到的歷史人物僅為后程、文王、召公三人,再無其他的歷史人物。相比較而言,《毛詩序》中則是以詩為史,將《詩經》中的每一篇與歷史上的某個人或者某件事對應起來,對詩歌中道德倫理來挖掘,極力去賦予詩歌政治、教化的意義。我們從《孔子詩論》和《毛詩序》所提及的人物,可以看出兩者的差別。《孔子詩論》對于《詩經》篇中沒有明確指明的人物用“王”“后”等泛稱進行代替,而《毛詩序》則是點明具體的歷史人物名稱如齊桓公、衛文公等,這種言之鑿鑿的語氣不容質疑。與《毛詩序》注重具體歷史人物及具體歷史事件相比,《孔子詩論》更多的是探索其中的性情和禮樂。例如,對《衛風·木瓜》的解說《孔子詩論》認為情感的表達借助物質來作為承載是天性使然,而《毛詩序》中則將其安插在齊桓公身上以此來贊揚齊桓公。對于先秦詩學,《孔子詩論》從作品的實際出發,準確的揭示詩篇的本來面目,以其獨特的“以情論詩”“以心悟詩”的理論品格在先秦詩學中獨具一格。
《孔子詩論》另一個重要的價值在于其中蘊含了豐富的哲學思想,豐富了先秦儒家的詩學理論,為了解《詩經》在先秦時期的社會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孔子詩論》的相關探討始終未離開人,無論是《甘棠》中褒贊美德,還是《關雎》中的人性的“以色喻于禮”,都體現了儒家“以人為本”的哲學思想。《孔子詩論》多次出現了“情”“性”“德”“命”等富有先秦哲學底蘊的批評性術語。人性教化是儒家關注的焦點,出現了《禮記·中庸》《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孟子》等儒家經典,我們可以把《孔子詩論》看作是這些哲學思潮的。發端。《孔子詩論》提出了“性情”理論,并且高舉“性情”大旗,歌頌詩歌的“性情”價值,極大地豐富了詩論中的哲學內涵。《孔子詩論》的哲學思想是其他的先秦詩學以及后面的詩學所欠缺的,因此更顯其歷史地位。
《孔子詩論》是在春秋時期詩學思想逐步走向系統化、專業化的背景下產生的,它的出現標志著先秦詩學逐漸走向成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孔子詩論》吸收了前人和當代的思想,突破了傳統的“斷章取義”的論詩模式,勇于采用全面系統的對詩歌進行品讀方式,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論詩理論,具有非常強的創新性。孔子是先秦儒家詩學的發端人,《孔子詩論》中以情論詩,以詩論禮對后來詩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荀子》許多的論詩觀點與《孔子詩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重情”和“以禮節情”的觀點在《荀子》中不斷閃現。《孔子詩論》同樣也對《毛詩序》產生了影響,《毛詩序》“詩言志”的詩學思想就是對《孔子詩論》思想的傳承。可以說,《孔子詩論》是先秦詩學的標桿,蘊含了豐富的哲學思想,它的“詩言志”“詩顯情”和“詩傳教”等詩學理念以及獨具一格的論詩理論品格成為了詩學發展重要的“橋梁”,《孔子詩論》的出世為深入研究先秦詩學提供了有力的憑據,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