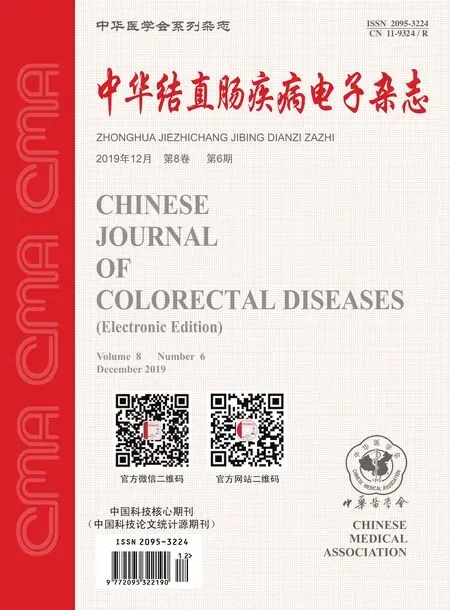“偏左,朝右”:基于原發部位結腸癌發生機制研究進展及臨床治療決策思辨
傅中懋 黃陳
結直腸癌是當今最常見的消化系統惡性腫瘤之一,2019 年美國結直腸癌的預測發病率與預測死亡率在所有惡性腫瘤中均排第3 位[1];在我國惡性腫瘤發病率中結直腸癌排第3 位,病死率排第 5 位[2]。根據胚胎起源的不同,結腸可分為左半結腸與右半結腸,右半結腸包括盲腸、升結腸與橫結腸,左半結腸包括降結腸與乙狀結腸,由于在臨床工作中無法直接明確胚胎分界線,所以大致采用脾曲作為左、右結腸的分界線。但這種分類方法不能精確指導臨床治療,有研究指出應采用基因組定位定義左右半結腸分界[3]。因為左、右半結腸癌在臨床表現、治療和預后上有明顯的差異,臨床中愈發重視結腸癌的原發部位。
一、左右半結腸癌的差異
左右半結腸癌患者在臨床表現、病理變化、影像學圖像、復發轉移機制、分子生物學、臨床治療及預后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隨著對這些差異深入了解,能指導實現患者的精準化、個體化治療。
(一)臨床表現及病理學差異
左半結腸癌(left-sided colon cancer,LCC)發病以男性為主,左半結腸腸腔體積小,腸內容物水分相對較少,且腫瘤多向腸腔四周浸潤生長,梗阻癥狀多見,除梗阻癥狀外還有腹痛、排便習慣改變、便血等,病理類型主要是腺癌,高分化程度,臨床確診早。右半結腸癌(right-sided colon cancer, RCC)主要見于老年女性,右半結腸腸腔體積大,腸內容物水分相對較多,且腫瘤多向腸腔單一部位浸潤隆起樣生長,梗阻癥狀少見,臨床癥狀以貧血,體重下降等消耗性癥狀為主,病理類型中印戒細胞癌比例明顯增高,未分化癌、黏液樣腺癌也在RCC 中常見,預后相對LCC 較差[4]。左、右半結腸癌的分布與年齡、性別呈明顯正相關性,有研究認為女性雌激素可通過降低結腸中次級膽汁酸鹽的生成,從而達到抑制腫瘤的目的,但隨著女性年齡的增長,雌激素水平的降低便會增加結腸癌的致病風險[5],而LCC 男性患者的發病與低纖維飲食,肥胖及吸煙飲酒不良生活習慣密切相關[4]。除這些因素之外,hMLH1 和MGMT 啟動子甲基化與癌癥發生密切相關,正常男性直腸黏膜上對于hMLH1 和MGMT 啟動子沒有一致的甲基化模式,但女性隨著年齡的增加,在右半結腸中hMLH1甲基化的等位基因比例明顯增加,且hMLH1 和MGMT 啟動子同時甲基化在女性的右半結腸中也更常見[6]。左右半結腸癌臨床特征見表1。
(二)影像學差異
對于結腸癌患者,術前較為精準的病情分析,能有效指導后續的治療。目前在臨床中對患者分期的判斷依賴于增強CT 及MRI。早期LCC 患者在CT 圖像中常表現為腸壁外緣光滑,周圍的脂肪間隙清晰;中晚期患者腸壁外緣變得毛糙,腸周脂肪間隙模糊甚至可見條索狀。而晚期的RCC 患者病變部位周圍脂肪層結構消失,常累及臨近器官及腹膜[7]。腸梗阻作為結腸癌患者臨床癥狀之一,在LCC 患者中尤為常見,在CT 圖像中可通過直接與間接征象給予鑒別,直接征象包括腔管狹窄,周圍臟器或組織受損等,間接征象包括腸管擴張,缺血性結腸炎等;在RCC 患者中,若同時伴有回盲瓣的功能障礙,可見小腸擴張。在MRI 中可看到腸壁受累情況,對于LCC 伴腸梗阻患者的腸壁明顯增厚,T1W1 為低信號,T2W2 信號稍增高,可見典型的“肩樣征”[8]。由于病變部位的炎癥或纖維化亦能引起與癌癥類似的影像表現,常常引起診斷的過高分期,甚至由于影像醫生的主觀性造成診斷的失真,而聯合應用人工智能輔助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而且有研究[9]通過對晚期結腸癌影像學特征進行人工智能分析,能準確有效鑒別Ⅲ、Ⅳ期患者,人工智能的應用會在患者的診斷、治療以及預后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0]。

表1 左右半結腸癌臨床特征
(三)復發轉移機制的差異
大約有1/5 的患者在首診時就存在著遠處器官轉移,LCC 易轉移至肝、肺,而RCC 常轉移至腹膜及淋巴結[4,11]。這與左、右半結腸解剖特點不同有關,左半結腸的靜脈血由腸系膜下靜脈,脾靜脈,門靜脈左分支匯入左半肝,而右半結腸的靜脈血由腸系膜上靜脈收集,腸系膜上靜脈與胃小腸側支血管形成豐富的血管吻合叢,同時淋巴管也有較多吻合,因此RCC 有著更高的淋巴結轉移。
在結腸癌患者中常發生KRAS 基因突變,而在RCC 患者中KRAS 基因突變更為常見。研究發現KRAS 基因突變與肝轉移有著較低關聯性,但與肺、腦轉移關聯性較好,值得注意的是發生KRAS 突變患者有著更低的肝轉移率和更高的卵巢轉移率[12]。還有研究發現在發生KRAS 突變的結腸癌患者中細胞因子甲狀旁腺激素樣激素與肺轉移密切相關,該激素可通過誘導內皮細胞凋亡與下調p38 MAPK 信號通路促使腫瘤細胞在肺內種植及轉移[13]。
對于RCC 患者而言,B 型快速加速纖維肉瘤(BRAF)突變更容易獲得,BRAF 基因是MEK/ERK 通路中最關鍵的激活因子,該基因突變會增加腹膜和遠處淋巴結轉移風險,但也降低了肺轉移的風險[14]。BRAF 突變常引起不良的病理類型如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及印戒細胞癌等,這也增加了RCC 患者病灶轉移風險。在BRAF 突變的結腸癌患者血清中,更容易發現由BRAF 基因誘導的長鏈非編碼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lncRNA 過度表達會促進上皮—間質轉化(EMT)以及增加淋巴結的遠處轉移。
PIK3CA 是常見的致癌基因,突變后可在RCC患者中高度表達。PIK3CA 基因突變主要發生于激酶區和螺旋區這兩個區域,該基因突變可顯著增強磷脂酰肌醇3-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的催化活性,同時還可以減少細胞凋亡,導致腫瘤浸潤轉移的增加。PIK3CA 基因突變通常合并BRAF 突變或者KRAS 突變。有研究發現PIK3CA 突變會增加腦轉移風險,當合并存在KRAS 突變時,2/3 的結腸癌患者會出現腦轉移[15]。
TP53 基因是一種重要的抑癌基因,該基因編碼的P53 蛋白能夠控制細胞周期,調節細胞生長,促進損傷修復,從而避免疾病發生。在LCC 患者中常伴有TP53 基因的突變,TP53 基因的突變會促進腫瘤微血管生長,增加肝轉移風險[16]。
(四)分子生物學差異
左、右半結腸不同的胚胎起源導致了其在分子水平上明顯差異,通過對DNA 序列的檢測,左、右半結腸中超過1 000 個基因有著不同的表達。結腸癌的發生進展涉及多基因參與,至少通過三條主要途徑發展[17]:染色體不穩定(chromosomal instability,CIN),微衛星不穩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和CpG 島 甲 基 化(CpG island methylator phenotype,CIMP)。導致CIN 的幾種機制包括:(1)抑癌基因如TP53 突變失活阻礙DNA 修復;(2)細胞內染色體不能正常分離,有絲分裂抑制;(3)染色體端粒功能出錯,癌變早期端粒縮短,癌變晚期端粒延長;(4)雜合性缺失,母方或父方等位基因的缺失,但在對應的同源染色體上仍然存在,雜合性缺失是CIN 陽性腫瘤的一個特征,至少25%~30%的等位基因在這些腫瘤中缺失。CIN 陽性腫瘤的特征還在于基因組的體細胞拷貝數改變(somatic copy number alterations,SCNA),從而導致異倍體結腸癌[18]。MSI 是短核苷酸重復序列處的遺傳不穩定性,由異常的DNA 錯配修復導致的高突變率引起,約10%的散發性結腸癌患者伴隨MSI。散發性結腸癌中的MSI主要是由于hMLH1 基因的啟動子甲基化導致轉錄沉默引起[19]。結腸癌中CIMP 的改變為含有CpG島(通常是抑癌基因的啟動子)基因位點過度甲基化,從而導致轉錄抑制,促進癌癥的發生[18,20]。
RCC 可通過ClMP 引起全基因組甲基化,在此過程中常伴有 MSI-H 表型和 BRAF 突變,同時RCC 也更容易通過MSI 獲得BRAF 突變。根據基因CpG 島甲基化程度高低可將結腸癌患者分為CIMP 高頻(CIMP-High),CIMP 低頻(CIMP-Low)和CIMP 陰 性(CIMP-negative)。在CIMP-H 組中MSI-H,BRAF 突變率最高,分別高達62.5%與77.3%[21]。MSI-H 突 變 常 伴 隨CIMP-H 可 能與MLH1 錯配修復基因缺失表達有關,此過程多發生于RCC 中[18]。KRAS、PI3KCA 突變增加與RCC 的發生相關,且TGFbR2、PTEN、AKT1、RNF43、SMAD2等基因突變在RCC中發現更多[17]。左右半結腸癌患者基因轉錄差異在TGF-β 信號通路中顯著,基因INHBA 在TGF-β 通路中差異性表達,在RCC 中編碼mRNA 能力及表達蛋白水平均高于LCC,INHBA 基因表達增加可能參與RCC的發生發展[22]。
約75% 的LCC 患 者 和30% 的RCC 患 者 發現有CIN 的腫瘤,LCC 中CIN 發生率明顯高于 RCC[19]。APC,SMAD4 和TP53 等基因突變發生率LCC 較RCC 高,而且LCC 多見點突變。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配體表觀調節素和兩聚調節素的過表達及EGFR 的擴增與LCC 密切相關,血管內皮生長因子1(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1,VEGF-1)
在LCC 中的表達也顯著高于RCC[4]。圖1。

圖1 左右半結腸癌分子生物學特征性差異
在RCC,LCC 中信號通路的表達差異也較大。在LCC 中富集Wnt 信號,而在RCC 中表達RAS,PI3-K 和轉化生長因子b(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TGF-b)信號。超過四分之三的右側腫瘤有RAS-MAPK/PI3-K 通路激活,而將近一半的左側腫瘤僅有RTK 通路改變。左半結腸生長與RTK(EGFR 為主)信號密切相關,結腸右側的RTK 信號較少,這可能與胚胎的起源相關。相比較而言,腫瘤沒有基因組途徑改變或僅RTK 通路改變的患者,生存期最長,而腫瘤有RAS 通路改變的患者生存期最短[17]。清楚分子生物學差異能有效判斷患者預后與指導用藥,從而改善結腸癌患者的預后。
(五)分子生物學差異對臨床治療的影響
RCC 與LCC 對分子靶向治療存在著明顯差異,腫瘤的原發部位可以評估抗-EGFR 治療效果。在FIRE-3 研究中,LCC 患者在應用一線化療藥FOLFOX 加用抗-EGFR 治療后,其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明顯高于接受一線化療FOLFOX 加 抗-VEGF 組 療(HR=0.63,95%CI: 0.48~0.85;P=0.002),但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無明顯提高(HR=0.90,95%CI: 0.71~1.14;P=0.38)。同 時 將 抗-EGFR 應 用 于RCC患者,患者的OS(HR=1.31,95%CI:0.81~2.11; P=0.28) 和PFS(HR=1.44,95%CI:0.92~2.26;P=0.11)均無明顯提高[23]。同時在CALGB 80405和PEAK 研究的結果中也得到類似結果。(表2)。 因此,RCC 患者對抗-EGFR 治療獲益小或不能獲益,這可能與RCC 中PTEN 表達水平較高有關,PTEN 可抑制PI3-K/AKT/mTOR 通路,降低抗-EGFR 治療效果[24]。此外,在一系列相關研究中對于LCC、RCC 患者采用一線化療藥+抗-EGFR治療后,LCC患者OS明顯高于RCC患者,說明抗-EGFR 治療更適合LCC 患者。見表3。同時KRAS、PIK3CA 基因突變可抑制抗-EGFR 治療效果,所以在抗-EGFR 治療前應該檢測KRAS及PIK3CA 基因狀態。
然而,腫瘤的原發部位不能預測抗-VEGF 的治療效果,抗-VEGF 治療組中RCC、LCC 患者的預后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有研究發現在RCC 患者中化療藥聯合抗-VEGF 治療比單獨化療能有效提高患者PFS(12.6 月vs. 9 月,P=0.017),但OS (27.5 月vs. 20.4 月,P=0.38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LCC 運用抗-VEGF 治療,其OS 和PFS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25]。近期也有研究表明應用抗-VEGF聯合全身化療可降低LCC 和RCC 患者的死亡率。在2019 CSCO 結腸癌診治指南中也指出對RAS/RAF 的野生型RCC 治療方案中主張兩藥/三藥化療±貝伐珠單抗,同時在轉化治療中提升了三藥化療±貝伐珠單抗的推薦強度[26]。

表2 CALGB 80405、FIRE-3、PEAK 關于結腸癌左半、右半患者治療預后結果

表3 FIRE-3、CALGB 80405、PEAK、CRYSTAL、PRIME、20050181 中抗-EGFR 對LCC、RCC 患者治療預后結果
免疫檢查點調節因子程序性凋亡蛋白 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可以通過抑制T 細胞的激活來對抗機體免疫系統,PD-1調節因子在腫瘤細胞及組織中均有表達,腫瘤細胞通過PD-1 可沉默腫瘤的免疫應答,若能阻斷PD-1 及其配體PD-L1 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發揮抗腫瘤作用[4,27]。抗PD-1 及其配體PD-L1 治療在MSI-H 患者中有效,由于抗PD-1 藥物出現,IV 期MSI-H 的RCC 患者預后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六)生存預后的差異
在預后方面,結腸癌患者的預后與原發腫瘤的分期、位置密切相關。即Ⅰ期預后無明顯差異,Ⅱ期RCC 患者預后較好,可能與II 期患者高MSI 率相關,總的來說Ⅲ/Ⅳ期LCC 預后要好于RCC 患 者[28]。
CIMP 和MSI 與結腸癌預后相關。有研究發現 CIMP-H 腫瘤有著病理分期晚、分化程度低、高黏液組織型的特點,CIMP-H 的結腸癌患者預后差,尤其CIMP-H 伴微衛星穩定(microsatellite stable, MSS)的患者。由于MSI 會增加細胞毒性T細胞浸潤和腫瘤微血管生長,在II~III 期患者中,MSI-H 患者預后優于MSS-H 患者,免疫應答活躍與良好預后相關,但IV 期患者即使有MSI-H,預后仍不佳[29]。近來,有研究將結直腸癌6 個獨立的分子分類特征進行整合,得到了4 個不同的分子亞型(consensus molecular subtypes,CMSs)。CMS1(MSI 免疫型)表現為MSI 和活化免疫系統,腫瘤為CIMP陽性,SCNA低表達型,有BRAF突變,常常發生在老年女性的右側結腸。CMS2(標準型)表現為MSS、CIN 和WNT/MYC 通路激活,腫瘤為CIMP 陰性,SCNA 高表達型,APC 和TP53 突變,發生在左側結腸,該亞型復發后生存率良好。CMS3(代謝型)的特征表現為MSS,具有CIMP低頻和SCNA 中間表達型,顯示KRAS 和APC 突變,并與上皮組織特征和代謝失調相關。CMS4(間充質型)表現為MSS,具有CIMP 陰性和SCNA高表型,發生在晚期,CMS4 較差的整體存活率與轉化生長因子-β 活化、間質浸潤、上皮間充質轉換激活、基質重塑和促血管生成相關[30]。RCC 主要是CMS1 和CMS3 型,但4 種CMS 亞型均可在RCC 中發現。CMS 分型與患者的復發及預后相關,在4 種CMS 亞型中,CMS4 患者OS 以及PFS 最短。對于復發轉移患者,CMS1 患者的OS 明顯變短,但CMS2 患者的OS 相對較長[30]。
目前,一致認同BRAF 突變的結腸癌患者預后欠佳,若轉移性結腸癌患者發現BRAF 突變陽性則不主張手術切除轉移灶。對于結腸癌術后的患者,若伴有KRAS 基因突變,其OS 和RFS 都會明顯縮短,且KRAS 突變更容易引起肺、腦等位置轉移[12],KRAS 基因突變可作為一個獨立的預測因素去評估患者的預后與轉移風險。同時BRAF和KRAS 的高頻突變與抗-EGFR 在RCC 治療療效差相關,對于BRAF 和KRAS 基因高頻突變的患者,即使積極治療,療效也欠佳。NOX4 基因(NADPH oxi-dase 4)的高表達在LCC 患者中可認為是復發預測因子,而CDX2(caudal type homeobox 2)的低表達可認為是RCC 患者的復發預測因子[31]。
二、臨床治療決策思辨
針對左右半結腸癌特征性差異對患者采取針對性、個體化治療尤為關鍵。LCC 患者臨床癥狀明顯,診斷時病理分期明顯早于RCC 患者,且對于Ⅲ、Ⅳ期LCC 患者的預后明顯高于同期別RCC 患者,對于LCC 患者即使有遠處肝轉移,也推薦積極治療。對于左右半結腸癌T1N0 患者主張內鏡下治療, T1-4N0-2M0 主張腹腔鏡下行根治手術,LCC 患者常伴隨腸梗阻癥狀,當腸道水腫嚴重時,主張 Ⅰ期切除、吻合+近端保護性造口或Ⅰ期腫瘤切除,近端造口遠端閉合,且隨著對支架置入深入研究,支架置入聯合腹腔鏡手術有望成為首選方式[32]。 左右半結腸癌患者化療方案基本相同,對于轉移性LCC 患者,一線化療藥+抗-EGFR(西妥昔單抗)能有效提高患者OS,同時抗-VEGF(貝伐珠單抗)對LCC 患者亦有效,但臨床中不推薦兩種靶向藥聯用,且在抗-EGFR 治療前應該檢測KRAS及PIK3CA 基因狀態。對于轉移性RCC 患者,主張一線化療藥+抗-VEGF(貝伐珠單抗)治療[26]。由于RCC 患者中MSI 多見,對于MSI-H 患者抗PD-1 及其配體PD-L1 治療能有效改善患者預后。RCC 患者病理類型差,預后不佳,手術后的患者更應加強隨訪的頻率,密切關注患者有無復發轉移。
綜上所述,RCC 和LCC 有著明顯的臨床和病理差異,相對于LCC,RCC 分化程度低,侵襲轉移能力強,對靶向藥物治療相對不敏感。同時仍有很多方面需進一步研究闡述其機理,如RCC 與LCC 在分子特征和復發轉移機制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是這些差異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腫瘤的結果尚未清楚。不同的分子特征會賦予RCC、LCC 獨特的病理類型,臨床特征,從而導致不同的預后結果。通過對左、右半結腸癌的研究,有利于指導個體化和精準化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