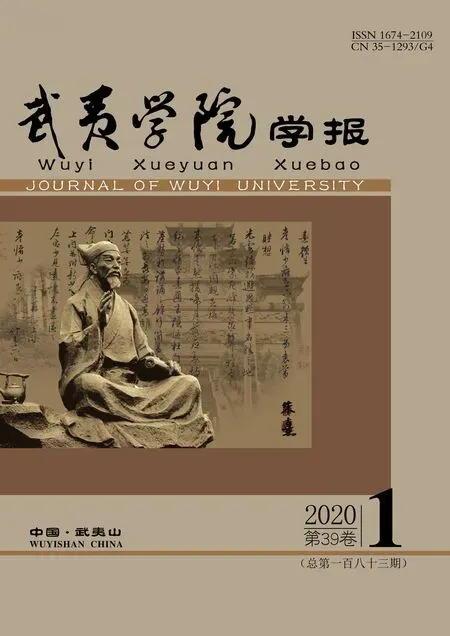白人殖民統治下印第安人的自我救贖之路
——以風歡樂詩集《美洲的黎明》為例
張來運,牛 蔚
(合肥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一、引言
風歡樂(Joy Harjo)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印第安詩人。其詩歌創作大多關照現代文明沖擊下的印第安部族的生存困境,以及印第安文化與美國殖民統治的沖突。她于2015 年9 月獲得美國斯蒂文斯終身成就獎,這是美國詩歌創作界極具影響力的獎項。此外,她還獲得“美國杰出青年婦女”的稱號。雙語版詩集《美洲的黎明》作為風歡樂詩集中的重要代表,是“當代國際詩人典譯叢書”中的一本,由其精心甄選的三十三首詩歌組成,分別選自她七部不同的詩集。在這些詩歌中,風歡樂試圖借助詩歌揭露白人殖民統治的殘酷剝削和印第安人被殖民后的生存困境,以自己強烈的責任心和民族意識積極為印第安民族探尋一條自我救贖之路。
目前學界關于風歡樂詩歌的研究較少,大多聚焦于風歡樂詩歌中蘊含的印第安民族記憶故事以及詩人表現出的頑強抗爭意志。洪流[1]研究發現,風歡樂詩歌主要著眼于印第安民族傳統,主張通過記憶追尋實現向印第安神話世界的精神回歸,且這種回歸具有均衡的位置與空間意識。遲欣[2]對風歡樂詩集《她曾有幾匹馬》中所蘊含的印第安部族文化中的精彩記憶故事及其體現的詩人的頑強抗爭精神進行分析。洪流和馬廣利[3]兩位學者對其詩歌中萬物相連的生態主題進行研究,發現風歡樂作品中凸顯出詩人對土地、非人類生命以及回歸傳統的思考。
同樣,在詩集《美洲的黎明》中,也不乏詩人對印第安民族傳統的彰顯以及對白人殘酷殖民統治的披露。但透過詩集,更引人深思的是詩人在險惡生存環境下嘗試探索的救亡圖存之路。而且,這條救亡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曲折漸進式的。隨著白人殖民入侵的不斷加深,風歡樂對于民族危亡的態度也隨之發生改變。詩人借用詩歌尋求救亡之路,現實沖擊之下,她對民族危亡態度的改變、對救亡圖存的自省思考都包蘊在其詩歌之中。其中,詩人有過無奈的哀號、奮起抗爭的決絕,更有迂回包容的求和。本文對風歡樂在《美洲的黎明》中展現出的印第安人自我救贖之路進行具體探究,以期加深當代人對印第安民族歷史境遇以及民族傳統的了解,為進一步探究美國土著民族文化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美洲的黎明》中的曲折式救贖之路
風歡樂的詩歌創作大多圍繞著當時殖民、暴力與槍殺遍布的美國社會展開,《美洲的黎明》也是著眼于白人的殖民剝削與印第安人的生存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風歡樂的詩歌是那個殖民動亂時代的產物。風歡樂談到自己的詩歌創作時也曾說過:“我一直都特別關注,在這樣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印第安人如何保持其位置和文化,我的詩歌與此緊密相關”[4]。
(一)《美洲的黎明》社會背景
1492 年哥倫布踏上美洲大陸后,歐洲文明開始在印第安部族發芽生長。不斷進行的侵略擴張,給世代生長于此的印第安人帶來滅頂之災,他們的家園遭到前所未有的踐踏,悠久的印第安文化也遭受毀滅性的破壞。1830 年,美國總統安德魯·杰克遜頒布《印第安人遷徙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政府購買印第安人在東部的土地,把印第安人移居至密西西比河以西、洛基山脈以東的大平原地區,由美國政府負責移民的費用,此外,每年向印第安人提供食物和必要的武器[5]。在美國軍隊的武裝押送下,印第安人被迫離開東部故土,移居到印第安領地。1838 年最后一批佐治亞州的印第安人也在士兵的槍口和刺刀下含淚離開家鄉來到西部,他們移民所經過的路線就是美國西部開發史上著名的“血淚之路”,這6 年間一共有9 萬印第安人被迫移居到西部,其中有很多人死在“血淚之路”的途中[5]。1864 年11 月29 日,約700 名隸屬于科羅拉多州第三騎兵軍團的士兵,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襲擊了居住在科羅拉多州南方印第安保留地的一個印第安部族,當地居住著約200 余名夏安族及阿拉巴霍族居民,這些居民遭到軍隊無情的屠殺,估計造成163 名印第安人死亡,其中三分之二是婦女及兒童[5]。在著名的沙溪大屠殺中,許多印第安人在死后遭到無情的肢解,他們身上的許多器官被美軍做成了飾品,以此作為戰利品。
白人在印第安部落大肆燒殺搶掠,掠奪完印第安人民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后,為進一步達到侵略目的,又重新制定安置計劃,以潛移默化的手段進一步同化印第安人,讓他們逐漸融入到占據主導地位的白人文化中去。聯邦政府試圖通過語言的訓練、歷史的歪曲以及將印第安傳統宗教和文化儀式視為“異端”和“愚昧”,以此來改變年輕一代印第安人的信仰體系,這不僅讓印第安人失去賴以生存的家園,更是陷入無盡的精神創傷之中。
(二)殘酷現實下的無奈哀號
風歡樂詩集《美洲的黎明》圍繞著印第安部落在白人黑暗的殖民統治下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和艱難處境展開。詩歌大部分以講故事的形式對白人忘恩負義的狂野行徑進行披露,將彌漫在印第安部落的殺戮與暴力、悲慘與苦痛表現地淋漓盡致。“血淚”“死亡”“戰爭”等詞幾乎出現在該詩集的每一首詩歌當中。在《錨地》這首詩歌中,詩人寫道:因為有誰會相信這傳奇般的驚悚故事,九死一生,卻在那些注定不能存活的人的身上發生?[5]詩人運用反諷的筆法書寫那些在白人眼中“不該存活下來的人”的印第安人,真切再現白人統治下的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面對死亡的詛咒、無情的槍殺、獨裁者的轟炸和保留地的動蕩不安,詩人忍受著無與倫比的痛,卻又別無他法,只能將這一切訴諸文字,用融合著自己血淚的筆墨記述著最悲慘的殖民地境遇。在詩歌《或許世界就此終結》中,詩人寫道:或許世界將終結于廚房里的餐桌,此刻,我們會狂笑,會哭泣,吃一口最后的美餐[5]。在這首詩中,用來滿足口腹之欲,享受生活的餐桌都可能變作生命的終結之地,可喪命之時,他們卻只能狂笑哭泣,毫無他法。白人侵略下,印第安人的聚居地隨時都有可能被掠奪,他們的平靜生活早已被打破,每天只能生活在惶恐之中。在殖民統治的恐怖陰影下,目睹民族生存受到威脅,詩人一句“或許世界將終結于此”寫盡印第安人悲慘的生存情狀,面對生死,詩人筆下的印第安人只能狂笑哭泣,吃一口最后的美餐,這對死亡無抗爭的接受,盡現詩人面臨死亡和鮮血的無奈和絕望。在白人殖民統治下,境遇悲慘的印第安人失去的不僅僅是生命,更是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立場和民族認同,詩人對此同樣無奈地發出哀聲,在詩歌《拱手承讓》中,詩人這樣表述:哦,你扼住了我的脖頸,我卻給你遞上項鏈。你對我開膛破肚,我卻愿意遞上屠刀。你已將我吞噬,我卻躺在火上將自己燒烤[5]。白人殖民統治帶來的不單單是掠奪和屠殺,殖民恐怖下,印第安人被迫放棄自己的立場,就連印第安民族的文化根源也將會不復存在,面對民族即將毀滅,《拱手承讓》中的述說滿是詩人的苦澀與哀傷。風歡樂在采訪中曾承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都不敢直面自己民族的歷史。面對這般慘痛的民族史,鮮血流淌,槍林彈雨,種族排斥屠殺,種種殘酷的現實甚至讓詩人對自己的民族身份產生疑問。詩歌《神秘》中詩人這樣寫道:我本人到底是:土著人、野蠻人抑或是魔鬼?[5]詩人這種對于自我身份的懷疑是整個印第安部族在血腥戰爭的背景下自我身份危機的映射。白人的暴力行徑將印第安人逼到無奈的絕境,在死傷和無望的悲痛中漸漸失去民族身份的認知,為民族抗爭的勇氣和信心也隨之消失。就像詩歌《恩澤》中所說:我說,恩澤是一個手托時間的女人,抑或是逃出記憶的白色野牛[5]。從該詩中可以看出,詩人希望能夠逃離殖民剝削的記憶,忘記這段殘酷歷史所帶來的創傷和悲痛,甚至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到她對于殘酷現實的逃避。因而,風歡樂通過運用敘事性的詩歌,一方面控訴白人的殘酷無情,另一方面也對印第安部族所面臨的身份危機進行全面揭露。在毫無人性的殖民統治下,詩人發出痛徹人心的無奈哀號。
(三)喚醒民族奮起抗爭的嘗試
在風歡樂的詩歌中,可以看到印第安人民面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沖突時的猶疑與無助,詩人用反諷的筆調批判印第安人民面對白人的殘暴行徑時的麻木與自我放棄。但冷靜思考之后,詩人并沒有就此沉浸在痛失同胞的悲苦與絕望中,而是逐漸從碎片式的民族歷史回憶中喚醒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并在重新定位印第安部族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沖擊的矛盾關系中,激發出自己作為印第安詩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詩歌為媒介,給予印第安部族尋求新生的勇氣和信心。風歡樂借助詩歌,努力嘗試著擺脫歷史陰影給印第安人帶來的心靈鉗制,面對民族危亡,她不單單發出哀號,更是開始勇敢地面對民族受屈辱的歷史,嘗試著喚醒印第安人的民族記憶與民族認同,與白人殖民統治進行積極抗爭。
首先,詩人試圖用印第安部落的壯美山河來喚醒印第人民的民族意識,喚起他們的抗爭精神。在印第安人的眼中,人與動物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在詩歌中她大力歌頌印第安部族的山川河流和雄壯萬物,詩人還在詩中反復倡導,現代社會的裂痕可以通過天地萬物的和諧關系來彌合。在這些詩歌中,詩人充分展現各個地域的美麗景色以及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統一,借助詩歌中呈現的和平景象,營造出一種安全和完整的氛圍,進而喚起印第安人民為維護民族安全而戰的抗爭意識。風歡樂在其詩歌中大量運用自然意象如:大雁、繁星、雨水、花朵、山脈、蒼鷹、駿馬等來展現印第安壯美的自然景觀。在其經典之作《她曾有幾匹馬》中,一群矯健雄壯的馬有著摧毀一切的力量,而且詩中說:她的馬,說他們無所畏懼,她的馬期待重生[5]。風歡樂筆下的馬不僅雄美健壯、激情靈動,而且具有不畏艱險、樂觀向上、堅韌不拔的精神品質。《鷹之歌》的主要意象是一只自由飛翔、頑強生長、毫無拘束的老鷹,詩中風歡樂這樣寫道:我們明白你早已看穿了我們,甚至我們要以極大的關懷與仁慈對待萬事萬物[5]。風歡樂的詩歌中,字里行間彌漫著詩意的壯美,她將整個印第安民族物化為自己筆下的動物意象,將自己的反抗精神寄托于各種動物意象中,也通過動物意象來呼吁印第安人民重拾民族記憶,奮起抗爭。作者通過描寫印第安部落雄壯的自然萬物,進而揭示這種天人合一、循環往復、與自然親密無間的和諧關系,書寫美洲文化的史實,進而喚起印第安傳統的部族文明和自我意識,擺脫那種集體無意識的精神創傷的狀態[6]。
其次,風歡樂還通過民族記憶的覺醒來修補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嘗試對部族歷史文化身份重新進行定位。詩人憑借勇氣和智慧不斷搜尋民族文化中精彩的民族故事,超越嚴峻的現實,走進歷史、再現歷史,進而實現印第安部族世界的精神回歸[7]。在《為圣人消解沖突》中,詩人跟著歷史的腳步,走過淚水之路的每一個地方,記錄下當地人們曾經的歡樂和成長。記憶是追敘歷史的依據,無論個人的歷史還是整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都有賴于我們個人或集體的記憶[8]。詩歌《恩澤》中,詩人凝固在過去的記憶中,尋覓著恩澤。詩歌最后寫道:我明了,有些超越了記憶的東西[5]。這種超越記憶的東西便是恩澤,也是民族傳統歷史賦予當地人的一種信仰和力量,正是這種民族歷史的回憶,才能在支離破碎的殘酷現實面前仍然鼓勵著印第安部族保持對民族傳統的敬仰以及對民族身份的認同。詩歌《黎明之夢的軌跡》中,風歡樂寫道:火山巖地緩慢燃燒,是因為神祗們的愛戀。那是個古老的故事,我們寓于其中,成了故事的主人公。我們靠近神靈的距離,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5]。這個故事融合印第安部族神話及靈視經驗,不僅對部族根源進行追溯,而且還大力彰顯印第安部族的特有的民族神話信仰。在《一種通往來世的地圖》 中,風歡樂更是用想象的力量,化身一個神話精靈,在“第四世界”末日中刻畫出“第五世界”的天圖之旅,正像通往天洞之路沒有開始,亦不會結束一般,因此這是一個無時不在的旅程。這也就暗示著印第安人即使處在民族文明毀滅的邊緣,也會像宇宙神靈般循環往復,生生不息。詩人用“原諒季”揭示對歷史記憶應有的態度以及對回歸過往的祥和與安寧的追尋,以此求得,真正能主宰自我命運的印第安民族與文化的生生不息[9]。面對生存絕境,風歡樂不只是用悲愴的語調記錄下她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切,她不單單對著困境記述哀號,而是借用民族歷史的力量和宇宙神靈生生不息的精神傳統直面白人殖民統治的黑暗和壓迫。詩人的《牢記》更是將這種對民族記憶、民族身份的呼吁和倡導推向新的高潮,詩人這樣寫道:牢記你誕生的一刻,你如何擁有了生命。牢記這一草一木、一花一樹、一鳥一獸、一蟲一物,它們都有自己的族群,也由于自己的歷史。牢記萬物皆運動,皆成長,牢記這一切包括了你!牢記,千萬要牢記![5]風歡樂用民族記憶不斷激勵鼓舞印第安民族直面慘淡的現實,同時鼓舞他們在尋找民族記憶中重新架構當代印第安部族文化認同,促使民族意識覺醒。
歷經面臨絕境時的悲情與無奈,繼而激發抗爭的奮力呼喚,詩人更是負重前行,摒棄所有的恐慌和畏懼,在民族文化的記憶與焦慮中,以文為武,在詩歌中進一步直接呼吁民族崛起抗爭,以圖民族生存與文化傳承。語言不僅是情感的承載,更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可以用來抵抗白人對印第安人的入侵、剝削、驅趕與壓迫。風歡樂曾寫道:“我們抵抗不公的待遇。我們要以對全體人們來說正直的方式來反抗,我們通過寫作、歌唱、創造新的藝術、恢復和延續早先的經典傳統,通過立法、制定新的法律、甚至通過把我們的論文、詩歌故事和藝術整理進入原住民的法律期刊來反抗”[10]。在風歡樂的詩歌中,這種積極抗爭的精神是隨處可見的。她認為印第安人應該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奮斗目標和自己的未來。她拒絕與主流文化同化并且以堅韌不拔的斗志來破除沖突,尋求新生。詩歌《不要給魔鬼投食》中,風歡樂以決絕的態度反對白人對于印第安部族的入侵和剝削。她將白人比喻成“魔鬼”,盡情控訴白人統治者在印第安部落的一切罪行。“有些魔鬼癥徘徊于你思緒的洪流,尋覓安家的落腳點。有些魔鬼處心積慮地闖入你的領地。”[5]白人在印第安部族肆無忌憚的燒殺搶掠,同時也侵蝕著印第安傳統文化,風歡樂對這種歷史創痛進行近距離的寫照與揭露,這是一種直面殘酷現實的勇氣;她慨然高唱“不要給魔鬼投食”,這更是一種對不公待遇的勇敢反抗,也是鼓勵全體印第安人民覺醒并奮起反抗的呼喚。其詩歌《日出》道出詩人對于美好未來的期盼和憧憬,現實世界的殘酷并沒有阻礙風歡樂前進的腳步,盡管與白人魔鬼抗爭的戰爭最終還是以失敗收場,但是她仍未放棄期待未來的勇氣和執著。她相信“終有一天,不屈不撓,我們的靈魂會目睹遞給太陽的禱文。我們跟隨生命的光影移動,我們將要奔赴那個屬于我們的地方。”[5]毫無疑問,她的詩歌給絕望悲傷中的印第安部族帶來新的希望和信仰,從精神層面給予當代印第安人援助之手。風歡樂想要用語言喚醒印第安人不容忘卻的民族記憶,喚起他們沉睡已久的抗爭精神。民族歷史的責任感驅使著風歡樂以詩歌的力量反抗白人的殖民統治,用自己的智慧撫慰印第安人的精神創傷,并不斷期待著重生。
(四)包容融合的和平共處策略
盡管風歡樂用詩歌力量積極鼓舞印第安人民奮起抗爭,但她不得不承認印第安部族的抗爭屢屢戰敗這一現實。在白人殖民擴張的鐵蹄下,印第安部族最終瀕臨民族滅亡。此時,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風歡樂展現出詩人的睿智與擔當,她積極調整民族救亡之路,改變原本強烈反抗和積極抗爭的救亡方式,開始探求一種包容融合的和平共處之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風歡樂在目睹頑強抵抗戰略對阻止白人殘暴行徑無濟于事之后,轉而提倡一種非暴力的、和平的、包容的民族平衡戰略。她在不斷的自省中積極轉換思路,借用詩歌懇切的表達,積極謀求美洲大陸的和平共存之路。在詩歌《后殖民時期的傳說》中,詩人寫道:“我們的孩子放下了武器,與我們一道拍打著想象的翅膀”[5]。詩人希望印第安民族放下自己的武器,用包容融合的態度對待白人的殖民同化。然而實際上,白人卻一次又一次的得寸進尺,不斷地屠殺當地印第安人。面對支離破碎的殖民現實,風歡樂并沒有放棄對于和平和自由的追尋,甚至以更加虔誠的態度為自己的敵人祈禱。詩歌《清晨,我為我的敵人祈禱》中詩人寫道:“它聽到了咬牙切齒的怒氣,也聽到了祝福”[5]。盡管白人在印第安部族犯下滔天罪行,但是詩人仍然將其視為朋友,以包容慷慨的態度對待白人殖民者。在詩歌《為圣人消解沖突》中,風歡樂依據現實情況,提出具有建設意義的和平共處策略。詩人提出消解沖突的基本原則,并提倡用有效的交流手段來展現和加強雙方的信任與尊重—詩人承認英語作為交流語言的合理性。詩中寫道:我們用英語一起商談,那是一種交易語言。這種交易語言能讓我們跨越諸多語言的界限[5]。詩歌第四部分“減少抵觸情緒,打破防御的鏈條”更是承載了詩人對印第安民族可以與白人殖民者和平共處的強烈呼聲和期盼,她寫道:“我和你已經不分彼此,只有我們。只有我們團結在一起,在那個地方,我們,好像我們就是樂曲。我們重新跳起藍調,停留在平緩的第五音程,為的是知此知彼,肝膽相照”[5]。在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的人文主義關懷,風歡樂并沒有逃避戰爭帶給印第安部族的百般摧殘,她在正視印第安部族的悲慘境遇的同時,又基于現實,希望在印第安民族做出妥協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和平民主的策略保留印第安部族的最后生息,重建和平安寧的美洲大陸。事實上,經歷九死一生的考驗后,印第安各部落的處境有了很大的改變,一些開放的民族已經與美國社會同化,而且與白人和其他種族通婚的現象都很普遍[12]。
面對殘暴的白人殖民統治,詩人以自揭傷疤的方式來喚起印第安人民對這段歷史的關注,她的歷史記憶中不但充斥著血腥戰爭、被迫遷徙、強制教育、種族主義和民族同化主義帶來的悲痛,同時也裝載著印第安部族雄美的地域景觀、悠久的傳統歷史文明,詩人希望以此來喚醒印第安人民對他們傳統部族身份的認知,進而實現印第安民族的救亡圖存。而最終,風歡樂認為真正切實有效的救亡之路就是倡行包容融合的和平共處策略,用包容之心不究過往,用英語來增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用理性思維積極融入到后工業時代的美洲大陸文明,尋求與白人和平共存、共謀發展的救亡之路。
三、結語
《美洲的黎明》可以說是一部民族救亡史,風歡樂以詩歌為武器,積極探索民族生存的途徑,希望實現印第安民族的綿延不息,實現美洲大陸的和平安寧。作為一部“救亡史”,詩集全面詮釋風歡樂在困境中救亡圖存的曲折嘗試過程,充分展現出詩人的理性與智慧。起初,面對白人的殘暴剝削和民族破碎的現實,詩人有著難以承受的絕望和無奈,她用血淚文字向世人哀號痛陳;但是,即便沉浸在悲痛之中,詩人也沒有放棄對白人殖民者殘暴統治的抗爭,她試圖用文字喚醒印第安人民的民族意識[13],《美洲的黎明》便根植于印第安部落文化,試擺脫印第安部族無歸屬狀態,增強印第安人民民族身份認知[11],進而喚起他們的抗爭精神,鼓勵印第安人民投入到解救民族危亡的實踐中去;抗爭失敗后,在民族危亡之際,她又提出包容融合的和平共存策略,基于民族生存現實,以求用印第安民族的包容妥協,維持印第安民族的長久發展,維系美洲大陸的和平安寧。因而,風歡樂的詩作是對美國土著民族歷史境遇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對其文化傳統的弘揚與傳承,讓當代讀者能夠更加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印第安部族的歷史發展,引發讀者思考與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