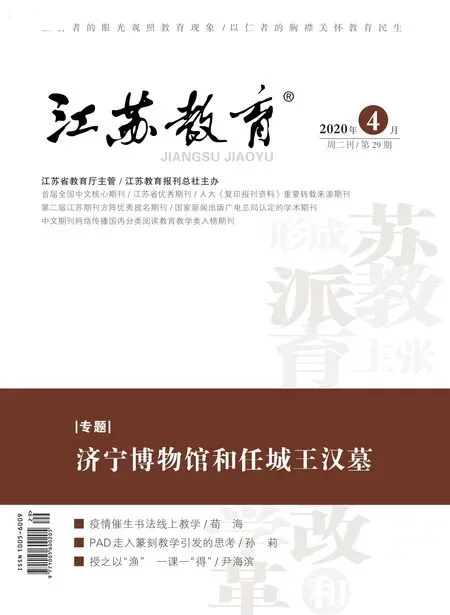卻顧所來徑 蒼蒼橫翠微
——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仙女鎮龍川小學寫字特色課程建設漫談
王 浩
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說:“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觀念、儀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祟拜對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這三者引導和消溶在以親子血緣為基礎的世間關系和現實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導向異化了的神學大廈和偶像符號,而將其抒發和滿足在日常心理——倫理的社會人生中。”而書法,正是代表“中國人的哲學活動從思維世界回歸到實際世界的第一境,它還代表擺脫此實際世界的最后一境”。相對于不同文明體系中建筑、雕塑、音樂等核心文化成果,熊秉明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
萬丈高樓平地起,承載了如此文化重擔的書法,更應及早在小學教育中得到呵護和弘揚。近年來,應揚州市江都區仙女鎮龍川小學邀請,筆者有幸深度參與龍川小學的寫字課程建設,目睹該體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謹從個人視角,對該校相關工作做一客觀梳理。筆者覺得他們的成功主要取決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辯證的認識
當下小學階段的書法教育,究竟和我們傳統的書法研習有怎樣的聯系和區別?龍川小學相關決策層就此問題,曾與本人及其他書法專家開展專題討論,筆者認為他們對此擁有清醒的認識:(1)書法教育首先是漢字書寫教育,是語文學科教育的重要組成,同時也是學生有效書面交流的基本保證。(2)書法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也是培養學生審美意趣,乃至健全人格的重要載體。
正是本著這樣切實同時具備文化高度的辯證性認識,該校無論是在校內師資的引導培養,還是在外聘教員的崗前交流,都注意到了硬筆書法實用性和文化品質兼顧的問題:(1)要求教師選擇硬筆書法教材時,例字應平正清晰,同時源于傳統碑帖,從審美上和經典一脈相承。這一點,在魚龍混雜的硬筆書法教育現狀中至關重要。目前來看,相當多的校外書法培訓機構,為了追逐時效性,紛紛推出所謂的書法速成班,其實質是把具備深刻文化內質的書法傳統簡化為簡單的視覺圖式,從根本上閹割了書法的文化屬性。(2)要求在時間比較充裕的假日課堂和社團教學中,有意識地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介紹傳統書法的人文背景:例如柳公權的“心正則筆正”說,蘇軾的觀點“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等等,讓學生在基礎性寫字訓練的同時,初步感受到中國書法所擁有的文化內涵。
二、完善的體系
龍川小學在書法課程建設中,就筆者所見而言,從師資配備、時間保障、理論歸納等方面,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教學研究體系。正是依托于這樣的制度性建設,學校的書法教育在全市范圍常態化高質量開展。
在職語文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及心理狀況,同時接受過三字一畫的嚴格訓練,是學校書法教育的主力軍。該校為了進一步提高教師素質,帶領他們走出校園看展覽,提高鑒賞能力;把書法名家請進校園搞講座,做指導,提升他們的業務水平。教師業務水平的提高直接作用于普遍性的教學成效。而對于那些興趣濃厚,基礎較好的學生,學校外聘專業能力過硬的書法家擔任他們的社團指導教師,并及時對外聘教師課堂效果予以評估。從教育學原理出發,給予他們教學技巧的建議和幫助,從而保證教學的成效。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龍川小學的書法教學時間設置靈活,形式多樣,筆者以為最可稱道的卻是每天語文教學中10 分鐘的習字時間。這10 分鐘太容易被侵占,太容易流于形式了。但是該校在制定《閱讀課堂教學評價標準》時,對這10 分鐘做出了詳盡的規定,其目的只有一個:保證學生這10 分鐘的時間是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的書寫實踐。現實證明,每天的10 分鐘帶來的是整體書寫水準的普遍提高,這就是體系約束的勝利。
理論源于實踐,反過來又對實踐具備指導、促進作用。龍川小學的決策者們對于書法教學理論體系建設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這個要求既針對于每位教學者,更針對于校級層面。他們善于發現書法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協力攻關,進而拿出指導性的意見方法。例如該校揚州市級課題《小學生硬筆書寫“練”、“寫”分離的對策研究》,針對性強,對于普遍的小學書法教學的改進具有重要意義。
三、科學的方法
筆者既參與了在職語文教師寫字教學的聽課與交流,也參與了學校書法社團的實際教學。在與在職語文教師的交流中,筆者感覺到大家逐漸都抓住了一個點,就是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讓學生確立明確的學寫字、寫好字的主體意識,并逐漸實現自主修正。課堂學習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學生確立了這樣的意識,每次完成作業、寫作文都會形成自覺的寫字練習。
至于書法社團的教學,筆者有許多切實的體會。面對高年級,并具備濃厚興趣的同學,筆者覺得寓教于樂是一個不錯的狀態。在這樣的社團教學過程中,筆者模糊了書法等級概念,也不做具體的成果要求,而是反過來聽取學生的訴求:比如有的學生希望得到更多字體的嘗試,那么就給與他嘗試的機會;有的學生希望切入毛筆字的學習,那么就幫助他們學習基本的毛筆書法技法;并及時穿插中國書法的重要知識于即興的演講中……筆者小時候讀過《窗邊的小豆豆》這本書,對小林宗作先生的教學方式甚為向往,但亦深知作為大規模的教學活動,絕無如此可能。近年來龍川小學的書法社團教學,應該算是一次具體而微的嘗試,效果非常好,師生之間確立了融洽的感情,寬松活潑的課堂氛圍。
四、濃厚的氛圍
筆者之所以滿懷興趣,全程義務參與到龍川小學的書法學科建設中,一方面是因為個人對于少兒文化教育的真誠情結,另外一方面則在于該校濃厚的書法文化氛圍。校長潘湘云兄二十多年前和本人相識于一位書畫師長門下,那時候他就寫一手嫻熟的草書。或許是在他的倡導和身體力行下,學校的書法文化氛圍相當之濃厚:學校的教學樓上有書法家的題字,學校的手提袋上也是書法家書寫的校名,在學校辦公場所、教室乃至走廊里,都懸掛著頗具水準的書畫作品……走進這樣的校園,對于書法教育工作者來說,如若家園,在這里感覺到校方對于書法藝術的高度重視。而所謂的教育,不正是言傳身教嗎?
也正是這樣的氛圍,自然給予相關教職員工以足夠的壓力和動力,在筆者以及其他書法家為教師開設的講座上,我們能夠感覺到:教師們提出了自己切實的思考,切實的困惑,進而引發了切實的交流。
一切關乎成功經驗的總結其意義絕非簡單的表彰,更在于啟發來者,更好地做好相關的工作,書法課程建設也不例外。希望筆者這些旁觀角度的點評,對于相關的集體和個人工作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