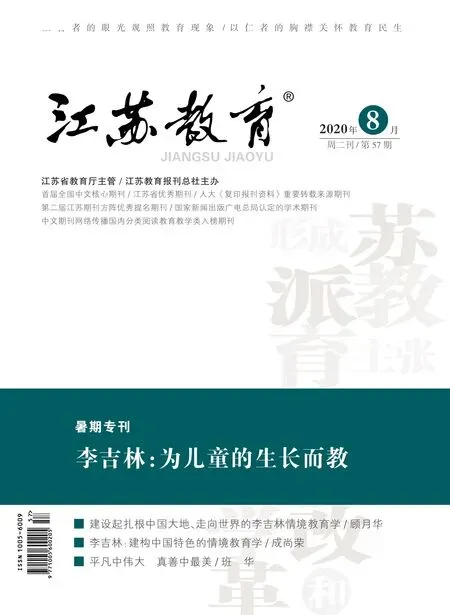談李吉林的教學觀
郝京華
觀念是人的一種意識形態,馬克思的一段話不僅形象地描述了觀念的特征,同時也指出了觀念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的重要性: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用蜂蠟建筑蜂房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1]
觀念與行為之間存在三種關系狀態:(1)可以意識與表達,也能夠付諸實踐;(2)可以意識與表達,但不能付諸實踐;(3)不能意識與表達,但能夠付諸實踐。[2]
教學觀是教學觀念的簡稱,“是教師從實踐經驗中逐步形成的對教學本質和過程的基本看法”(Larsson,1983)。觀念決定人的行為這一哲學命題轉化為教學觀念與教學行為的關系便是:教師的教學觀念決定了其教學實踐的各種行為。教學觀念應是教師素養的核心要素。
與教師的教學知識相比,教學觀念具有明顯的情感參與和主觀判斷,因此,它是主體性的、個人化的認識,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它對教師的影響更大、更直接。
李吉林老師的教學觀屬于“可以意識與表達,也能夠付諸實踐”類,但分散在她等身著作中的各篇文章中。本文擬對李吉林老師的教學觀做一點整理。因篇幅所限,本文只涉及知識觀、學習觀、目標觀這三個與教學觀有關的單一觀念;又因時間及學養的局限,偏見及膚淺在所難免。
李吉林老師的教學觀可以分為核心的教學觀(對教學本質及過程的基本看法)以及多個與核心教學觀有關聯的單一的其他觀念,本文擬從與核心教學觀有關聯的其他觀念入手,最后匯聚到核心教學觀的解析。
一、知識觀
李老師的知識觀是情境教學主張的認識論基礎。李老師從知識的形成過程這一原點出發,認為:知識產生于一定的情境中。李老師是這樣表述她的觀點的:“知識產生于特定的情境中,是人類在具體情境中發現,并逐步發展起來的。離開了特定的情境,知識就成了文字符號,沒有了任何存在的意義。知識都是產生于一定的情境中。”她以語文為例:當作家拿起筆去構思、去創作時,他必然進入他所寫作品的那一系列情境中。事實上,作品的題材就來自生活的情境,作家創作時心中再現了那些情境,并用語言文字、用筆去描述那一系列生活情境以及自己對生活的感悟和內心要表達的情感。所以,閱讀教材中的每篇課文,幾乎都表現了特定情境中作家要向讀者抒發的“情”和闡發的“理”,這就是所謂的“作者胸有境”。[3]9李老師還以阿基米德發現浮力和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為例,力圖說明“任何知識都是在具體情境中產生的”這一普世道理。
這樣的知識觀與后人學習知識有什么關聯呢?畢竟,理解他人知識的過程與發現、創造知識的過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就像猜謎與被告知謎底一樣,其結果也是不一樣的。發現、創造知識的人獲得的結果有兩個:一個是知識本身;一個是認知方式、思維習慣乃至情感世界發生的變化。通過“傳遞—接受”的方式學習的知識得到的只能是第一個結果,因為第二個結果無法通過告知而獲得,它得靠實做,靠親歷——在類似知識發現、創造的情境中親歷,如此,才能在占有知識的同時,占有鐫刻在知識中的認識能力,獲得相應的情感體驗。這就是說,后人(包括兒童)在學習前人創造的知識時也需要情境,在類似的情境中,后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前人創造的知識,學習前人的認知方式并獲得相應的情感體驗。筆者認為,這恐怕是李老師心心念念要創設情境的根本原因。
現代情境認知理論指出去情境學習的弊端:在脫離情境脈絡的條件下獲得的知識,經常是呆滯的和不具備實踐作用的(Whitead,1929)。如,學習解經典教科書中的脫離真實境脈的數學方程,就容易形成孤立的、單純的和過于簡單的理解(Spiro et al,1991)。學習者可以解決近遷移的問題……但在一個遠遷移的或是新任務的問題中,學習者不能靈活地加以運用或批判地進行推理(Perkins,1988),這一觀點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情境在后人學習知識時的重要性。
二、學習觀
情境是學習發生的前提條件,但并非必要條件。學習發生的必要條件是學習主體在情境中的主動建構活動。不知是李老師自己在教學實踐中摸索出來的,還是受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影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她強調“兒童是學習的主體,知識必須是由兒童自主建構的”。兒童該如何建構知識呢?李老師提出了“角色扮演”這一概念。她說:“僅僅為學生提供豐富的環境是不夠的,還需要讓他們積極參與其中,教師創設情境為學生提供豐富的環境,同時又通過角色扮演等幫助學生進行一系列的實踐操作活動。”[3]11我們應該注意到,李老師這段話并不是針對語文學科講的,她沒有把“角色扮演”與其他具體的情境創設方法并列在一起,冥冥之中,她賦予了“角色扮演”更高的價值。
“角色扮演”這一概念起先是在語文閱讀教學中使用的。李老師說:“情境教學中的角色有兩種:一是進入角色,二是扮演角色。所謂進入角色,即假如我是課文中的××;而扮演角色,則是擔當課文中的某一角色,進行表演。由于讓學生自己進入角色、扮演角色,課文中的角色不再是在書本上,而就是自己或直接班集體中的同學,這就促使學生帶著角色轉換的真切感受理解課文,對課文中的角色必然產生親切感,很自然地加深了內心體驗。”[3]37這里,李老師揭示了“角色扮演”在閱讀教學中的重要性。
“角色扮演”這一概念能否遷移到其他學習領域,是否具有普世的方法論價值呢?筆者認為:能!完全能!必須能!
先看看近期課程、教學領域出現的一些新口號——“像科學家那樣……像工程師那樣……像數學家那樣……像歷史學家那樣……像社會學家那樣……”,這難道不是典型的“角色扮演”嗎?為什么要像他們那樣?怎樣像他們那樣呢?
蘇聯的發展性教學流派曾經從學理上解答了上述問題:“學生的思維盡管與科學家的、藝術家的、道德和法律理論家的思維有某些共同點,但又不能與這些人的思維混為一談。學生不能創造社會道德的概念、模式、價值觀和規范,而是在學習活動中獲取它們。”“學生在自己的學習活動中再現人們創造概念、模式、價值觀、規范的那個實際過程……”使教學“以壓縮的形式再現知識產生和實際歷史過程……”[4]164-165“在作為學齡早期主導的學習活動過程中,孩子們不僅要再現符合社會意識形態之基礎的知識和技能,而且要再現歷史上產生了的那些能力,如反省、分析、思維實驗等,這些能力是理論性意識和思維的基礎”[4]146。
上述觀點讀起來可能有些費解,但對理解“角色扮演”來說十分關鍵,我們可以嘗試對它做更通俗的解釋:要想使學生真正理解人類創造的知識,特別是增長自己的能力,唯一的途徑和方法就是讓學生以知識創造者的身份“重演—再現”這些知識的形成過程,但這種“重演—再現”不是原生態的,而是課程設計者和教學設計者精心組織安排的(即所謂壓縮的形式)——既要考慮教學內容對學生的發展價值,又要考慮學生的可接受程度和興趣。
“角色扮演”的目的原來是在發展學生的心理能力,這應是“角色扮演”的普世價值所在,也應是“角色扮演”的本質屬性所在。
三、教學目的觀
教學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教師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答案,盡管顯性的表述可能十分接近。教學目的觀與教學價值觀緊密相連,故對教師的教學行為影響巨大,教學活動組織的不同大多來自教學目的的差異。
李老師在多個場合旗幟鮮明地表達過自己的教學目的觀:“情境教學從起步開始,就有著鮮明的目標,那就是為了兒童的發展。這已經成為整個情境教育的核心理念。”她還說:“如果我們仍然注重傳授知識、記憶知識,只能延誤兒童發展的最佳時期,使潛在的創造性受到壓抑,將來怎么能做到有所發明有所創造呢?”[3]125
什么是發展?發展的一般性定義是:隨著時間推移在人身上發生的變化。變化可概括為三個主要方面——生理的發展、智力的發展、情感和社會性的發展。影響發展的因素可分為自然(包括遺傳和非干預性的社會環境)和使然——通過干預(包括教學)促進人的發展,李老師顯然持使然立場。
在使然的教學目的觀中也有不同的傾向,在教育功利色彩濃郁的今天,單一傾心智力發展的大有人在。李老師的發展觀則是全面的,智力發展和情感社會性發展在李老師教育良心的天平上是平衡的。她既重視兒童思維能力、創造能力的發展,也重視兒童美感、道德感、好奇心、求知欲乃至悲憫情懷的發展,她認為這些情感和人的幸福感(包括未來和當下)息息相關,也和學生的學習活動息息相關,她說過:兒童的情感會形成一種驅動的力,促使他們主動投入、參與教學過程的力。
目的和手段是一對重要的哲學概念,二者的關系是手段要為目的服務,目的要靠手段才能實現。和李老師教學目的觀相連的教學手段(方法)觀又是什么呢?這就是創設和優化教學情境。和國際上其他倡導情境教育的學者相比,李老師的情境側重于人為的情境,其他學者多強調的是真實情境。人為的情境是簡化過的情境,是按照需要雕琢過的情境,是美化過的情境。真實情境固然重要,但對于兒童來說,它過于復雜,再說時間也不允許。何況,美化過的情境更能觸動兒童的心靈,這就是李老師說的“優化”。優化的手段多種多樣,僅語文學科就有圖畫再現情境、音樂渲染情境、表演體會情境、生活展現情境、實物演示情境等。李老師的教學方法(手段)是教學目的觀的有機組成部分。
四、教學觀
如前所述,教學觀是教師從實踐經驗中逐步形成的對教學本質和過程的基本看法,它建立在知識觀、學習觀、教學目的觀、師生觀等的基礎之上。師生觀是關于活動主體——教師和學生的觀念,是對教學活動中兩者的角色、關系等的基本看法。之所以沒有對李老師的師生觀做專門的闡述,一是因為篇幅原因,二是因為李老師的師生觀可以從她的學習觀中發現端倪,概括地說,就是:學生是學習意義的建構者,不是被動接受灌輸知識的容器;教師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引領者,而不是知識的輸出者。
教學本質關心的問題是“什么是教學”;教學過程關心的問題是“教學展開的程序及結構的應有狀態該是怎樣的”。這兩個問題之間有內在的關聯性。
20 世紀上半葉,對教學本質的看法還停留在“特殊認識說”上——教學是幫助學生認識人類已經發現、創造的知識經驗。與特殊認識說相關聯的教學過程則是:感知(教學材料)—理解(教學材料)—鞏固—運用。20 世紀下半葉,先是有“發展說”——教育的目的在于促進學生的發展,尤其是智力的發展。后來較為辯證的“認識—發展說”逐漸占了上風。“認識—發展說”認為,教學和發展應是統一的過程。一方面,學生在教師的引領下,把人類文化中選取出來的知識經驗內化為自身的知識經驗;另一方面,在掌握知識經驗的同時,實現著認知能力、情感社會性的發展。“認識—發展說”并沒有像“特殊認識說”那樣清楚地列出教學過程的樣態,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它倡導的發現法、探究教學、問題教學、學習環等教學方法中拎出幾個關鍵環節:問題—探究—交流—共識。
李老師的教學觀可以歸為“認識—發展說”。屬概念雖然一致,但種概念有別。在如何引領、如何促進學生的學習和發展問題上,“認識—發展說”并沒有給出一致的結論。李老師給出了她獨有的答案。
李老師說:“客觀教學環境及兒童本身的自我運動,成為兒童發展的重要因素。”關注教學環境對兒童發展影響的學者不止李老師一人,但對教學環境內涵的解釋完全不同。前者說的教學環境包括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物質環境涉及教學的場地、設備等內容;精神環境包括班風、師生關系和教學氛圍(如是支撐型還是防范型),這些都是與教學內容無關的環境。而李老師說的環境是與教學內容有關的環境,她稱之為情境,這個情境是人為設計的、與教學內容有關的、能促進學生學習和發展的“心理場”。李老師說:“人為地創設特定的、富有典型意義的情境,使學習情境優化,作用于兒童的感知,引起兒童觀察、思維、想象一系列的智力活動。同時,由于情境本身富有豐富的美感、鮮明的形象,伴以教師情感的抒發、渲染,又激起兒童的情緒,使兒童純真的情感參與學習活動。這樣,主客觀的一致,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的和諧,使整個情境成為一個可以多向折射的心理場。”[3]75與教學內容有關的情境根據需要可以是擬人的童話故事情境,也可以是問題解決的生活情境,還可以是明辨是非的道德法庭情境……在這樣的情境中,學生卷入學習活動是自然發生的,但又是有方向的、有導航的——教師是那風箏的牽線人。
通過創設情境,讓學生卷入學習活動,獲得未來社會期望的認知與發展。這,或許就是李吉林老師教學觀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