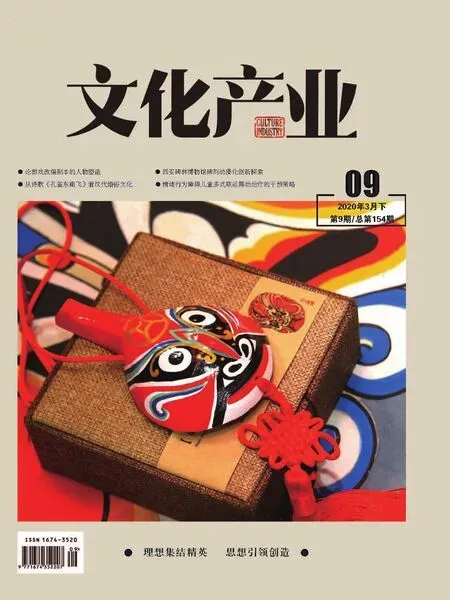《左傳》中謀士形象及其價值探析
◎徐一丹
(東北石油大學人文科學學院 黑龍江 大慶 163000)
縱觀千古,歷朝歷代君王的身邊都不可無名臣謀士輔佐。春秋戰國期間社會動亂、戰爭頻繁,謀士的作用在此時更顯突出。此時的戰爭不只是國與國的抗爭,更是各國謀士實力的較量。以《左傳》為例,其中刻畫的名臣謀士形象舉不勝舉,無論是舉足輕重的名臣還是隱逸高潔的謀士,都盡力實現自己人生的價值,用其才智與謀略盡心盡力地輔佐君王。本文將著重從《左傳》中的《鄭伯克段于鄢》《蹇叔哭師》《燭之武退秦師》《曹劌論戰》,分別探析潁考叔、蹇叔、燭之武、曹劌的謀士形象及其價值影響。
一、《左傳》中的廟堂之臣
身為一國之臣,臣子必當以輔佐君王治理天下為己任,愛國、忠君、體恤百姓。百姓疾苦,臣子當為民請命、安撫民心;君王憂思,臣子便當為君王排憂解難、建言獻策;國家危難,臣子更應義無反顧勇當先鋒,為國拋頭顱灑熱血。真正做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一)從《鄭伯克段于鄢》看潁考叔
《左傳》第一篇就是《鄭伯克段于鄢》,主要記述了春秋前期,小霸鄭莊公平定家族內亂之事。鄭國莊公之弟共叔段,聯合其母姜氏欲奪權篡位,而莊公卻聽任弟弟母親的所作所為,使得共叔段與母親越陷越深,最后“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左傳·隱公元年》)“置姜氏于城穎,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左傳·隱公元年》)本文著重論述的就是反對“莊公置母于潁”這一不孝做法而主動獻策的謀士——潁考叔。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為人正直、孝順又甚是機敏。聽說莊公驅趕母親姜氏于潁地,認為姜氏雖為母卻不行為母之事,但莊公作為兒子不能不孝,作為國君更不能違背倫理將母親驅逐,便進獻于公。莊公賜之食,潁考叔卻食舍肉,公問其故便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左傳·隱公元年》)隨后又反問莊公“敢為何謂也?”(《左傳·隱公元年》)莊公遂“語之故,告之悔。”潁考叔便為莊公想出了“闕地及泉,隧而相見”的解決方案。潁考叔為什么這樣說、這樣做呢?原因有二:其一是主觀原因,潁考叔知道莊公對于驅趕姜氏的做法感到懊悔卻又礙于君王身份無法收回成命。如若是臣子直接提出收回成命,便相當于直截了當的批評國君,是挑戰一國之君的權威。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公然指責君主的過失不僅無法為國君排憂解難反而會適得其反,招來殺身之禍。因此潁考叔通過“食舍肉”這一行為刺激莊公,觸及其思母情緒,使莊公親口“語之故,告之悔”達到了既可以為莊公排憂解難,又保證了自身安全的效果。其二是客觀原因,國君下達的成命不可收回,君子一言且駟馬難追,更何況堂堂一國之君?因此潁考叔想出了這一既不違背莊公“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的誓言,又可以成全莊公與姜氏母子之情的辦法——“黃泉相見”。采取這一辦法與母親隧中相見的莊公不禁感嘆“大隧之外,其樂也融融”(《左傳·隱公元年》),使母子如初。通過本篇對潁考叔為莊公獻策的分析,可以看出潁考叔不只是孝順正直的君子,更是一位有謀略忠國君的好臣子。
(二)從《蹇叔哭師》看蹇叔
《蹇叔哭師》是《左傳》中著名的《秦晉崤之戰》的一部分,作于僖公三十二年。本文主要探討的是公元前627年秦穆公發兵攻打鄭國前夕,憑借自身豐富的政治、戰爭經驗和人生閱歷,對秦、晉、鄭的三方情況進行詳細具體的分析,并將此次戰爭的潛在危險一一道于君王,多次哭諫勸阻的忠良之臣——蹇叔。
蹇叔雖為官多年卻一直淡泊名利不趨炎附勢,與世無爭又一心為國。蹇叔豐富的政治經驗及自身的論戰能力使得他在知曉秦穆公夜訪的目的之時能夠清楚的分析秦、晉、鄭三國形式而對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繼而指出“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又言“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秦穆公即當局者,縱使蹇叔清楚列舉了不應作戰的原因、指出作戰必敗的結果,不撞得頭破血流、不全軍覆沒秦穆公便不會相信。因此一意孤行的秦穆公隨即便“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發兵已經說明蹇叔的勸諫無用,決心已定,任誰也無法阻止此次出師。但忠直耿介的蹇叔卻一心為國冒死哭諫“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直言此次出師結果,希望能以此阻止災難發生卻因此遭到了詛咒、辱罵。作為臣子,在秦穆公夜訪之時,蹇叔便已盡到臣子之責,于軍隊之前冒死哭諫已是超出了本職而僅僅出于對秦國的一片忠心。而哭子行為就是他對隨軍隊出師的即將犧牲的兒子,對即將滅亡的秦國所做的最后一次掙扎。直接指明“晉人御師必于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即使這樣忠心的諫言也未能使秦穆公回頭。蹇叔的論戰與哭諫展現的不只是為君臣子的智與忠,更能見其勇。論戰見其深謀遠慮、顯其智;勸諫見其戰略眼光、顯其忠;哭師見其忠正果敢、顯其勇;而哭子見其情深意切、盡顯慈父悲戚。得此忠智之臣,夫復何求?
二、《左傳》中的鄉野謀士
自古以來,才略過人的名士不勝枚舉。但除了這些居廟堂之位而憂君的名臣,還有那些未入朝堂或未得重用卻仍心系國家危亡、關心百姓疾苦的愛國忠君的義士。這些愛國義士雖與世無爭、淡泊名利,但于國家危難之際,仍能臨危受命以“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一片赤誠之心挺身而出,發揮其才能,救國于水火之中。
(一)從《燭之武退秦師》中看燭之武
《燭之武退秦師》作于僖公三十二年,記述了秦晉聯軍欲攻打鄭國,臨危受命只身去見秦穆公,于強秦面前不卑不亢最終說服秦國退兵的愛國義士——燭之武。
燭之武是個智勇雙全的愛國義士,雖位卑卻未敢忘憂國。秦晉聯軍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為由欲攻打鄭國。鄭國危難之際,佚之狐勸諫:“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由此引出燭之武這一人物。對于多年未被賞識,燭之武心中不免會有怨憤,因此燭之武才會說“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可即使心有不滿,國難當頭之時燭之武也并沒有因為之前的成見而坐視不理,而是只身一人勇退強秦。燭之武并不只是空有一腔孤勇,支撐這份勇氣的是燭之武的智慧。面對強秦,燭之武先言“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暗示秦國攻打鄭國對秦國并沒有好處;再以“鄰之厚,君之薄也”來提醒秦穆公,協助晉攻打鄭只會壯大晉國而弱化秦國;又以“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從側面暗示秦穆公退兵鄭國的好處;最后以秦穆公親身經歷來證實“夫晉,何厭之有”,使秦伯說、與鄭盟,退師鄭國。燭之武雖為鄭國卻閉口不提鄭國利益,而是以秦國立場分析退師鄭國對秦國的利益,通過旁敲側擊使秦國退師鄭國。燭之武雖是一介小小的養馬官,懷才不遇對君主有著不滿甚至怨憤,但國難當頭仍能挺身而出,堅決維護國家利益,可見其是個有勇有謀的愛國義士。
(二)從《曹劌論戰》看曹劌
《曹劌論戰》作于莊公十年,記述的是著名的齊魯長勺之戰,本篇詳于曹劌的論戰過程。以曹劌戰前三問、作戰時的二“未可”,二“可矣”敘述展開。
曹劌有勇有謀略,與其鄉人不相為謀,而有遠見。雖不是朝臣,為了國家戰爭能夠取得勝利,便請見莊公。從戰前準備、戰中追擊兩方面與莊公論戰。見公即問:“何以戰?”啟發莊公從神明、貴族、民心三方面作答,最后以民心所向作為作戰的政治前提,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左傳·莊公十年》)從而為莊公作戰做好政治準備。于正式作戰進攻時提出進攻時機——齊人三鼓后擊退敵人。莊公欲乘勝追擊前卻被曹劌打斷,“下視其轍,登軾而望”(《左傳·莊公十年》)后方“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莊公問其故,曹劌并沒有故作姿態,也未求封賞,而是一一解釋,使其明白為國為君要順應民心、帶兵作戰切忌急躁冒進。曹劌不僅協助莊公打贏長勺之戰,更是使莊公學會為君之道。曹劌雖出身鄉野,卻有卓越的論戰能力,了解作戰的政治需要——民心所向;明白作戰時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更有著不同鄉人與肉食者的家國觀念——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由此可見曹劌的謀略膽識與悠悠愛國之情。
三、《左傳》中的“謀士精神”及其價值
無論是像潁考叔、蹇叔那樣的名臣謀士,還是像燭之武、曹劌一樣的愛國義士都是國家不可或缺的寶貴人才。所謂“國不可一日無謀臣”,歷代歷朝皆如此。古代謀士所形成的“謀士精神”,蘊含著高尚的道德品質及人格修養價值。
古代謀士具有超凡的智慧謀略和膽識、為人正直,謀士們對君王忠直耿介、一心為君為國的浩然之氣對后人有很大影響。潁考叔的獻言,警醒后世要守孝悌、孝順父母,不可不孝;蹇叔的多次哭諫,是忠國忠君之典范;燭之武的臨危受命與曹劌的進諫,昭示世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于危難之際不可推卸為民為眾之責任。孔子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而筆者認為“不讀《左傳》無以行”。
《左傳》中記錄的大小戰爭不計其數,臣子輔佐國君保家衛國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更可貴的是那些本可悠閑度日、與世無爭的智士高人,在君主困頓、國家危亡之時能夠以一顆赤誠之心挺身而出;不為榮華名利、不計較個人得失榮辱,一心為國為民之生死存亡,而將個人生死得失置之度外。古代謀士的忠孝義勇,也體現出一定的民族大義與民族氣節,對后世影響深遠。
四、結語
左丘明在《左傳》中塑造了眾多人物,特點鮮明、性格豐滿,又以禮之規范評判筆下人物。對于暴虐昏庸、貪婪荒淫之輩毫不留情的批判,對贊揚忠良耿介之士亦不加保留的贊揚稱頌。作者并不是單純描寫人物,而是與戰爭或是王室斗爭等結合展現人物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尤其是對于文中的謀士,作者著大量筆墨進行刻畫,無論是名臣還是鄉野謀士,作者都一視同仁,使《左傳》在“為學”的價值以外更多了“為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