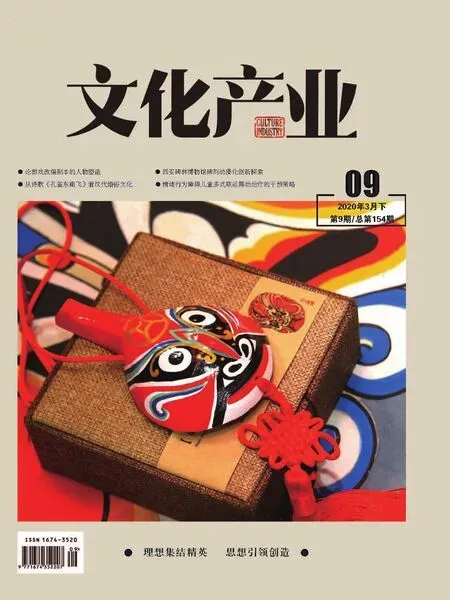《戰國策》語言藝術特色分析
◎范雨欣
(東北石油大學人文科學學院 黑龍江 大慶 163000)
《戰國策》由西漢劉向編校整理成書,亦名《國策》,全書共分十二國策,主要包括戰國至秦漢時期縱橫家們的謀略主張和辯論游說之辭,也因此而得名;這部經典史書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國別體先例。由于戰國時期的士大夫階層地位上升的社會背景和七雄并起、諸侯紛爭不斷的歷史背景,《戰國策》雖繁多冗雜,但反映了思想藝術較為活躍的社會歷史特征。除了極高的史料價值,《戰國策》還具有豐富的語言特色,其語言藝術在先秦文學史上空前成功,它的出現是先秦歷史散文的一個新高峰。
一、投其所好
縱橫家們同為給君主籌謀劃策的謀士,卻不一定有著相同的人生目標,有一部分人是為了功名利祿,榮華富貴;也有一部分是真正為國為民而盡心出謀劃策。不過,他們的一致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夠被君主所重視采納。在那個時代,社會、經濟、軍事多方面動亂不安,各諸侯國間的關系劍拔弩張,多昏君庸主。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縱橫家們提出的建議,往往需要投君所好,既能提高君主對提議的重視程度,又可以獲得君主的認同,使其樂意接受自己的提議。
在《東周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中,周君惶恐秦奪取九鼎,并告知顏率這件事,于是顏率赴齊借兵求救,他從兩方面說服齊王借兵援周:一是“存危國,美名也”,即是從獲得美名的角度向齊王說明同意借兵的益處;二是“得九鼎,厚實也”,即是從得到財物的角度向齊王透漏若借兵救周則遺之九鼎以回報。綜合兩點利益,齊軍出兵救援東周,于是秦兵撤退。無論是美名抑或是財富都是君主十分看重的,也正因如此,才成功打動齊王得以救周。
在《趙策四·觸龍說趙太后》中,趙太后剛開始執政,秦國便加緊對趙國進攻,趙遂求援于齊,齊要求把趙太后最小的兒子長安君作為質子,盡管大臣們都極力勸諫,可趙太后仍是以“老婦必唾其面”回應。觸龍拜見太后,他沒有開門見山,而是從身體健康情況入手,從散步到飲食,再借為自己的小兒子謀求官職,從父母對子女的愛入手,使趙太后逐漸放下防備,步步遞進,引導太后明白其中情理。再以“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打破太后最后一道防線,使太后明白與其保全長安君眼前,不如為長安君的將來打下群眾基礎。最后太后主動要求將長安君做質子以謀求功名與百姓愛戴。
二、含蓄委婉
由于一切謀略都要以社會現實要求為基點,縱橫家們往往需要揣摩游說對象心理,善于對自己的言論進行雕飾,減小語言刺激,達到更好的效果,以求更好保全自身,倘若說辭不被采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住性命。
在《齊策六·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中寫到,“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斫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充分說明了言辭過于直接或不合君主的心意,很可能會遭受殺身之禍。
在《魏策四·唐雎不辱使命》中,秦王欲以五百里土地與安陵國進行交換,而安陵君縱然心中萬般不愿,在強大殘暴的秦國面前,卻只能以“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表明對秦王的感激,再委婉間接地以“受地于先王,愿終守之,弗敢易”來推卻秦王的提議。身為小國國君,在國家實力懸殊的情況下,為了不引起秦王暴怒,而遭受大國的攻擊壓迫,保全自己國家的領土,言辭委婉實難以避免。
在《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中,“臣之所聞,攻占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沖,折之祍席之上。”委婉地以“臣之所聞”引起下文,說明攻戰的方法不在于用兵之勝,而在于后發制人則諸侯可趨役的道理。
在《秦策一·張儀說秦王》中張儀曰:“臣問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愿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以及后文的“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一舉破天下之從。”“大王斬臣以殉于國,以主為謀不忠者。”向秦王提出主張,卻又擔心直言進諫會受到責罰,故使用了一系列謙敬詞匯以緩和言辭的直接性和批評性,使建議更容易被采納。
三、善用修辭
《戰國策》語言具有辯麗恣肆的特征,常常運用大量的鋪陳排比以及夸張渲染,使辯論的氣勢更恢宏,感染力更強。謀臣智士們十分善用鋪陳排比,以塑造宏大的敘事場面和宏偉的辯論氣勢。如《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用,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在這段話里,蘇秦通過鋪陳夸張,“西北南東”“萬乘”“千里”等充分說明了齊地形之優越便利,國家繁榮,又富有氣勢,易被其言語聲勢所感染。
夸張的手法在《戰國策》中也十分常見,如《魏策四·唐且為安陵君劫秦王》中,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以夸張的手法刻畫秦王殘暴的形象,雖為夸大,反而使人更有畫面感,增強了天子之怒的可聯想性。
各國戰爭不斷,紛爭連綿,謀士們在外交上更需精心鉆研自己的言辭,以引起對方的共鳴,常會選用生活中可見的動植物或生活物象,借此讓對方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意圖,接受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也可以側面委婉表達自己的想法,更有說服力。如《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諫》中,鄒忌從日常生活的“吾孰與城北徐公美”發現“王之蔽甚矣”的現象,于是齊威王頒布命令接受百姓意見,“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后,時時而漸進;期年之后,雖欲言,無可進者。”門庭若市,則是將宮廷門院進諫的人多比喻成像市場廟會一樣擁擠,從側面體現了大王受到的蒙蔽確實很深,與后文形成對比,體現了實施該命令的正確性。《韓策二·楚圍雍氏五月》中,楚國圍困雍氏已有五月,韓派尚靳出使秦國:“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崤,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愿大王之熟記之。”借用唇亡齒寒的物象抽象成韓與秦之間恰恰就是唇與齒的關系,起到警示秦王的作用,為說服秦王增強感染力,提高其對楚圍困雍氏的重視度和參與感,而不是以單純旁觀者身份隔岸觀火。
四、旁征博引
策士們往往集中使用多個平行論據,以論證同一觀點,使其理論觀點更容易得到信服。如《秦策三·蔡澤見逐于趙》范雎欲赴秦國爭相位,蔡澤打算說服范雎主動退出自己做相,用三個歷史依據來證實自己的看法,“主圣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志,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知,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論證功成則當身退,否則可能會得到商鞅、白起等人的慘痛下場。范雎聽其言,感受到潛在危險,故不日便辭隱。《秦策三·范雎曰臣居山東》中,范雎對太后、穰侯、涇陽君、華陽君濫用權力,無所顧忌的現象不滿,擔心國家的大權旁落被奸人利用而向秦王進諫,援用詩經加以論述:“《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加以舉例齊閔王和李兌主父來警示秦昭王,使其意識到危機,從而有“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這些鞏固自身地位的行為。
《齊策四·馮諼客孟嘗君》的狡兔三窟,是《戰國策》中最典型的寓言之一。第一窟為“焚券市義”,馮諼焚燒百姓的債券,助孟嘗君得到薛地民心;第二窟為“謀復相位”赴梁游說梁王,使其為孟嘗君空出相位,一方面營造了孟嘗君的高聲望,另一方面使得齊國君臣對孟嘗君更為忌憚,再次聘其為相;第三窟為“立廟于薛”,宗廟作為祖先崇拜觀念的物化形式具有不尋常的意義,而孟嘗君在自己的封邑上擁有宗廟,實實在在地穩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最后,馮諼對孟嘗君說:“三個洞窟已經完成,您姑且安然自得吧。”一個淵圖遠算的智士形象清晰可見。
五、通俗明快
言辭雖經過雕琢打造,但為了意見接受者能夠更清楚地理解其理論脈絡、緣由,往往需要用通俗易懂的口語加以闡釋、梳理,也可以通過簡單的語言描述,拉近與君臣間的關系。
如《楚策一·張儀為秦破從連橫》中張儀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捍關。捍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幾。”張儀為使楚王更清晰地了解他的意圖,用大量的言辭從時間距離等各方面推測,說明若強秦攻楚,等待弱國援助是不可取的,望大王仔細考慮,與秦楚結為互不侵犯的友好之邦。
《秦策一·陳軫去楚之秦》中,陳軫常常到楚國去,張儀懷疑他對秦國不忠便向秦王反映,希望秦王將其趕走或殺掉。于是秦王召見陳軫,詢問他到底想到哪里去,陳軫回答想要到楚國去。他表明他要順應大王和張儀的懷疑,故意到楚國去,從而可以證明自己是否有為楚國做事的傾向。于是他借用誂者與長妻少妻的故事,即“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即面對誂者,長妻大罵他,少妻順著他,當有兩妻者死,誂者反而更愿意娶長妻,為的是若娶長妻,長妻能夠忠于自己。以此來論證,自己身為秦國臣子,卻再三把本國國情告訴楚王,楚王定不會留他,即自己并沒有傾向楚國,而是忠心于秦。由此,秦惠王認為他說得十分在理便繼續給他好的待遇。
六、結語
戰國時期,謀臣策士擁有較高地位,他們的言行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場戰爭的發動與否、成敗與否,具有十分巨大的影響力;他們對各國國情十分熟悉,奔走游說,出謀劃策;他們善于對游說對象心理進行揣摩;他們能言善辯,總是能夠正確推測事態的發展走向;他們的語言經過精心設計,體現出投君主所好、含蓄委婉、善用修辭、旁征博引、通俗明快的幾大特征和辯麗恣肆的總特征。
《戰國策》作為一部國別體史書,其歷史意義顯而易見,真實展現了戰國時期縱橫家們的形象特征和多元化的社會背景。在文學層面,縱橫家的語言藝術堪稱先秦之最,值得學者們去深入研究與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