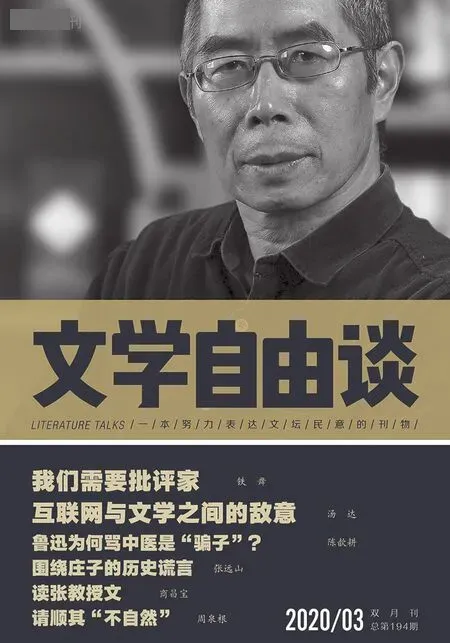傅雷何以對他前揚而后抑?
□金 梅
傅雷與劉海粟,一位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一位是著名畫家,兩人又是交往三十多年的朋友。然而,傅雷對劉海粟的看法與評價,卻是前揚而后抑的。其間,原因何在呢?
傅雷于1928 年初到達法國留學,專攻文藝理論,劉海粟則于同年下半年去法國考察美術,劉請傅雷輔導學習法語,兩人以此認識。這期間,劉海粟幫助傅雷挽救了傅與朱梅馥的婚約,為了平復傅的情緒,劉還與同在法國留學學畫的劉抗等人,相伴傅雷同去意大利、比利時等國,一邊旅游,一邊參觀各大博物館收藏的文藝復興以來的文物遺跡和名家畫作。對此,傅雷對劉海粟的關照感激不盡,兩人的友誼日深。為了感謝劉海粟,傅雷反復推薦,說服法國教育部收藏了劉海粟的一幅畫作。
1931 年“九一八”當天,傅雷與劉海粟等一起回到上海。過了一個多月,應劉海粟之請,傅雷撰寫了《論劉海粟》一文,熱情肯定了劉海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后首先采用女性模特裸體寫生的創新精神,介紹了他遍觀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文物墨跡與杰作的收獲,擴大了劉海粟在學術界的影響;后又與劉海粟主編了《世界名畫集》,并把《論劉海粟》一文作為序言,將劉海粟與世界著名畫家并稱,可見其對劉海粟的器重。劉海粟則“投桃報李”,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之名,邀請傅雷出任該校辦公室主任,兼講西方美術史。至此,傅、劉的友情達到高潮。
隨著傅雷與劉海粟的頻繁接觸,傅對劉的為人與作風的了解日漸深入,對他的看法開始發生了變化。
傅雷是一個正直、公道的人。由于看不慣劉海粟的作風,他在上海美專工作了不到兩年,萌生了辭去該校教職的想法。他在寫于1957 年7 月的《傅雷自述》中說,上海美專校方“對我個人極好,但對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母親一死(1933 年秋)便辭職”。
“對別人刻薄”的突出例子,是對待留法歸來的畫家、教授張弦的態度。校方每月發給張弦的薪水,不足以使張弦維持日常最低生活水平。1936 年暑期,張弦“定欲”回老家,甚至有“無錢也將徒步歸去”之語。不料回家后卻染上了時疫,不久去世。傅雷得知后,向上海美專校方提出了四點建議,最后一點是,上海美專應在校內舉辦一次張弦遺作展,除了紀念他,也可趁機為他的子女籌措一筆學費。但校方遲遲沒有回音。不得已,傅雷只得在市內另找場所,終于為張弦舉辦了遺作展。傅雷還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了《我們已失去了憑藉》一文,以悼念張弦。文章回顧了張弦坎坷潦倒、貧困無助的一生,稱他雖貧窮無奈,但始終保持著一個藝人的人格與畫家的風范,精心盡力地培育后生。有如文章題目所內含的深意,認為張弦的突然去世,使藝術界失去了依靠與評人論藝的標尺。兩相對照,可見上海美專那位負責人的為人與作風。
2014 年5 月,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書全編》一書,首次收錄了傅雷夫婦1955 年9、10 月間寫給傅聰的兩封信(這在歷年出版的《傅雷家書》的各種版本中均未收錄過),信中敘述了夫婦倆照料劉海粟女兒倫倫(劉英倫)的情景,以及劉海粟對待女兒的態度。倫倫系劉海粟與學生成家和于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所生的女兒,后劉海粟與成家和分手,成家和移居香港,女兒歸了劉海粟;但劉海粟對女兒極少照料。傅雷與成家和亦師亦友,夫婦倆與她關系很好。傅雷夫婦在信中說,倫倫在家中很少有人跟她說話,她很孤獨、寂寞;劉海粟在家中愛吹噓他那一套,倫倫聽不入耳,就躲到一邊去自己呆著。1955 年夏,倫倫得了嚴重的胃腸病,家里人又不管她。傅雷夫婦得知后,與倫倫所在學校商定,把她接到自己家三樓住了一段時間,為她請醫生來治病,陪她到醫院化驗,上街為她購買藥品、采買她愛吃的食物。為了平復她的情緒,夫婦倆經常細聲細語地開導她、勸慰她。為了倫倫的病,夫婦倆樓上樓下、家里家外地忙個不停。他們把倫倫看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為她忙碌,毫無怨言。傅雷在信中敘述這段情景時說:
倫倫這孩子實在嬌嫩,身心雙方都如此。她思想的細密,感覺的敏銳,都是少有的。她好比一朵幼弱的花,被我們從大風雨中搶救出來了。現在只要繼續治療、靜養,半年后必有希望恢復健康。胃病最劇的幾天,吃東西都是媽媽與我輪流喂的。今仍終日睡著,絕對不許下床。她父親每周來一次,但只和我談天——吹捧,我不提倫倫的病,他自己從來不提,也從來不提上樓去看看她。像這種自私的父親,可說天下少有;而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居然不沾上一星自私,還痛恨自私,還處處體貼別人,正義感那么強,也可以說“出污泥而不染”了……倫倫的病,又一次的發揮了我們父性母性,同時對我也多了一次觀察人性的機會……
劉海粟對待女兒尚且如此,對待他人態度不是可以想見嗎?作為文學翻譯家的傅雷,對美術亦有相當的研究。他寫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一書,其獨到的見解,至今無人超越。他對劉海粟創作上的進展,也自會長期關注著。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致新加坡畫家劉抗的信中,以不點名而用一個雙方都能理會到是在指誰的名詞說,他以為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后,劉海粟的創作,無論在用筆、用墨上都沒多大發展,沒什么可以稱道之作。這與他寫于三十年代初的《論劉海粟》一文中的贊揚,形成鮮明的反差。傅雷的看法,是否準確、有否偏見,由于筆者不懂美術,這里難置一詞,只能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提出來,供方家研討。
筆者在這里敘述傅雷與劉海粟交往的一段歷史,并非為了給文壇、藝壇增添一則軼事,以供談資,更重要的,是為了突出《傅雷家書》中反復強調的一個文藝理念,即:在傅雷看來,欲為藝術家者,首先要學為人,其次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家;用傅雷的話說,就是要“做一個德藝俱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在傅雷的文藝理念中,是要德藝俱備,以德為先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當傅聰出國留學專攻鋼琴藝術時,傅雷就以五代南唐詞人馮延巳為例教育傅聰說:馮延巳善于細膩體貼地描寫物態,詞作中多佳句,如《謁金門》中的“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等句,常為后人所誦讀。但傅雷因馮的為人(馮貪贓枉法、聲色犬馬等劣跡多多),對馮作有成見——所謂“成見”,就是指馮的人品極差,故對他的詞作評價不是太高。傅雷對傅聰舉出這一例子,就是為了強調他一貫的文藝理念,即:欲作藝術家者,是要“德藝俱備,以德為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