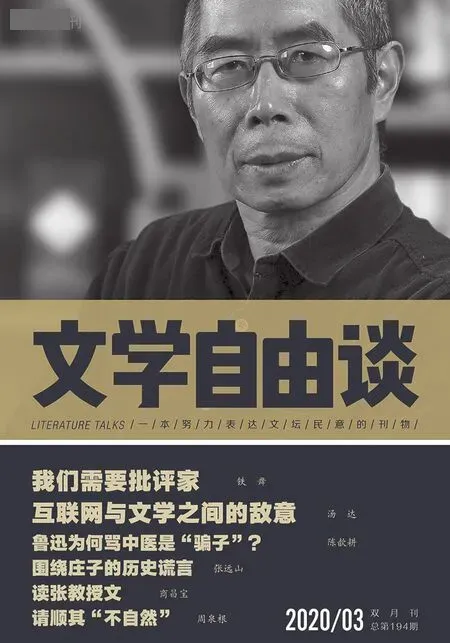尺牘滿紙云煙,書簡字字見情
□古遠清
在邁入古稀之年時,我就開始編輯海內外作家寫來的眾多尺牘。曾打印后裝訂成冊,后來忙于做“臺港澳百年新詩學案”,更重要的是難于找到“婆家”出這類書信,便蹉跎了這么久。直到2019年桂花飄香的季節,在華中師范大學召開的《桂子山詩選》出版座談會上,華師出版社社長周輝揮覺得《當代作家書簡》這個選題很新穎,爽快地答應“我來幫你出”。于是趁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之際,“躲進小樓成一統”,甘當宅男,在自我隔離的春節,“閑”出了成果,將從舊金山、悉尼、首爾、東京、曼谷、香港、臺北、北京、上海來的尺牘,足有厚厚的一大冊,像鮮花一樣插在我早已滿坑滿谷的書房。
研究作家的生平及創作道路,最便捷的方式是讀其作品。但作品畢竟是公開出版的,而專門寫給收信人的帶有私密性的尺牘,是不設防的;甚至有時下筆時非常隨意,沒有任何顧忌,故研究作家不能只滿足于讀作品,有條件的話最好能讀讀他的書信或日記。我沒有收集過別人的日記,但從本書所刊載的書信中,畢竟可看出不同作家和學者的迥異風格。比如同是詩人,寫實派的臧克家給我的六十八封信中,從不出現“酒”字,而在美國的臺灣現代詩的倡導者紀弦,短短的一封信就兩次提到酒,還自詡為“四大飲者”。作家如此,學者也不例外,如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和洪子誠,一個爽朗,一個矜持;一個喜歡和作家交朋友,一個和自己的研究對象小心翼翼地保持距離;一個樂于為別人寫序,一個對索序者有超強的“免疫力”,洪子誠的書也從未有別人寫的序。
我原先研究大陸文學,且以研究大陸新詩為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撰寫《中國當代詩論50家》時,和臧克家、公木等眾多詩人通信。那時候沒有電腦、手機,更沒有微信,甚至連電話都沒有普及,這是“壞事”同時也是好事。正因為通訊工具不發達,連打國際長途都要經過審批,所以古人說的“魚雁往來”就發揮了作用。如果當時不是揮毫寫字而是敲鍵盤,許多作家可能會至少選擇一聲鈴的電話而不是一張紙。
尺牘雖短情意長。重溫這批字字見情的書信,我感到友情的可貴。我在海峽對岸出版了十六本書,每本書的背后都有故事,這些書信便記載了我與他們交往的過程。這些當年還未曾識面的朋友,或及時給我送來急需的資料,或幫我整理文稿,或幫我找到全套的臺北《文訊》雜志。去天國多年的臺灣作家何欣、劉菲以及還在臺北辛勤筆耕的李魁賢,都伸出過他們的援手。這些書信,可說是兩岸文學交流的見證。當然這里也有曲折——或受政治氣候的影響,或因文學觀的不同產生了碰撞,其中臺灣高準等人的書信,便記載了這種交流所走過的不平坦道路。
古人說:“文窮而后工。”文人總是未能擺脫貧困,未能一路凱歌。哪怕到了二十世紀,窮文人還是居多。基于這個原因,當年那些境外作家,都不習慣打昂貴的越洋電話,但據說美國的鄭樹森除外,他跟文友聯絡,總喜歡“煲電話粥”。我不是他的摯友,從未接過他的電話,故收在本書中他的信件,雖也有,但卻像當年的電報那樣短。而從八十年代末和我有密切接觸的詩人藍海文,總喜歡從維多利亞海灣那邊打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電話,因而本書中他的書信缺席。上面提及的紀弦,喝酒豪爽,寫信吝嗇,因為是以賣稿為生,故與我通信時在考慮節省郵資的同時,還要考慮節省紙張。他那些飄洋過海、帶著異國風情飛到我書桌上的航空信,雖然也帶著花邊,但其“面積”比鄭樹森的信要小,且信的內容全都寫在信封的反面,折疊起來封好就成了一封信。我每次拆這種不是明信片但其環保作用相當于明信片的“尺牘”時,都非常小心。大名鼎鼎的臺灣作家陳映真,數次寫信均在后面注明“廢紙利用,請原諒”。所謂“廢紙”,就是已經用過的打印紙的反面。而作家們寄書,許多人都習慣把別人給他的舊信封翻轉過來再用,余光中也不例外。不過,余光中不是經濟上的“窮”,而是“窮”于時間,是為了省事,且公家也沒有給他配大信封。
從寫信不僅可以看到文人的經濟狀況和工作狀態,也可以從用紙上看到兩岸四地文學制度的某種差異,如臧克家的信紙上面赫然印有魯迅字體且是紅顏色的“中國作家協會”,而港臺朋友給我寫信,大部分用的都不是公家信箋,那怕是在香港某大報當老板的董橋,給我寫信用的都是打印紙。由于是私人通信,也可能是為了知名度,有些文人還自印信紙,上有紅色的某某信箋字樣,連“港化”了的暨南大學教授潘亞暾,也是用自制的“潘亞暾信箋”給我寫信。有的臺港作家的通訊地址太長,如某區某路某街某巷某樓某號,某號又有“之一”“之二”之別,或A座B座之分,便自刻了通訊地址的長印章蓋在信封的下角。這種信封既有手書又有“木刻”,可謂是土“洋”結合,好看極了。在當今郵政瀕臨下崗的年代,不妨看作是當年文人通信的一種風景。
就《當代作家書簡》這本收入近兩百位作家書信的風格而言,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用純正的中文寫成。我還沒有接到過臺灣作家用閩南話或客家話寫的信件。泰國作家和中國臺港澳作家給我寫的書信,普遍用繁體字。臺灣的高準還一再聲明,誰給他寫信如果不用繁體寫名字,即“準”字下面加“十”字,他就不理睬不回信。當然境外作家也不是都厭惡簡體字,他們給我寫信時有繁簡混合的,如余光中的信就有不少簡體字,有些還是他自己造的。至于信中的稱呼,改革開放前大陸作家給我的信,一律稱“同志”,而臺港澳作家從不用這個稱呼。
面對封城后門可羅雀的大街小巷,還有“保衛大武漢”這類帶悲壯色彩的紅幅標語,正可以給我作關起門來整理書信的“時代背景”。關門謝客本是為了躲避“瘟疫”,另一方面也是把編注書信看作是獻給自己的祈禱書,是為了舒緩封城后那異常郁悶的胸口,這是作自我精神調整與告別過去再好不過的機會。對我而言,告別過去是告別古稀之年,向耄耋之年大踏步前進。為了不使自己老來寂寞,便不時打開曾被關山(也就是海關)阻隔的書信翻翻。在春寒的夜晚,我一邊翻閱,一邊欣賞著作家們不同風格的書法。我衷情地感謝古老的漢字,感謝奇妙的書法,是它們撫慰著、愉悅著在疫情中避世的我。談及書法,這里有盡人皆知的克家體、光中體、沙河體、董橋體。這些“體”不僅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具體說來,胡秋原的手書如飛沙走石,臧克家的書法似流水行云;丁景唐的書法筆意古厚,錢谷融的書法味厚神藏;余光中的書法力透紙背,黃維樑寫字端正強勁;流沙河用筆瘦硬健朗,有耿介之氣,董橋的書法發乎性情,滲透著風骨與情趣;張炯的書法存縱逸之氣,而孫光萱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楊匡漢的書法翰墨遄飛,劉登翰的草書臥虎藏龍;袁良駿的書法潦草得似天書,李魁賢的書法晦澀得如謎語;陳映真的草書筆挾雷電之勢,而鄭明娳的書法有點似湘繡;臺灣另一女作家涂靜怡給我的信,筆觸纖細,而顏元叔給我的尺牘,字大墨飽——雖然他們用的都是鋼筆或原子筆。也有例外,如香港的曾敏之用毛筆寫的信滿紙云煙,美國的王鼎鈞用宣紙寫的信有如一首朦朧詩。在信的抬頭上(有些未收進書中),也是千變萬化,諸如:古兄、古公、遠公、古先生、古教授、古大俠、遠清先生、遠清老師、遠清老弟、遠清教授、遠清學友、遠清學兄、遠清文友、遠清詩友、遠清道兄、古教授道席、古教授惠鑒、遠清先生臺鑒、親愛的古老師、遠清吾兄啊……不管什么稱呼,我都來者不拒,一一“笑納”。至于“親愛的古老師”,那是男性學者寫的。還有堪稱絕倒的上海某文化名人的粉絲所寫的匿名信,不妨也公布出來“奇文共欣賞”。該信開頭直呼我“古蓄生”,頓時有大糞澆頭之感,再讀書信中一再出現的“你這個王八蛋早該三十年前就死掉,×你媽!”的粗鄙詞句,頓感寫信者在給我上演恐怖片。當然,也有不恐怖挺溫馨的,如帶雅醇味的“古公”,系北大教授張頤武二十年前的“發明”,這有點抬舉我了,但我總覺得這種稱呼是不是把我喊老了?《臺港文學選刊》主編楊際嵐有一次會上稱我為“古大俠”,我連忙說自己不是唐文標,愧不敢當。我想這位先生是想為我取諢名“古大炮”,但覺得有點直露,便借陳映真稱我為“獨行俠”一詞加以改造。“古大師”的諛稱,應屬新加坡女作家蓉子的專利了,我這回不再笑納而只能誠惶誠恐地“謝冕”。我有自知之明,她說的應該是“大學老師”的簡稱吧。至于和我親近一點的作家,如加拿大的洛夫稱我為“遠清吾兄”,香港的黃維樑稱“老古”,澳門的朱壽桐稱“古老”,大陸的洪子誠則稱“遠清”。
我不僅喜歡閱讀文友的書信,而且有收藏尺牘的癖好。比如讀者來信,我就很重視,不像某些人看完后就丟到字紙簍里。這些不相識的讀者來信,有索字的,有索書的,有索序的,有要我簽名寄書的,有托我幫其在海外留學的,有請我幫他在新加坡讀書的公子找監護人的。最有戲劇性的是那封高喊“救命”的信。此信“作者”系一位家住湖北農村的讀者,她失戀后想自殺,后買到我在三聯書店出版的《留得枯荷聽雨聲——詩詞的魅力》。這“枯荷”稀釋了她干枯的心靈,讀后用詩傾吐她的滿肚苦水,我從中感受到她對生活的絕望,便連忙勸她讀讀舒婷的詩《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大樹都被暴風折斷,不是一切種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夢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她感到我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便要求到武漢與我見面,目的是幫她找工作。我回信說自己違背了“學而優則仕”的古訓,從未做過官,手中沒有權力辦這件事,但可以幫她認識一些寫詩的朋友。后來果然成功了,從此她感到生活充滿陽光,稱我為“救命恩人”。這是正能量的。再說一個“負能量”的來信:澳門一位中學教師要寫博士論文,希望我能越俎代庖。他明碼實價,說一個字一塊錢人民幣,也就是一萬字一萬元(這在二十年前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萬元戶”),我想這事有違師德,既無時間更不能做。
我研究華文文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在武漢這個非沿海城市,必須廣交文友,才能取得豐厚的資料。我一支筆用來寫作臺港文學史,另一支筆則用來在信箋上馳騁。讀朋友的來信,本是一種精神享受,可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紛飛如雪的信函,我無法與他們書翰往返,這就成了余光中所自嘲的不堪“信托”的人。這不堪“信托”,不僅表現在無法做到有信必復,還體現在遺失了一小批珍貴的書信,如徐遲為拙著《詩歌分類學》作序時,用一個大信封裝了用鋼筆寫的序的原稿,還附了一封給我的信,另有一封給《收獲》雜志主編李小林的信也誤裝在里面,可這兩封信哪怕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未能找到。
編印世界各地朋友寫給我的書信,是一種冒險行為,弄不好別人會告我侵權,因而我盡可能取得寫信人的授權,但不可能全部做到。這時有人告訴我,魯迅不是還未經徐懋庸的同意發表其書信,并將其“示眾”嗎?夏志清編輯張愛玲給他的信,也未得到張愛玲或后人的授權吧。幸好我在這本書中已把不宜公開的內容作了刪改,有些還隱去姓名。如果有人要與我對簿公堂,那就“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廣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