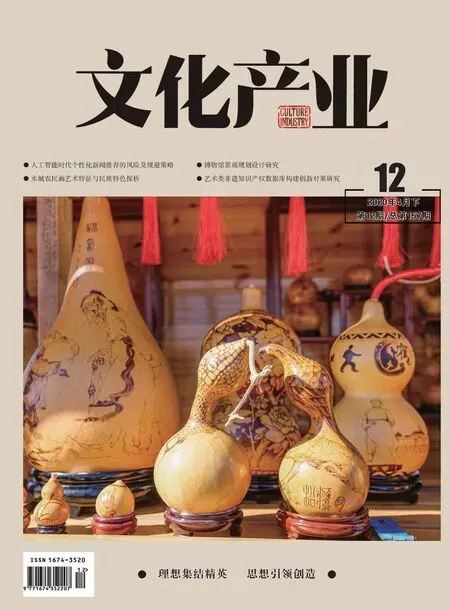“新”之何在:再議亦舒都市小說的新女性形象
2020-01-02 22:21:23楊含笑
文化產業
2020年12期
◎楊含笑
(河北傳媒學院 河北 石家莊 050000)
當今社會何為“新女性”?又“新”在哪里?在具體環境中,對女性的形象有不同的思考與相應形態的塑造。為順應時代潮流又如何去維持“新”,已經成為當前文學作品所共同關注的話題。當我們在談論“新女性”時,不應僅僅只有都市女性去覺醒,但又必須是先讓都市女性覺醒。
亦舒依據不同時代背景及生活狀態對“新女性”這一概念進行追本溯源與多角度分析,探索新女性所面臨的雙重困境及我們女性想要去往幸福道路的渴望,激發女性心目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呼吁女性正視自己、得到尊重。
一、亦舒小說中“新女性”的主要表現
亦舒是現代“女性主義”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為我們塑造了許多新型女性形象。這些形象和傳統女性不同,她們是在繁華城市中的“小人物”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身事業建設中去,主張走出家庭,在經濟上完全不依靠男性,這是亦舒所理解的現代女性。其“新女性”特征主要表現為平等的兩性關系、對父權的反抗以及得到應有的尊重等方面,鼓舞了現代女性不斷成長。
亦舒使現代女性意識到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應正視自己本身,不再把生活或希望寄托于男人和孩子身上,主張以互相尊重的態度去看待男女雙方特有的優勢與劣勢。亦舒的小說在當代女性文學中產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喚醒了女性心中渴望已久的平等的生命力。
(一)崇尚兩性平等
從亦舒的愛情觀中我們能夠看到,她所認為的愛情是個性獨立、不需要依附男性來生活;……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