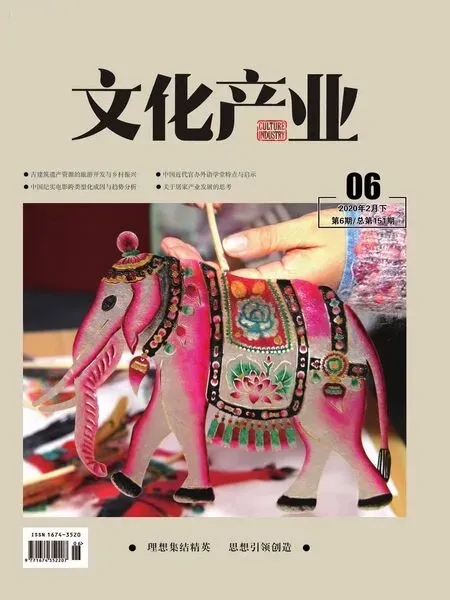網絡環境下的“囧”與“槑”之辨析
◎周湘嫻
(長江大學文學院 湖北 荊州 434023)
在網絡信息化時代,各種各樣的圖文資源及網絡語言大量出現。除卻簡稱類(英語或漢語詞語首字母縮略,如 ppt=PowerPoint;xswl=xiao si wo le 笑死我了)、諧音替代類(如88=bye-bye)、詞語借用(即語言社團間的借用,如“潛水”一詞指網上長期不上線或不發表言論的行為)、顏文字(即一種表情符號如(* ̄) ̄)=微笑)這四類常見的網絡語言類型,近些年以“囧”“槑”為代表的古代生僻字也漸漸活躍于網絡交際中,成為新一代網絡語言的典型。
一、“囧”與“槑”的前世
“囧”源于甲骨文,是一個象形文字,表示圓形的窗戶,其中均勻分布的三撇代表著鏤空的裝飾。后來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基礎上進行整改的小篆和漢字隸變之后的隸書與現在的“囧”字字形基本相似,外面的“口”相當于窗戶,里面的“八”和“口”像是窗戶的雕花和結構。蔣瑞在《甲骨文“囧”形義新證》對“囧”字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分析,認為目前主要存在四種說法:1.窗戶說。許慎《說文·囧部》:“囧,窗牖麗廔闿明。象形。”2.倉廩說。屈萬里:“囧字,當為倉廩一類之物,于此則作動詞用,‘米囧’,意謂新米已入倉廩也。”3.祭祀說。于省吾先生:“囧為祭名,契文亦作,通盟。即《周禮》詛祝盟詛之盟……囧米連文,盟謂要誓于鬼神。”4.地名說。李孝定于囧字取形贊成窗戶說,于辭義則認為是地名說:“卜辭囧為地名,且多與米字同見。”如:《史記·周本紀第四》:“孔安國曰:‘伯囧,臣名。’”蔣瑞經過考證得出“囧”取形于大明之日,在甲骨文中用作祭祀地名。他認為“囧”字的原始形態都為圓形,取形于圓形物體,“囧”中的彎曲線條呈現流動狀可解釋為“火焰”,因此認為“囧”為放大光明之日,也由此說明在古代“囧”多用于人名或地名表示“光明”。
“囧”同樣可以根據“聲訓”的方法通過語音分析來解釋詞義。如:王筠在《說文釋例》中解釋到:“讀若明同,既以明說其義,而復言此,是賈侍中直謂囧明一字矣。”《廣韻·梗韻》:“囧,光也。彰也。”由此可見“囧”造字之初通過象形表示窗戶,后來引申為光明之意,可以通過“朙(明)”“烱(炯)”等字反映出來。
“槑”與“囧”做對比略顯不同,在第六版《現代漢語詞典》中,“槑”沒有單獨的查閱單元而是作為“梅”的異體字形式存在。目前對于“槑”字本源有以下解釋:1.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六篇上木部》釋為:“某,酸果也。從木從甘。闕。槑,古文某,從口。”由此可見,“槑”同“某”。2.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某,酸果也。此是梅子正字。為何‘某’義訓酸而形從甘?甘者,酸之母也。幾食甘多亦作酸味。水土合而生木之驗也。”3.清代王筠《說文釋例》稱:“某之古文槑,既不可云從林從吅,則仍是從木從口矣。”4.《康熙字典》引《類篇》云:“呆,同槑省,或某,通作梅。”由此可見,“槑”和“某”(或“楳”)均為“梅”的異體字。1955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其中就包括“梅”的兩個異體字——“楳”和“槑”。因此,“槑”是明文規定“停止使用”的廢字。
從“聲訓”的角度看,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果部·梅)有:“梅古文作呆,像子在木上之形。梅乃杏類,故反杏為呆。書家訛為甘木。后作梅,從每,諧聲也。或云:梅者媒也,媒合眾味。”許慎《說文解字》亦收入“梅”字,釋為:“枏(ná n)也。可食。從木、每聲。”“枏”同“楠”,《說文》對“枏”的解釋是:“梅也,從木、冄聲。”二字可以彼此互訓。由聲訓的方式亦可知“梅”從“某”(或從“呆”)。
綜上所述,“囧”乃象形字,其原始義為“窗戶”后來又產生出“地名”“祭名”等多種義項,但最常見的還是由“窗”引申出的“光明、明亮”之意,這也可以通過聲訓的方式解釋“囧”的光明義,如:jiong(囧炯冏烱);“槑”則是“梅”的異體字,古時與“某”同(即梅子)后來與“楳”“梅”在語音語義上趨于相同,成為“梅”的異體字,所以根據語言的經濟性原則,“槑”是廢字不應再使用。
二、“囧”與“槑”的今生
原本因長相太過奇怪且與內涵不符而逐漸被人遺忘的古漢字“囧”,在這個溝通無邊界的網絡世界被重新啟用。“囧”的重現最初來源于哪里?民間盛行這樣一種說法:它與日本流行的網絡用語“Orz”密不可分,“Orz”不是一個英文單詞而是一種類似于漢字的“象形文字”。“O”代表一個人垂在地面的頭,“r”表示支撐在地面上的胳膊,“z”則表示跪在地上的腿,總之構成的是一個垂頭喪氣的人形,表達的含義自然也是人失意沮喪時的狀態。說它是一種顏文字(即一種表情符號,利用特定字符編排其組合次序形成的新型美術作品)也未嘗不可。后來臺灣民眾受此啟發,將古漢語中的“囧”字替代“O”成為“囧rz”,使一個抽象的頭(O)變為具體化的面部表情(囧),更加能夠展現人的豐富的內心世界。并且“囧”表情內涵豐富,隨著流傳范圍越來越廣,人們便只保留“囧”字,用于日常的語言表達。由于“囧”生動的外形:外面的“口”象征人臉的輪廓;里面的“八”好似人郁悶時皺起的八字眉;下方的“口”像是因驚訝而張大的嘴,人們常用它來表達自己難以言說的心情,諸如:郁悶、驚訝、無奈、困惑等等。正因如此,它的用法也是多種多樣,如作名詞《一日一囧》(網絡視頻名稱)、作動詞《明星穿錯衣 囧你沒商量》(騰訊女性頻道2009.11.2)、作形容詞《人在囧途》(電影名稱)。360搜索“囧”可以發現23900000個相關信息,特別是徐崢指導的“囧”系列電影,讓古漢字“囧”家喻戶曉,煥發生機并擁有了新的含義。然而“囧”字的語音為何沒有隨語義一同發生變化呢?這依然可以用傳統“因聲求義”的方式來解釋,如今的“囧”和“窘”讀音完全一致,容易讓人聯想到窘迫的“窘”,從而將“囧”原本就包含的新意“窘迫不安”同樣賦給“囧”字,這樣一來“囧jiong”的讀音就可以保留。根據王寅《論語言符號象似性》中將象似性定義為:語言符號在音、行或結構上與其所指之間存在映照性相似的情況。“囧”除了在外形結構上與新義一致外,和“窘(jiong)”在讀音上也一致,其意義也與“窘”相似。
“槑”對于現代社會同樣是一個古生僻字,但探究其的來源可以發現,它并不同“囧”一樣“舊詞新用”而是作為“梅”的一個異體字“廢詞活用”。這也決定了它適用范圍的有限性,即只存在于虛擬的網絡空間,幾乎不會出現于實際生活的交際之中。“槑”最初流行據說是因為網友的一個帖子:“看到一個人的名字叫‘x槑’覺得很奇怪,便問那人是不是叫‘x呆呆’,結果對方大怒,糾正不是‘呆呆’是‘槑mei(第二聲)’”。此貼一出,“槑”便開始在網上活躍起來,同“囧”一樣,網友們更樂意從它的外形結構上定義它,給它附上“很傻很呆”的義項,“槑”即為呆上加呆,比如“槑頭槑腦,指呆頭呆腦,來源于《鄉村愛情》的爆笑喜劇。隨著“槑”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又引申出幼稚無聊,矯揉造作等意義,如“看完槑片(幼稚無聊的電影),大家都槑住(呆住)了。”由于用傳統聲訓的方法無法解釋網友們早已習慣約定的“呆”的義項,所以部分網友更愿意將“槑(mei)”讀成“呆(dai)”,這種現象一方面由于語言的任意性,另一方面在于漢字造字的特殊性,因為漢字多數為形聲字(即由一個意符和一個聲符組成)所以有些人容易將某些字當成形聲字,將其讀音錯念為其某一偏旁的讀音,所謂“秀才認字認半邊”就是這個道理。但“槑”畢竟是“梅”的異體字,它的重新啟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外形的特點,與它本身的含義及讀音毫無關系,像這一類字還有很多,它們都是通過自身結構特點引起了網友們的注意,進而流傳開來。由于生僻字適用范圍的有限性,它們只在網絡上流傳甚廣,官方的定義和讀音并沒有改變,所以用拼音輸入法交流還是需要掌握它們正確規范的讀音,于是“槑”的讀音也被網友玩壞了,比如:“槑完槑了(表示一直很呆)”出自于“沒完沒了”;網上還流傳著“槑讀作mu為關中方言表示責備”。總之,網友們通過諧音的方式,增加“槑”字的用途,既符合經濟性原則,又體現出“槑”這類網絡詞用法的靈活性。
三、“囧”與“槑”之辨析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囧”與“槑”的產生及發展,它們都曾作為讓大眾一度困惑的生僻字進入網絡世界,憑借著自身優越的外形條件而受到網友們的青睞。盡管網絡環境給了他們第二次重生的機會,但“囧”的影響力遠比“槑”大得多。這一方面在于他們自身演變的規律,“囧”字作為一個原始的象形文字,其音形義之間存在著穩定的相互關聯,直至今日“囧”(《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為“冏”)也保留著原始音形義而存在并衍生出不少與其相關的文字如:窘炯烱;“槑”則由原來的會意字漸漸被易讀的形聲字“梅”所取代,其熟知度及受它影響的漢字都不及“囧”字。另一方面從外在使用環境來看,“囧”不僅在網際間流行,更滲透到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例如李寧的“囧”鞋創意營銷、徐崢的“囧”系列電影……究其原因還在于現代的“囧”字形象更加豐富,所表達的含義更廣,不僅可以表示消極的郁悶,也可以表示積極的幽默,并且其形音義三者相契合符合人們的認知習慣;而如今網上流行的“槑”字除了與“呆”在形象上符合一點并沒有其它共同特征,除了借用“呆”的含義外可供網友聯想的網絡內涵也存在局限性,即使有時利用其自身諧音造詞(如槑完槑了)也是表達“呆頭呆腦”的含義,并且如今網絡上類似于“槑”這類“會意字”大量存在如:烎、玊、燚……他們僅僅因為外形新穎可以通過“形訓”的方式被網友征用,不像“囧”這類“象形字”競爭小淘汰率低,字形不但類同人臉內涵豐富,字義也與如今“窘”字一致,使人自然將它們倆的字義聯系在一起。
“囧”和“槑”都是近些年來網絡流行的熱門古漢字,它們之所以在眾多已被時代淘汰的漢字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還是在于它們生動脫俗的“形象”。然而如何像“囧”一樣產于古代興于現代并繁衍出一系列“囧”文化,成為網絡古漢字的佼佼者?還在于文字本身形音義的相似性符合現代人們的認知(如“囧”與“窘”的相似性),不像“槑”這類“會意字”僅依照外形結構走紅,形音義結合并不緊密容易造成人們識記的混亂。雖然它們的本義早已與現在大相徑庭,有些人甚至稱它們為“網絡新字”而不是“古漢字”,但無法否認它們在幾千年前就存在,它們不是被創造而是被發掘出來的,它們被附上符合現代社會的意義色彩被廣大網友所接受并傳播,不僅豐富了現代交流的語言系統,也引發了國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字的興趣與關注。
在繽紛多彩的網絡時代,越來越多的視頻、圖片、影音、錄像作為信息資源涌入大眾的視野。為了適應現如今日益圖像化的時代,適應人們日益追求直接觀感的心理,“囧”和“槑”這類形象化的古漢字正好符合人們交流的豐富性和趣味性,網友們將能直接表達自己表情、心情或態度的語言用一個“漫畫式”的古漢字代替,既簡潔又特別,特別突出了中華漢字作為一種表意文字的強大魅力。即使是在當代社會,沉睡上千年的生僻漢字只要符合社會大眾的審美和需要,也能被重新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