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黑格爾的“東方哲學是宗教哲學” 說
□朱 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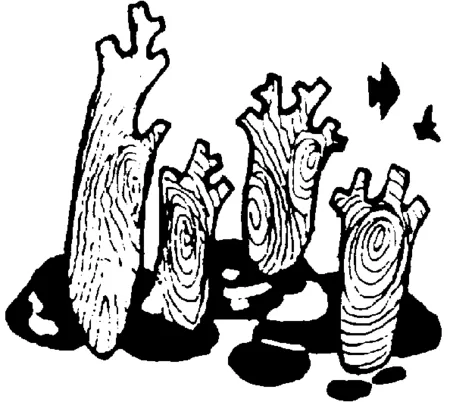
一、“東方哲學是宗教哲學”提出的背景
“東方哲學是宗教哲學”這句話出自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所著《哲學史講演錄》一書。當時,德國的哲學處于政權與教權沖突的漩渦之中,無法受到足夠的關注。于是,黑格爾呼吁具有哲學研究傳統的日耳曼民族發揮出自己的民族性,重新拾起對哲學的興趣,以便在“世界精神”忙碌于現實,無法回復自身的時候,為其開辟道路使其回復自身,得到自覺。希望哲學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是黑格爾所期待的。他認為,要想大眾對哲學有所重視,必須以對哲學這個概念的界定為起點。而對哲學概念認識的首要條件就是厘清哲學所要研究的內容。宗教與哲學作為思想的產物,二者密切相關。研究哲學,必須同宗教、政治、科學、藝術有所區別。“由于宗教與哲學不分的看法流行,為了要使哲學史與宗教觀念有一更明確的界限,對于足以區別宗教觀念與哲學思想的形式略加確切考察,應該是很適合的。”(《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64頁)于是,在這樣的語境下,“東方哲學”被黑格爾用以區別宗教與哲學以及說明“哲學應是什么”這個命題。
對東方哲學的敘述被黑格爾安排在全書正文開始前的導言部分,而且他曾明確表達:“東方哲學本不屬于我們現在所講的題材和范圍之內”(《哲學史講演錄》第115頁),這表明在他看來東方哲學應該被排除在哲學史的范圍之外。在《哲學史講演錄》中,他稱:“東方哲學是宗教哲學”(《哲學史講演錄》第113頁),甚至說:“我們所叫做東方哲學的,更適當地說,是一種一般東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種宗教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我們是很可以把它認作哲學的。”(《哲學史講演錄》第115頁)這里所稱的東方哲學特指印度哲學與中國哲學。且東方哲學之所以被稱為宗教哲學,乃是因為“在古代東方,宗教與哲學是沒有分開的,宗教的內容仍然保持著哲學的形式”(《哲學史講演錄》第64頁)。經過考證,可以發現,其實黑格爾在說這句話時并沒有特地區分印度哲學與中國哲學,根據他后文的敘述,“東方哲學是宗教哲學”中的東方哲學指的乃是印度哲學。因為在別處他曾提到:“在波斯和印度的宗教里有許多很深邃、崇高、思辨的思想被說出了。”(《哲學史講演錄》第64頁)
二、東方哲學是宗教哲學解
(一)印度哲學是宗教哲學
印度哲學被稱作宗教哲學乃是因為在印度的宗教中包含著哲學的內容,但是它卻不具有哲學的形式,宗教觀念停留在普遍性中,沒有發揮出主觀性因素進入到個體的心靈,因此精神還停留在有限性中。具體來說,印度宗教的神靈與哲學中的最高理念一樣具有普遍性,這種普遍性顯示了哲學的觀念與思想,但是印度宗教普遍化的形象在進入個體心靈時無法形成主觀人格化的階段,那么這種普遍化就是表面的,并未深入內在,因此是有限的、不徹底的。
乃至整個東方宗教的情形便是:“只有那唯一自在的本體才是真實的,個體若與自在自為者對立,則本身既不能有任何價值。也無法獲得任何價值,只有與這個本體合而為一,它才有真正的價值。但與本體合而為一時,個體就停止其為主體,(主體就停止其為意識),而消逝于無意識之中了。”(《哲學史講演錄》第117頁)這便是黑格爾所描述印度宗教的概況,至于印度宗教不能稱作哲學而只能是宗教哲學乃是因為:印度宗教的神靈與哲學的最高理念都以普遍性的形式作為自己的起始,并且以追逐無限為各自的目標。宗教作為思想,指向人的內心和性靈,打開了主觀性的范圍,引導精神進入有限的表象方式的范圍。永恒的東西作為精神的對象必然是進入有限的意識中被感覺到,因此在宗教中,“為這真的、永恒的事物所寄托的精神乃是有限的,精神之意識到它的方式也只包含在對有限的事物和關系的觀念里和形式里”。但是精神作為普遍的、無限的、自己認識自己的存在,它不會拘泥在有限性中,只會在無限中自己認識自己。所以精神必然要超出個體性,進入它的對方(主觀者的心靈),達到普遍者與特殊者的統一。印度的宗教,最高存在僅停留在外在的、客觀形式的意識中,并未深入內在,進入個體的心靈。主體與個體是表面的統一,并未實現真正的合一,所以還未達到哲學的階段。此外,宗教是理性自身啟示的作品,是理性最高、最合理的作品。盡管宗教與哲學都以絕對本質、無限普遍的理念以及世界的本質、自然、精神的實體為認識對象。只不過最高理念呈現在宗教中以當下的直觀與感覺的表象的形式,且宗教通過默禱、禮拜等儀式與它的對象——上帝統一。而哲學是通過思想、思辨的形式與最高理念合一,它是關于真理的科學,其目的在于認識真理之必然性,真理存在于知識中,真理既不能在直接的直覺中也不能在外在的感覺直觀或理智的直觀里被把握,只有在反思中才可以為我們所認識。
(二)中國古代沒有哲學
黑格爾在談中國哲學時,提到了孔子、《易經》以及道家的學說。他評價孔子的學問是“一種道德哲學”(《哲學史講演錄》第119頁)。因為在他看來《論語》中所記載的孔子與弟子的談話,僅是一些常識道德,并且這種道德每個民族都具有,所以毫無出色之處。孔子的學問被稱為是“道德哲學”,是因為《論語》中的言論缺乏思辨性,“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這與黑格爾所理解的哲學標準不契合,因此稱不上真正的哲學。《易經》顯示了中國古代的思想不再停留在感性、具體的階段,而是形成了抽象的、純粹的范疇。但是這種純粹的思想的范疇還不夠深入,還沒有達到概念化,僅僅停留在最淺薄的思想層面。而哲學作為概念的思維,是思想進一步規定的產物,它的發展是不斷向內的深入,所以《易經》所表達的思想也稱不上哲學。談到道家的思想時,他認為“道”中包含了原始的理性,它產生宇宙、主宰宇宙。但是這種理性不同于哲學中思辨的理性,是一種超自然的理性,就像《道德經》中對“道”所描述的那樣不可捉摸。并且道家將萬物的起源規定為“無”,認為“無”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在黑格爾看來這乃是一種否認世界存在的做法。并且如果僅停留在否定的規定中,那萬物的起源就無法解釋,所以“有”應是作為萬物存在的根本,然后才有“無”,“無”是對有的揚棄與超越。
三、東方哲學為什么不是哲學
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宗教、哲學是精神這一范疇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不同形態,是精神在不同環節的顯現。宗教、哲學都是思想的產物,作為絕對精神的意識形態,它們是精神自我認識過程的必要階段。“哲學是這樣一個形式:什么樣的形式呢?它是最盛開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個形態的概念,它是整個客觀環境的自覺和精神本質,它是時代的精神、作為自己正在思維的精神。”(《哲學史講演錄》第56頁)精神對宗教外在的、有限的意識的揚棄便產生了哲學。邏輯上,哲學的起始在于:處于自在階段的精神在宗教內感到自己是不自由的,隨著精神的覺醒,它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便開始沖破束縛,由自在向自為轉變,將宗教作為自己的對象,并在這對象中認識自己,克服對方并將其作為自己發展的一個環節,最終到達哲學的階段。這一過程在歷史上則顯示為:當一個民族有了自由意識,并且將“思想自己建立自己”的自由原則作為本民族存在的根本,便具有哲學產生的條件。從根本上講,人是自由的,因為“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說,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哲學史講演錄》第26頁)。一個民族當它以普遍性為思考的對象時,我們便稱它開始有了自由。但是在東方,“意志的有限性是東方人的性格,因為他們的意志活動是被認作有限的,尚沒有認識到意志的普遍性”(《哲學史講演錄》第95頁)。意志的不自由導致思維的有限性,因此精神就無法思維普遍,意識到自己是獨立自主的、自由的。歷史上:“在東方只是一個人自由(專制君主),在希臘只有少數人自由,在日爾曼人的生活里,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皆自由,這就是人作為人是自由的。”(《哲學史講演錄》第99頁)其實,東方那唯一專制的人——皇帝也是不自由的,因為自由是建立在別人也自由的基礎上的。
哲學的發展是不斷進步的,是世界精神不斷沖破有限性而朝向對無限的追求。在東方,世界精神是停滯不前的:“它的文化、藝術、科學,簡言之,它的整個理智活動是停滯不進的;譬如中國人也許就是這樣,他們兩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達到和現在一樣的水平。” (《哲學史講演錄》第8-9頁)哲學概念只在表面上形成哲學的開始,但是真正的哲學需要思想不斷的向內反省,對概念的證明才是哲學真正要做的事情,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哲學是在發展中的系統,純粹哲學表現其自身作為在時間中進展者的存在,它的目的在于認識那不變的、永恒的、自在自為的。它的目的是真理。哲學認識真理是通過一系列的理念實現的,即揭示出理念各種形態的推演和各種范疇在思想中被認識的必然性。哲學的發展亦依賴于理念的發展,理念是自身區別、自身發展的。理念發展的動力來自于內在的矛盾,矛盾的運動是由自在而自為的,所以理念必須要通過外化自己、認識自己、發展自己沖破自在達到自為。因此,理念的發展并非停滯不前,從它的本質來看,它就不是靜止的,它的生命就是活動。哲學的運動乃是自由思想的活動,是思想世界、理智世界如何興起,如何產生的歷史。
四、結語
對黑格爾“東方哲學是宗教哲學”說的理解,應該分兩個方面:印度哲學是宗教哲學;中國古代沒有哲學。黑格爾對東方哲學的所有評判乃是基于精神哲學的立場,精神作為黑格爾哲學的最高范疇,是評判各民族是否存在哲學的標準。一直以來,東方宗教的特質便是將自然視為實體,西方宗教則是將精神作為實體,文化背景的差異是造成黑格爾對東方宗教、哲學評價有失偏頗的主要原因。再者,從黑格爾對中國哲學只言片語的評價中,明顯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僅僅用孔子的學問、《易經》、道家思想來舉例證明中國沒有哲學是非常片面的。而在黑格爾那里,對秦以后的中國思想發展狀況只字未提。如此種種是造成他對中國哲學誤會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