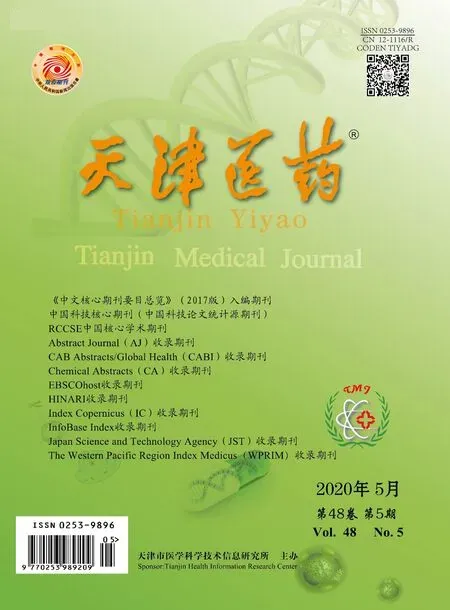創傷性腦損傷相關神經炎癥的研究進展
宋鴿,劉曉銀,史新宇,葉益超,張賽△
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問題,全球每年有超過5 000萬患者,其中我國TBI 患者的數量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給社會和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負擔[1]。重度TBI 具有高病死率的特點,且近60%的幸存者存在后遺癥,包括身心疾病、工作障礙等[1]。在TBI 后幾分鐘內,受損區域及周圍正常組織的分子通路被激活,導致神經炎癥、興奮性氨基酸毒性、線粒體功能障礙、氧化應激、鈣離子超載和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破壞等,從而造成腦缺血、水腫、細胞毒性腫脹和顱內壓升高。其中,神經炎癥在TBI 全病理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對其病理機制的研究是TBI 精準治療的關鍵。因此,本文簡要闡述了與TBI有關的神經炎癥反應的最新進展,為TBI相關疾病的治療研究提供理論基礎。
1 TBI與神經炎癥
腦創傷后的神經炎癥的特點是顱內細胞的活化、白細胞的遷移和募集、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等介質的上調和分泌。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原發性損傷會導致細胞膜破裂,血管破裂和BBB破壞,隨后發生一系列繼發性反應,包括離子失衡、興奮性氨基酸釋放、鈣超載和線粒體功能障礙等,最終造成細胞死亡。在此病理過程中會釋放大量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活化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并且募集循環免疫細胞。炎癥反應對TBI 后的碎片清除、修復和再生至關重要,而炎癥失調會造成急性和慢性腦損傷[2]。因此,了解TBI 后相關炎癥反應的調節機制十分重要。以下將從TBI后急性炎癥反應的分子調節機制和細胞調節機制進行介紹。
2 分子調節機制
TBI 后,顱內細胞會釋放大量內源性因子,如炎癥小體、線粒體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熱激蛋白和高遷移率族蛋白B1(high-mobility group box 1,HMGB1),它 們 作 為DAMP 與 核 因 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和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通路的Toll 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 TLR)相結合,引起多種趨化因子(chemokine ligands,CCL)及其受體(chemokine receptor,CCR)和促炎性細胞因子的釋放,包括CCL2/CCR2、CXCL12/CXCR4和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中的IL-1β和IL-6等[3]。
2.1 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 細胞因子是由免疫細胞(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等)和非免疫細胞(內皮細胞、神經膠質細胞等)分泌的一類可溶性多肽,與免疫活化和炎癥反應相關。根據細胞因子對炎癥的不同調節作用可分為促炎性因子(如IL-1、腫瘤壞死因子-α)和抗炎性因子(如IL-10)兩類。TBI 后,CNS的星形膠質細胞、小膠質細胞和神經元分泌大量IL-1β,可加劇神經元損傷[4]。在局灶性TBI 小鼠模型中,阻斷IL-1α 和IL-1β 受體后能減弱其炎癥反應并改善認知功能[5]。有臨床研究證實,孤立性TBI患者入院時出現全身性炎癥反應綜合征是預后不良的重要預測指標[6]。中度或重度TBI 患者傷后6~24 h腦脊液和血漿中IL-8 水平會增高,并與TBI 后6 個月擴展版格拉斯哥預后量表(GOSE)功能評分呈負相關,且IL-8水平的升高也會導致傷后12個月內抑郁癥狀的增加[7]。與之相反,IL-10可減少促炎性細胞因子的合成,調節機體免疫及炎癥,但IL-10的表達水平與TBI損傷嚴重程度呈正相關[8]。
趨化因子是細胞因子家族中的一個大亞群,可將免疫細胞吸引到損傷或感染部位。與TBI有關的趨化因子、受體及其配體有很多種,包括CCL2/CCR2、CXCL8/CXCR2、CXCL12/CXCR4、CXCL10/CXCR3等。受損腦組織中趨化因子CXCR2升高,可誘導中性粒細胞向損傷部位遷移[9]。與正常小鼠相比,CCR2 敲除小鼠經歷TBI 后,巨噬細胞的浸潤減少,神經元密度顯著增加,運動能力、空間學習和記憶能力得到了改善[10]。CXCL12/CXCR4軸在中樞神經系統的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有研究證實,大鼠經受液壓沖擊損傷后,CXCL12可促進神經干細胞和神經祖細胞向受損腦區的遷移,與其受體CXCR4結合后可增強神經前體細胞的增殖[11]。
2.2 DAMPs DAMPs是一種相關胞內蛋白,當機體組織受損時,由損傷或壞死細胞釋放,在細胞內常以螯合分子的形式存在。DAMPs 與巨噬細胞、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和其他先天免疫系統細胞上表達的模式識別受體(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相結合,并通過促進細胞因子的分泌來維持免疫應答,作用于損傷部位,引起炎癥反應[12]。
2.2.1 HMGB1 DAMPs分子中的HMGB1是一種非組蛋白染色體結合蛋白,在穩定核小體結構、調控轉錄因子及DNA 的復制、修復和重組中發揮重要作用,是TBI 后炎癥反應的核心成分[13-14]。HMGB1 可通過受損和壞死的細胞被動釋放或免疫細胞主動釋放,并與晚期終末糖基化產物受體(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RAGE)和TLR 等表面受體結合,然后通過NF-κB 途徑觸發信號級聯[15]。NF-κB 發生核易位后,細胞釋放大量促炎性細胞因子,引發炎癥反應的級聯擴增。有研究證實,使用HMGB1抑制劑可維持TBI小鼠的BBB功能,減少顱內促炎性細胞因子(如IL-1β、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的釋放,減輕腦水腫程度的同時具有神經保護作用,減少細胞凋亡并改善其功能[16]。
2.2.2 mtDNA 線粒體廣泛分布于神經元軸突、末梢和樹突上。TBI 后急性線粒體破壞導致線粒體結構、功能和代謝的改變,引起供能障礙,可導致大量的神經元死亡。線粒體的成分釋放到胞外時會產生DAMPs的作用,線粒體DAMPs包括mtDNA、N-甲酰肽和線粒體轉錄因子A。一個細胞含有多種mtDNA,細胞損傷后釋放到循環中的mtDNA 可以通過TLR9 激活中性粒細胞p38 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號通路,并促進全身性炎癥反應綜合征的發展[17]。有研究證實,反復性的輕度TBI 30 d后,下丘腦和杏仁核中的mtDNA 數量依舊顯著升高[18]。在豬彌漫性TBI模型中,血液中mtDNA的相對拷貝數在6 h和25 h時升高,而在豬液壓沖擊腦損傷模型中,mtDNA的相對拷貝數顯著降低,并于25 h時達到最低值,且在血液中釋放緩慢[19]。
2.3 炎癥小體 炎癥小體是一種胞質多蛋白復合物,可被DAMPs激活,進而活化caspase-1,釋放成熟的IL-1β 和IL-18,從而促進細胞凋亡,并可調節固有免疫,引起機體的炎癥反應[20]。在多種炎癥小體中,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蛋白(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NLRP)中的NLRP1 和NLRP3 與TBI 相關度最高。有研究證實,在患有重度TBI 的兒童和成人的腦脊液中,NLRP3 或NLRP1 增高與預后不良有關[21]。NLRP3抑制劑可減少TBI 小鼠小膠質細胞活化、白細胞募集和IL-1β的分泌,同時減輕腦水腫和組織損失,改善認知和神經功能[22]。NLRP1 和NLRP3 可作為未來TBI治療的靶點。
3 細胞調節機制
受損神經元組織釋放的趨化因子可募集免疫細胞。根據TBI 的腦損傷范圍(局灶性或彌散性)不同,這些細胞的反應也略有不同。局灶性損傷的特征是中性粒細胞早期浸潤,然后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巨噬細胞和淋巴細胞向損傷部位遷移[23]。在彌漫性腦損傷中,早期的細胞反應主要包括小膠質細胞積聚和星形膠質細胞增多,而幾乎沒有中性粒細胞浸潤[24]。
3.1 中性粒細胞 局灶性腦創傷后最先滲透到CNS的循環免疫細胞是中性粒細胞,通常在24~48 h內可達到峰值[23]。研究發現,TBI 后中性粒細胞的數量顯著增加,它們被募集到大腦受傷部位的同時,破壞BBB,并釋放自由基、蛋白酶和促炎性細胞因子,加劇組織損傷[25]。有文獻報道,IL-23/IL-17 軸可調節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分泌并間接影響中性粒細胞生成,而受創傷的腦組織中趨化因子CXCR2升高,可誘導中性粒細胞遷移[9]。中性粒細胞可通過血管細胞黏附分子與內皮細胞結合,并沿內皮層滾動,隨后在整合素的作用下浸潤于腦受損部位[26]。同時,中性粒細胞釋放的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基質金屬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 9,MMP-9)會影響TBI 后小膠質細胞反應[27],并可驅動TBI的繼發性損傷級聯反應。
3.2 小膠質細胞 小膠質細胞是CNS的巨噬細胞,在大腦中可發揮清除碎片、改善突觸調節的作用,并通過吞噬和消除突觸來改善突觸回路,在TBI 后的炎癥中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28]。最新數據表明,小膠質細胞的功能與其表面的抗原有關,在不同的刺激條件下表面抗原會發生變化,從而發揮不同作用[29]。正常情況下,帶有分支樣突起的小膠質細胞胞體處于靜息狀態,其細胞表面抗原表達低。TBI后,小膠質細胞可以在M1和M2表型之間切換,少量促炎性因子可誘導M1型小膠質細胞生成,進而釋放高濃度促炎性因子(如干擾素-γ、腫瘤壞死因子-α、IL-1β)、趨化因子、ROS,導致慢性神經炎癥、氧化應激和神經變性,并抑制神經再生。M2樣小膠質細胞則釋放抗炎細胞因子,從而減少炎癥[30];此外,小膠質細胞還具有較強的吞噬活性,并通過促進CNS 損傷后的神經發生和髓鞘再生來改善大腦修復[31]。有研究發現,輕度TBI 造模5 d 后經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的大鼠可在24 h 內產生過量的促炎性細胞因子,3 個月后仍然有持續的小膠質細胞活化和行為缺陷存在[32]。
3.3 星形膠質細胞 星形膠質細胞在腦中含量豐富,是TBI后炎癥反應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BBB的維持十分重要。腦損傷發生后,星形膠質細胞迅速激活或增殖,其中細胞骨架蛋白、波形蛋白、膠質原纖維酸性蛋白和S100的表達上調,并向損傷部位遷移,原發性局灶性腦損傷的部位被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層包圍[33]。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可防止谷氨酸毒性,并通過防止谷氨酸毒性、防止氧化還原應激、調節線粒體修復機制、防止葡萄糖誘導的代謝應激、防止鐵毒性、在DNA損傷的情況下維持組織穩態的方式來保護神經元[34]。與此同時,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形成的神經膠質瘢痕可作為損傷區域的屏障,抑制炎癥細胞的遷移,從而限制神經毒素向未受影響的大腦區域擴散,但是神經膠質瘢痕也可損害軸突的生長[35]。
4 繼發性腦損傷(secondary brain insult,SBI)
SBI 是指原發性腦損傷后觸發了一系列復雜的內源性病理生理過程而造成神經細胞損傷。超過50%重度TBI 患者出現SBI,致使其病情惡化[36]。SBI 涉及多個細胞過程,包括ROS 生成、神經炎癥、內質網應激、線粒體功能障礙、細胞凋亡和興奮性毒性[37-39],而常見的引起SBI 的因素包括缺氧、低血壓和體溫過高等,這些因素與TBI 后炎癥反應的關系密切,同時引起腦組織缺氧或營養不良,導致細胞能量衰竭[40]。
4.1 腦缺氧 腦缺氧是由于氣道阻塞、呼吸衰竭、胸肺部或其血管受到任何其他傷害所致。重度TBI并發肺挫傷、誤吸、肺炎、肺不張和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的患者患低氧血癥的概率很高,可增加患者的病死率[41]。TBI后供氧不足引起的細胞能量危機會導致電解質失衡,異常的興奮性神經遞質的釋放,并進一步破壞線粒體代謝,從而導致自由基積聚過多。隨著神經炎癥反應的繼續,凋亡相關蛋白可啟動細胞凋亡[42]。臨床前模型也證實了這一觀點,TBI 后低氧血癥加劇腦水腫和缺血、神經炎癥、海馬神經元細胞死亡、軸突損傷和短期行為缺陷[43]。與控制性腦皮質撞擊小鼠相比,合并遲發性低氧血癥的小鼠損傷后6 個月的神經病理學評估顯示,合并癥小鼠顱內白質星形膠質細胞增多,病變體積擴大,空間學習、記憶和社交能力缺陷[43]。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可調節巨噬細胞釋放細胞因子和其他炎癥調節因子,并刺激巨噬細胞吞噬作用。有研究證實缺氧腦創傷患者的GM-CSF的水平長期高于正常氧氣攝入腦損傷患者[44]。
4.2 低血壓 TBI常伴有由急性顱外傷或神經源性導致的血流動力學改變。TBI 伴隨低血壓的患者病死率增加[45]。最新的重度TBI管理指南和腦創傷基金會的建議指出,對于50~69 歲的TBI 患者,將收縮壓維持在≥100 mmHg(1 mmHg=0.133 kPa);對于15~49 歲或>70 歲的TBI 患者,收縮壓≥110 mmHg 可降低病死率[46]。入院前低血壓的鈍性腦創傷患者血漿中細胞因子(IL-1β、IL-6、GM-CSF、IL-7 和IL-17)和趨化因子(CCL1、CCL3和CXCL10)的水平高于正常血壓的鈍性腦創傷患者[47]。血清淀粉樣蛋白A1(serum amyloid A1,SAA1)有強促炎作用,參與了許多促炎性細胞因子如IL-1α、IL-1β、IL-8、IL-6 和腫瘤壞死因子-α 的產生。與大鼠TBI 模型相比,TBI合并失血性休克大鼠血清中SAA1水平更高,可進一步增加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表達,導致炎癥損害[48]。也有研究指出,在TBI 合并出血性休克豬模型中,促炎性細胞因子(如IL-6、IL-8和腫瘤壞死因子-α)水平急劇增加,激活天然抗凝途徑,引起內皮細胞脫落[3]。
4.3 高溫 TBI后,顱內炎癥、血栓性靜脈炎和下丘腦損傷會引起機體體溫升高,而患者體溫的增高程度與其在重癥監護病房停留時間和病死率呈正相關[49]。在輕度TBI 大鼠模型中,體溫增高可明顯增加原發性腦損傷的炎癥反應,呈現以M1型為主的小膠質細胞/巨噬細胞表型,同時小膠質細胞和巨噬細胞活化模式發生了改變[50]。有臨床試驗證實,顱腦損傷合并發熱患者的IL-6 水平在24 h 內持續顯著增高,而IL-10 的水平則是在傷后24 h 才發生明顯上升[51]。與此同時,TBI 后中度低溫治療可啟動自噬和細胞凋亡的負調控,發揮抗炎和神經保護作用[52],并促進新生神經元細胞的長期存活及成熟[53]。
本文概述了TBI后急性和慢性階段發生的復雜炎癥反應以及SBI 的相關病理生理過程,總結了近幾年TBI研究中有關神經炎癥反應的分子調節機制以及細胞調節機制,進一步了解此過程將有助于設計合適的療法,以減少神經損傷,并同時利用促進神經修復和再生的特性,以達到改善TBI 患者預后的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