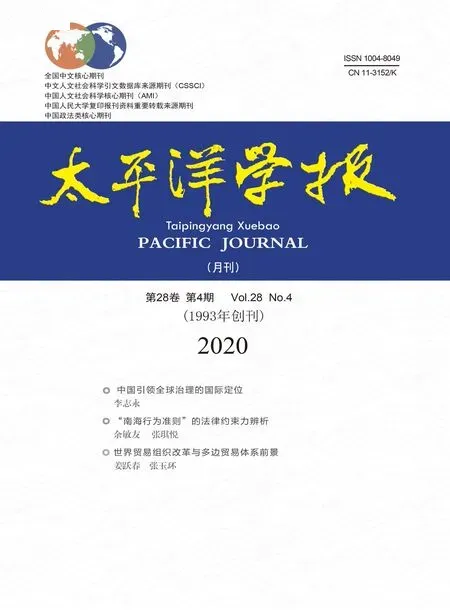“南海行為準則”的法律約束力辨析
余敏友張琪悅
(1.武漢大學,湖北 武漢430072)
“南海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的法律約束力爭議是中國與東盟國家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磋商至今始終面臨的主要分歧。2018年8月“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Single Draft Negotiating Text of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SDNT,以下簡稱“準則”草案)仍未明確“準則”的法律約束力問題,由此為各國官方磋商與學界研究留下了空間。以往學者對“準則”法律約束力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各當事國官方層面對此問題立場主張的差異,以及爭議的解決對“準則”現階段達成共識與在未來發揮作用的影響,而較少從國際法層面探討“準則”法律約束力爭議背后的理論依據與判斷標準。盡管“準則”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并且文件本身具有特殊性,但對其研究不能脫離國際法與海洋法理論與實踐。本文從國際法角度探討“準則”的文件形式、締結程序、實質內容是否有為各當事國創設國際法上權利義務的意圖,以此為切入點,研究國際法上關于一份國際文件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判斷標準,區分“準則”中直接與間接反映現行國際法規則的條文的法律約束力的差異,指出各當事國在實踐中應當自覺遵守“準則”規定,善意履行國際義務,發揮“準則”預期作用,具有重大意義與實際價值。
一、各相關方關于“準則”法律約束力立場主張的演變
1.1 東盟從主張“準則”為政治性文件轉變為主張其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
早在20世紀90 年代,東盟尚未對“準則”的法律約束力問題提出質疑。東盟將“準則”定性為一份政治性文件,不具有嚴格的法律意義,①[越南]陳長水:“海上問題的妥協與合作——《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的案例”,《南洋資料譯叢》,2015年第1期,第16頁。無需建立強有力的執行機制,“準則”的實施應基于各當事國善意。②Le Hong Hiep,“Vietnam’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ISEAS Perspective,Issue 2019,No.22,2019,p.5.自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實施以來,各當事國違反《宣言》的情形使大多數東盟國家意識到,沒有約束力的“準則”難以實現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目的。由此,東盟開始注重以國際法編制的規則約束各當事國在南海的行為,③趙國軍:“論南海問題‘東盟化’的發展——東盟政策演變與中國應對”,《國際展望》,2013年第2期,第89-90 頁。希望制定具有約束力的“準則”。④Carlyle A.Thayer,“ASEAN,Chin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3,No.2,2013,p.762012年東盟在《東盟關于南海區域性行為準則的建議要素》(ASEAN’s Proposed Elements of a Regional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與“東盟關于南海問題的六點原則”(ASEAN’s Six-Point Principl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中強調“準則”的國際法屬性。⑤See:Carlyle A. Thayer,“ASEAN,Chin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3,No.2,2013,p.76;“ASEAN’s Six-Point Principl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July 20,2012,https:/ /www.asean.org/storage/images/AFMs%20Statement%20on%206%20Principles%20on%20SCS.pdf.2017年8月“準則”框架通過后,東盟秘書長黎良明(Le Luong Minh)表態稱,“準則”必須具有法律約束力以確保有效。⑥“ASEAN and China Adopted COC Framework”,The Star Online,August 7,2017,http:/ /www.thestar.com.my/news/regional/2017/08/07/asean-and-china-adopt-coc-framework-code-on-mar?itime-disputes-brings-stability-to-the-issue-says-chi/.
1.2 東盟成員國從分歧轉向一致,主張“準則”具有法律約束力
東盟成員國從對“準則”法律約束力存在爭議轉向趨于一致。越南持續強調“準則”應具有法律約束力,并在“準則”草案中提議:“準則”需經各當事國內部程序批準,將批準文件交存至東盟秘書長后生效;秘書長應根據《聯合國憲章》第102 條在聯合國登記;“準則”非經各當事國協議不得終止、失效。越南還提議設置詳細嚴格的執行監督機制,主張建立監督“準則”執行的委員會,并為委員會設置詳細的運作機制。相比其他國家“由中國—東盟落實《宣言》高官會和聯合工作組會議負責執行監督”的提議,越南提議的該監督委員會明顯更加嚴格。越南還要求,當事國退出“準則”應經委員會或所有國家協商一致決定,并在12個月后生效。⑦Carl Thayer,“A Closer Look at the ASEAN-China Single Draf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The Diplomat,August 3,2018,https:/ /thediplomat.com/2018/08/a-closer-look-at-theasean-china-single-draft-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從越南的上述主張可見,雖然明知“準則”的最終磋商結果不能成為條約,但越南仍試圖將其視為“硬法”,要求其具有法律約束力并確保執行,以創設國際義務約束中國。⑧同②,pp.5-6.越南學界觀點與官方意見一致。2014年,越南外交學院南海研究中心主任陳長水(Tran Truong Thuy)認為,中國和東盟應當最終形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地區性行為準則,有效管理各當事國行為,確保任何一方免受威脅。⑨Tran Truong Thuy,“South China Sea Dispute:Implications of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for Coming Future”,The 3 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South China Sea:Cooperation for R eg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o-organized by the Diplomatic Academy of Vietnam and the Vietnam Law yers’ Association,3-5 November,2011,Hanoi,Vietnam.越南國際法研究所副所長阮氏蘭英(Nguyen Thi Lan Anh)主張,有約束力的“準則”不僅有價值而且必要,原因在于它能夠改善《宣言》的不足,更好地維護南海地區和平與安全,促進區域合作。①Nguyen Thi Lan Anh,“Content and Roadmap for a Legally Binding Code of Conduct in the East Sea,Vietnam Law”,Vietnam Law and Legal Forum,September 29,2014,http:/ /vietnamlawmaga?zine.vn/content-and-roadmap-for-a-legally-binding-code-ofconduct-in-the-east-sea-4902.html.
菲律賓強調《宣言》在南海爭端管理方面的不足,特別是《宣言》因不具有法律約束力而引發的低水平執行問題,未能滿足東盟國家的根本需求。菲律賓將“準則”具有法律約束力作為國家立場的主要落腳點,②白續輝:“追蹤與研判:《南海行為準則》制定問題的研究動向”,《南洋問題研究》,2014年第1期,第35頁。將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更具綜合性、有效性的“準則”視為“準則”與《宣言》的最大區別。③Ian Storey,“Assessing the ASEAN-China Framework for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ISEAS,August 8,2017,Issue 2017,No.62,p.2;“ASEAN,China Agree to Start Talks on South China Sea”,Philstar.com,November 13,2017,https:/ /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17/11/13/1758610/asean-china-agreestart-talks-south-china-sea-code.
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與上述觀點有所不同。馬來西亞起初明確反對在“準則”草案中使用正式條約的語言,不同意將“準則”制定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協定。2018年馬來西亞在“準則”草案中提議,“準則”的性質應取決于各當事國的意圖,即是否有意為各當事國建立法律約束力關系。如果“準則”的某些要素引自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條約,這些既存的法律約束力關系仍將維持。此外,馬來西亞還主張,在未能明確“準則”適用的具體地理范圍的前提下,不能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準則”。④Hoang Thi Ha,“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Declaration to Cod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SEA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EAS P erspective,Issue.2019,No.5,2019,pp.17-18.關于生效的條件,馬來西亞與文萊主張“準則”自簽署時開始生效。
印度尼西亞在20世紀90 年代主張將“準則”定性為政治性文件,而非法律性文件。2011年11月,在印尼召開的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印尼時任外長馬蒂·納塔賴加瓦(Marty Natalegawa)表示,希望盡快形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準則”,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問題,⑤“促進區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肩負重任”,《人民日報》,2011年11月17日,第3版;張明亮:“原則下的妥協:東盟與‘南海行為準則’談判”,《東南亞研究》,2018年第3期,第72 頁。體現出印尼主張的轉變。但在2018年1月,印尼外長雷特諾·馬爾蘇迪(Retno Marsudi)表示,印尼將積極努力促使東盟國家與中國達成切實有效的“準則”,實現南海地區的安全穩定,⑥Retno LP Marsudi,“Indonesia:Partner for Peace,Security,Prosperity”,The Jakarta Post,January 11,2018,https:/ /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8/01/10/full-text-indonesia-partnerfor-peace-security-prosperity.html.并反復強調“準則”應切實可行(practical)和有效(effective),而未再提及“準則”的法律約束力問題。
1.3 中國從強調“準則”的政治屬性轉變為其性質可以探討,要求“準則”實質有效
在早期的磋商中,中國一度強調“準則”屬于促進睦鄰關系、維護南海地區穩定的政治文件,而不是解決具體爭端的法律文件。2018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聯合聲明及“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 年愿景”中要求,“全面有效落實《宣言》,在協商一致基礎上早日達成和通過一個實質和有效的‘準則’”。⑦“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 年愿景(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年11月15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wj_682530/t1613344.shtml。李克強總理在第21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強調,深化海上務實合作,啟動并推進“準則”磋商,有效管控爭議,保持南海局勢穩定。⑧“李克強在第21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8年11月15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1613230.shtml。2019年7月31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曼谷出席中國—東盟外長會后會見中外媒體時表示,“準則”毫無疑問具有實際效力,相信未來達成的“準則”一定是一份更具效力、更符合地區實際需要、有更多實質內涵的高質量的地區規則。⑨“王毅回應對COC磋商的四個疑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年8月1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wjbzhd/t1685094.shtml。可以看出,近年來,中國官方從堅持“準則”的政治屬性轉變為可以討論。中國態度的轉變為中國在未來磋商中贏得了回旋余地,即如果“準則”按照中國預期的方向發展,中國有可能接受“準則”具有法律約束力;如果“準則”條款的意圖或條款的實施將造成對中國在南海行使正當合法行動的限制,中國很可能主張“準則”不具有法律約束力。①See:Hoang Thi Ha,“Trends in Southeast Asia,from Decla?ration to Cod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SEAN on the South China Sea”,ISEAS Perspective,Issue 2019,No.5,2019,p.27.中國態度的轉變事實上也反映出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分歧在縮小,從而擴大了達成共識的基礎。
我國學者對“準則”的法律約束力問題存在分歧。2003年臺灣地區學者宋燕輝認為,“準則”作為指導性文件而非條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準則”的遵守應當基于自愿。②Song Yann-huei,“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New Millennium:Before and After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2003,No.34,p.247.這一主張的原因在于,在南海島礁的領土主權與管轄權爭端尚未最終解決之前,中國與東盟國家不希望被迫受到“準則”的約束。③See:Song Yann-huei,“The South China Sea Declaration on Conduct of Par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Taiwan’s Perspective”, Mari?times Studies,Vol.2003,Issue.129,2003,pp.13-23.但他強調,“準則”當中基于國際法規則的條款對各國具有約束力。④Song Yann-huei,“Codes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aiwan’s Stand”, Marine Policy,Vol.24,Issue 6,2000,p.450.2015年學者駱永昆指出,主張“準則”具有法律約束力會導致與2000年中國與東盟高官磋商達成的協議相悖。該協議將“準則”認定為促進睦鄰友好與地區穩定的政治性文件,而非解決具體爭議的法律文件。更為關鍵的是,如果“準則”具有法律約束力,那么“準則”應由哪一機構負責監督實施仍有待明確。⑤駱永昆:“‘南海行為準則’:由來、進程、前景”,《國際研究參考》,2017年第8期,第10 頁。但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羅國強教授在2014年提出,由于《宣言》在性質定位、對象選擇、具體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法律約束力的缺失令其體現不出預期的影響和效果,因此制定有約束力的國際法律文件解決南海爭端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⑥羅國強:“東盟及其成員國關于《南海行為準則》之議案評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7期,第87頁。金永明教授在2015年提出,為進一步管控南海問題爭議,消除《宣言》缺少組織機構與懲罰措施的缺陷,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準則”就顯得特別重要。⑦金永明:“南海問題的政策及國際法制度的演進”,《當代法學》,2014年第3期,第18-26 頁。也有媒體與學者推測,“準則”法律約束力的表述可能不會在“準則”文本中出現。⑧匡增軍、黃浩:“從南海仲裁案看‘南海行為準則’爭端解決條款的制定”,《武大國際法評論》,2018年第1期,第94-95頁;黃瑤:“‘南海行為準則’的制定:進展、問題與展望”,《法治社會》,2016年第1期,第24頁。實際上,“準則”的框架與“準則”草案將各當事國的首要目標確定為“建立一個基于規則的框架,包含一套指導各方行為和促進南海海洋合作的準則”,兩份文件均運用了“基于規則的框架”的表述,而未運用東盟國家長期設想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措辭。⑨Ian Storey,“Assessing the ASEAN-China Framework for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ISEAS Perspective,Issue 2017,No.62,2017,p.4.
1.4 域外國家敦促中國與東盟國家早日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且有效的“準則”
美國從不甘心成為“旁觀者”,企圖時刻掌握“準則”磋商進程,并采取具體行動,包括為“準則”的磋商設置最后期限,推動東盟方面單獨就“準則”達成協定后向中國施壓。⑩韋宗友:“解讀奧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太平洋學報》,2016 年第2期,第31頁;Bonnie S.Glaser,“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Updat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2015,pp.1-4.2018年10月,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發表《消除南海爭議:地區藍圖》報告,提出建立以“南海仲裁案”裁決為基礎的權利分配方案和海洋合作方案。?“Defusing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A Regional Blue?print”,A Report of the CSIS Expert Working Group on the South China Sea,October 11,2018,https:/ /amti.csis.org/expert-workinggroup-scs/.2018年8月,澳大利亞學者卡爾·塞耶(Carl Thayer)發表評論,大幅披露“準則”草案這一仍在磋商過程中的保密文件,不僅意在公開“準則”草案內容,也表明美國在談判國中有線人、代言人存在。由此可見,盡管美國未能直接參與“準則”的磋商,但仍可能憑借其與東盟國家的密切聯系,掌握最新動態甚至操縱磋商走向。①高圣惕:“‘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需排除外來干擾”,《遠望》,2018年第9期,第16頁。這意味著要完全排除美國的干預幾乎毫無可能。
美國對“準則”法律約束力問題已施加了實際影響。2015年3月,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發表《維護規則:應對亞洲海域威脅》報告,建議美國應與其盟國和伙伴國家執行有約束力的“準則”,產生集體壓力,應對威脅性行為。②Alexander Sullivan and Patrick M.Cronin,“Preserving the Rules:Countering Coercion in Maritime Asia”,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March 11,2015,https:/ /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preserving-the-rules-countering-coercion-in-maritime-asia.2017年8月,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三方戰略對話部長聯合聲明對“準則”框架表示認可,呼吁相關方及時達成“準則”,確保其“有法律約束力、有意義、有效,與國際法保持一致。”③陳慈航:“美國在‘南海行為準則’問題上的政策論析”,《國際政治研究》,2018年第4期,第69-70 頁;駱永昆:“‘南海行為準則’:由來、進程、前景”,《國際研究參考》,2017年第8期,第11頁;“Australia,Japan,US Call for South China Sea Code to be Le?gally Binding”,NDTV,August 7,2017,http:/ /www.ndtv.com/world-news/australia-japan-us-call-for-south-china-sea-code-tobe-legally-binding-1734552。2017年10至11月,美國先后在與泰國、新加坡、越南等國的聯合聲明中,呼吁在南海問題上早日達成有效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區域行為準則。④陳慈航、孔令杰:“中美在‘南海行為準則’問題上的認知差異與政策互動”,《東南亞研究》,2018年第3期,第82頁。印度也明確支持將“準則”制定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機制。⑤陳相秒:“‘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正在取得積極進展”,《世界知識》,2017年第7期,第27頁。以上域外國家政府及其學者幾乎一致認為,“準則”具有法律約束力將成為“準則”與《宣言》最本質的區別,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二十年來努力談判磋商的重要價值。⑥安剛:“如何理解‘南海行為準則’框架文件的達成”,《世界知識》,2017年第17期,第32 頁。域外國家對“準則”磋商的干預,是否有助于解決“準則”的法律效力爭議及“準則”的順利達成,有待時間和實踐的檢驗。
二、“準則”法律約束力之爭的事實性因素
2.1 規則實施層面:“準則”的實施將對各當事國造成不同影響
盡管“準則”將對各當事國在南海的行為采取同等限制、賦予相同的權利與義務,但是“準則”的實施將為中國與東盟國家帶來不同的實際影響。在“準則”實施前,中國能依靠綜合國力、海軍實力、科技能力、雄厚財力的顯著優勢,在南海采取廣泛的行動,增強對主權范圍內海域的實際控制。“準則”實施后,為實現“準則”的預期目標,我國將進一步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爭議復雜化、擴大化和影響和平穩定的行動。由此,“準則”將對中國產生更多的實際限制。相反,“準則”對東盟國家在南海行動的實際影響更少,并且東盟國家通過集體談判磋商對中國施壓,進一步限制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從中獲益更多。
實際上,東盟國家在“準則”制定初期即有限制中國在南海行動的意圖。“準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5年中菲美濟礁領土爭端后,菲律賓尋求東盟國家的幫助,期望通過制定“準則”限制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動。⑦Carlyle A.Thayer,“ASEAN’s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Litmus Test for Community-Building?”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10,No.4,2012,p.2.由此,東盟國家主張“準則”應具有法律約束力,其意在賦予“準則”更高的法律位階,以鞏固東盟國家在南海的既有利益與預期利益,并避免重蹈《宣言》因缺乏法律約束力而無法有效約束和規范管理各國在南海行動的覆轍,這里主要針對中國。伊恩·斯托里(Ian Storey)在2013年印證了這一觀點。他認為,美國對于“準則”的支持只是為了限制中國,而非限制其他聲索國在南海的行動。⑧Ian Storey,“Slipping Away?A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Eludes Diplomatic Efforts”,i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Bulletin,No.11,2013,http:/ /www.files.ethz.ch/isn/162591/CNAS_Bulletin_Storey_Slipping_Away.pdf,p.5.
2.2 制度設置層面:各當事國對南海爭端解決機制的要求不同
“準則”的爭端解決機制條款與法律約束力爭議存在內在聯系,二者均為各當事國的主要爭議。“準則”爭端解決機制條款的目的不在于解決領土主權與海洋劃界爭端,而在于處理“準則”解釋與適用過程中產生的爭議。無論是對待“準則”爭端解決機制條款,還是長期以來的南海爭端解決,中國始終堅持國家間的爭端應由直接當事方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并反復強調不接受任何訴諸第三方爭端解決方式及強加于中國的解決方案。此外,賦予“準則”文件整體以法律約束力將意味著賦予爭端解決機制條款以法律約束力,由此將進一步引發涉及南海的爭端被濫訴諸國際司法途徑的可能性。
東盟國家對爭端解決機制條款的提議與中國存在區別。特別是越南在“準則”草案中提議,“根據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解決所有領土與管轄權及海洋劃界爭議”。當通過談判、磋商無法解決爭端時,越南主張利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的爭端解決機制。越南還強調“準則”中的任何規定不得排除各當事國合意選取《聯合國憲章》第33(1)條中規定的爭端解決方式。如果上述提議被采納,則“準則”適用的爭端仍存在被濫訴諸國際司法途徑的可能性,使我國在南海維權中陷入困境與被動局面。綜上,我國與東盟國家對南海爭端解決機制的不同要求與不同偏好是引發法律約束力爭議的重要因素。
然而,爭端解決機制條款存在調和的可能性。中國與東盟國家間有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成功實踐。中越北部灣劃界談判經過幾代人三階段前后27年的努力,最終根據國際法與國家實踐,適用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結合北部灣的實際情況,公平合理地完成了海域劃界與漁業資源安排。兩國于2000年12月15日簽署領海、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劃界協定及漁業協定。這為我國與東盟國家解決南海爭端積累了寶貴經驗,①“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情況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0年12 月25日,https:/ /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t145558.shtml。也充分展現出我國與東盟國家有能力、有智慧通過友好協商解決海洋爭端,為未來的南海海洋劃界談判奠定了前期基礎。②張琪悅:“新中國成立70 年來中國海洋法律外交實踐與能力提升”,《理論月刊》,2019年第10期,第15頁。這一事例也表明,中國與東盟國家存在以政治途徑解決爭端的傳統,能夠成為“準則”爭端解決機制條款達成一致的基礎。
同時,有大量的國際實踐表明,領土主權與海洋爭端大多最終是通過爭端各當事國直接談判或磋商的政治途徑解決。國際仲裁或國際司法僅為當事方之間直接談判提供必要的幫助。而且,“準則”草案在實質磋商階段仍未明確將訴諸國際司法途徑納入爭端解決條款。盡管當事國的提議不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爭端解決方式的選擇在各當事國均同意的前提下才有效。由此,各當事國對爭端解決機制的不同要求雖然被視為影響“準則”法律約束力爭議的重要因素,但不能成為決定因素。③Mark J.Valencia,“The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Significant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for ASEAN”,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September 28,2018.http:/ /en.nanhai.org.cn/index/research/paper_c/id/199.html.
2.3 外交策略層面:各當事國在對外交往中選擇工具的傾向不同
東盟國家與中國力量對比懸殊,缺乏必要的實力支撐和外交資源,在政治談判與外交博弈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④韋民著:《小國與國際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頁。由此,東盟國家對南海局勢的發展變化更為敏感,南海地區無政府與無序狀態對其也有更多影響。這決定著東盟國家更注重運用“基于法治的多邊機制”維持南海秩序與解決爭端。⑤Jim Mclay,“Making a Difference:The Role of a Small State at the United Nations”, Juniata Voices,April 27,2011,https:/ /www.juniata.edu/offices/juniata-voices/media/mclay-making-a-dif.pdf,p.123.面對南海潛在的安全問題,東盟國家更傾向于依靠國際規范和國際規則,①Robert G Patman,“New Zealand’s Place in the World”,in Raymond Miller ed., New Zealan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Victoria,Austral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85-103.倡導與發揮國際道德的作用,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這體現出東盟國家小國外交的典型行為模式——發揮多邊外交的作用,通過“準則”構建穩定的多邊機制和區域性規則。
相反,中國作為地區大國,更傾向于通過外交談判磋商等政治途徑解決爭端。雖然中國也受益于多邊機制與國際法治,并將其納入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南海問題上,“準則”試圖將相關爭議納入國際規則框架,這將使中國無法最大限度地發揮綜合國力與外交優勢。因此,中國與東盟在對外交往中選擇工具傾向性的差異,導致雙方對于“準則”的依賴程度不同,對“準則”法律約束力的預期存在差異。
三、“準則”法律約束力之爭的國際法問題
3.1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規范的形式問題
(1)行為準則的文本形式在國際法上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尚無定論,其實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程序要件的影響
第一,行為準則種類多樣、差異性大、界限模糊,難以通過定義涵蓋各種情形。《馬普國際公法百科全書》將其描述為“包含一系列書面規則和原則的規范性工具,可以監管具體或普遍領域的問題。但通常聚焦于特定行為,意在達成一個共同的行為標準”。行為準則涵蓋面廣,適用于描述具有上述特征的無約束力的文件,包括原則、宣言、指導方針等。②Jürgen Friedrich,“Codes of Conduct”,paras.1-2,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 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我國學者周士新在2015年提出,無論是1992 年《東盟南海宣言》、2002 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還是2011年中國與東盟國家達成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指導方針》,都屬于廣義的“行為準則”,并且這些規則的約束力都不強。③周士新:“關于‘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前景的分析”,《太平洋學報》,2015年第3期,第22 頁。
盡管在國際法理論中,一般情況下行為準則被視為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但由于行為準則通常能夠反映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或將各國自愿遵守的、具有約束力的規則納入一個總體上不具有約束力的文件中,④Jürgen Friedrich,“Codes of Conduct”,paras.1-2,16,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這意味著行為準則可能同時兼具有約束力與無約束力的混合性質。因此,對于行為準則性質的判斷應當結合具體條款進行具體分析。
第二,無論是文件的形式還是名稱,都不能成為確定當事國之間已達成文件的地位與性質的依據。⑤Philippe Gautier,“Non-Binding Agreement”,para.12,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條(甲)規定:“稱‘條約’者,謂國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亦不論其特定名稱如何。”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數據庫,1969年5月23日通過,1980年1月27日生效,http:/ /treaty.mfa.gov.cn/Treaty/web/detail1.jsp?objid =1531876068204。由此,參照適用以上條款,“準則”作為國家間締結的以國際法為依據的國際書面協定,不應以特定名稱作為判斷其性質的依據。
這一觀點在大量國際司法判例中得以證實。國際法院在1978年“愛琴海大陸架案”判決中指明,一項文件是否構成協定,不能僅憑借該行為或事項的文件形式,而是根本上取決于文件所處理的行為或事項的性質。⑦ICJ,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Greece v.Turkey),Judgment (19 December 1978),p. 40,para.96.國際法院在2002年“喀麥隆訴尼日利亞陸地與海洋邊界案”判決中指出,兩國元首簽署的《馬魯阿宣言》(The Maroua Declaration)雖然以“宣言”命名,但該宣言中的實質內容構成條約法管轄的邊界條約,屬于兩國間的書面協定。⑧ICJ,Case Concerning the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ron v.Nigeria: Equatorial G 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 (10 October 2002),p.130,para.263.上述案例能夠證明,文件名稱不會成為影響其效力的決定性因素,而是應當以文件的實質內容作為判斷標準。2001年也有越南學者指出,在現實情況下,“準則”的名稱可能只是隱喻,而非使用的法律術語,①See Kriangsak Kittichaisaree,“A Code of Conduct for Hum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32,Issue.2,2001,pp.131-132.并且名稱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若完全依賴國際法理論對行為準則文件形式與名稱的法律約束力做出判斷,難免有失偏頗。
第三,“準則”的實施效果與發揮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程序要件的影響,應當考慮起草主體、起草場所、生效條件等情況。②Jürgen Friedrich,“Codes of Conduct”,para.15,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 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首先,“準則”起草的主體具有適格性。“準則”由各國外交部及相關政府部門官員磋商,而后由各國外交部長或國家領導人通過。各國家代表始終具有代表權,并在相應的職權范圍內履行職責。根據國際法院在2006年“剛果境內武裝活動案”判決中的表述,外交代表的行為可以視為代表國家,其行為對國家具有約束力。③ICJ,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Rwanda),Judgment(3 February 2006),p.25,paras.46-47.因此,各國外交代表簽署“準則”的行為能夠對該國家產生約束力。其次,“準則”起草場所具有合法性與權威性。“中國與東盟國家在中國—東盟落實《宣言》高官會與聯合工作組會上開展磋商,在中國—東盟(10+1)外長會、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通過與簽署案文。再次,“準則”履行簽署或批準程序后生效。參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十二條與第十四條的規定,“根據具體情形,簽署或批準接受表示承受條約約束之同意。”根據國際法院在1994年“卡塔爾訴巴林案”的判決,在雙方外交部長簽署文件后,不支持巴林外交部長事后表示其意圖僅為訂立“政治諒解備忘錄”而不是訂立一項國際協定。④ICJ,Case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 ahrain (Qatar v. Bahrain),Judgment(1 July 1994),p.14,para.27.因此,國際法院認為,雙方在簽署文件后應當受到雙邊協議的約束。同理,根據國際法院在2017年“索馬里訴肯尼亞海域劃界案”中對“生效的規定”的分析,通過檢驗索馬里與肯尼亞達成備忘錄的實際條款,國際法院認定備忘錄作為書面文件,記錄雙方在某些方面達成的協議,受國際法的約束。在備忘錄中加入生效的規定,表明該文件具有約束力。⑤ICJ,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Somalia v.Kenya), Judgment (2 February 2017),p.16,para.24.綜上可知,一份文件在滿足程序要件的前提下,能夠對各當事方產生約束力。文件的形式與名稱并非判斷標準。
(2)選取“準則”的文本形式具有比較優勢與合理性
中國與東盟國家選取行為準則的文本形式,雖然表面上削弱了“準則”的法律約束力,但行為準則與條約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與合理性。
在制定程序方面,行為準則相對簡單,更容易達成一致。而條約起草的速度較慢、效率較低,具有高度政治化、精細化的制定過程和繁瑣的批準程序,存在批準國數量少的風險,也具有靈活性較為欠缺、不容易適應國際實踐新發展等特點。⑥Jürgen Friedrich,“Codes of Conduct”,para.37,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 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相比之下,采取行為準則的文本形式有利于克服政治僵局,具有更高的接受度;更容易根據南海地區情勢的新變化,及時調整文本內容,從而適應當前形勢下南海危機管控與開展合作的需要。伊恩·斯托里早在2013年就指出,盡管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準則”更有助于改善南海局勢,但似乎更難達成協議。⑦Ian Storey,“Slipping Away?A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Eludes Diplomatic Efforts”,i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East and South C hina Seas B ulletin,No.11,March 20,2013,http:/ /www.files.ethz.ch/isn/162591/CNAS_ Bulletin_ Storey _Slipping_Away.pdf.這也是2002 年各國選擇先達成形式上不明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宣言》,以此作為“準則”的階段性成果與前期基礎的重要原因。從國家意愿來看,各國不愿意在爭端尚未明朗的情況下,針對敏感的主權與政治性問題制定法律位階較高、約束力較強的法律規范。再次,與條約不同,鑒于“準則”的法律約束力仍未確定,“準則”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是開放的,能夠給予各當事國官方與學者更多的討論機會,有助于通過官方磋商與學術探討逐漸積累共識,達成各國均能接受的結果。
3.2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規范的實質問題
(1)“準則”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取決于是否有明確意圖為各當事國創設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
國際文件的具體內容與通過文件時的具體情況能夠證明該文件是否有為當事方創設國際法上權利與義務的明確意圖。這是判斷文件是否具有約束力的關鍵。①See Thomas Buergenthal and Sean D.Murphy, P ublic Inter?national Law,3rd edn,St.Paul,Minn,West Group,2002,pp.102-103;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Oppenheim’ s International Law,9th edn,Vol.1,Parts 2 to 4,London and New York: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1996,pp.1199-1204.國際法院在1994年“卡塔爾和巴林海洋劃界和領土問題案”判決中指出,即便是會議記錄(the Minutes),如果其中列舉了各方已經同意的承諾,以此為各方創設了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則會議記錄構成國際協定,而不僅僅是對各方討論情況的敘述及對合意與分歧的總結。②ICJ,Case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 ahrain (Qatar v. Bahrain),Judgment(1 July 1994),pp.13-14,paras.25,30.即使國際協定并未以文字形式表述,例如以口頭協定、單方面聲明等形式呈現,也可以為各當事國確立有約束力的權利和義務。這一論斷的原因在于,約束力并不來源于形式,而來源于對于相關事項確立權利義務關系的意圖。③中國國際法學會著:《南海仲裁案裁決之批評》,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頁。同理,國際法院在1961年“柏威夏寺案”管轄權判決中稱,通常情況下,國際法注重強調各當事國的意圖而非特定的形式。各當事國可自由選擇愿意采取的形式,只要能從中清晰辨別意圖即可。④ICJ,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Thailand), Judgment (26 May 1961),p.18.相反,若一份國際文件無意為當事國創造權利和義務,并且違反其規定不產生國家責任,則屬于沒有約束力的協議。該文件可能用來表達純粹道德或政治承諾,有別于嚴格的法律規則。⑤Philippe Gautier,“Non-Binding Agreement”,para.14,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除分析是否有明確權利與義務的意圖外,國際法院為判斷文件的法律約束力還設立了另一套標準:結合文件實際用語、起草與簽署的具體情況、各方嗣后行為進行綜合分析。國際法院在1978年“愛琴海大陸架案”判決中表明,一項文件是否構成協定,根本上取決于文件所處理的行為或事務的性質;而確定行為或事務的真實性質,必須首先考慮文件實際用語和起草文件的具體情形。⑥ICJ,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Greece v.Turkey),Judgment (19 December 1978),p. 40,para.96.國際法院在1974年“法國核試驗案”的判決、1978年“愛琴海大陸架案”與羅伯特·詹寧斯(Robert Jennings)在《奧本海國際法》著述中都做出類似表述,認為需要根據當事方的意圖、文件所載的條款、使用的文字判斷其約束力。⑦ICJ,Nuclear Tests Case(Australia v.France),Judgment(20 December 1974),p.18,paras.44-45;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9th edn,Vol.1,Parts 2 to 4,London and New York: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1996,pp.1188-1189.國際法院在1994 年“卡塔爾訴巴林案”中再次引用與強調這一標準,即確定協議是否具有約束力性質,國際法院必須考慮其實際用語和起草的具體情況。⑧ICJ,Case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 ahrain (Qatar v. Bahrain),Judgment(1 July 1994),pp.12-13,para.23.盡管這套標準與“是否有明確權利與義務的意圖”提煉的關鍵詞不同,但其實際內涵與判斷標準具有相似性。各當事國的真實意圖能夠根據其在文件起草與簽署過程中的表現、文件使用的實際用語、嗣后行為做出推斷。這兩種判斷方式已經在多個案件中得以運用,獲得各方認可,⑨ICJ,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Greece v.Turkey),Judgment (19 December 1978),p.40,para.96;ICJ,C ase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Qatar v. Bahrain),Judgment (1 July 1994),pp.12-14,paras.23-29;ICJ,Case Concerning the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ron v. Nigeria:Equatorial Guinea Intervening), Judgment (10 October 2002),pp.128-130,paras.262-263.逐漸成為判斷一份文件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共識性標準。上述兩套標準能夠相互印證、融會貫通、補充適用。
當前,“準則”案文仍處于第二輪審讀過程中,尚未通過官方渠道公開。但根據《宣言》文本、國外披露的“準則”框架與“準則”草案、中外學者對“準則”草案的評述可知,“準則”意圖在《宣言》的基礎上,更加詳細明確地賦予各方義務,如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其他普遍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特別是尊重國家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他國內政。“準則”將要求各方承諾全面有效地執行《宣言》與《落實<宣言>指導方針》。在具體行為方面,“準則”將要求各方采取自我限制,促進相互信任與信心,預防與管理意外事故,確保海上航行與飛越安全和自由,落實促進海上務實合作義務,為和平解決爭端創造良好的環境。“準則”也將引發各當事國的嗣后義務,如設置必要的執行監督機制,定期審查“準則”的內容與實施情況,遵守“準則”的生效、失效及退出條款。“準則”也將明確賦予各方權利,如從事海洋科學研究、行使航行與飛越自由、在特定海域勘探開發自然資源與捕魚、打擊海上犯罪、保護海洋環境。①Carl Thayer,“A Closer Look at the ASEAN-China Single Draf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The Diplomat,August 03,2018,https:/ /thediplomat.com/2018/08/a-closer-look-at-theasean-china-single-draft-south-china-sea-code-of-conduct/。綜上,“準則”具有明確意圖為各當事國創設權利與義務,符合在國際法上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協定的標準,能夠對各當事方在南海的行為產生約束力。
(2)即使“準則”文本整體的法律約束力尚未明確,其中反映既有國際法規則的條款也具有明確的法律約束力
即使“準則”磋商可能不會嚴格依照條約的締結程序,并且“準則”最終磋商結果不會以條約的形式呈現,但“準則”中必將包含屬于國際法淵源的內容。這些內容明確具有法律約束力,各當事國應當遵守。《馬普國際公法百科全書》也指明,行為準則通常包含明確的與具體的規范,部分規范可視為對現行國際規范的具體化,及對國際習慣的反映。由于行為準則體現出普遍接受與廣泛適用的共識,因此能夠為各國的行為產生法律義務。②Jürgen Friedrich,“Codes of Conduct”,paras.21,25,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準則”中直接反映現行國際法規則的條款,均能視為“準則”對現行國際法相關原則、規則的再次確認,成為既有國際條約在“準則”中的具體適用。例如,反映國際強行法規范的“禁止使用武力”,③Michael Wood,“Use of Force,Prohibition of Threat”,para.12,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引自國際公約與條約內容的“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它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簽署的國際文件所規定的“尊重航行及飛越自由,維護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保護海洋環境與海洋生物多樣性”、“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開展海上搜尋與救助”、“打擊海上跨國犯罪”等。各當事國應當遵守并善意履行上述國際義務。
(3)即使“準則”部分條文不具有明確的法律約束力,也將對各當事國產生事實上的約束效果
盡管“準則”部分內容具有政治屬性,但不能否定這些條款也能夠產生實際的約束力。“準則”草案中多處使用了“承諾”這一表達,英文表述為“undertake”,屬于在一項協議中,各方承擔義務的表達。國際法院在2007年“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訴塞爾維亞和黑山關于適用《防止和懲治滅種罪公約》案”的判決中,將“承諾”一詞解釋為:“‘承諾’的一般含義是賦予一個真實的諾言,使自身受到約束,給予一個保證或承諾,表示同意或接受一項義務”。“‘承諾’作為在條約中經常使用的詞語,規定了締約方的義務,并不僅僅用來提倡或表示某種目標”。④ICJ,Case Concerning Application of the C 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 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Bosnia and Herze?govina v.Serbia and Montenegro),Judgment (26 February 2007),p.72,para.162.“承諾”具有“諾言、保證、負責”的含義。“準則”的通過與簽署能夠表達國家同意接受“準則”的約束,同意承諾履行“準則”的各項條款。以上含義與“準則”條款本身的性質并無直接聯系。
各當事國應當善意履行在“準則”中的各項承諾與義務,遵守誠實信用、有約必守、禁止反言的要求。國際法院在1972 年“澳大利亞與新西蘭訴法國核試驗案”判決中均強調,誠實信用原則是創設和履行法律義務的一項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也是條約法中“有約必守”規則的基礎。各當事國有權要求由“準則”產生的義務得到遵守,①ICJ,Nuclear Test Case(Australia v.France),Judgment (20 December 1974),p.268,para. 46;ICJ,Nuclear Test Case(New Zeal?and v.France), Judgment (20 December 1874),p.20,para.49.避免在后續行動中采取與“準則”規定相悖的行為,以此維系彼此間簽署“準則”這一先前行為所產生的合理期待與信賴利益,②Thomas Cottier, J?rg Paul Müller,“Estoppel”,para.1,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有助于實現“準則”建立信心與信任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約必守”規則反映了基本的、普遍同意的原則,適用于包括條約在內的所有法律關系。③Anthony Aust,“Pacta Sunt Servanda”,para.1,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 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因此,盡管“準則”不構成條約標準,各當事國也應當恪守“有約必守”的規則。即使部分條文不具有明確的法律約束力,但因中國與東盟、中國與東盟國家、東盟成員國之間簽署與實施的多邊或雙邊文件得到相互印證與加強,因此能夠對各當事國在事實上產生約束的效果。綜上,“準則”中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條文也同樣對各當事國產生一定的約束力與法律影響。
四、結語
綜合分析中國與東盟國家立場主張,各當事國對“準則”的法律約束力問題已達成部分共識,認為“準則”應當實質有效,能夠對各方行為產生約束;分歧在于“準則”的法律約束力是否表現為法律強制力,以及是否能夠訴諸國際司法途徑解決爭議。各當事國對于“準則”法律約束力的分歧不在于約束的程度,而在于約束的具體事項與方式。如何在鞏固共識的基礎上消除分歧,是中國與東盟國家未來需要面臨的重要問題。
“準則”法律約束力爭議的解決路徑有三。第一,明確賦予“準則”法律約束力,使“準則”的內容與形式向條約方向靠攏。這一路徑的優勢在于,能夠確保“準則”有效約束各國行為,避免各方在“準則”磋商中耗費大量的外交成本之后,仍無益于南海和平穩定;劣勢在于,“準則”可能成為個別國家限制他國在南海從事正當合法行為的工具。此外,一旦“準則”明確具有法律約束力,將引發執行監督機制、爭端解決機制等條款的細化規定,不僅增加磋商中的工作量,而且為“準則”的最終達成增加難度。
第二,明確不賦予“準則”法律約束力,使“準則”成為《宣言》的升級版,僅具有政治屬性。這一路徑的優勢在于,能夠促進“準則”的內容與形式更加靈活,能夠減少各當事國對“準則”案文內容的爭議,更容易達成共識,能夠提升磋商效率、加快制定進度,使“準則”盡早發揮作用;劣勢在于,盡管“準則”的“基本任務”與“最后條款”更加詳盡完備,但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宣言》缺乏法律約束力而導致執行不力的問題。明確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準則”也對各當事國自覺遵守規則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準則”這一路徑缺乏合理性與現實性。
第三,不在條文中明確規定“準則”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但通過其他途徑賦予“準則”具體條款以法律約束力。根據上文分析可知,“準則”中明確反映既有國際法規則,即引自中國與東盟既有文件中的規則應當明確具有法律約束力;各當事國經磋商已經達成共識的內容可以具有法律約束力;各當事國意見存在較大分歧、在實際用語中做出模糊化處理、在磋商中做出較大妥協,從而致使真實意圖受損、未正當行使起草簽署程序及履行嗣后義務、可能非法限制中國在南海正當合法的行為、純粹的倡議性條款,不應當具有法律約束力,原因在于以上類別的條文不滿足國際法上對具有法律約束力文件的程序與實體內容的規定。這一路徑的優勢在于,避免對“準則”法律約束力問題一概而論,將對“準則”文件整體法律約束力的爭議轉化為對具體規則的細節做出分析,區別對待不同條款的法律約束力問題。而劣勢在于,未能從“準則”文件整體角度對爭議問題下定論,增加對具體條款分析論證的成本。
為解決“準則”法律約束力爭議,中國與東盟國家應當始終以南海地區的整體利益為重,適當顧及彼此合理的利益主張,積累共識、減少分歧,推動“準則”早日達成;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增強“準則”的適用性與有效性;盡最大可能地激發當事國的善意,促使其自覺遵守“準則”義務。各方不應將“準則”僅作為限制與約束各當事國在南海行為的工具,而應當更加注重發揮“準則”的規則導向作用,引導各當事國自覺履行“準則”中的承諾,主動承擔維護南海區域秩序的義務,使“準則”有效發揮管控南海危機、建立信心信任、推進務實合作、有效緩解南海爭端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