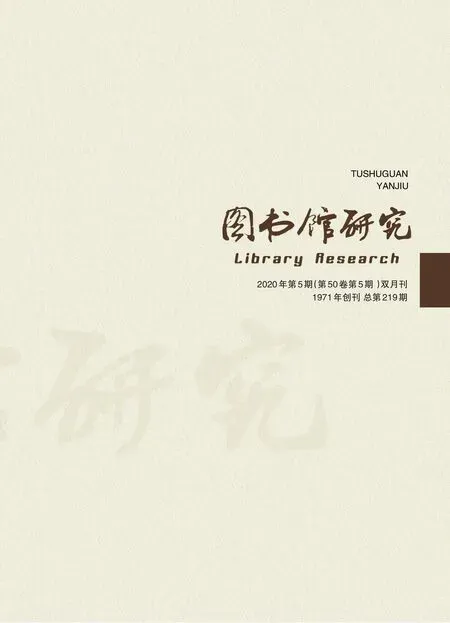試論公共圖書館文創產業誤區及未來發展方向
鄧 輝
(陜西省圖書館,陜西 西安 710061)
2016 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文化部等多部門《關于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若干意見的通知》[1]。通知鼓勵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文化單位開展文創產業,并力爭到2020年逐步形成形式多樣、富有競爭力的文化創意產品體系,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不斷升級的文化需求。2017年1月文化部、國家文物局確定或備案了包括37 家公共圖書館在內的154 文化創意產品試點單位,囊括了國家圖書館和全國大部分省級(副省級)圖書館[2]。近年來隨著財政過上“緊日子”,多地公共圖書館經費被縮減,此時文創工作對圖書館服務的造血功能就顯得愈發重要。然而數年過去,雖然主管部門和圖書館對文創工作十分重視,但各地圖書館文創試點實際效果卻不盡人意。
1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業困局
首先,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線上銷售慘淡,對此通過管窺國家圖書館文創產品線上銷售狀況便可略知一二。國國家圖書館對文創產業的認知很早,其官方淘寶店“國圖旺旺”于2016 年便已上線,比故宮博物院官方淘寶店還早2個月上線。可是張曉陽等人對比國家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淘寶官方店2018 年7 月文創產品銷售數據,發現國家圖書館淘寶店粉絲數只有0.2萬人,而故宮博物院卻高達108萬,同時國家圖書館淘寶店月銷量只有區區15 筆左右,而故宮博物院淘寶店卻近2.2 萬筆,其中差距不言而喻[3]。國家圖書館有著比其他公共圖書館更多的資金與人員支持,更具影響力的IP,以及更為靈敏的市場嗅覺,然而文創銷售依然不佳,其他公共館文創產品銷售可想而知。
其次,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的實體店發展亦不容樂觀,且浪費了寶貴的場地空間。各地公共圖書館往往將圖書館入口兩側等位置最好的場地劃給了文創店鋪,以吸引讀者進店消費。然而,筆者實地調研了南京圖書館、陜西省圖書館等多家省館,發現各館文創店鋪每日顧客寥寥,實際運營門可羅雀。
最后,公共圖書館過往文創產業改革措施效果欠佳。例如,2017 年9 月文化部倡議建立了“全國圖書館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聯盟”,塑造更強的文創產品銷售、研發和品牌運營網絡,并于2019年初聯盟主導開展了“品牌發展計劃”[4],然而實際效果依然欠佳。全國圖書館文創聯盟雖然整合了全國公共館的文創資源,其在淘寶的官方旗艦店近一年來粉絲數也只有區區的0.8萬人左右。2019 年10 月該店產品銷售最多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芥子園畫傳創意筆記本”也只有110筆成交量。由此估計該店年銷售額不會超過20萬,相對于文創產業的投資額,其凈利潤可以忽略不計。
2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業困局的原因
雖然以往很多研究都注意到現階段公共圖書館文創產業的困局,但研究者往往把原因總結為制度、人才和創意不足等多個方面原因[5]。可本文認為現階段圖書館文創產業困局的核心原因,在于圖書館業界和學界都在一味地照搬博物館文創產業思路。這導致現階段圖書館文創產品既不適合自身特點,還受到產品市場規模和競爭對手的天然限制;而相對于這些因素,激勵制度、人才隊伍等因素則都屬于細枝末節。
2.1 圖書館文創研發過度模仿博物館
本輪公共文化單位的文創熱潮始于故宮原院長單霽翔對故宮博物院一系列成功的改革。此后,文化與旅游部等相關部委意識到相關文創產品消費潛力后,便決定在全國推廣相關經驗,所以圖書館業界和學界在思考文創產業發展時,都不免會借鑒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思路[6][7]。因此,現階段圖書館和博物館文創產品研發思路高度類似,產品主要集中在日用品(杯子、手提袋)、裝飾品(手鏈、鑰匙鏈)、文具類(筆記本、鉛筆)、復制品(古籍)五大類為主,而創意主要表現在通過將各類館藏以印刷的形式植入產品,而只有少量圖書館提供體驗式服務[8]。
由于研發思路和產品類似,圖書館和博物館在現有文創市場上實際上是競爭關系,然而以往學者采用SWOT 分析圖書館文創產業發展前景時,忽略了博物館實際上是圖書館文創產業最顯著的外部威脅[9],因此造成各類政策建議都沒有關注圖書館和博物館文創產品的區分度。
2.2 文創制造業、零售業屬于“夕陽產業”
有圖書館學學者總結過往文創產品的定義后,指出文創產品包含3點特征,分別是“①文創產品的最終形態包括產品物質產品和文化創意內容。②文化創意內容是設計師依靠智慧、天賦和技巧對文化內涵的創意展示。③文化產品的核心是所蘊含的文化符號和創意內容,以滿足人們精神文化的需求”[10]。圖書館學界對文創產品強調物質載體,實際上是深受博物館文創產品研發思路影響的表現,并不符合國家產業(品)分類。
實際上,由于文化創意和產品無法割裂,創意的載體也形式多樣,因此文化產品并不強調物質載體。國家統計局《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8)》是國家對“文化產品”的權威定義。根據國家統計局對“文化產品”的定義,文化產品包括文化類貨物和文化類服務,并在細則中指出文化類教育培訓、會展等文化服務都屬于文化產品。文創產品本質上是強調具有創意的文化產品,而文化服務屬于文化產品,因此包含大量創意的文化類服務也屬于文創產品。
現階段圖書館實際上是在發展“文創貨物” 相關產業,從事文化制造業和文化零售業,而文化制造業和文化零售(批發)業屬于夕陽產品,消費者需求非常有限。根據2018 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2017年中國規模以上文化制造業實現營業利潤2 784 億,從業人員人均凈利潤5.72 萬元,同年限額以上文化零售(批發)企業實現營業利潤581億,從業人員人均凈利潤10.6萬元。作為對比,2017 年中國規模以上文化服務企業實現營業利潤4 448 億,從業人員人均凈利潤13.2萬元。人均利率是文化制造業的2.3 倍,文化零售(批發)的1.26 倍。因此,文化制造業和零售(批發)業市場規模有限,必然限制圖書館文創產業的發展和利潤率。
2.3 圖書館從事文創制造業、零售業的劣勢
在認識到圖書館、博物館文創市場的競爭后,筆者通過SWOT模型重新分析圖書館在文創制造業、零售業市場的劣勢。博物館主要工作是征集、典藏、陳列和研究各類文化物,并為公眾提供相關知識和教育;而圖書館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收藏文獻資料以供人閱覽,也同時為公眾提供相關知識和教育。總之,博物館的主要工作是圍繞文物,而圖書館的主要工作則是圍繞文獻。
圖書館館藏特點限制圖書館文創貨物的研發、社會力量參與和市場規模。博物館石器、陶器、銅器、金銀器、瓷器、漆器、玉器、工藝品、書畫等相關館藏資源遠超圖書館。這些文物的精美元素更容易植入文創貨物。與之相對,圖書館館藏以文獻為主,鎮館之寶往往是各類古籍,很難被植入文創貨物。同時,雖然博物館、圖書館知名藏品往往都是孤品,但古籍更多是“孤版”,而金石、瓷器、書畫等文物則形式與內容上都屬于孤品,所以博物館藏品更容易與社會力量合作。最后,博物館藏品的知名度、地域性和實用性,造成博物館文創貨物的市場規模必然高于圖書館藏品。
圖書館讀者年到館數量、重復到館人數、讀者集中度、消費能力等限制圖書館文創貨物的銷售。首先,博物館年接待人數高于圖書館:根據2018 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2017 年全國公共圖書館接待讀者7.4 億人次(總流通人次),而同年博物館接待9.7 億人次。同時,文化貨物屬于耐用品,重復到館人數會影響銷售量:博物館服務人群中游客比重較高,重復參觀人數少,而圖書館讀者以本地百姓居多,重復到館人數多。最后,博物館多處于大城市,參觀人群集中、消費能力強,而圖書館讀者流量相對分散,消費能力也較差。2017年縣(區)級圖書館接待了超過全國50%以上的讀者。
總之,由于圖書館文創貨物制造和零售市場并不存在優勢,因此借鑒英國[11]、美國[12]、澳大利亞[13]等地圖書館文創經驗,大力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紀念品[14],依然不會對公共圖書館擺脫現有文創產業困境有所幫助。
3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業的有償文化服務可行性
圖書館文創產業發展的方向是以豐富的讀者數據為基礎,向公眾提供精準化、系統化、多層次的培訓、講座和會展等有償文化服務,相關服務包括文藝演出、作品陳列、藝術展覽、文化培訓、圖書發布、幼兒托育、閱讀障礙癥干預(治療)等。
3.1 公共圖書館有償服務的法律基礎
國內外法規對圖書館從事有償文化服務都留有政策空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保障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國家允許公益性文化單位向公眾提供“優惠的文藝演出、陳列展覽、電影電視、藝術培訓等”服務。可見國內法律允許公共圖書館從事一定程度的有償文化服務。同樣,國外很多公共圖書館法規及實施細則都規定,圖書館可以從事教育培訓、會展等有償服務,并收取合理的費用。比如,《韓國圖書館法實施令》第十九條規定第四點明示“圖書館培訓及教育手續費”,澳大利亞圖書館法明確規定圖書館有償延伸服務包括文化教育服務、專業進修服務等[15]。不過羅兆英在總結全國12家公共圖書館管理條例時,發現條文中有償服務還是以文獻復印、科技查新等傳統基礎服務為主[16],因此未來公共圖書館開展有償文化服務還有巨大的空間。
3.2 公共圖書館有償服務的優勢
雖然圖書館、博物館同為公眾提供知識和教育,但圖書館文化類服務更具優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7 年圖書館舉辦講座、展覽和培訓近16 萬次,而同期博物館舉辦展覽等活動只有2萬多次。因此,圖書館為公眾提供知識和教育的頻率與種類都遠超博物館,也具備更加豐富的經驗,并更受大眾的認可。
其次,圖書館服務范圍和人群相對博物館更廣,讀者對知識需求的層次更深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的頒布,圖書館總分館和社區圖書館工作加速推進[17][18],公共圖書館服務范圍不斷擴大,而博物館服務半徑相對較小。同時,圖書館讀者年齡段更加豐富,特別是青少年讀者、老年讀者較多,因此讀者對文化需求種類更廣。最后,圖書館讀者重復到館人數較多,這表明讀者對知識需求層次更深,也有更多教育培訓類文化服務需求。
最后,圖書館相對于博物館具有信息優勢。圖書館借閱系統保存了讀者大量借閱信息。這些信息可以反映讀者偏好[19]。新時期隨著“信用借書”服務的推廣,圖書館甚至可以通過信用信息獲得讀者消費能力等信息[20][21]。因此,圖書館可以將讀者的身份信息、借閱信息和消費(信用)信息結合,描繪出準確的用戶畫像,提高業務營銷精度[22]。
3.3 公共圖書館有償服務符合共贏原則
圖書館向讀者提供有償的付費文化服務,既可以拓展自己的服務內容,也可以滿足大眾的文化需求。現階段圖書館開展的許多精品文化服務往往供不應求。以大連圖書館白云書院國學培訓班為例。大連圖書館白云書院于2000 年8月創立,院舍700余平方米。學院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豐富大眾文化生活,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為宗旨,在每年寒暑期都會開設免費的國學義塾。近些年社會開始愈發重視傳統文化,大眾報名國學班熱情高漲,可是受制于圖書館場地限制,大連圖書館白云書院每次招生也只能在60人左右,學位供不應求。
顯然,全國各地有很多圖書館服務面臨和大連圖書館白云書院培訓班類似的困境。政府提供的資金根本無法滿足讀者更深層次的需求。圖書館通過有償服務的形式募得資金,聘用更多、更優質的師資,租用更大的教學場地,不僅可以滿足公眾、社會需求,也可以提升圖書館服務質量。
4 策略和建議
4.1 公共圖書館積極開展有償服務融入時代
近年來“知識付費”產業興起,表明新時期大眾對知識有著更加精準化和多樣化的需要。傳統的圖書館功能以知識(文獻)整理、組織和傳播為中心,更多扮演知識中介者的角色,很少作為知識生產者向讀者提供知識。因此葉繼元認為在知識付費時代,圖書館面臨著職業主體性消解和中介性消解雙重挑戰[23]。
知識付費對公共圖書館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知識付費表明公眾在意的并不是知識是否有償,關鍵在于知識是否有價值。上文分析表明,公共圖書館在提高文創服務方面有著天然優勢。因此,未來圖書館應該通過打造各類有償文化服務,為讀者提供更加深層次、精準化的文化服務,讓公共圖書館成為讀者和知識間的橋梁,并讓自身更好地融入付費知識時代,實現服務的轉型[24]。
4.2 建立圖書館有償文化服務負面清單制度
首先,過往法規對于圖書館可從事的有償服務規定過于模糊。《公共文化保障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公共文化設施開展與功能、用途不符的服務活動”要承擔法律責任,《公共圖書館法》第二十九條也規定“公共圖書館的設施設備場地不得用于與其服務無關的商業經營活動”,而“與其服務無關”的規定過于模糊,會使得圖書館從事有償服務面臨不確定性。
其次,近些年文化和旅游部發布的《關于在文化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25]等多項文件鼓勵營利性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建設,但相關合作充滿風險。因為在讀者和公眾看來,圖書館在和社會資本合作時,組織相關講座、展覽、培訓,無形中就是給社會資本信譽背書。因此,管理部門應該明確圖書館禁止和各類養生、醫療、投資等類社會資本開展任何合作。
近些年政府力推“負面清單”制度,通過減少投資門檻,提高市場活力,相關措施同樣適用于公共文化領域[26-27]。從減少政策不確定性和不必要的信用背書的角度看,本文認為主管部門應當以負面清單的法律細則形式,早日明確圖書館不可從事服務的邊界,這樣不僅可以從“法無禁止即可為”的角度鼓勵圖書館開展適合自身的有償文化服務,也可以規范圖書館現有服務的范圍。
4.3 建立圖書館有償服務所得公示制度
圖書館需要明確有償文化服務收益用途,并對資金的使用進行公示。公益性、非營利性是公共圖書館最突出的屬性,向大眾提供優質文化服務是公共圖書館的根本職能。《公共文化保障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公共文化單位“收取的費用,應當用于公共文化設施的維護、管理和事業發展,不得挪作他用”。同樣,美國《新澤西州圖書館法》等相關法規明確規定圖書館收入應該用于圖書館建設[28]。
因此,本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圖書館文化服務的主要收益應該主要用于人員激勵、改善設施、文獻采購、設備更新等方面。同時,《公共文化保障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政府和公共文化單位應該主動接受公眾、媒體的監督。因此,為了限制主管部門和圖書館將有償服務所得挪為他用,影響公共圖書館公益屬性,公共圖書館應該建立有償服務所得公示制度,提高公眾和圖書館理事會的知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