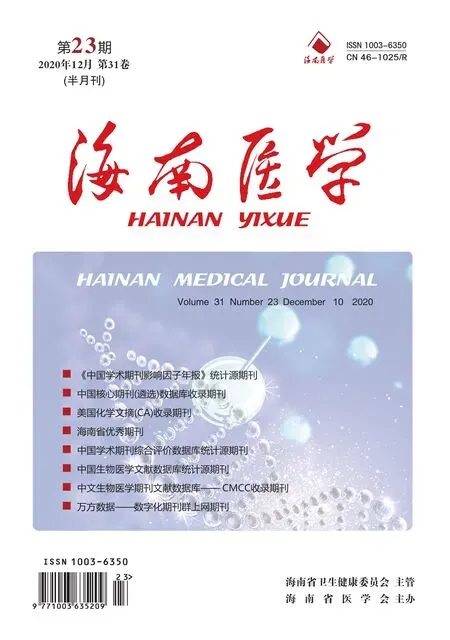MicroRNA與冠脈支架內再狹窄的研究新進展
包乙君 綜述 趙然尊 審校
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心內科,貴州 遵義 563000
近年來冠心病嚴重威脅了人類的健康,已成為世界各國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冠心病主要治療方案包括:改變生活方式、藥物干預和血管重建術。其中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是主要的血運重建治療策略。但PCI術后支架內再狹窄是影響遠期療效的最重要并發癥之一。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BMS)的使用消除了部分有利于形成再狹窄的因素,將再狹窄發生率從50%降低到20%~30%[1];藥物洗脫支架(drug eluting stent,DES)時代的到來將再狹窄率進一步降低至10%以下[2]。目前,對于再狹窄機制尚未完全闡明,支架置入后新生內膜形成和新生動脈粥樣硬化形成是支架內再狹窄最重要機制。近年來研究顯示,microRNAs可能通過多種途徑或機制參與新生內膜形成、炎癥反應以及新生動脈粥樣硬化形成,進而涉及再狹窄。本文通過文獻復習綜述了microRNAs 在冠脈支架內再狹窄的發生機制以及防治等方面的研究新進展。
1 MicroRNAs概述
MicroRNAs (miRNAs)是一類內源性、小的非編碼RNA,長度為19~25 個核苷酸,通過與靶信使RNA(miRNAs)的3'-非翻譯區(UTR)結合,在轉錄后水平調控各種基因表達。1993 年第一個miRNA 即Lin-4 在秀麗隱桿線蟲中被發現[3]。2002 年發布了主要miRNAs 數據庫,包含來自五個物種的218 個microRNAs基因座,且總數仍持續增加[4]。最新的miRBase 序列數據庫包含38 589 個條目,來自271 個生物的發夾前體microRNAs,這些發夾前體產生總共48 860 個不同的成熟microRNAs序列[5]。已知MicroRNAs參與調節心臟的多種疾病包括:心血管系統的發育、動脈粥樣硬化、高血壓、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療再狹窄等[6]。
2 冠脈支架術后再狹窄的病理生理機制
冠脈支架術后再狹窄(in-stent restenosis,ISR)是指支架內全程和或支架兩端5 mm 節段內的管腔丟失,導致管腔狹窄程度≥50%。而臨床定義為需要靶病變或靶血管的血運重建癥狀性的再狹窄,表現為心絞痛或急性心肌梗死等。根據Mehran 分類系統,可以將ISR分為四型:①Ⅰ型,即局灶型,可以細分為連接型、邊緣型、單一局灶型和多點局灶型;②Ⅱ型,即彌漫型;③Ⅲ型,即增殖型;④Ⅳ型,即閉塞型。因此了解ISR 的病理生理發生機制對ISR 的治療更有指導意義。既往在普通球囊(無支架)血管成形術(plain old balloon angioplasty,POBA)中,ISR 的機制主要包括:血管重構和彈性反沖。而支架內血管成形術后的再狹窄涉及內皮損傷、內皮功能失調及新生內膜增殖和新動脈粥樣硬化形成,其中新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過程與內皮細胞的不完全再生有關,導致一系列的急性或慢性炎癥反應,新生脂質的攝入過多以及新生內膜中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加速發展[7]。由此,導致ISR 的三個主要過程是:彈性反沖、內膜增殖和新動脈粥樣硬化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內膜增殖,這主要是內皮損傷引發炎癥反應,并且在介質中擴散變化,導致血小板、纖維蛋白的沉積以及巨噬細胞的黏附進而導致內膜增生;還有另一種現象主要是由于血管平滑肌的增殖及其隨后的消融遷移,導致管腔變窄。許多研究發現microRNAs 是參與上述過程的重要調節因子[8]。
3 MicroRNAs調節內皮細胞參與再狹窄
一個正常的內皮系統非常重要,因為它參與了血管張力的調節,并通過抑制炎癥、血栓形成及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和遷移來抑制內膜增生。支架植入術后引起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EC)的機械性損傷,導致一系列炎癥反應、血栓形成等,從而引起支架內再狹窄的形成。因此維持內皮細胞完整性及其正常功能對ISR的形成具有抑制作用。在血管內皮細胞中miRNA表達最高的是miR-126,它參與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和血管發育的調節。有研究發現miR-126 是血管完整性的主要調節因子。它由血管內皮抑制素(VE-statin)基因的內含子7編碼,也被稱為EGF樣結構域7 (EGFL7),由E-26家族轉錄因子ETS1/2控制。在斑馬魚中敲低miR-126 會導致胚胎發育過程中血管完整性喪失和出血,miR-126 的功能部分是通過直接抑制VEGF 通路的負調節劑,包括Sprouty 相關蛋白、SPRED1 和磷酸肌醇3 激酶調節亞基2 (PIK3R2)產生的[9-10]。miR-221/222 族參與維持內皮細胞的穩態和支持內皮細胞靜態表型。例如,將人肝竇形內皮細胞暴露于臨床劑量的電離輻射會導致AMP 激活蛋白激酶(AMPK)和p38絲裂原激活,AMPK和p38 MAPK途徑均通過上調基質金屬蛋白酶2 (MMP-2)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2 (VEGFR-2)來促進輻射誘導的人肝竇形內皮細胞血管生成行為[11]。有研究觀察到輻射照過的人類臍靜脈內皮細胞可誘導血管生成相關的miRNA 表達,包括miR-221/222 簇,它本身不支持新血管生成,但有助于維持已組裝的新血管內皮細胞的穩定性和完整性[12]。實際上,在EC中,miR-221/222簇顯示出抗血管生成活性,并阻止了內皮向血管重塑和新血管形成的激活。miR-221/222 負責建立EC 的靜態表型并維持血管內皮的穩態。
內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在內皮功能的調節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通過產生一氧化氮(NO)來充當血管張力和體內平衡的主要調節劑。NO的產生對于促進內皮完整性和內皮再生至關重要,最近已報道鳥苷三磷酸環水解酶1 (GCH1)是miR-133a 的靶標。GCH1 缺乏對于內皮功能障礙中eNOS 解偶聯至關重要。miR-133a在內皮細胞中的異位表達參與了許多種心血管疾病(CVD)危險因素誘導的內皮功能障礙。有趣的是,他汀類藥物通過抑制異常的miR-133a 表達來預防內皮功能障礙,從而上調GCH1 基因表達[13]。此外,miR-199a-3p 與miR-199a-5p[14]、miR-155[15]、miR-21[16]也參與NO 失調的內皮功能障礙。關于支架植入后受損冠狀動脈的再內皮化這樣的結構提供了一個非生理表面黏合,并產生了較高的剪切引力,而高剪切應力則損害EC 功能[17]。最新的研究表明miR-93 和miR-484 受剪切引力的調節參與內皮細胞功能障礙[18]。
4 MicroRNAs調節炎癥反應參與再狹窄
支架植入術后引起內皮損傷,促使一系列炎癥反應。炎癥反應參與冠脈支架術后再狹窄各個階段,對平滑肌細胞的表型轉換、增殖及遷移,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及新生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等都尤為重要。EC的損傷使EC活化,激活EC后,它們會表達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白介素(IL)-8、細胞間黏附分子1(ICAM-1)、血管黏附分子1 (VCAM-1)、E選擇素、P選擇素和其他炎性因子,吸引淋巴細胞和單核細胞與內皮結合并浸潤到動脈壁中,炎癥由此便開始發生[19]。此過程涉及許多細胞和細胞因子的參與[20],ZHU 等[21]發現miR-155和miR-221/222通過靶向血管緊張素Ⅱ(Ang Ⅱ)刺激的人臍靜脈內皮細胞(HUVEC)中的血管緊張素Ⅱ型受體(AT1R)或轉錄因子Ets-1參與內皮炎癥和EC 遷移。YANG 等[22]證實了Smad3 是miR-216a的潛在靶標基因,miR-216a抑制Smad3蛋白表達并介導下游IκBα降解,從而激活了內皮細胞中N-κB響應黏附分子(如ICAM1 和VCAM1),從而促進了內皮細胞對單核細胞的黏附能力,進而促進內皮炎癥。ZHENG 等[23]證明了miR-24 的過表達顯著抑制importin-α3(KPNA4)基因的轉錄和翻譯,并負調控內皮炎性因子TNF-α的表達。miR-24 通過阻斷NF-κB信號通路、調節內皮細胞的炎癥以及抑制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和遷移而發揮其在動脈粥樣硬化中的作用。SU 等[24]研究發現,miR-181a-5p 和miR-181a-3p通過分別靶向TAB2 和NEMO 來阻斷NF-κB 激活和血管炎癥,從而延緩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進而抑制血管炎癥和動脈粥樣硬化。
內皮的損傷到炎癥的激活,再到單核細胞成為組織巨噬細胞并內化脂蛋白顆粒并產生泡沫細胞(新生動脈粥樣硬化的標志),泡沫細胞分泌炎性細胞因子、活性氧和其他介質;巨噬細胞會死亡,包括通過凋亡而死亡,形成成熟斑塊的脂質或“壞死”核心;巨噬細胞的作用放大了局部炎癥反應。YANG 等[25]證明了miR-155 在oxLDL 刺激的巨噬細胞中促進炎癥和巨噬細胞遷移增強了STAT3和NF-κB信號傳導,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炎癥。CEOLOTTO 等[26]通過對有和沒有動脈粥樣硬化的患者的血漿樣本中篩選了一組179種分泌的microRNA,并在隨訪至11 年的患者中進行了橫斷面和前瞻性驗證,發現miR-30c-5p通過清除劑受體CD36 被氧化的LDL (oxLDL)下調,并通過Dicer 抑制miR加工。反過來,miR-30c-5p的下調負責oxLDL對巨噬細胞IL-1β釋放,Caspase-3 表達和凋亡的影響,并確定了miR-30c-5p在微粒中的減少是早期動脈粥樣硬化的啟動子,它通過傳遞促炎性促凋亡信號和損害內皮細胞的愈合來實現。
5 MicroRNAs調節血管平滑肌細胞參與再狹窄
在生理條件下,血管平滑肌是一種高度特化的幾乎靜止的細胞群,其主要功能是維持血管張力,確保血管的收縮。它們在成熟血管中呈現分化狀態,增殖率較低(≈5%),表達一組特殊的收縮蛋白(如平滑肌肌球蛋白重鏈、平滑肌肌動蛋白、Calponin等)。然而,血管平滑肌細胞具有顯著的可塑性,可以很容易地進行表型轉換,在炎癥反應和各種炎癥介質(包括細胞生長因子和趨化因子等)的刺激下,從高度專一化的收縮狀態轉變為合成或增殖狀態,隨后增殖和遷移速度增加,收縮蛋白的表達水平降低[8]。血管平滑肌細胞的表型轉換、增殖及遷移參與再狹窄,在這種情況下許多microRNAs 參與血管平滑肌的調控。眾所周知,miR-143和miR-145被認為是血管發育過程中和血管疾病中血管平滑肌細胞表型轉換的主要調節因子[27],其表達模式與α-平滑肌肌動蛋白(ACTA2)、平滑肌肌球蛋白重鏈和calponin 表達所定義的分化表型相關[12]。miR-125a-5p 在血管平滑肌細胞中高表達,但在血管損傷后表達下調。它的過度表達足以減少血管平滑肌細胞的增殖和遷移,并能促進選擇性血管平滑肌細胞標志物如α-平滑肌肌動蛋白(ACTA2)、肌球蛋白重鏈11 (MYH11) 和 平 滑 肌22 α (SM22 α) 的 表 達。miR-125a-5p直接靶向ETS-1是一種參與細胞增殖和遷移的轉錄因子,在血管平滑肌細胞PDGF-BB 途徑中起關鍵作用。miR-125a-5p可抑制PDGF-BB通路,因此其是VSMCs 表型開關的潛在調節因子[28]。miR-21 也參與血管平滑肌細胞表型轉換的調節,HUANG 等[29]的實驗證明了miR-21 不僅在促進人主動脈平滑肌細胞(HASMCs)的α-肌動蛋白中起重要作用,而且還通過AKT 和ERK 信號通路改變了人主動脈平滑肌細胞(HASMCs)的細胞形狀,進一步證明了miR-21是調節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遷移的重要調節因子。
在血管再狹窄中miR-221 和miR-222 兩種miRNAs均能促進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是通過抑制靶基因p27 (Kip1)和p57 (Kip2)來實現的,miR-221 和miR-222的基因敲除減弱了血管成形術后大鼠頸動脈內膜增生[30]。最近的一份報告還報道了糖尿病小鼠血管平滑肌細胞和動脈中miR-221和miR-222水平的升高。有趣的是,抑制這兩種miRNAs可防止糖尿病動脈損傷引起的血管平滑肌細胞異常增殖[31]。FENG等[32]實驗發現,體內頸動脈損傷后的大鼠血管平滑肌細胞中miR-93 上 調。miR-93 是通過Raf-ERK1/2 途徑介 導的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和遷移的發生。 此外,TORELLA等[33]的實驗表明,miR-133在體外和體內均在血管平滑肌細胞(VSMC)中穩定表達,發現miR-133參與了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和遷移的調控。腺病毒介導的miR-133 的過度表達可以減弱球囊損傷后的內膜形成,而抑制其內源性水平則會產生相反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miR-133通過靶向轉錄因子Sp-1和Moesin 減少了血管平滑肌細胞的增殖和遷移[34]。SUN等[35]研究發現miR-206在損傷血管壁增殖性血管平滑肌細胞中的表達明顯增加,miR-206 通過靶向ZFP580 參與血管成形術后血管平滑肌細胞的表型轉換和新生內膜病變的形成。 通過慢病毒介導的miR-206 減少了球囊損傷后新生內膜的形成,這些發現可能為血管成形術后再狹窄提供新的治療靶點。miR-181b通過激活PI3K和MAPK信號通路促進血管平滑肌細胞的增殖和遷移。根據這一結果,抑制內源性miR-181b 可抑制大鼠頸動脈成形術后新生內膜增生[36]。據報道,miR-663通過負調控JUNB和肌球蛋白輕鏈9 (MLC9)靶向作用于人血管平滑肌細胞的遷移和分化標志基因。此外,miR-663 在體內的過表達減少了小鼠頸動脈結扎所致血管損傷后新生內膜損傷的形成[37]。miRNAs介導的抑制平滑肌細胞增生和新內膜形成的例子還包括miR-9[38]和miR-599[39]。
6 MicroRNAs涉及新生動脈粥樣硬化
支架內新生動脈粥樣硬化(in-stentneoatherosclerosis,ISNA)的形成過程與內皮細胞的不完全再生有關,導致一系列的急性或慢性炎癥反應、新生脂質的攝入過多以及新生內膜中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加速發展[7]。ISNA 的形成這個概念最早在2010 年被提出。關于microRNA 與新生動脈粥樣硬化之間的關系,可能與microRNA調節內皮細胞的完整性、炎癥反應等有關,如上所述,但目前尚未明確提出關于調節ISNA有關的microRNA。
7 總結
針對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療再狹窄的問題,多數學者認為該過程是多因素共同導致的,包括:炎癥因子的激活、內皮細胞的不全再生、平滑肌細胞的增殖、遷移、新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等。目前有多種治療方法可用于治療冠脈支架內再狹窄,而且治療通常涉及不止一種技術,包括:藥物治療、舊球囊血管成形術(POBA)、血管近距離放射療法(VBT)、切割球囊等。然而心血管介入治療再狹窄的問題,仍然是目前的熱點問題,需要提出新的針對支架內再狹窄的解決手段。MicroRNAs 被發現參與心血管介入治療再狹窄的多種調節,因此基因洗脫支架的新發展是支架技術的重大突破。這種支架不僅可以提供抗炎和抗血栓藥物,還可以攜帶miRNA和siRNA等ncRNA。此外,目前對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療再狹窄的認識還很有限。因此,盡管ncRNA在動物模型和臨床試驗中顯示出潛在的益處,但心血管疾病患者的ncRNA支架植入仍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