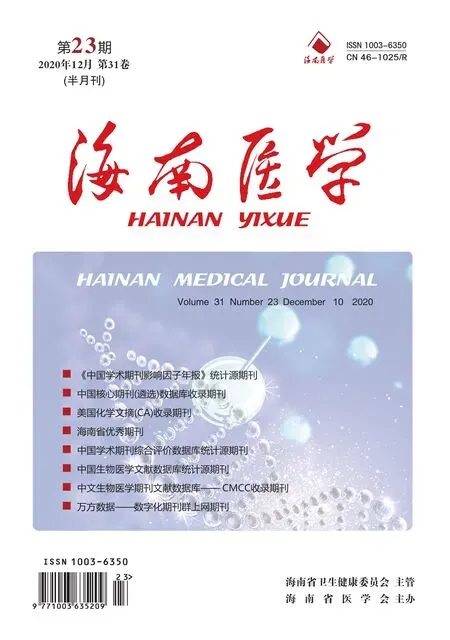彌散張力成像應用于早產兒腦白質損傷的研究進展
黃炳龍,劉玲,李承燕 綜述 敖當 審校
廣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兒童醫學中心,廣東 湛江 524001
早產兒腦白質損傷(white matter injury,WMI)主要發生在胎齡小于32周白質發育未成熟的早產兒,是早產兒腦損傷最常見形式,也是造成慢性神經系統發育不良主要原因。存活下來的早產兒常伴有腦癱、認知障礙、行為缺陷及運動障礙等后遺癥,對家庭及社會造成極大影響。彌散張力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是目前唯一可用于研究白質纖維的無創技術,能夠可視化白質結構,評估白質纖維髓鞘化程度,對WMI早產兒的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具有重要意義。
1 早產兒腦白質損傷
1.1 病因及常見危險因素 早產兒WMI是由于腦供血障礙而引起的缺血性損傷,其損傷機制復雜。早產兒腦發育不成熟,腦室周圍主要由終末血管供血,且血管的自我調節能力差,全身血流動力學瞬間變化可導致缺血或出血。此外,在胎齡24~32 周的早產兒腦內主要含有少突膠質前體細胞(oligodendrocytes precursor cells,OPCs),其易受缺氧、缺血、感染及氧化應激等損害,致使神經纖維軸突斷裂[1]。目前可引致WMI 的危險因素包括:小胎齡、胎兒宮內生長受限、腸外營養時間較長、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男嬰、胎膜早破、低出生體質量、窒息、感染、動脈導管未閉、長時間機械通氣、敗血癥等[2-5]。
1.2 病理類型 按神經病理學分類,早產兒WMI 主要包括腦室周圍白質軟化(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PVL)、腦室周圍出血性梗死(periventricular hemorrhagic infarction,PHI)及晚期腦室擴張。目前PVL 包括囊腫形成的腦室周圍白質深處的局灶性壞死和腦白質中更彌漫的非囊性成分[6],其中囊性損傷最嚴重,現已少見[7]。囊性WMI或囊性PVL是指腦室周圍白質中壞死和液化的區域,最終演變成多個囊腫,與腦癱的發生密切相關;非囊性WMI 則主要以OPCs彌漫性丟失、軸突受損、星形型膠質細胞增生為特征[8],與早產兒運動障礙及認知、行為缺陷等相關。早產兒腦白質以OPCs為主,因此WMI主要表現為彌漫性損傷。
1.3 臨床表現 早產兒胎齡及出生體質量越小,越易發生WMI[9],且大多會留有神經系統后遺癥[10]。有研究顯示,全球每年早產兒出生率超過10%[11],小于32周早產兒的發生率也逐年增高,2008年達到1.1%[12]。隨著新生兒重癥監護技術不斷提高,小于32周早產兒的存活率逐年增高,同時也增加了WMI和神經系統發育不良風險[2]。有研究表明神經系統發育不良的風險與胎齡成反比[13]。在胎齡小于32 周的早產兒中,存活者中有5%~15%出現不同程度腦癱及感覺神經受損;高達25%~50%出現認知障礙、行為缺陷及社交困難等[14]。此外,出生體質量也是影響早產兒神經系統發育不良風險的主要因素,出生體質量小于1 500 g的早產兒顱內出血發生率達20%~25%,而出生體質量在500~750 g的早產兒顱內出血發生率更是高達45%[15],約10% 的極低出生體重兒(very low birth weight,VLBW)出現腦癱,50%出現認知和行為缺陷[16]。
1.4 臨床診治的局限性 因早產兒WMI缺乏特異的神經系統癥狀和體征,即使WMI 嚴重的早產兒,也可能只是出現反應差等非特異性表現,故難以與全身性原發疾病癥狀及體征鑒別。同時,目前對早產兒WMI的治療尚無特異性的有效方法,因此早期識別早產兒WMI及早期判斷WMI程度顯得尤其重要。
2 傳統影像學的缺陷與彌散張力成像檢查優勢
早產兒WMI缺乏特異的神經系統癥狀及體征,早期篩查主要依靠影像學、振幅整合腦電圖(amplitude-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m,aEEG)等檢查。新生兒顱腦彩超是篩查早產兒WMI的主要方法,檢測囊性病變的靈敏度高,但對非囊性WMI的敏感度不高[17]。因早產兒WMI以非囊性病變為主,所以頭顱彩超診斷的敏感度低。aEEG 可用于評價腦發育成熟度、判斷腦損傷的嚴重程度,還可通過分析其背景活動及綜合評分預測神經學預后。研究表明生后6 h 內aEEG 異常對診斷腦損傷具有很大意義,并可作為評判身進行預后的指標之一[18],但易受自發腦電及外界干擾等。頭顱MRI平掃對于檢測更微小及非囊性病變優于頭顱彩超[19],但不能量化白質損傷程度[20],有研究發現,頭顱MRI平掃預測神經系統發育結果的能力有限,高達25%的MRI 結果正常的患者在隨訪過程中會出現中度或重度的發育遲緩[21]。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能夠在組織學上或在頭顱MRI 平掃基礎上髓鞘形成之前對白質通路進行可視化和定量[17],但在WMI形成囊腔空洞或瘢痕增生情況下,敏感度下降。目前已有相關研究表明DTI能夠反映大腦發育過程中白質和灰質的微觀結構變化,確定神經纖維束的分布和組織的各向異性特征[22],評估白質纖維髓鞘化程度,對判斷疾病輕重、評估預后有一定幫助。
3 彌散張力成像原理及其參數意義
3.1 原理和機制 DTI 是一種新的MRI 成像技術,在DWI 基礎上,使用至少六個方向的磁梯度來探測不同方向上水分子的擴散[23]。擴散是分子由于熱能而不斷運動。在沒有限制的環境下,水分子隨機擴散,并在與其他粒子碰撞后改變方向。如果擴散受到物理邊界的限制,擴散將受到限制,從而導致擴散變為非高斯[24-25]。例如,大腦中軸突、神經元細胞體、神經膠質細胞和大分子的存在構成了一種異質環境,阻礙并限制了擴散。在體外無限均勻的流體中,分子的擴散運動向各個方向運動的概率幾乎是相同的,這稱為彌散的各向同性;但在具有固定排列順序的組織結構中,如神經纖維束,水分子在各個方向的擴散是不同的,由于軸突的結構和生理變化,水分子更多與白質纖維的長軸平行的方向彌散,而很少沿垂直于神經纖維束走行的方向進行擴散,這稱為彌散的各向異性[26]。這種彌散各向異性是DTI識別不同部位腦白質的基礎。腦白質聯合纖維各向異性程度最高,其次為腦白質的投射纖維(內囊),再次丘腦、腦灰質(尾狀核)的各向異性程度最低[27]。
3.2 彌散張力成像相關參數及意義 DTI 常用的參數有各向異性分數(fractional anisotropy,FA)和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FA指水分子彌散的各向異性程度,能夠反映水分子彌散的方向性,定量評估腦白質纖維、髓鞘發育及損傷的情況。FA范圍為0~1,接近0提示纖維束的細胞膜、髓鞘以及軸索發育不成熟或被破壞;FA 值接近1,提示具有良好完整性[28],在白質通道中較高,在灰質中較低,腦脊液中接近為0[29]。ADC 指水分子平均彌散能力,與腦組織的細胞密度、髓鞘化程度及水分子含量相關,ADC值越高,組織內水分子彌散運動越強。DTI其他相關參量還有平均彌散率(mean diffusivity,MD)、軸向擴散張量(axial diffusion tensor,AD)、垂直擴散張量(radial diffusion tensor,RD)。
4 彌散張力成像的臨床應用進展
4.1 DTI在嬰兒腦發育中的應用 早產兒[30]和足月兒[31]在圍產期DTI特征是MD、RD和AD降低,而腦白質中FA 升高。且早產兒隨著日齡增加,FA 值逐漸增高,ADC值逐漸降低[32]。FA的增加發生在髓鞘形成之前,這在組織學上是明顯的,且歸因于伴隨髓鞘形成前狀態的白質結構的改變,包括軸突膜成熟和微管相關蛋白的增加,軸突口徑的改變,以及少突膠質細胞數量的增加[33]。在此階段,胼胝體壓部和膝部的無髓但高度組織化的連合纖維的FA 值最高。另外,FA的增加還與髓鞘成熟有關,在足月前后內囊后肢的投射纖維中FA 值最高[34]。郭莉莉等[35]發現足月兒和早產兒腦內內囊后肢FA 值均高于前肢,胼胝體壓部高于膝部,側腦室后角旁白質高于前角,內囊和胼胝體高于側腦室前角白質,說明白質的成熟遵循不同的時空模式,不同的纖維束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速度成熟,從后到前和從中心到邊緣的方向成熟[36-39]。此外,早產兒及足月兒DTI 的參數值存在明顯差異,早產兒在半卵圓中心、額葉白質、胼胝體膝部等FA值明顯低于足月兒,即使早產兒在胎齡得到糾正后FA 值仍低于足月兒,且胎齡越小,不成熟區域范圍越大[40]。除了評估白質之外,對皮質灰質的DTI研究還發現,早產兒的皮質發育發生了變化。皮質成熟的特點是FA 和MD減少,反映樹突分枝和突觸形成增加[41-42]。與足月兒相比,糾正胎齡至足月的早產兒的FA 和MD 升高,表明該人群的皮質發育受損[43]。
4.2 DTI在腦白質損傷的應用 CHAU等[28]研究發現,在對157 名早產兒進行DTI 檢查,48 例(30%)發生了腦白質損傷,腦白質損傷的程度越重,基底節和腦白質區域FA值越低。與常規MRI檢查結果正常的早產兒相比,腦白質損傷的早產兒表現出白質FA 降低,MD 和RD 增加[44]。另外發生WMI 的VLBW 患兒(糾正胎齡至足月)在胼胝體、內囊后肢、大腦腳、皮質脊髓束區域的FA 值明顯低于正常足月兒[45]。王雪源等[46]對早產兒缺氧缺血性腦損傷(hypioxic-ische-mic brain injury,HIBD)糾正胎齡至7~8個月時進行DTI測量及預后評估,發現內囊后肢、胼胝體壓部、額葉白質、頂葉白質、枕葉白質的FA 值預后較好的比預后較差的高,內囊后肢FA 值對HIBD患兒的預后判斷的診斷效能最高,靈敏度為90.6%,特異度為100%。另外,FA 值的高靈敏度及特異度可彌補缺氧缺血性腦病(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損傷后亞急性期ADC 的“假正常化”。WARD 等[47]對20 名HIE 新生兒(初查時間0~3周)進行DTI檢查,發現初查時間在第2~3 周的重度HIE 患兒內囊后肢及額、枕葉深部白質的ADC 值較初查時間在第1 周內者高,但FA 值卻持續降低。因此,在亞急性期FA 值較ADC 值更能準確反映病情。除了FA 值可評估預后外,ADC 值也被運用于HIE結局及早期神經系統預后預測。BRISSAUD等[48]發現內囊后肢ADC 平均值低于0.8×10-3mm2/s 的HIE患兒會遺留嚴重的神經系統后遺癥甚至死亡。因此,WMI程度和神經系統不良結局在一定程度上可通過DTI表現出來。
5 展望
DTI 能夠反映大腦發育過程中白質微觀結構變化,確定神經纖維束的分布[22],評估白質纖維髓鞘化程度。因其具有無輻射、可視化、可量化以及非侵入性檢測白質纖維結構的特點,有望被應用于科研和臨床評估腦發育情況及WMI 疾病等更多領域。目前局限性有:(1) DTI對于早產兒腦發育及WMI的探索尚缺乏大樣本、多中心、長時間隨訪的研究數據,同時早產兒腦發育及WMI 的標準MRI 圖譜尚未建立完善;(2)它只能描繪體素中的單個纖維群,無法在存在交叉纖維的情況下恰當地表示組織的微觀結構,并且DTI 衍生的測量方法缺乏組織特異性,因為這些測量方法可能會受到多種微觀結構特征的影響。此外,在受限的環境中,擴散不再是高斯,張量模型偏離信號。因此對于復雜腦白質結構的研究,DTI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