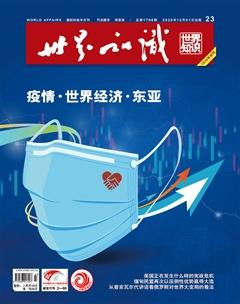拜登任期,歐洲尋求重塑跨大西洋關系
胡黌
“像你們中的許多人一樣,我一夜之間就成為佐治亞、賓夕法尼亞和亞利桑那州各郡選票變化趨勢的專家!”在11月10日的歐盟使節會議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講話中發出了上述感慨。這恰是歐洲對于此次美國大選高度關注的縮影。從大選本身,到未來歐美關系的走向,在追蹤著曾經的“最親密盟友”的這場歷史性選舉的過程中,歐洲也在觀察與爭論中籌劃著自己的未來。
期待落空的歐洲
拜登“如愿”鎖定勝局固然讓歐洲主流輿論松了一口氣,但他勝利的過程與方式、以及其中蘊含的變數帶給歐洲更多的是不解及憂慮。
大選前,歐洲對拜登大勝賦予了雙重期待。一方面,歐洲希望拜登的上臺能夠讓美國“回歸”國際舞臺,讓歐美關系重煥生機。另一方面,歐洲認為此次大選將是西式民主制度“自我糾錯機制”發揮作用的時刻。一場拜登的“藍色狂潮”將說明四年前特朗普的上臺僅是偶然,“反特朗普”才是當今美國的主流。
但大選的走勢給歐洲潑了一盆冷水。美國大選開票當晚,特朗普的暫時領先和自行宣布的勝選讓歐洲陷入了沉寂。四年前的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的情景似乎正在重現。歐洲政治人物中唯有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在社交媒體上為歐洲打氣,“要相信美國的投票制度與選舉結果”。然而失望的情緒還是開始彌漫。政治新聞網(politico)很快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為《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歐洲已是輸家》。文章指出,無論是特朗普,還是一個僅以微弱優勢勝出、缺乏兩院一致支持的拜登,都無法幫助歐洲實現其在各領域的“雄心壯志”。盡管拜登最終鎖定勝局,但歐洲的期待卻已落空。正如《法蘭克福匯報》概括,“特朗普主義長存”,并將持續塑造華盛頓的政策。
歐洲人看到,一方面,美國并沒有通過選舉實現“自愈”。7100萬特朗普支持者昭示著美國的深層分裂。在疫情完全失控以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特朗普支持者的數量及群體覆蓋面仍然在擴大。而特朗普對待選舉已經注定失敗事實的態度及方式,美國選民之間的不斷對峙,都為美國的分裂火上澆油。另一方面,美國“內向”的勢頭也仍將持續。參議院尚未“翻藍”,拜登未來四年的執政或仍將面臨來自共和黨的強大阻力。拜登政府的執政重心和優先項仍將放在國內議題。他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歐洲人亦存有疑慮。正如馮德萊恩所說:“優先項和觀念的轉變要比政治人物或政府的變化來得深遠的多,這種轉變也不會因為一次選舉就停止……而這無疑將對歐洲、以及跨大西洋聯盟的下一篇章產生影響。”

歐洲對于2020年美國大選高度關注。圖為2020年11月2日,英國倫敦一處廣告牌上正在展示倫敦廣播公司(LBC)有關美國大選節目的預告。
歐美關系已回不到過去
當然,對于大多數的歐洲領導人而言,告別特朗普無論如何都是值得慶賀的。歐洲主要領導人在第一時間通過社交媒體向拜登送上祝賀,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很快與拜登通電話。
拜登的上臺使得跨大西洋關系重啟成為可能。重申對北約的支持,回歸全球衛生、氣候治理框架等都是拜登上臺后可能的舉措,也將受到歐洲的歡迎。雖然過去四年中特朗普對歐洲“極限施壓”的一系列議題仍將橫踞在拜登時代的跨大西洋關系之上,如北約國家軍費開支、美歐貿易逆差、直接連接俄羅斯與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等,但拜登無疑將更多尋求與歐洲的對話與協調,采取更為柔性的方式。
歐洲自然歡迎美國政策“回歸正常”,也期待與美國加強從抗疫到安全的多領域合作。但與此同時,歐洲政客、學者們也清楚地意識到,歐美關系已經“回不到過去”。歐美之間應該尋求重塑跨大西洋關系,而不僅僅滿足于重啟或是恢復如初。
那么,未來的跨大西洋關系將“新”在何處呢?就目前情況而言,在“新格局”中,歐洲期望通過更多聚焦“新領域”推進跨大西洋合作方向的調整。馮德萊恩在使節會議上就提到,需要打造一個“適合當今世界的新的跨大西洋議程”,并將“衛生、氣候、數字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系的改革”確定為合作重點。可以將在傳統合作領域或多或少存在的爭議暫且擱置,而在新疆域中尋找合作增量。這或許將是跨大西洋合作實現突破的可行思路。
與此同時,歐洲也意識到需要推進跨大西洋合作的“新模式”。其中,既包括新的責任分擔機制,如默克爾在與拜登通電話時強調“德國與歐洲將承擔更多責任”;也包括馮德萊恩以及許多學者所提到的,歐洲在合作中的主動性,尤其是在議程設置方面,不再“等待美國的指示”,更多根據歐洲自身的利益出發。這些“新模式”實際上也旨在解決跨大西洋合作中歐美“失衡”的老問題。
在未來跨大西洋合作中,雙方各自內政掣肘、認知分歧、利益沖突等一系列問題仍將不斷出現。但對于歐洲而言,拜登上臺的最大意義就在于他或許能使美歐雙方平等地回到談判桌前,共同尋找建設性的、合作的解決方案。
伙伴關系不等同于“盲從”
在過去四年中,美歐在諸多問題上的分歧都在不斷加深。在如何看待并應對中國崛起方面,歐洲也始終與美國保持距離。相較于特朗普政府將中國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并采取全政府的手段瘋狂打壓的立場與做法,歐洲的立場相對冷靜:其一,歐洲雖視中國為“制度性對手”,但同時強調其與中國的關系“至關重要且是多面的”;其二,歐洲并不愿意成為中美博弈的犧牲品,更不愿成為中美博弈的戰場;其三,在許多涉華議題上,歐洲雖然與美國的看法有相似之處,但“絕不認同美國的做法”。
拜登的上臺并不會改變歐洲對于中歐關系的基本判斷,歐洲仍將著力在經貿、氣候變化、多邊治理等方面尋求與中國的合作。與此同時,由于拜登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將采取對抗性相對較弱的方式,更多尋求對話并在多邊主義框架內展開,這無疑更對歐洲人胃口,也將賦予歐美在諸多涉華議題上加強對話和協調的可能性。事實上,目前歐美間相關的對話與協調已經展開。在美國大選前不久,在歐方倡議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對話,啟動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的定期外交對話。根據官方表態,雙方旨在以“專門論壇”的形式,探討包括“人權、安全與多邊主義”等所有與中國相關的議題。這一對話將持續進行,預計也將在拜登任內延續。而這種對話將如何落實到雙方的政策及行動上,仍有待觀察。
就當前大選后歐洲領導人及政客的表態來看,整體上仍然是謹慎而微妙的。主要強調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是基于共同的價值觀,在雙邊及全球事務上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而中國更多是作為“潛臺詞”出現,亦或是點到為止。正如歐洲人所強調的,伙伴關系并不等同于“盲從”。上文提到,未來的跨大西洋關系“新模式”中,歐洲人將更多基于自身的利益與價值觀行事,在中美關系、中美歐關系中,也將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