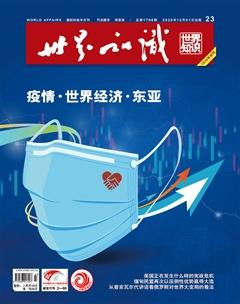俄羅斯與“后蘇聯空間”

馮玉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蘇聯解體雖然使俄羅斯失去了超級大國地位,但它仍是“后蘇聯空間”的霸主,對原蘇聯國家的政治生活和地區安全走向擁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實際上,在蘇聯解體近30年后,波羅的海國家已“加盟”“入約”,格魯吉亞、烏克蘭與俄已反目成仇,阿塞拜疆同土耳其的關系更加牢靠,中亞國家也正積極推行“多元化外交”。
近來,白俄羅斯危機、納卡戰火重燃以及吉爾吉斯斯坦內亂都讓俄羅斯左右為難、進退失據。
俄羅斯對“原蘇聯國家”國內政治進程已難以置喙。盡管在此次白俄羅斯危機中俄最終選擇了支持盧卡申科,但俄希望看到的是盧卡申科淡出政壇。然而,盧卡申科竭盡所能使俄放棄希望白俄羅斯權力更替的想法,并證明自己不可替代。當前,俄在白俄羅斯已缺乏全方位的社會政治影響。盡管俄軍方和情報部門與白俄羅斯同行保持密切關系,但俄并未積極廣泛地做白俄羅斯精英階層的工作,聯系范圍僅局限于盧卡申科及其身邊的人。俄與白俄羅斯反對派、活躍的年輕人以及整個白俄羅斯社會缺乏合作。
處理復雜地緣政治關系的糾結感。俄羅斯在新一輪納卡沖突中面臨的局勢是戰略伙伴阿塞拜疆攻擊自己的盟國亞美尼亞。亞美尼亞是俄在南高加索地區重要的戰略支柱,與俄有著密切的傳統和現實聯系。而俄羅斯與阿塞拜疆關系復雜,既是戰略伙伴也是競爭對手。在納卡沖突中,俄如力挺亞美尼亞,則可能讓阿塞拜疆漸行漸遠,甚至最終成為新的敵人;但如果不對亞全力支持,則會引發盟友的不滿并導致俄主導的安全與經濟聯盟的整體性松動。在多重壓力之下,俄最終不得不選擇了平衡立場:為盡快結束流血沖突做出努力,但避免直接介入軍事行動。
作為盟主在承擔義務和獲取收益之間的落差感。普京執政以來,著力推進“后蘇聯空間”的重新一體化,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歐亞經濟聯盟是其最重要的兩根支柱。然而,“盟主”不僅意味著權力,也意味著責任。因此,多年來俄一直以提供能源補貼、安全保障等形式換取一體化成員國的“忠誠”。但實際上,集安組織和歐亞經濟聯盟任何成員國的全方位外交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使其與俄羅斯的盟國關系受到侵蝕。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特列寧近來強調“盟國關系應基于自愿和對等原則”。在經濟領域,特列寧也認為“俄羅斯的經濟一體化伙伴創造不出一個大市場,也不是寶貴資源的來源。與他們的合作是有益的,但不應像帝國時期,尤其是蘇聯時期那樣出資資助,而應是互惠互利的”。
地區中等強國強勢介入“后蘇聯空間”的危機感。曾幾何時,俄羅斯把美國、歐盟等與原蘇聯國家發展關系的行為視為對其在后蘇聯空間主導地位的威脅,但納卡地區戰火重燃卻表明,土耳其這樣與俄羅斯有著復雜歷史糾葛和現實利益沖突的國家才是對其的巨大挑戰。盡管俄土兩國的整體國力對比是俄強土弱,但土耳其對俄而言也具有不少“非對稱優勢”,歷史上曾持續300年的俄土爭斗正在以新的面貌重現:在民族宗教問題上,土耳其歷來對韃靼斯坦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有著強烈影響。現實上,土耳其倡導的“突厥語國家聯盟”在南高加索和中亞有不少擁躉;在地緣政治問題上,正是在土耳其的全面支持下,阿塞拜疆才有決心迫使亞美尼亞接受阿方的和平條件。由于這場戰爭,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地區的存在已具有全新的性質;在能源安全問題上,由于供應結構的變化特別是東地中海和黑海巨型天然氣田的發現,土耳其今年已基本停止從俄的天然氣進口,未來不僅有可能實現“能源獨立”,甚至有可能對俄向歐洲的天然氣出口形成挑戰。也正是由于對俄土沖突升級的擔憂,俄羅斯才沒有選擇在納卡問題上與土耳其公開對立,反而是以“柔軟身段”邀請土加入調解納卡沖突的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
未來,俄羅斯在“后蘇聯空間”面臨的問題,不僅將對其歐亞一體化政策產生諸多掣肘,也將影響到其整體對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