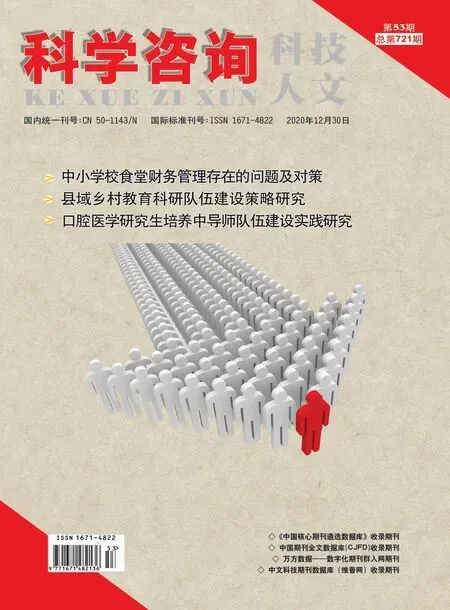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現狀及策略研究
——以重慶市W 區公辦幼兒園為例
馬 力 向 菁
(吉林外國語大學教育學院 吉林長春 130000)
一、問題的提出
幼兒園教師懲戒是基于當今在幼兒園“鼓勵教育”“賞識教育”下所提出的“逆鼓勵化”,是幼兒教師通過正確的懲戒方式使幼兒認識、反思并改正自己的錯誤,使其不合理行為發生改變的一種教育方式。本研究以重慶市W區公辦幼兒園為例,從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的適時性、適當性、適度性三個方面對幼兒園教師懲戒進行剖析,以此了解幼兒園教師懲戒現狀,并提出相應的優化策略[1]。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及取樣
本研究選擇重慶市W區兩所幼兒園共140名教師為調查對象,共發放問卷140份,回收有效問卷135份。選取研究者所在重慶市W區幼兒園為觀察點,以幼兒園大中小各一班級作為觀察研究基地,根據研究者所制作的《幼兒教師懲戒行為觀察記錄表》進行六周的觀察與分析,并對園所的六位教師(大、中、小班各兩名)和一位園領導進行訪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采用觀察法、問卷法、訪談法。為了獲取真實的懲戒情景,本研究采取自然觀察法中的事件取樣法,采用自編《幼兒教師懲戒行為觀察記錄表》在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可能發生的時間段進行觀察,并對觀察中的問題進行細致分析,為探索更為合理的懲戒行為提出改進策略。本文使用的《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使用現狀調查問卷》分別在三個維度對幼兒園教師的懲戒行為進行調查。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問卷《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使用現狀調查問卷》,從幼兒園教師的基本情況,幼兒園教師懲戒的適時性、適度性、適當性三個方面對幼兒園教師的懲戒行為進行調查。運用SPSS23進行信效度檢驗,問卷的Alpha系數達到0.811,同時采用因子分析進行效度檢測,得出KMO值為0.773,Bartlett球形檢測值為0.000,說明該問卷適用于檢測幼兒園教師懲戒的適時性、適度性、適當性。
三、研究結果分析
通過研究,適時性的平均值在3.9957分,接近答案“同意”的分值,適當性的平均值在4.0467分,接近答案“同意”的分值;適度性的平均值在4.0414分,接近答案“同意”的分值,說明問卷分值差異不大,較多分布于“同意”這一范疇,幼兒教師也能較好地把握懲戒行為的適時性。
(一)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的適時性
1.幼兒園教師以課堂規范作為懲戒的參考
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幼兒園教師懲戒也是一樣。幼兒園教師行使懲戒權時,需要遵循一定的標準,這不僅是幼兒園教師懲戒的基本前提,更是幼兒園教師所要遵守基本規范。通過對幼兒園教師的訪談發現,幼兒園教師認為教師懲戒的主要依據來自師生共同制定的課堂規范、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對幼兒的要求以及教師課堂管理中的行為或思維習慣。
2.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實施的前提在于觀察
觀察是實行有效懲戒的前提,要指導好幼兒,必須首先了解幼兒,而觀察幼兒是了解幼兒的基本方法。筆者通過對研究對象的問卷調查觀察,共收集到了135份有效數據。其中“通常在指導幼兒失范行為之前,我會先觀察幼兒行為”的平均分為3.95,其中“同意”項占比為49.6%,說明幼兒園教師在對幼兒的違規行為進行懲戒前,會通過一定的時間進行觀察,而非基于幼兒園教師的主觀判斷。
3.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實施較為及時
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是否具備及時性是判斷教師懲戒適時性的標準之一。根據觀察,幼兒園教師大多會選取“活動中指導”的方式對幼兒的違規行為進行懲戒,而較少選用“活動后指導”的方式對幼兒違規行為進行懲戒。同時,問卷中顯示,50.4%的幼兒園教師都認為幼兒園教師應該對幼兒的違規行為進行“及時性指導”。但問卷中顯示,小、大班的幼兒園教師更傾向于發現即指導,即立即采取適當的行為對幼兒違規行為進行懲戒;中班教師更多偏向于當違規行為干擾課堂時再做懲戒。
(二)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的適度性
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的適度性體現于兩個方面,一是懲戒數量上的適度,二是懲戒質量上的適度。以小班25分鐘的美術活動“大雨和小雨”為例,一節課中,共記錄違規行為為30條,教師進行懲戒和提醒的行為共有16條,且大多數懲戒都是以簡單的語言和眼神提醒為主。
1.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量”的適度
通過對幼兒園違規行為中花費懲戒時間的分析,筆者發現,在指導時間上1/3以下的人次占比最多,大中小之間的比率分別為23、20及34。其中又以大班占比最多,說明大班幼兒相較于小、中班幼兒違規行為次數更少,教師也更傾向于將時間花在維持課堂紀律以外的地方;小班占花費時間“1/2”的人次最多,說明小班幼兒才進入幼兒園,對集體活動的規范認識上還存在一定不足,因此需要教師花更多時間進行規范性的懲戒。總體來說,教師在懲戒的次數和時間上會因幼兒年齡段的重點任務不同,而有側重性地對幼兒的違規行為進行懲戒。
2.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質”的適度
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質”的適度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對幼兒個體懲戒的適度,對幼兒提出的需求或問題的處理等,給予恰如其分的反饋,之后繼續觀察幼兒的行為是否有改變;二是對幼兒全體懲戒的適度,就是說在每一次集體活動中適當地設定一些活動目標,然后根據預設的這些目標觀察幼兒的反應。
(三)幼兒園教師懲戒行為的適當性
1.懲戒方式靈活多樣
教師在區域活動過程中,采取較多的懲戒方式是干預(占比75.6%),包括轉移注意、鼓勵強化、嘮叨及自發引導。其中忽略(包括順從和放任)和制止(包括發出指令和強制制止)分別占比11.9%以及10.4%,懲罰(剝奪和訓斥)最少,僅占2.2%。表明教師更傾向于采用積極的懲戒方式對幼兒進行懲戒。但需要注意的是,懲戒與懲罰并不相同。
2.懲戒策略的多變性
對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性格的幼兒提供不同的指導策略,也是衡量教師指導有效性的因素。筆者在觀察中發現,教師對一些內向、害羞的幼兒在集體教學活動中多采用摸頭、手勢等肢體動作;對經常產生失范幼兒行為的幼兒則多以忽視、訓斥為主。
3.適當進行角色轉變,激發幼兒的學習自主性
多變的指導也需要教師把握懲戒重點,依照遇到的情境不同適當地轉變教師角色,融入集體教學活動。在集體教學活動中,教師經常扮演的是一名“傳業者”的角色。為了真正教有所長,則對教師的反思能力提出了要求,教師對自身懲戒行為的反思旨在修正錯誤的、不良的教學方法和指導策略等。個人的反思影響著教師指導能力的提升,靈活多樣的集體教學活動指導策略對教師的反思能力提出了要求。
四、優化建議
(一)提升教師教育智慧,適度運用懲戒
當幼兒出現違規行為時,教師可以正確利用懲戒手段對幼兒的違規行為進行管理,但幼兒園教師需要明確的是,懲戒的目的在于戒除學生的不良行為,因此,教師不可將懲戒作為管理幼兒的“靈丹妙藥”,應合理運用懲戒的手段,將懲戒作為一種正確的教育手段合理運用。
(二)加強理論學習、明確懲戒的必要性
在相關的問卷發放中,筆者發現,教師都有些許“談懲色變”。部分教師認為幼兒園不該懲,甚至不敢懲。但在相應的觀察之中,筆者也發現了教師懲戒的身影。這說明,教師將“懲戒”與“懲罰”等同,并沒有深刻明確“懲戒”對幼兒的積極意義。懲戒的目的是戒除幼兒的不良行為,使幼兒具有良好的品德,因此,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認為懲戒是具有教育性的[2]。向葵花在《重新審視懲戒教育》中也強調,“懲戒教育,作為一種正面教育,主要是指通過實施批評、處罰手段使受罰者痛苦,但并不損害其身心健康[3]。”
(三)營造和諧的家園合作環境
幼兒的和諧發展不僅依靠教師,幼兒園良好的教育,更依靠于幼兒所處家庭的良好教育。有相關研究表明,一個優秀的幼兒是“5+2”共同努力的結果,五天的幼兒園生活需要兩天的家庭生活共同來鑄造和完成。因此,懲戒的實施不僅是依靠幼兒園中的教育,更需要家庭的維持。幼兒園也需要向家庭傳達正確的教育理念,為更好教育幼兒做好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