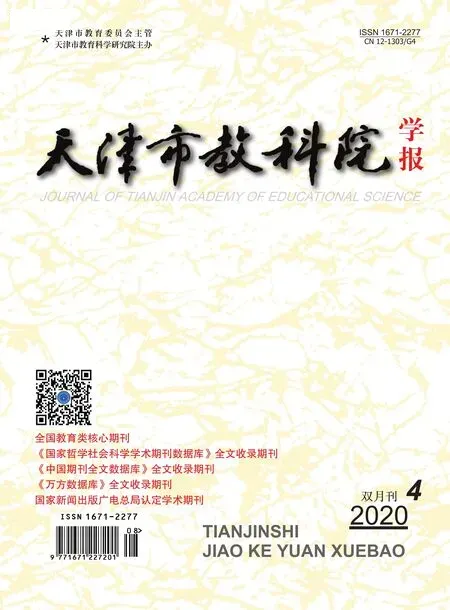教育理論話語的實踐轉向
張軍鳳
長期以來,“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是教育理論研究者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研究者們對“教育理論脫離教育實踐”這一“真問題”[1]的辯論、反思和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教育理論聯系教育實踐”的對策建議,反映出對于“脫離”教育實踐的焦慮感和志于“聯系”教育實踐的使命感。“教育研究的實踐轉向已經成為眾多研究者的共同旨趣”[2]。于是,教育理論研究者“回到實踐”,在與教育實踐工作者的對話交流中,能夠以一種讓他們明了的話語方式表達教育理論,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文獻綜述
“對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關系的探討,已經形成了多層面立體式的景觀”[3],有諸多的關系假說,例如:相對說、依賴說、獨立說、統一說、雙向脫離說、合理脫離說、共生共存說、結合說、相互滋養說等,其中,由葉瀾教授領銜的“新基礎教育”“秉持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合作,理論和實踐的共生”[4],通過“研究性的變革實踐”,提出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是一種“相互滋養”[5]的新型關系,應該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觀點。該觀點并不是純粹理性思辨的產物,而是基于研究團隊長期以來扎根教育實踐,對“理論如何聯系實踐”形成了真實的體驗和認識。
事實上,如果我們要對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做更進一步的理解,就必然回到“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這個哲學命題上,并回答如下三個基本問題:何為理論?何為實踐?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如何?與理論哲學將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的做法不同,實踐哲學主張理論與實踐的相互統一。“理論”一詞源于希臘動詞“觀看”(theatai),它是一種哲學家的沉思、旁觀和凝視,是“真正參與一個事件,真正地出現在場”[6]。理論的沉思被視為哲學家的生活方式。“實踐(Energeia,praxis)一詞,是指行動本身即善的目的性行動,這種行動本身具有內在目的,這個內在目的本身就是實在善(real good)”[7]。實踐是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動、智慧的行動。理論是知的行動,它不僅“是一種理性洞察(旁觀和凝視),同時,對實踐的生活同樣可以旁觀和凝視”[8]。“理論與人的理性緊密相連,是人類表達實踐理性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理論是實踐不可缺少的,不是與實踐分離的”[9]。在實踐哲學視角下,教育體現了實踐的內在本質,教育實踐是人類最重要的實踐之一,它是“培養優秀人性的活動,指向人的福祉”[10]。與此同時,教育理論是一種“實踐性理論”,是“有關闡述和論證一系列實踐活動的行動準則的理論”[11]。也就是說,“教育理論作為實踐之知,并不是關于‘教育是什么’的客觀真理,也不是讓人得心應手的一整套操作技能,它是根植于教育實踐的知道怎樣做的智慧,是選擇教育活動進行教育判斷所必需的智慧”[12]。
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之所以如上文所言,存在著多樣化的形態,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教育理論主體和教育實踐主體的多樣性”[13]。在李政濤教授看來,“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歸根到底是教育研究主體和教育實踐主體之間的交往和相互轉換的問題”[14]。而已有的相關研究常常是沒有主體的研究,缺乏 “主體意識”。因此,進一步探討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最終的落腳點還是在各自的主體身上,即教育理論研究者和教育實踐工作者。前者通常指的是大學教師、教育研究機構的專門研究人員,后者既包括學校的校長、教師,也包括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和管理人員。就雙方關系和定位而言,葉瀾教授認為雙方應通過“合作研究”結合為一個“共生體”[15]。石中英認為教育理論研究者“最多只能是教育實踐的‘提議者’而非‘指導者’;最好是教育實踐工作者的‘伙伴’,而非他們的‘導師’”[16]。李政濤教授認為雙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主體,在角色上雙方可以實現角色的轉化,“每一類主體都既是理論人,又是實踐人,都肩負著發展理論和推動實踐的責任”[17]。可見,無論從實然層面還是應然層面,眾多的教育理論研究者已經明確意識到自身要以平等的姿態和教育實踐工作者一起“回到實踐”,這是解決“教育理論脫離教育實踐”的根本之策。對此,吳康寧教授就曾提醒教育理論研究者不僅要具備理論品質,也需具備“實踐品質”,即“改造教育實踐的擔當、接觸教育實踐的欲望和感悟教育實踐的能力”[18]。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教育理論研究者“回到實踐”的工具或手段是什么?或許,部分關于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中介的研究能夠帶給我們一些啟發。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例如,教學改革實驗(張武升)、教材(曾天山)、教學模式(楊小微)、行動研究(宋秋前)、教育政策(王金霞、智學)、教育思維(劉慶昌)、真實的教育問題(劉德華、付榮)、實踐智慧(侯云燕、王晉)、教育智慧(段建宏)、敘事研究(秦初生)、教育技術(王良輝)、教育實踐問題(余清臣)等。由上述可見,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中介是豐富而多樣的,這也意味著教育理論研究者和教育實踐工作者的合作存在著諸多的可能性。不論是宏觀層面的教育政策,還是微觀層面的敘事研究,不論是教育技術的使用,還是行動研究的應用,不論是教育智慧的領悟,還是教育實踐問題的解決,要讓這些“中介”真正發揮作用,都離不開教育理論研究者和教育實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發揮教育理論研究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否則,似乎很多“中介”的運作都將面臨“癱瘓”的困境。
“回到實踐”賦予了教育理論研究者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而帶著什么樣的理論“回到實踐”,或者說教育實踐工作者能夠明了什么樣的教育理論,就成了一個更為急迫的問題。李潤洲教授認為“教育理論要想恰當、貼切地表達教育實踐,需要從觀念敘述、實體敘述、宏大敘述及單一本質敘述轉變為現實敘述、關系敘述、事件敘述及多元本質敘述”[19]。余清臣教授認為“為了獲得核心的話語空間地位,教育理論不能只使用一種語言形式或語體,還可以轉換為‘生活版’或‘白話版’的形式”[20]。吳康寧教授認為“教育理論的呈現除了純學術化的方式之外,還需要有為教育實踐工作者所適應、喜歡以至于習慣的非學術化的通俗易懂的呈現方式”[21]。面對教育實踐工作者,教育理論研究者不能只使用一種純學術化的方式來呈現教育理論,而應實現教育理論話語的多樣化表達,以促進教育實踐工作者的理解。本文試圖從教育理論話語的實踐轉向切入,以期為教育理論研究者“回到實踐”和教育實踐工作者“親近理論”助力。
二、教育理論話語在教育實踐中的現實遭遇
任何理論從根本上說都是一個“解釋框架”[22],教育理論也不例外。作為一種實踐性知識的教育理論,它為人們提供了認識教育“事理”[23](事理是相對于心理、物理而言的)的獨特視角,與此同時,它也天然地形成了自身獨特的話語體系。“話語是思想、觀念和情感的語言表達”[24]。不管是解釋教育現象、論述教育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揭示教育特征和規律,還是解決教育問題,教育理論以教育學專業術語作為語言表達的基本手段,并由此構成以概念、命題、范疇和邏輯等內容為主體的關于教育事理的知識體系。
教育理論知識和流行于教育實踐工作者中的教育實踐知識,二者都是對教育經驗的重構,但在性質上有著明顯的區別。相比較而言,前者是理想的、理性的、邏輯的、抽象的、普遍的、公共的,后者是現實的、感性的、形象的、情境化的、個別的。若從話語形式上看,前者主要是通過以體現學術旨趣為上的學術化語言來傳情達意,后者是教育實踐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創造的更具通俗性的生活化語言。
兩種知識在性質特點和話語形式上的區別,內在地反映了教育理論研究者和教育實踐工作者看待教育事理所具有的不同動機和話語偏好。前者出于鞏固學科地位、維護學術話語權力的目的,“本能地”排斥了生活化語言的侵擾,例如,在論文標題上將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脫離”說成“阻隔”,就顯得更有學術味,也更加迎合同行們較為挑剔的口味。后者往往專注于對教育現實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出于“本能的”自我防御,他們對不接地氣、晦澀難懂的學術化語言缺乏理解的熱情和研讀的興趣,而通常采取漠視或排斥的態度,認為教育理論研究者并不真正了解基層的教育實踐情況,其“制造”的大量的教育理論缺乏實踐依據,大多是拍腦袋的產物,“太抽象、太空泛,只是一系列新奇的術語堆積”[25]。于是,教育理論“因缺乏起碼的‘實踐感’而實際上成為一種帶有濃厚自戀色彩的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并因此而被教育實踐工作者們普遍束之高閣”[26]。可見,雙方即使在人格和地位的平等上達成了“契約”,也不能保證在話語上的平等,教育理論話語的學術性及其自帶的一種想象中的“高貴范兒”和教育實踐話語的通俗性構成了“氣質”上的不相協調。而解決這一問題的責任仍在教育理論研究者一方,因為“在總體邏輯上,理應是‘教育理論聯系教育實踐’在‘教育實踐聯系教育理論’之前”[27]。
在教育理論研究者群體內部,一些人已經針對這種日益嚴重的學術語言自戀情結以及由此反映出對教育實踐工作者的漠視態度而在學界提出了警示。顧明遠先生就曾講道:“當前有不少教育理論文章言必稱海德格爾,文必引哈貝馬斯,堆積一大堆西方話語,連我們這些長期從事理論工作的人都讀不懂,不要說一般教師了。這種學風不改變,中國的教育理論體系永遠建立不起來。”[28]還有論者尖銳地指出“在當下的教育研究中,這種動輒就為實踐立法并對之進行合理化論證的現象流布甚廣而且尤為深重,而且業已導致教育研究中的‘大話’充斥、‘空話’連篇、‘假話’盛行、‘獨斷’囂張”[29]。教育理論工作者“從總體上存在一種‘實踐的無知’”[30],“他們把教育理論的呈現視為自我陶醉的文字游戲,較少考慮教育實踐者特別是從事中小學教育教學一線工作者的接受水平,一方面充塞大量從譯著里引出的晦澀難懂的理論概念,另一方面又布滿云里霧里的考據。宣傳教育理論的刊物也把故作高深和晦澀的語言表達奉為圭臬”[31]。學界中看似繁榮和高產的教育理論“市場”很可能是一種假象,真正有價值的教育理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筆者以“教育理論”“教育實踐”為主題爬梳的近100篇教育核心期刊論文中,發現在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關系研究的視野下,關于當前國內教育理論的案例并不多見,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生命·實踐”教育學、主體教育理論、新教育、情境教育理論、嘗試教學理論等,很多研究者在文中上萬字的論述中幾乎沒有案例,有的也只是拿素質教育理論說事,或者是列舉建構主義教育理論、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赫爾巴特的《普通教育學》,以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作為佐證。這是否說明了作者有難言之隱不方便以當代的教育理論為例,抑或是表明上得了臺面、能夠關照甚或解決教育實踐問題的教育理論實際上不甚了了。
在教育理論研究者中較為盛行的這種自我麻醉式的語言習氣,一方面,抬高了教育實踐工作者學習教育理論知識的話語門檻。學習教育理論,首先要理解教育的基本概念,熟悉教育理論研究者的思維方式,并能夠掌握教育理論學術語言的基本規范,這對于擅長運用日常語言的教育實踐者來說,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很多中小學校圖書室中陳列的教育理論期刊基本上成了一種空洞的擺設,教師們即使擁有學習這些“純正”教育理論的熱情,也會因為在閱讀上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障礙而就此“擱淺”。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教育理論在教育實踐工作者中的影響力。由這些紛繁復雜的學術語言符號“組裝”而成的教育理論,客觀上對教育實踐工作者造成了一種時空中的疏離感。他們會認為,這些教育理論論著(學術論文)中所提出的較為抽象的概念、命題、框架、模型等研究成果與他們日常的、在學校中或課堂上的、當前的、具體的教育實踐缺乏緊密的關聯,而要將這些理論運用到自己的教育實踐之中,更是無從下手。教育理論在他們眼中只落得個“好看但不中用”的名聲。
三、教育理論話語問題的原因分析
本文并不否認教育理論研究者使用規范的學術話語的應有價值。掌握學術話語是教育理論研究者的一項基本功,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學術研究的基本訓練,實即理解、熟悉和運用特定學術話語的過程”[32]。本文所質疑的是許多教育理論研究者“已經只會、或者說僅僅習慣于用學術的語言去闡述教育理論、用學術的套路去展開教育理論”[33],并將教育理論轉手“推送”給教育實踐工作者的這種不良習氣。究其原因,我們可以從當代中國教育理論話語突顯的問題和教育理論研究者自身存在的問題兩個層面略做探討。
當代中國教育理論話語從整體上表現為“中話西說”[34]有余,而本土話語創新乏力。“中話西說”指的是研究者們習慣于用西學話語展現中國的教育事理,剖析中國的教育問題,并呈現研究者自身的教育思想。研究者們最為擅長的研究路向恐怕就是基于如人本主義、后現代主義、現象學等理論視角,對中國教育的獨特審視,而這其中恰恰缺乏的是基于本國視角和我們自己的理論。可以形象地說,為中國教育理論研究打底、潤色、添彩的主角仍然是像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康德、懷特海、杜威等一大批西方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教育家,而不是我們的孔孟、老莊、韓愈、朱熹、王陽明等古圣先人,也不是像蔡元培、陶行知、晏陽初、葉圣陶等我國近現代涌現的卓越的教育家。由于對西學話語的過分依賴、亦步亦趨,體現本土特色的理論話語體系始終不得建立,盡管一部分教育理論研究者已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難能可貴的理論成果,但在理論研究者群體中仍不足以形成一種具有普遍共識和行之有效的對話語言。
教育理論研究者自身也存在諸多問題,具體可概括為三種心態。一是自大心態。一些人對自身作為研究者的身份定位擁有一種優越感,這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所謂“下基層”“深入基層”就可看出,他們自認為和教育實踐工作者不在同一個位層上,而是處于上層的。一些研究者對于自身所熟悉的教育理論也存有一種優越感,把教育理論作為解決教育實踐問題的靈丹妙藥,這顯然是低估了教育實踐的復雜性。二是浮躁心態。一些研究者開展“理論研究的功利性太強,從而產生了大量的粗制濫造、重復研究、學術失范的垃圾成果,混淆了人們的視聽,敗壞了理論研究的聲譽”[35]。三是被壓迫心態。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教育理論話語權實際上仍掌握在權威教育學者和知名教育理論學術刊物的手里,研究者要想在這些高級刊物上發表文章,必須符合這些刊物所主導的學術話語體系的規范,并得經過評審專家的層層審核。研究者若要發表自己的理論見解,就必須用符合要求的學術語言和話語邏輯,這可看作是對研究者自由表達教育思想的一種語言壓迫。受上述三種心態的影響,研究者就很容易滋生慣于用學術腔調與教育實踐者交流的痼疾。
四、以讓教育實踐工作者明了的話語方式表達教育理論
當教育理論研究者和教育實踐工作者相遇的時候(通常是在如教育局會議室、校長辦公室、教師辦公室或課堂等教育實踐場域之中),我們相信,雙方均懷有渴望被對方理解的需要,否則,雙方坐在一起談話的意義何在?問題在于,雙方能否通過有效的談話以達成互相理解的目的,并就有關問題的分析和解決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如果研究者單純使用與同行交談或寫學術專著相似的學術話語,滔滔不絕地將眾多花哨的概念、命題、主義或模式等傳授于教育實踐工作者,將很難得到他們對教育理論的認同,原因在于雙方在話語方式上不協調,在交流效果上無法實現同頻共振。因此,教育研究者應在寫作中、在與教育實踐工作者的對話交流中,使用讓教育實踐工作者明了的話語方式表達教育理論。
會講故事。善于講故事,這是人類的天性。人們正是通過編制出種種共同的虛構故事而集合在一起,開展合作,繼而形成了一個個的組織和團體。正如尤瓦爾·赫拉利所講的“人類語言真正最獨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夠傳達關于人或獅子的信息,而是能夠傳達關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36]。故事雖有虛構的性質,但它不是謊言,它“被用于在人群中傳播因果信息和教訓,同時也被用于分享經驗、組建集體式的共同記憶力,并表明和宣傳一種態度。當一個共同體認同一段特定的故事時,他們也正在接受故事暗含的立場”[37]。教育理論研究者如果能夠將教育理論的解讀寓于故事情節之中,使其具有時空、人物、事件、戲劇性的懸念、沖突和想象等故事元素,就有助于疏解教育理論對于教育實踐工作者的陌生感、拒斥感,繼而增強教育理論對教育實踐工作者的親和力和認同感。
善用隱喻。“人類的思維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隱喻性的。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38]。我們通常是借助那些已經理解的其他概念來掌握一個并不熟悉的概念,而隱喻正是這樣一個有助于概念理解的語言和認知工具。在教育研究中,我們使用規范的學術性語言來界定概念,并且對于一個概念的界定往往需要借助于其他的概念。例如,我們把“教師”界定為“擔任教學工作的專業人員”,這里,我們只有先了解了“教學工作”和“專業人員”這兩個概念,才能進一步理解“教師”的概念。然而,即使教師們記住了“教師”這個概念的定義,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能真正理解它,原因在于我們對這個概念的界定顯得“太學術了”。事實上,大多數教師關于“什么是教師”的理解是隱喻性的,例如,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蠟燭、園丁、春蠶、孺子牛、慈母等。如果一位教育理論研究者去問一位小學教師“學習的概念是什么?”這也是在自討沒趣。因為,教師根本不可能記住并說出一個關于學習的學術性概念。他(她)更愿意用例如學習是“從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之旅”[39]、學習“并不是往頭腦里灌輸知識,而是在心中燃起一盞明燈”[40]等這樣的隱喻性的語言表達自己的理解。
多舉案例。案例并非虛構的故事,它是一個業已完成的、真實的事件。正是由于案例具有完成性和真實性的特點,它的可信度較強,因此也就成為教育理論“落地”的一個可靠證據。就教育實踐工作者而言,他們對一個鮮活案例的信任度可能會勝過一個看似完美和科學的理論。這是因為教育實踐工作者往往從實踐的角度出發來評價一個教育理論的“優”與“劣”,盤繞在他們頭腦中的問題通常是如“這個理論有用嗎?可操作嗎?”“誰已經或正在運用這個理論?”“有沒有關于這個理論應用的典型案例?”等實踐指向性的問題。他們會更加關注理論的實踐意義而不是理論的學術價值,更加關注行動的要領而不是關于行動的動員。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典型案例,就是理論聯系實踐、應用于實踐的“樣板”,它試圖以例證的方式向教育實踐工作者展示這是一個“好理論”,它及其所代表的教育理論更易于贏得教育實踐工作者的信任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