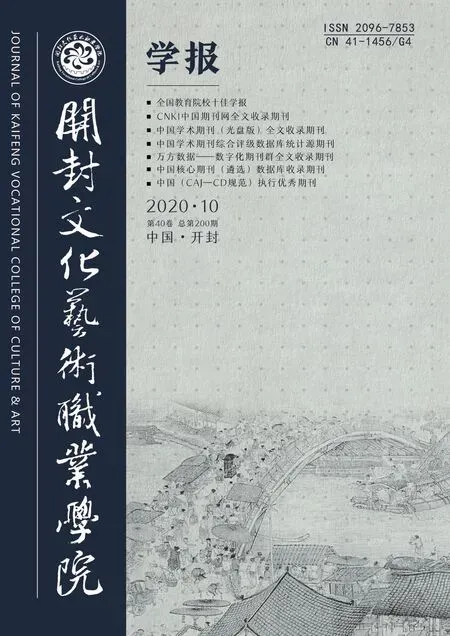論建安時期的騷體文學
張曉紅
(山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一、建安時期騷體文學界定
騷體即楚辭體,以屈原辭作為范式,以 “兮” 字句為本質特征一種的獨立文體,包括騷體賦和騷體詩[1]。
(一)建安時期 “騷” 與 “賦” 的融合
“賦” 興盛于漢代,相較于詩歌和小說而言,它沒有明顯固定的特征。對此,郭紹虞先生認為,賦作為一種文體與詩歌和散文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很大的不同,詩歌和散文有其特定文體特征而賦沒有。中國文學的多種文體中,特征最不明顯的可以說是“賦” 了。賈誼在長沙遭遇貶謫,用騷體寫了《吊屈原賦》,第一次將“騷”與“賦”結合;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正式將 “楚辭” 納入 “賦” 的范疇。
騷與賦的融合使騷體賦應運而生。騷體賦指采用楚騷體式,以賦命題的作品,直接脫胎于楚辭的母體。騷體賦作為賦體文學的一個重要類別,以其抒情性和曉暢明麗的語體特征豐富了賦體文學,騷體賦在建安文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建安時期 “騷” 與 “詩” 的融合
建安時期,文壇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文體形式之一是五言詩,此間的騷體發展呈現出與五言詩融合的趨勢,所表現出的特征是在繼承《詩經》和《楚騷》傳統的基礎上,糅合漢樂府 “緣事而發、感于哀樂” 的寫實手法。加之騷體作為我國詩歌發展的源頭之一,騷體呈現出許多“詩化”特征。同時,出現了用“詩” 命名騷體的現象,如曹丕的《寡婦詩》、蔡琰的《悲憤詩》和曹植的《離友詩》等。
綜上所述,建安時期騷體文學的界定基本從時間、內容、體式三個方面出發。發生在建安時期的,有楚騷體式,以賦和詩冠名的,感于哀樂、即興而發的作品稱為建安騷體文學。
二、建安時期騷體文學的轉變
建安騷體文學與兩漢相較,題材有了較大擴展,不再有強烈的對社會不滿的精神狀態,更注重表現內心世界。體制上表現為短小精悍,句法上騷散結合,藝術風格逐漸轉向慷慨悲涼,這一系列的變化呈現出個性化與抒情化的顯著特征。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空前高揚的時代,建安時期的詩人通常另辟蹊徑,展現自己的獨特風貌,如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曹植骨氣奇高等。
(一)騷體文學的詩化
騷體文學的發展和轉變受所處時代主流文化的影響,其發展到建安時期出現了 “詩化” 傾向,即騷體與當時的五言、七言詩體句融合在一起。
1. 以詩的題材入騷體
戰國時期,屈原、宋玉的騷體作品題材比較簡單,大部分抒發自己的哀怨不平之情。兩漢時期則局限于悲士不遇、玄思神游、紀行抒懷、悼騷寓志等較為狹窄的題材領域,至東漢更因模擬之風而日趨類型化與模式化[1]。到了建安時期,騷體題材有了進一步擴大,有描寫戰爭的,如曹丕的《浮淮賦》、曹植的《東征賦》;歌物詠物的,如曹植的《酒賦》《鸚鵡賦》;描寫民生疾苦的,如曹植的《九愁賦》、曹丕的《寡婦詩》;抒發真摯情感的,如曹植的《洛神賦》、王粲的《登樓賦》,其中《洛神賦》通過夢幻之境,描寫人神間的真摯情感;抒情賦,如曹丕的《登臺賦》、曹操的《滄海賦》;抒發男女之思的,如曹植的《感婚賦》《靜思賦》。如此,詩的題材就被引入騷體文學中,擴大了騷體文學的表現范圍,同時也使騷體文學的特征逐漸模糊。
2. 語言淺近,結構不落俗套
漢大賦以 “美刺” 為主,語言綺麗婉約。建安作家繼承了《詩經》和漢樂府質樸無華的語言特色,更貼近生活,更傾向于抒發真實情感,語言淺顯易懂[2]。比如,軍旅紀行題材的作品,作者直接敘述事情、抒發情感,基本不再用前代紀行賦托古諷今的手法,即使是寫景抒情的作品也是以景襯情,直接抒情。例如,王粲的《思友賦》先寫登高望遠,睹景思人,再寫看到的景物,最后寫悼念之情。這篇騷賦作品,通俗易懂,語言曉暢明麗。
(二)體制短小,騷散結合
建安騷體文學的發展變化還表現在文章體制短小精悍與騷散結合上。漢代騷體文學的篇章字數一般為400 字以上1 000 字以下。建安騷體則有明顯的短篇化趨勢。除此之外,純粹的騷體句式受到很大沖擊,四言、六言等句式進入騷體作品,出現大量不帶 “兮” 字的散體句式[2]。短篇化的騷體增強了一些活潑與生動之美,已不同于東漢騷體的單調。游國恩先生認為:“《鵩鳥賦》是把散文的形式融合在騷體里,賈誼是從《楚辭》到漢賦的過渡作品的頭一個作者。”[3]25-27
三、建安時期騷體文學的審美特征
(一)時代風格
文學家的思維活動與客觀物象緊密相連。一時期的社會風貌對文學作家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劉勰評價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4]42由此,把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歸結為兩種:一種是 “慷慨悲涼”,一種是 “清真自然”。建安騷體文學在這種整體的風格氛圍中也不例外。東漢班固說:“《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 發。”[5]513-514建安主要作家大多直接參與戰爭,或身經戰亂,對戰爭的無情與慘烈有著切身的體驗與認識。因此,與詩歌一樣,建安時期的許多騷體作品在內容上也與當時的戰亂有著密切聯系。“三曹” 與 “建安七子” 也間或用騷體來直接描寫戰爭和軍旅生活,如阮瑀《紀征賦》寫曹軍征伐荊州,曹丕《述征賦》亦述討荊州事,又應玚《撰征賦》記曹軍北伐所見等。
(二)個性風光
騷體文學發展到建安時期,呈現出的個性化和抒情化特征有其特定的原因。這不僅與當時的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有關,而且與騷體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有很大的關系,還與騷體和五言詩、散文等文體的相互聯系有關。但是,騷體文學轉變的最根本原因是作為創作主體的建安時期的作家自身心理素質的轉變。在文學創作過程中,創作主體的思維、心態、個體風格、審美方式等因素與其生活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有很大的關系。建安人格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關注自我人格的獨立和個性的發展。他們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實現這種追求:一種是隱逸山林、保持高潔,如 “建安七子” 的阮瑀年輕時師從蔡邕,因戰火紛爭而辭官,逃向山林隱居;另一種是極力追逐功名利祿,希望建功立業,最為典型的是曹丕、曹植兄弟。例如,曹植的述志詩《雜詩》(仆夫早嚴駕):“仆夫早嚴駕,吾行將遠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涂,東路安足由。 ”[6]13表示其愿意效力朝廷,伐吳建功。曹丕則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7]482建安文人的這種個性風格離不開這一特定的時代風格,特定的時代造就了建安騷體文獨特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