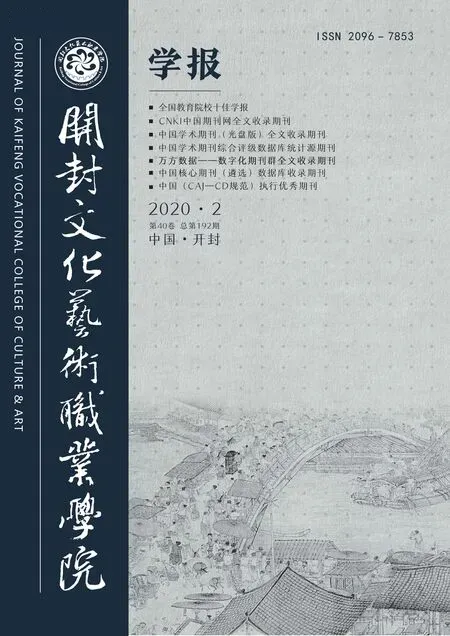近八年《妄稽》研究情況綜述(2011—2018)
竇 晴
(聊城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山東 聊城 252000)
一、研究概況(2011—2018)
(一)文字考釋
部分研究者僅就某字或某句作深入考釋,旁征博引,或證明整理者觀點的正確性,或?qū)ψ至x訓(xùn)讀作解釋說明,如蔡偉、抱小、黔之菜等。蔡偉對簡6“”右側(cè)部件隸定“夭”的正確性作補(bǔ)釋,認(rèn)為其讀音為“镺”,意為長短之長[1];抱小對簡7—8“面盡魿臘”意為“面部之皮膚甚為乾枯”之釋作補(bǔ)證[2];黔之菜論證“孝弟茲悔”一句,稱“悔”可讀為“敏”,語音上“悔”為之部韻,“敏”與其押韻;語義上“悔”(敏)和“孫”(遜)對文,與傳世文獻(xiàn)“敏遜”或“遜敏”相連的情況類似[3]。
但是,多數(shù)研究者是通識全文,將與整理者不同的意見,或雖與整理者意見相同但有更佳例證的觀點提煉出來,形成文字考釋合集。如下:
何有祖對文字考釋提出10 個意見,分別是:(1)簡2“貇”和簡14—15“貇”從豹省聲,讀作貌;(2)簡15“詛”或許讀如字,意為詛咒;(3)簡29“豦”讀作“噱”,意為大笑;(4)簡34“鶱”下部所從應(yīng)為“鳥”;(5)簡35“茝”字以里耶秦簡8-2101“茝”為例,補(bǔ)證整理者的釋字;(6)簡39“哀”字所從呂,為“雍”初文,疑讀作雍;(7)簡40“顴”隸定為“獾”,讀作顴;(8)簡43—44“自教”應(yīng)讀為自效;(9)簡69“”在文中與“短”相對,因此為“長”;(10)簡74“脂”字右部從水從旨,與里耶秦簡8-56“徑”右部寫法相同,應(yīng)釋為涇[4]。
王挺斌對文字考釋作了10 處補(bǔ)充,分別是:(1)簡2 與簡50 釋讀為“肯”的字當(dāng)為“骨”;(2)簡28“壴”(豎)當(dāng)釋為“壹”;(3)簡31“”字如果嚴(yán)格隸定,右邊當(dāng)從“力”;(4)簡36“丸”字應(yīng)為“宂”(冗);(5)簡38“?”當(dāng)為“讙”或“護(hù)”;(6)簡40 的“獾”應(yīng)為“獲”;(7)簡55“死”字當(dāng)釋為“列”;(8)簡64“動”當(dāng)釋為“勭”;(9)簡72+73“妄稽喜差(嗟)”中“喜”表嘆息,可讀為“嘻”;(10)簡74“淫”應(yīng)更似簡40 的“涶”[5]。
喜島千晴補(bǔ)充了8 處釋讀:(1)簡4—5 中“子私”即娶妻之事;(2)簡6“臂八寸,指長二尺”中“八寸”“二尺”表示極長或者極短的抽象數(shù)量,由此“”應(yīng)訓(xùn)為短;(3)簡7“勺(扚)乳繩縈,坐肄(肆)於席”的“勺”可釋為“扚”,形容乳房很長,“縈”訓(xùn)為收卷,“繩縈”謂繩子重疊如環(huán),“肆”可訓(xùn)為陳列;(4)簡7—8“面盡魿臘”的“魿”可釋為“鱗”,“鱗臘”兩字形容妄稽臉部皮膚的狀態(tài),另簡25+26 中“魿”也可以釋為“鱗”;(5)簡11“雞鳴善式,乃尚(當(dāng))人閒(諫)”的“式”應(yīng)讀為“飾”,“人”可能是“入”的誤釋;(6)簡16“謀毋失?子”的“?”有可能是“朋”的抄寫訛誤;(7)簡18“小妾不微(?)”的“小妾”疑為妄稽自稱,“微”訓(xùn)為美;(8)簡19“不念生故”的“生”不可假借為“徃”,“生故”即生計[7]。
衣?lián)嵘J(rèn)為簡7—8“面盡魿臘”中“魿”字應(yīng)作“?”;“長髮誘紿”中的“紿”當(dāng)為“給”,意為豐足;“毋及(急)求勝”的“勝”當(dāng)為“媵”;“乃尚(當(dāng))人間(諫)”中的“人”字應(yīng)改為“入”[8]。
(二)字體字形
目前,僅以《妄稽》所收錄文字進(jìn)行字體字形研究的學(xué)者極少,多數(shù)是以北大簡全部材料與其他文字材料作對比分析,如孫暉、丁玫月與張孟晉,但因研究成果較為宏觀,因此結(jié)論也適用《妄稽》。
孫暉以北大簡對比其他西漢出土簡帛、石刻、銅鏡銘文等,概括出北大簡保存完好、內(nèi)容具文獻(xiàn)意義、可填補(bǔ)西漢中期書法出土文物的空白、書法妙絕等四大價值[9];丁玫月對比北大簡(西漢中期)文字與張家山漢墓文字(西漢早期)的異同,指出西漢中期文字筆畫的規(guī)范化、風(fēng)格特色上扁平化、八分體開始形成以及部件偏旁的簡化現(xiàn)象等變化[10];張孟晉結(jié)合北大簡、睡虎地秦簡、武威漢簡等材料,總結(jié)漢代字體演變,并追求演變原因,認(rèn)為抄書的需要是導(dǎo)致橫扁形體的原因,并將之命名為“抄書體”[11]。
僅就《妄稽》一篇進(jìn)行字體字形分析的學(xué)者極少,所知者如勞曉森根據(jù)《妄稽》“美”字寫法來補(bǔ)正《周馴》的字,對《妄稽》五個“美”字作具體分析,并總結(jié)了《妄稽》“美”字的兩種寫法[12]。
(三)竹簡編連
楊元途對簡文編連提出了以下意見:(1)簡 52—53 原本視為缺簡,但作者考證簡背劃痕和文義認(rèn)為,不缺簡,可銜接;(2)簡63—64 原本依簡背劃痕可視為缺簡,但據(jù)文義和句式來看并不缺簡,因此不排除廢簡的可能[13]。
勞曉森認(rèn)為簡71 左右的編連有誤,其從押韻和文義連貫出發(fā),以簡70 與簡72 直接編聯(lián),即將“方”與“樂窮極”合為一句。勞先生提出,編連之后,簡69、70、72、73 文句文義連貫通順,而且皆押之職部韻[14]。
張傳官提出簡85、86 可與簡71、50 編連,簡42 可編入簡26、41 和簡27 之間;簡61、62 不可直接編聯(lián);簡84、83 可與簡87 遙綴[15]。
(四)文學(xué)研究
黔之菜提出《妄稽》通過對比手法塑造人物,增強(qiáng)藝術(shù)表現(xiàn)力;提出《妄稽》是已知的以“妒妻悍婦”為題材的最早的文學(xué)作品;并據(jù)妒妻的結(jié)局悲劇性,總結(jié)該類題材文章的勸誡作用,窺探當(dāng)時時代背景下文章出世的價值[3]。
廖群聚焦《妄稽》篇的俗賦特征,從文體的沖突戲劇、題材的婚姻故事、賦體的合韻性三方面,論證其屬于誦賦的準(zhǔn)確性,并以妄稽其人的丑女特征與其他丑女形象作對比,以此推測文章的主旨含義[16]。
二、《妄稽》篇研究的成就與不足
總的看來,2011—2018 年的《妄稽》篇的研究在眾多學(xué)者的研究引領(lǐng)下碩果累累:
其一,文字識讀的范圍得以在整理者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擴(kuò)大,釋讀的準(zhǔn)確性在討論中提高,這不僅有益于《妄稽》篇的釋讀、提高文章可讀性,對于同時期或相近時期出土的文獻(xiàn)的釋讀也提供了可供借鑒的依據(jù);同時,對于文字演變規(guī)律的研究具有參考意義。
其二,研究方法有所拓展。在文字釋讀的語音解析、字形分析方面,并用歷時分析、參照對比等方法,關(guān)注文字更細(xì)微、具體的部件;字體字形分析與文字釋讀分析并不孤立,如運(yùn)用字體演繹的趨勢規(guī)律推測字義,提供了視角獨特的文字考釋方法;竹簡編連突破依靠簡背劃痕的藩籬,從上下文義方面開始推敲。
其三,開始出現(xiàn)文獻(xiàn)文學(xué)性研究。《妄稽》殘字?jǐn)?shù)量太多,文獻(xiàn)連貫性差,將文獻(xiàn)的語言數(shù)據(jù)用于文學(xué)研究具有一定困難,但仍有研究聚焦到了其文學(xué)意義乃至社會意義上,對于了解西漢中期家庭倫理或社會風(fēng)氣很有幫助。
當(dāng)然,也有薄弱之處:
其一,文字釋讀的部分觀點只給“讀若某某”的結(jié)論,既未明確考釋過程,也未見佐證材料,其準(zhǔn)確性有待考證;部分觀點以現(xiàn)代觀點揣度文章本意,具有“望文生義”的嫌疑。
其二,針對《妄稽》篇文學(xué)研究的數(shù)量極少。其實文獻(xiàn)前半篇竹簡頗為完整,對妄稽、虞士等主人公的外貌、社會環(huán)境的渲染、人物身份的襯托等描寫頗為豐富,仍有研究價值,文獻(xiàn)殘缺性并非全然阻斷了文學(xué)研究。
其三,對文字釋讀的研究方法仍待創(chuàng)新,尤其是文字歷時研究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鑒于目前對西漢中期文字詞匯的意義、字形發(fā)展規(guī)律缺乏系統(tǒng)的把握,目前的研究較為分散,尚拘泥于專字、專詞釋讀研究,宏觀研究、規(guī)律把握不足,需將《妄稽》與前后期文字乃至不同載體文字研究聯(lián)系起來,以掌握文字演變的基本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