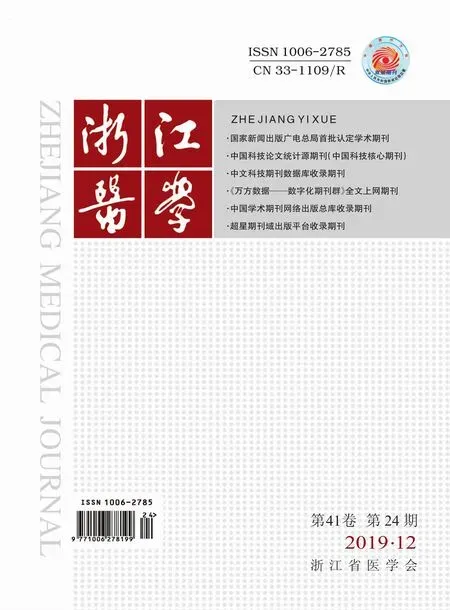推拿結合康復療法對缺血性腦卒中后手功能障礙患者腦功能變化的研究
狄樺 杜紅根 汪凡 呂亞婷 丁忠祥 朱博文
研究顯示,超過80%的腦卒中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手功能障礙[1],且只有3%的患者手功能能恢復到原來的70%以上,15%的患者只能恢復到約原有功能的50%[2]。由于手部功能與日常生活能力緊密相關,因此恢復手功能的能力對患者生活質量尤為重要。
運動治療是腦卒中后手功能障礙的首選療法。目前主要有運動療法、作業療法、物理因子療法和各種腦、神經、肌肉刺激技術等[3],但由于手部活動精細,功能受損后恢復相對困難,因而在傳統康復治療基礎上探求各種可能對手功能提高有效的方法顯得十分關鍵。我們在臨床中發現推拿對于手功能的恢復有著良好的改善作用,但機制不明,因此本研究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 技術探討在康復訓練基礎上聯合推拿療法對腦卒中后手功能障礙的改善效果及可能的作用機制。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15年1至12月在浙江省人民醫院康復醫學科、神經內科及針灸推拿科住院部和門診就診的缺血性腦卒中后手功能障礙患者30例。納入標準:(1)無磁共振檢查禁忌者;(2)符合缺血性腦卒中后手功能障礙診斷標準[4]的右利手患者;(3)患側手Brunnstrom分級Ⅰ-Ⅴ期;(4)納入研究前未接受中醫推拿、康復治療;(5)患者自愿加入本試驗,并由本人或直系親屬代為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反復腦卒中發作或既往發作者;(2)合并蛛網膜下腔出血、顱內腫瘤、頭顱外傷患者;(3)重大疾病者;(4)生命體征不穩定的患者。按照Brunnstrom分級水平分層,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推拿聯合康復治療組(研究組)及康復治療組(對照組),每組15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手功能障礙水平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本研究經浙江省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同意,研究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的比較
1.2 方法
1.2.1 干預方法 兩組均由固定的康復治療師根據患者具體病情,給予Bobath、Brunnstrom、運動再學習的康復訓練[5],1次/d,40min/次。研究組在康復治療后加用推拿治療,推拿治療由指定推拿醫師進行,1次/d,30min/次。兩組均以10d為1個療程,每個療程間隔2d,共治療3個療程。推拿治療操作如下:患者取俯臥位,以摩法沿督脈由下到上摩長強穴至大椎穴3遍;由上至下按揉足太陽膀胱經背部第一側線、第二側線3遍;由下至上捏脊3遍;擦腎俞、命門,以熱為度。患者取俯臥位,以指按法或掌按法刺激背部異常反應點(具有條索狀、結節樣反應物的部位或肌肉緊張、痙攣的位置)5min。患者取仰臥位,拿揉患側上肢5min;按揉手三陰經,手三陽經并配合肩、肘、腕、指間等相應關節的被動運動10min;點按臂臑、曲池、手三里、外關、內關、合谷諸穴,每穴30s;從上至下搓揉患肢3遍。分別捻患指,從掌指關節到手指尖,并拔伸指尖關節各3遍,健側與患側均進行操作。
1.2.2 磁共振檢測方法 使用浙江省人民醫院放射科SEIMENS Trio 3.0T高場磁共振標準頭顱CP極化線圈完成 rs-fMRI掃描。采用 FE(field echo)三軸位,9s,定位相。TSE(turbo sPin echo)T1加權相軸位、T2加權相軸位,FLAIR(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軸位,總計4min3s。磁共振實驗參數:全腦高分辨率3D-T1-MPRAGE 像:TR/TE=8.5/3.2ms,flip angle=15°,matrix=256×256,field of view=250×250mm2,slice number=176,slice thickness/gap=1/0mm,3min27s。基于 Matlab平臺下使用SPM8、DPARSF軟件、REST軟件完成靜息態功能磁共振數據。通過MRIcro軟件將DICOM數據轉換,剔除靜息態數據中前10個重復的時間點及頭動校正平動大于1mm或轉動角>1°的數據。功能圖像重切為3mm×3mm×3mm 的體素。濾波處理頻帶范圍 0.01~0.08Hz。圖像進行平滑處理。將手運動區(額葉眼動區)作為種子點(坐標:X=15、Y=0、Z=78)。
1.3 觀測指標
1.3.1 Fugl-Meyer手運動功能評分量表[6]觀測手的粗大運動功能及上肢遠端(手)高水平運動功能的恢復。評分標準為每項檢查內容根據完成情況分別獲得0、1和2分,共計66分,分值高表明手運動功能佳。
1.3.2核磁共振觀測指標(1)低頻振幅[7](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差值:ALFF 通過利用Bold信號的高低,反應體素自發活動水平的高低,從而直接顯示區域性大腦活動的改變。(2)種子點功能連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由于標記的種子點(本研究以手運動區,坐標:X=15、Y=0、Z=78作為種子點)與各個腦區之間Bold信號波動呈時域相關性,即區域間血氧水平信號波動表現出高度的時域相關,因此通過種子點FC便可觀測哪些區域與種子點組成了一個緊密相關的神經網絡。兩組患者入組時及治療結束后,由顯著差異的體素提取出:差異點所在的腦區、腦區所在布洛德曼分區(brodmann area,BA)的分區情況、腦內具體坐標、團塊中所包含的的體素個數。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0.0統計軟件。將種子點與全腦其他體素時間序列系數進行Fisher變換轉換成近似高斯分布,取兩組差值標準化后行雙樣本t檢驗,以P<0.05并團塊的體積不少于5個體素認為有統計學差異。計量資料以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治療前后Fugl-Meyer評分的比較結果 見表2。

表2 治療前后Fugl-Meyer評分的比較
由表2可見,治療前兩組患者Fugl-Meyer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Fugl-Meyer手指運動功能評分較治療前均顯著提高(均P<0.01),研究組改善程度優于對照組(P<0.05)。
2.2 ALFF差值結果 見表3、4。

表3 ALFF值增高的腦區

表4 ALFF值降低的腦區
由表3、4可見,與對照組相比,研究組額上回、中央前回、中央旁小葉、中央后回、顳下回、海馬旁回及扣帶回ALFF值增高,小腦區山頂及后葉ALFF值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 種子點FC結果 見表5、6。

表5 功能連接增強的腦區

表6 功能連接減弱的腦區
由表5、6可見,功能連接增強的腦區有:左側額中回、右側楔前葉、右側中央后回、左側枕中回、右側梭狀回、左側顳下回、右側島葉、右側海馬旁回、右側小腦后葉、右側小腦山坡。功能連接減弱的腦區有:左側中央后回、左側尾狀核、左側小腦前葉、左側小腦山坡。
3 討論
Fugl-Meyer手運動功能評分結果說明,推拿對腦卒中后患者的手功能恢復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腦卒中后,由于患側大腦的結構或功能上的缺失,導致對健側大腦抑制出現失衡。加之健側大腦代償性的活動增強,又加重患側的抑制作用,進一步導致雙側大腦失衡。因此我們推測:推拿是否可以通過增強雙側運動功能腦區的活動或增強運動相關腦區功能連接功能,從而幫助腦卒中后患者手功能的恢復?
為了觀測推拿后腦區的活動情況以及是連接功能的存在與否,本研究選擇ALFF差值來觀測腦區活動情況,選取手運動區(額葉眼動區)的種子點(坐標:X=15、Y=0、Z=78)來觀測其他腦區與之的網絡連接情況。人的隨意運動包括運動準備及運動執行[8]。而手運動的準備中樞位于初級運動區,主要受中央前回等腦區控制[9],執行中樞位于次級運動區,由扣帶回等區主導[10]。本研究結果發現:研究組患者的右側中央前回及左側扣帶回運動區素體個數均表現為ALFF增高,說明推拿可使卒中后手功能患者的手部隨意運動能力增強。右側額上回、中央旁小葉及中央后回均表現為ALFF增高,說明推拿對于卒中后患者手功能運動的籌備、執行以及激活復雜運動也有一定的幫助。而顳下回、海馬旁回及扣帶回素體個數ALFF增高,表明對于憑借記憶組織并啟動復雜的運動序列有促進作用。研究表明,手功能的運動激活的雙側腦區呈不對稱性[11],且以對側為主[12],而同側運動通路是否有利于患者功能恢復仍存在爭議[13]。ALFF值降低的腦區結果顯示:左側小腦后葉及右側山頂ALFF值均降低,這不僅說明推拿可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健側小腦腦區的活動,協助腦區恢復平衡,而且也為同側腦區運動通路激活促進患者功能恢復提供了證據。
在腦卒中后,由于大腦網絡神經發生了損害和改變,使腦網絡的連接也發生變化——大腦皮質間的有效的連接和增效代償的減少。腦卒中后運動功能恢復即大腦功能重塑的過程,在中皮層水平的代償表現為周圍皮層重構[14],新的皮層間連接模式形成,包括代償區或之前并無直接聯系的區域間形成新的連接模式[15],這些均可在fMRI上有所表現。手運動大部分復雜運動功能有賴于雙側小腦的激活完成,雙側小腦同時參與手運動的籌備、執行過程。種子點FC結果顯示:小腦的連接功能呈雙側性改變,右側腦區功能連接增強較多,左側腦區以降低功能連接為主,且激活區域與ALFF結果中的激活區基本重疊,這表明推拿治療可促進腦卒中后手功能障礙患者的雙側小腦腦功能的網絡連接。邊緣系統中,海馬旁回中的素體數為3 511,這說明兩組間海馬區,體感皮層、體感聯合皮層、視覺性、聽覺性、運動性語言區、視覺性語言區以及邊緣系統在內的情緒、高級認知功能區存在著一定差異。大樣本回顧性研究表明人類左側海馬區的大小該區域與運動功能明確相關[16]。海馬區主要負責學習和記憶,卒中后運動模式的重建與改變與海馬區功能亦有一定關聯[17]。因此我們推測推拿對上肢及手運動功能的改善可能是通過記憶、情緒、高級認知功能區對運動-學習模式的影響來實現。
量表是目前對于腦卒中后手功能的主要評估方法[18],而卒中后的治療是長期持續性的,并非一過性,因此選擇一種合理的評價指標,消除量表中具有主觀性評價的偏倚,對于探索手功能康復的機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本研究中,我們通過fMRI對前后間隔3個療程的卒中后手功能患者進行數據掃描,降低患者即時產生的酸脹疼痛、緊張情緒等效果造成的假陽性結果,并剔除兩組間相同干預,進而觀察推拿對腦卒中后手運動功能恢復的情況,從中樞水平上對作用的機制進行探討,以期為臨床中長期持續性干預手段的機制探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