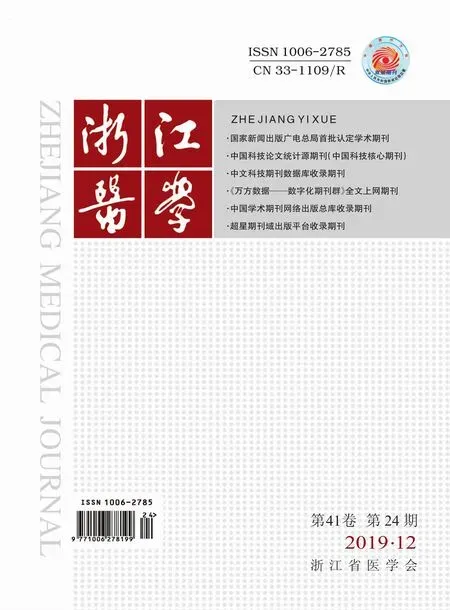心房顫動導管消融術后并發肺靜脈狹窄2例
楊婧 黃小萍 徐寧
作者單位:315010 寧波市第一醫院呼吸與危重癥科
環肺靜脈電隔離術已經成為當今治療心房顫動的主要方法,肺靜脈狹窄(pulmonary venous stenosis,PVS)是心房顫動患者導管消融術后嚴重并發癥之一,極易引起誤診、漏診。現將我科收治的2例心房顫動導管消融術后PVS患者的臨床資料報道如下。
例1患者,男性,31歲。因“反復咳嗽、咳痰3個月,再發伴咯血3d”于2018年9月1日入院。患者3個月前曾行心房顫動導管消融術,術后1周出現發熱、咳嗽,當時胸部CT提示左肺下葉炎癥,左側胸腔少量積液,予抗感染治療后體溫好轉,但咳嗽反復。3d前患者咳嗽較前加重,出現少量痰中帶血,胸部CT提示左肺炎癥伴左側胸腔積液。入院體檢無明顯陽性體征。入院后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針(商品名:鋒泰林,上海上藥新亞藥業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H19990179)抗感染,實驗室檢查提示血常規、超敏C反應蛋白(hs-CRP)、D- 二聚體、腫瘤標志物、血氣分析均在正常范圍,多次痰培養及痰找抗酸桿菌無異常,心臟超聲未見明顯異常。經治療后患者咳嗽稍好轉,但仍有痰中帶血,復查胸部CT,左下肺病灶較前增多。考慮患者有心房顫動導管消融手術史,發病是否與導管消融相關,遂行多層螺旋CT肺血管造影,結果提示左肺下靜脈開口處管腔局限性狹窄(圖1)。此時再次復查心臟超聲,提示左下肺靜脈血流顯示欠佳。患者PVS診斷明確,轉至心內科行靜脈支架植入手術。患者術后隨訪1個月,訴咳嗽、咯血癥狀均緩解,復查胸部CT,左下肺病灶基本吸收,胸腔積液消失。
例2患者,男性,57歲。因“反復咳嗽、咳痰伴咯血2個月,加重1周”于2015年4月24日入院。患者2個月前無明顯誘因下出現咳嗽,伴有痰中少量血絲,患者未予重視,癥狀反復。1周前上述癥狀加重,咯鮮紅色血塊,伴有發熱,最高體溫37.8℃,胸部CT提示左肺炎癥,左側胸腔積液。外院予抗感染治療效果不佳,且咯血量增多,遂轉至我院。患者6個月前曾因心房顫動行導管消融術。入院體檢提示左下肺呼吸音偏低,血常規示白細胞數5.8×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63.4%,hs-CRP 37.9mg/L,D二聚體、血氣分析、痰培養均未見明顯異常。當時予莫西沙星針(商品名:拜復樂,拜耳醫藥保健公司生產,國藥準字J20140110)抗感染,CT肺血管造影示左下肺靜脈干閉塞(圖2),PVS診斷明確。患者出院自行至上級醫院行靜脈支架植入手術,1周后電話隨訪,訴未再咯血。討論PVS是心房顫動消融術后并發癥之一,定義為肺靜脈內徑較消融前減小20%以上[1],其發生與導管消融術的消融技術、部位、射頻能量、溫度等因素相關[2]。既往報道中該病的發病率差異較大,0~42%不等[2]。近年來,隨著對PVS風險認識的提高以及導管消融技術的改良,該病的整體發生率已降至1%左右[3-4],但由于缺乏典型的臨床癥狀,實際發病率或高于臨床預估[5-6]。

圖1例1患者的CT肺血管造影(箭頭示左下肺靜脈局限性狹窄)

圖2 例2患者的CT肺血管造影(箭頭示左下肺靜脈干閉塞)
導管消融術后PVS的病理生理機制尚不清楚。有動物實驗顯示,射頻能量會損害血管壁和支氣管,導致內膜增厚、血栓形成、細胞外基質沉積和彈性層的增殖,最終導致肺靜脈狹窄[7]。有研究者追蹤了導管消融術后患者肺靜脈的狹窄情況,發現2年隨訪期間共有11例肺靜脈出現明顯狹窄,而在導管消融手術結束時通過血管造影檢測到狹窄率超過50%的肺靜脈僅有5例,這表明PVS是逐步進展的[5]。根據肺靜脈的狹窄程度,分為輕度(20%~49%),中度(50%~69%)及重度(70%以上)[1,8],癥狀的發展和嚴重程度一般與所涉及的血管數量及狹窄程度有關[8]。癥狀多出現在術后平均(4.0±3.0)個月[9],往往無明顯特異性,表現為咳嗽、咯血、胸痛、反復呼吸道感染等,嚴重狹窄患者還可出現呼吸困難及運動耐量下降,完全靜脈阻塞的患者則有發生肺梗死的風險,表現為嚴重的胸痛和咯血[9-10]。除非大部分肺靜脈引流受到影響,肺動脈高壓的發生概率一般較小[11]。然而由于代償及側支循環建立的原因,部分患者可無明顯臨床癥狀[8],因此極易被漏診、誤診。從我院收治的2例患者臨床資料分析:(1)癥狀均出現導管消融手術后3個月內;(2)臨床表現無特異性;(3)胸部CT提示病變均位于左下肺,表現為滲出性改變及少量胸腔積液,積液產生的原因可能與靜脈回流受阻有關。因此對于有心房顫動病史,術后3個月內出現呼吸系統疾病表現,尤其合并咯血、病灶位于左下肺的患者,需要高度警惕PVS的可能。
肺靜脈造影目前仍為診斷PVS的金標準,不僅可準確檢測靜脈狹窄的程度,還可測量肺動脈壓力,但是其為有創檢查,風險較大。CT肺血管造影及磁共振血管成像(MRA)通過三維重建從不同角度直接顯示解剖結構,評估肺靜脈狹窄的部位與程度,可作為臨床首選[10,12]。經食管超聲心動圖(TEE)可以根據血液動力變化診斷PVS,但由于食管的干擾,TEE無法監測到遠離左心房開口部位的深靜脈狹窄[13],有一定局限性。在診治例1患者時,第1次超聲檢查未能發現病變,之后在提醒了超聲醫生后,再次復查才發現左下肺靜脈血流異常,因此臨床解讀這類患者的超聲檢查結果時,需警惕因操作者主觀因素導致的遺漏。
無癥狀、輕度狹窄的患者一般無需治療,但建議根據PVS的程度隨訪觀察或3個月后復查CT肺血管造影或TEE[2]。Fender等[9]對124例導管消融術后的PVS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發現,對部分無癥狀的患者進行治療干預后,患者的心肺功能均能得到改善,提示這類患者雖未表現出臨床癥狀,其心肺功能水平已隨著PVS的出現而呈現一定程度的損害。對于有癥狀及重度PVS的患者,需要接受介入治療。現有的介入方案主要包括球囊擴張和支架植入,哪一種更好仍有爭議,但這兩種方案術后均有一定的再狹窄率[14-15]。經治療后,大多數患者的臨床癥狀能得到緩解。
綜上所述,心房顫動導管消融術后PVS的發生率目前雖不高,但屬于嚴重并發癥。在心房顫動導管消融術后3~4個月常規行CT肺血管造影或MRA有利于早期發現及診斷PVS[2]。對于有心房顫動消融手術史、術后出現呼吸系統疾病表現的患者,應特別注意PVS的可能性,避免漏診、誤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