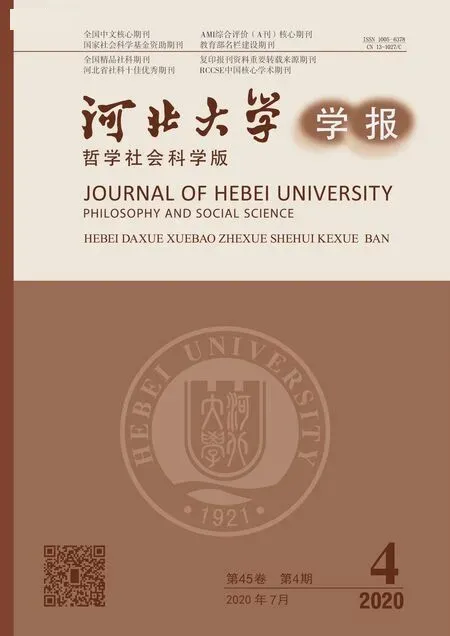儒、商互動與晚明郎署文學權力之下降
薛 泉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儒(士)、商互動問題,是明代文學史上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話題,同時也是研治晚明文學不可或缺的文學、文化常識。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探究,多囿于其對士風、文風之浸染,鮮有涉獵其與郎署文學權力之關系。深入考察儒、商互動的文化意蘊,及其與郎署文學權力下降之關系,不僅關乎對晚明文學歷史定位的客觀體認,還牽涉對明代文學,尤其是對晚明文學發展、演變歷程及其動力的宏觀審視與整體把握,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奢靡世風下的儒、商互動
迨及嘉靖年間,由于土地兼并嚴重,徭役日重,加之陽明心學之浸潤、朝廷控制力的減弱,明代工商業漸趨繁盛,市民階層日益壯大。包括文士在內的明人,生活方式、審美情趣、思想觀念等,較之其前,皆已發生很大變化。許多文人士大夫對人生富貴的追求,對物欲、人欲的追逐,不僅不再遮遮掩掩,甚至還有堂而皇之的闡釋。王文祿即稱: “人恒言富貴,不言貴富,富先貴,何也? 廉子曰:‘財利者,民之心義之和也。’由今觀之,貴亦求富而已。”[1]卷二《良貴篇》,第351頁結合自身低級官吏出身,王氏將廉子之言普泛化,由民及官,推演出 “貴亦求富” 的觀點。有些士人非但對傳統儒家所排拒的奢靡不以為然,反而別出心裁,為之注腳。陸楫即言: “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 奢侈不但無害、不可恥,反可催生出新行業,提供諸多就業機會,有益百姓生計。若人皆節儉,不尚奢華,有人會因此營生成為問題。只要不暴殄天物,奢侈又何妨! 陸楫還引經據典,為奢侈的合理化,尋求理論依據,稱此 “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2]卷六,第640頁。嘉靖、萬歷初人葉權、萬歷間的王士性等,持論也多相類①(明)葉權撰,凌毅點校:《賢博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頁。(明)王士性撰,呂景琳點校:《廣志繹》卷四,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9頁。。
與富貴、奢侈觀念緊密相關的,是對世俗物欲、色欲的追逐。有士人已毫不掩飾,赤裸裸地展示對此之企羨。如袁宏道《龔惟長先生》所欣羨的五種 “真樂” ,即 “五快活” ,除第三種 “快活” 屬精神層面的追求,余皆為物質層面的奢豪企羨。明中后期,追逐人欲、物欲的奢靡風氣, “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3]卷三《莊氏二子字說》,第85頁,快速蔓延至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張瀚就慨嘆道: “二三十年間,富貴家出金帛,制服飾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為隊,搬演傳奇;好事者競為淫麗之詞,轉相唱和;一郡城之內,衣食于此者,不知幾千人矣。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4]卷七,第139頁欲望追逐是無止境的,甚至到不問家之有無的地步: “人之有欲,何所底止? 相夸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嘆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為人笑也。文之敝至于是乎? 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3]卷三《莊氏二子字說》,第85頁在 “以侈靡相高” 全民競賽式的消費潮流中,商品 “原有的‘自然’使用價值消失了,從而使商品變成了索緒爾意義上的記號,其意義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參考系統中的位置來確定。因此,消費就決不能理解為對使用價值、實物用途的消費,而應主要看做是對記號的消費”[5],它已成為社會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成為崇富尚虛的時代標識。
不過,物欲、色欲的逐取,在多數情況下還是要 “問家之有無” 的,需以金錢、財力為后盾。這就不能不牽涉與之相關的擇業,以及對商賈、商業的看法與定位問題。 “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6]卷十三,第111頁,為官致富是士人不二的人生抉擇。嘉靖以后,有士人顛覆了這種擇業觀,對四民之末的商賈及商業,開始重新審視,商賈的作用逐漸得到正視。嘉靖四年(1525),王守仁為蘇州商人方麟作《節庵方公墓表》就稱: “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就其心。”[7]卷二十五《外集》七,第1036頁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九《贈芝麻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中,蔣生自以為 “經商之人” ,不敢高攀出身仕宦之家的馬小姐,馬父卻道: “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 商賈也逐漸得到時人的同情與理解。李贄即謂商賈 “挾數萬之貲” ,既要 “經風濤之險” ,還要 “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 ,方可謀利,此 “何可鄙之有?”[8]卷二《又與焦弱侯》,第49頁況且,正是由于他們,物品才得以流通,農業生產才更有保障,恰如張居正所言: “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9]卷三十六《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第465頁而且,商人也是能 “修高明之行” 的。李夢陽引王文顯語即云: “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10]卷四十四《明故王文顯墓志銘》,第1257頁汪道昆所謂 “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11]卷五十五《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閔氏合葬墓志銘》,第1146頁,也著眼于此。如此,商賈在四民中的次序,便躍居至士之后、農工之前,即所謂 “商賈大于農工”[12]。由此直接導致事商者大增,有的 地 區 “去 農 而 改 業 為 工 商 者,三 倍 于 前 ”[6]卷十三,第112頁。 尤 其 是 徽 州 地 區,竟 “三 賈 一儒”[11]卷五十二《海陽處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銘》,第1099頁,且經商已儼然成為第一等職業。汪道昆就稱徽州風俗 “左儒而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11]卷十八《蒲江黃公七十壽序》,第381頁。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疊居奇程客得助》亦稱: “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 如此一來,科舉失利者,可在家人的理解與支持下,安心事商。馮夢龍《古今小說》第十八卷《楊八老越國奇逢》載,楊八老 “年近三十,讀書不就” ,與妻商量,決定棄儒從商,妻勸其 “不必遲疑” 。后來,楊八老歷盡艱險, “安享榮華,壽登耆耋” 。對某些士子來說,經商不僅可致富,還有反哺效應,頗益于科舉。如農家子弟徐敦,家貧, “試有司不利” ,選擇從商,三十歲致富后, “復謝賈事儒” ,晝夜苦讀,補為州學生。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官至南京監察御史[13]卷二十六,第442頁。如果沒有經商致富為依托,徐敦可能會無法安心讀書,獵取功名。這實是一種 “出儒入商”[11]卷四十《儒俠傳》,第856頁,出商入儒的士商互動行為,為當時不少人所接受。如,休寧人金源有 “兩女弟,為蘇、汪家婦” , “其可儒者資之為儒,其可賈者資之為賈”[14]卷六十九《金子長家傳》,第194頁。程所聞之父六虛翁, “子姓二十許人” ,也是 “力任儒則儒,力任賈則賈” 。在他看來, “賈以本富,無淫于末;儒以行先,毋后于文”[14]卷三十五《程翁壽序》,第253頁。這樣,一家之中可 “儒、賈并興” ,各有所得。海陽人張于彝,教其三子,因材施教,不拘科舉一途,其家即以 “儒、賈二業并興” ,為人稱道[14]卷二十四《張于彝詩序》,第32頁。這是根據自家實際做出的選擇,能儒則儒,能商則商,就如汪道昆所言: “蓋詘者力不足于賈,去而為儒;贏者才不足于儒,則反而歸賈。”[11]卷五十四《明故處士谿陽吳長公墓志銘》,第1142頁在此,儒、商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于此,蘇州商人方麟,看得較明了,他 “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 。其友問: “子乃去士而從商乎?” 他笑曰: “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士乎?”[7]卷二十五《外集》七《節庵方公墓表》,第1036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傳統本末觀念的一種挑戰。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 “出儒入商” 的背后,依然著有傳統觀念的底色。社會對商賈持寬容態度,人們羨慕商賈生活的奢華,并不等于普遍認同 “商賈大于士” 。經商為第一等職業,主要是在一些商貿活躍的地區。在多數人心目中,依然是 “士大于商賈”[12],讀書為官仍為人生最佳歸宿,徐敦棄商從儒,便是力證。陜西商人王來聘,更是了然于此,他曾數次訓導子孫: “四民之業,惟士為尊;然而無成,不若農賈。”[14]卷一百六《鄉祭酒王公墓表》,第154頁從商是讀書無成后的無奈選擇,即使在商業發達的徽州地區,也有人如此。休寧人詹杰,令長子經商,次子讀書,看似通脫,實則因長子非讀書材料。當他得知次子喜好古文辭,而不攻時文時,便怒罵道: “若薄制科業不為,若能舍而自取通貴乎? 今國家方重科第,以籠豪杰殆盡,而吾詹獨寥寥焉,使我愧稱詹。且吾所以不棄若賈者,何意也?”[15]卷九十一《詹處士墓志銘》,第486頁詹杰以詹姓登第者寥寥,深感慚愧。他寄予厚望的次子,偏又喜古文辭,怎不令其怒發沖冠! 他 “所以不棄若賈” ,是要以雄厚的財力作為子嗣博得高第的物質后盾。看來,由商入儒,走仕途經濟之路,仍為許多商賈家夢寐以求。汪道昆雖言其鄉 “左儒而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 ,但其骨子里依然 “右儒而左賈” : “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則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不萬鐘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單厚然乎哉,擇術審矣。”[11]卷五十二《海陽處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銘》,第1099頁“弛儒而張賈” ,非長久計,僅為 “畢事儒不效” “才不足于儒”[11]卷五十四《明故處士溪陽吳長公墓志銘》,第1142頁之權宜,實屬無奈之舉。若要 “為子孫計” ,終究要 “弛賈而張儒” 。對多數儒生而言,最終目的是博得一第。然而,因科舉錄取名額有限,再加之時運等因素制約,即使有足夠的才華與財力,成功概率也微乎其微。屢敗屢試的歸有光,體會剴切: “天下士歲試南宮者,無慮數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3]卷十九《曹子見墓志銘》,第467頁蟾宮折桂,難于上青天。袁中道 “望五之年,得此一第”[16]卷二十五《與四弟五弟》,第1069頁,已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相對來講,從商致富的成功率要大得多: “士而成功也,十之一;商而成功也,十之九。”[17]《豐南志》第五冊《百歲翁狀》,第251頁這是士人取其次而從之,出儒入商的重要動因。
正因 “士大于商賈” ,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及其所擁有的社會聲望,頗為世人看重,一些心有所求的商賈,不惜花費巨資,主動與其結交,尤其是時賢、名流,更受青睞。歙縣商人鮑簡錫經商浙東,就 “結納四方名流,縞纻往還,幾無虛日”[17]《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卷二《仲弟無傲行狀》,第144頁。黃明芳也 “好接斯文士,一時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徵明、祝允明輩,皆納交無間”[17]歙縣《竦塘黃氏宗譜》卷五《雙泉黃君行狀》,第86頁。黃氏交際圈中,不僅有文人名士,還有王鏊一類的高官、名流。商賈希望借此能進入主流文化圈,或提升自身影響與價值。即便不能如此,也可求得名人詩文、字畫等,以附庸風雅。文人士大夫對商人的態度,也今非昔比,從上文王守仁、汪道昆、李維楨等言論,不難感受到。士大夫文人所以樂意與商賈交往,也多有個人利益考量。王世貞與徽商詹景鳳的一番對話,頗耐人尋味:
鳳洲公同詹東圖在瓦官寺中,鳳洲公偶云: “新安賈人見蘇州文人,如蠅聚一膻” 。東圖曰: “蘇州文人見新安賈人,亦如蠅聚一膻。” 鳳洲公笑而不答。[18]
士、商交往與互動,多基于雙方互惠互利,這為詹景鳳一語中的,王世貞只好 “笑而不答” ,料其也無以對答。在與商賈互動中,不少文人士大夫的人品、節操也隨之勢利化、世俗化,甚至墮落,淪為視金錢 “如蠅聚一膻” 之徒。文元發曾嘆隆、萬間士風道: “昔之士大夫,每持風節,不屑與非類交游;不似今之人,視銅臭之夫,如蠅之集膻也。”[19]商賈求名、士人逐利,成為士、商互動的基礎與重要動因。鐘惺《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即云:
富者余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余之貲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20]卷三十五,第649頁
文人刻書資金短缺,商賈以余貲相助,著述者可流芳后世,出資者也可因之留名。一舉兩得,各得其所,何樂而不為? 士、商互惠互利,表現多端,此僅其一。
儒、商的互動,使這兩個階層的關系變得密切起來,造成了商而士、士而商,士商相混的現象,模糊了士商界限。這對晚明文學,影響深遠。一方面,它促使包括郎署文人在內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學寫作、文學觀念,不斷商業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還是 “性靈” 說的催生劑。同時,也使得一些郎署文人開始鐘情通俗文學,自動參與到通俗文學的創作、刊刻、批評與傳播中。這從內外兩個層面,對郎署文學造成重大沖撞,致使郎署文學權力下降①文學權力的內涵,非常豐富、復雜,因行文所限,不展開論析。本文所謂文學權力,主要指文學話語權,故文中二者時而互用。文學話語權是掌控文學輿論、文學導向,以及文學影響的一種特殊權力。還可理解為行動者對有價值文化資本的大量占據與擁有,以及對文學場域中有利位置的占據。。
二、儒、商互動與上層社會適用文體的普泛化、世俗化
“如果說樹碑立傳的儒家文化向來是由士大夫階層所獨占的,那么16世紀以后的整個商人階層也開始爭取它了”[21]。這也是商賈樂于與文人、士大夫交往的一個重要動機。另一方面,在與商賈的交往過程中,郎署文人應請托,為商賈及其親人撰寫了不少壽文、碑銘志傳、序跋之類的文章。現流傳下來僅為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因藏于私家,未刊行于世,或已散佚。僅保存下來的,也頗能說明問題。遠且不論,弘治、正德年間,李夢陽就曾與商賈作家有交往,并為之撰寫了一些墓志碑傳。如《空同先生集》中的《處士松山先生墓志銘》(卷第四十三)、《梅山先生墓志銘》(卷第四十三)、《鮑允亨傳》(卷第五十七)、《明故王文顯墓志銘》(卷第四十四),就分別為蘭陽商人丘琥、徽商鮑弼、鮑允亨,以及蒲州商人王文顯所作。《方山子集序》(卷第五十)、《潛虬山人記》(卷第四十七)、《缶音序》(卷第五十一),即為商賈文人鄭作、佘育、佘存修詩文集而作。
嘉靖以還,此現象更為普遍,不僅商賈如此。唐順之曾諷之曰: “仆居閑,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后則必有一篇墓志。”[22]卷六《答王遵巖》,第276頁萬歷二十九年(1601),李樂所撰《見聞雜記》,進一步佐證了唐順之之言論: “唐荊川先生集中誚世人之死,不問貴賤賢愚,雖椎埋屠狗之夫,凡力可為者,皆有墓文。此是實事。”[23]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張嘉孚亦言: “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即有一部遺文;生但余幾錢,死即有一片志文。”[24]卷六《恥志文》這一方面是為附庸風雅,另一方面也是為墓主 “不可俾遂泯泯無傳”[25]卷二十九《南京大理寺卿孟公墓志銘》,第247頁。受此風淫染,王世貞、汪道昆、李維楨等,也為商賈及其親人撰寫了許多此類文章。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稿》中,為商人撰寫的碑銘墓表志傳行狀,較之李夢陽等人,數量激增。陳建華先生統計,李夢陽《空同集》中有傳記45篇,為商人所作4篇,約占總數的9%。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墓志銘(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銘、墓碑、行狀)總數有90 篇,為商人所作15篇,約占總數的16.6%。《弇州山人續稿》中墓志銘(種類同上)的總數250 篇,為商人所作44篇,約占總數的17.6%[26]。陳書錄先生統計,《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稿》中,墓志銘(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銘、墓碑、行狀)總數340篇,為商人所作59篇,約占17%。另外,《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稿》中,還有多篇為商賈作的傳記,傳主多為徽州、蘇州商人[27]。商人出身的汪道昆,為商人及其親屬所作碑銘志傳之類的文章,數量更多。《太函集》中,有傳記(包括傳、行狀、墓志銘、墓碑、神道碑)212篇,其中為商人及其家庭成員所作就有112篇(傳主本人為商人者77篇;其余為商人家庭成員,如父母親及妻子等),超過傳記總數的50%。另外,還有為商人或其父母親所撰33篇壽序或贈序,其中大部分都有關于商人生平事跡的記載與描述。無論在汪道昆以前,還是與他生活在同一時期的非徽州籍作家,恐怕沒有誰為商人樹碑立傳如此之多[28]。此類文章多半是 “因賈人之請”[29]3,應其 “好名之心”[30]《煤客劉祥墓志銘》,第429頁而作。而且,已有不少商人以正面形象進入了文學作品。如潘處士 “有心計,言利事,析秋毫。然如布帛之有幅焉,毋過取。又立義不侵”[14]卷八十七《處士潘君墓志銘》,第533頁;樊傅 “積而能散,振人之厄,好義聲聞四遠”[14]卷九十六《樊季公馮孺人墓志銘》,第720頁;金泮 “多知善謀,察時宜物情,應之屢中,又闊達有大度”[14]卷一百一十四《金仲子暨配孫孺人行狀》,第320頁。這類商人在 “三言” “二拍” 等小說中,比比皆是。郎署文人為商賈及其親友大量撰寫壽序、墓銘墓表志傳行狀,使得這些原本多用于上層社會的應用文體,開始走向商賈、市井細民,日漸普泛化、世俗化。
為他人撰寫壽文、碑銘墓表志傳行狀,自唐宋來有收取潤筆費的慣習,盡管時遭人詬病。在商業大潮沖擊下,伴隨著賣文治生行業的興盛,中晚明文人、士大夫為人撰文,也隨之商業化,收取潤筆費或公開標價售文,愈發顯得天經地義。
就連王世貞之類的高官,也難以免俗。鄧儼之子鄧仲子 “間而損書幣以其姊夫左參議熊惟學之狀” ,向王世貞 “請傳” ,王欣然應允,為之撰《鄧太史傳》[15]卷七十三,第291頁。這實是一種變相的售文現象,也是一種世俗的商業行為。賣文之收入,對某些人來說,還頗為可觀。李夢陽晚年罷官家居, “以其據紛華之地,而多賣文之錢”[30]《李崆峒傳》,第606頁,生活相當滋潤。差者也基本能維持生計,屠隆離職返鄉后,主要靠 “賣文為活”[31]卷二百八十八《文苑四》,第7388頁。有的名流賣文還明碼標價,如張鳳翼不屑于以詩文、字翰交接貴人。乃榜其門曰: “本宅缺少紙筆,凡有以扇求楷書滿面者,銀一錢;行書八句者,三分;特撰壽詩、壽文,每軸各若干。” 盡管如此,不妨礙 “人爭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32]。隨著買方市場的擴大,還催生出賣文代辦人或經紀人。如,李維楨 “其文章,弘肆有才氣,海內諸求者無虛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 ,其 “門下士招富人大賈,受取金錢,代為請乞,亦應之無倦”[31]卷二百八十八《文苑四》,第7386頁。
對于求文者說,這是一種文化消費;對應求者而言,不失為一種治生手段,至少也可平添些許額外收入。求文者關注的是能否得到名人之文,供其講排場,附庸風雅;而對作品質量,一般不甚關心。再說,他們也多缺乏相應的鑒賞能力。應求者于此,多心照不宣,撰文時往往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歸有光《陸思軒壽序》即云:
東吳之俗……獨隆于為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于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為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故凡來求文為壽者,常不拒逆其意。[3]卷十三,第334-335頁
求壽文者,只為壽宴上壁間生輝,赴宴者多 “飲酒而已” ,真正的欣賞者,鳳毛麟角。鑒于這種情形,應求者以為 “文不必其佳” ,撰寫時也不會花太多心思。因有幣贄收入,故 “常不拒逆其意” 而 “應之無倦” ,無形中工作量劇增。撰者為圖省心,加之文體特征所限,寫作上多流于程式化①歸有光《李氏榮壽詩序》: “余嘗謂今之為壽者,蓋不過謂其生于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概其生平而書之,又類于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 (明)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卷十二,第306頁。,有人干脆事先為 “活套詩” ,以備隨時應付:
受其費者,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有利其贄而厭其求者,為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33]卷十五,第189頁
以上說的是嚴格意義上的 “活套詩” ,至于套用他人成句的寫作現象,更屢見不鮮。王世貞有多首壽九十老翁詩作,起句就直接套用白居易 “九十不衰真地仙”[15]卷二十,第333-336頁詩句。還有人乃至取先前舊作,易名應酬,忙中出錯,貽人笑柄:
張士謙學士……或冗中為求者所逼,輒取舊作,易其名以應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謙文為贈。后數月,復有人求文送別駕,即以守文,稍易數言與之,忘其同州也。二人相見,各出其文,大發一笑。[34]卷四,第33頁
有些應求者,特別是那些有名望者,因出于種種原因,不愿或不便親力親為,常請人捉刀代筆。徐渭即做過此事: “某自稍知操筆以來,當郡邑諸公于去來贈餞間,靡不來以管毫授者,曰:禮則然也。然禮然而心未必然者,固亦不能無矣,蓋彼雖不言,而某固陰察其然也。”[35]卷十九《送山陰公序》,第563頁連王世貞之類的名流,也有請人代筆之嫌。屠隆就曾向王世貞請為代筆之役,以貼補家用。就應求者言之,無論親為還是請人代耕,多 “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為之”[35]卷十九《肖甫詩序》,第534頁,容易導致 “其所為文者,與其人了不相蒙”[36]。如果再遇上文學素養不高的代筆者,代文質量,可想而知。
總的說來,此類文章 “多率意應酬,品格不能高也”[31]卷二百八十八《文苑四》,第7386頁,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郎署文學的寫作質量,削弱了其影響力,弱化了其文學權力。
三、儒、商互動與 “性靈說” 的催生及郎署文人對通俗文學的關注
在儒、商互動的過程中,出身于商賈的文士,其個體性格、行為方式、消費理念,不僅影響著郎署文人的寫作風貌,甚至還制約著其文學觀念的衍化,催生出新的文學觀念,從內部自我削弱郎署文學權力。如李夢陽意識到詩歌抒情的重要性,強調 “感觸突發,流動情思” ,追求 “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10]卷五十一《缶音序》,第1462頁的審美效果,就與和徽商佘存修、佘育的交往、互動,甚為有關。王世貞晚年 “自悔” ,所標舉的 “性靈” 說,也與商賈影響,有一定關聯。蘇州為明代商貿發達地區,生于斯長于斯的王世貞,難免會沾染些商賈習氣;入仕后,他輾轉各地為官,與商賈多有交往,從中獲益良多。如,徽商程子虛曾拜謁他, “以文事相命,大出其槖裝為贄” 。為刊刻李攀龍全集,王世貞還特請其出資相助: “足下如有意乎不朽于其間,為數卷助,何如?”[37]卷一百二十八《答程子虛書》,第138頁他甚為欣賞那些商賈出身的文人特有的氣質、性格,稱道徽商詩人吳汝義 “好以吟詠自適”[37]卷六十九《吳汝義詩小引》,第157頁,稱贊蘇州商賈張實 “讀書獵大較,不好為章句,棄之。北走燕,遴其游閑公子,日馳章臺傍,揳琴,揄袂,砧屣,陸愽,從耳目,暢心志,衡施舍。蓋期年而橐中千金裝行盡,乃歸” ,并稱 “雅已從吳門豪少年慕說隱君(張實)者” ,主動向其子張獻翼 “征其事” ,以為之傳[37]卷八十四《張隱君小傳》,第321頁。這與請托為文,無論在寫作動機,還是為文心態上,皆不可同日而語。商賈文人的 “吟詠自適” “從耳目,暢心志” 的性格與作風,也濡染著王世貞,與其 “性靈說” ,有諸多契合之處。
前、后七子郎署官奉行 “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 策略所導致的擬古寡情,向來為世人詬病,王世貞晚年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此進行了反思。他重新評估其早期作品以及李東陽、蘇軾之作,并以其推崇的李攀龍擬古樂府為突破口,斥責機械擬摹,謂之 “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并看,看則似臨摹帖耳”[38]卷七,第1066頁,指責其摹擬痕跡過濃。在王氏看來, “剽竊模擬” 乃 “詩之大病”[38]卷四,第1018頁,他批評 “后之人好剽寫余似,以茍獵一時之好,思踳而格襍,無取于性情之真”[37]卷六十六《章給事詩集序》,第154頁,提倡 “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38]卷一,第964頁,認為 “未可以時代優劣也”[38]卷四,第1007頁。為此,他援引 “性靈” 一詞論詩,《藝苑卮言》有曰:
顏之推云 “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為捫舌。[38]卷八,第1088頁
在 “自悔” 少年為詩作文或染 “神厲志凌之病” 的同時,王世貞拈出 “性靈” 一詞,別有深意。這一詞,多次出現于其論詩中①如《湖西草堂詩集序》: “顧其大要在發乎興,止乎事,觸境而生,意盡而止。毋鑿空,毋角險,以求勝人而劌損吾性靈。”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六,《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36冊,第616頁)《鄧太史傳》引熊惟學之語,稱傳主鄧儼: “喜為詩,謂其能發性靈,開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繪。君子以為知言。”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三,《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37冊,第292頁)《余德甫先生詩集序》稱余曰德: “歸田以后,于它念無所復之,益搜劌心腑,冥通于性靈,神詣獨往之句,為于鱗所嘉賞。”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五十二,《明別集叢刊》第3輯第37冊,第58頁)。王世貞 “性靈” 說的核心,是注重真性情的抒發,它開啟了郎署文學向公安派 “性靈” 文學過渡之津梁。而恰恰是公安派以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39]卷四,第187頁為旨歸,重創了后七子郎署文學: “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其功偉矣”[40]丁集中《袁稽勛宏道》,第567頁“其(袁宏道)詩文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復靡然而從之”[41]卷一百七十九《袁中郞集》,第1618頁。可以說,王世貞先從內部自我消解了郎署文學權力,之后又遭公安派的猛烈掊擊,郎署文學權力大為下降。
公安派興起后,文人標舉 “性靈” ,已成為時尚。郎署文人也難脫其寖染。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鄭元勛,在晚明商業大潮的滌蕩下,力主 “以文自娛” 說。陳繼儒《文娛敘》有曰: “往丁卯前,珰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愿為文昌,但愿為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元勛)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42]卷首,第1頁“以文自娛” ,同時還可 “悅人” ,鄭元勛《文娛自序》云:
文以適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俠客、忠臣、騷人、逸士,皆能快其臆而顯攄之,故能談歡笑并,語怨泣偕。彼有隱約含之不易見者,進則為圣為佛,退則一玩鈍者之不及情而已。吾以為文不足供人愛玩,則六經之外俱可燒。六經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悅人性情也。[42]卷首,第1頁
“文以適情” “怡人耳目,悅人性情” 之內涵,較 “以文自娛” ,稍顯寬泛,顯然與公安派性靈說有相通處。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 “就詩文批評本身而言,文娛說產生的基礎是性靈說。創作上獨抒性靈的自適態度,與鑒賞上以美為宗的文娛說是相輔相成的。”[43]這進一步從內部削弱了在公安、竟陵沖擊下日漸式微的郎署文學影響力,使其文學權力不斷下降。
不僅如此,儒、商互動還引起郎署文人對通俗文學的關注,使其自覺參與到通俗文學的創作、編刻、批評與傳播之中。由于市民階層的壯大,商業文化與時俗之浸染,借助于江南地區發達的刻書業,通俗文學迅速興盛起來。葉盛稱: “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婦,尤所酷好。”[44]卷二十一,第213-214頁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包括郎署文人在內的不少士人,開始關注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樣式,認識到其獨特的審美價值。陸深、都穆、文徵明、沈周、祝允明等人, “好藏稗官小說” “其架上蕓裹緗襲,幾及萬籖,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粱肉,讀者習為故常;而天廚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45]卷二《藏說小萃序》,第576頁。戲曲方面, “今則自縉紳、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為新聲者,不可勝紀”[46]卷四,第167頁。
前后七子派郎署文人,也難脫此風羈絆。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等就關注過民歌、時調,康海、王世貞、汪道昆等,還親自參與到戲曲、小說創作與刊刻、傳播中。尤其是王世貞、汪道昆、屠隆等,更專注于此。
王世貞不僅創作了傳奇《鳴鳳記》,還有系統的戲曲理論,后獨立成冊,是為《曲藻》,表現出對通俗文學的高度關注。其中,關于南北曲的用詞、各自的長短優劣、戲曲 “體貼人情,委曲必盡”[47]33等問題的闡發,頗有理論價值。汪道昆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編成《大雅堂雜劇》四種,即《五湖游》《高唐夢》《洛水悲》《遠山戲》,并刊刻于自家書坊—— “大雅堂”①劉尚恒:《安徽古代出版史述要》,《安徽出版資料選輯》第1輯,黃山書社1987 年版,第170頁。劉學林:《試論徽州地區的古代刻書業》,《文獻》1995 年第4 期,第202 頁。。屠隆少年時就喜好戲曲,嘗自言: “少頗解此技,嘗思托以稍自見其洸洋,會奪于他冗。”[48]《棲真館集》卷十一《章臺柳玉合記敘》,第198頁其流傳下來的戲曲有《曇花記》《彩毫記》《修文記》三種,稱為 “風儀閣傳奇” 。猶如王世貞,屠隆不僅創作戲曲,還注重理論的歸結。藝術上,他大力提倡 “雅俗并陳、意調雙美” “雖尚大雅,并取通俗諧□,□□不用隱僻學問,艱深字眼”[48]第11冊《曇花記·凡例》,第4頁,以為 “傳奇之妙,在雅俗并陳,意調雙美、有聲有色、有情有態。歡則艷骨,悲則銷魂。揚則色飛,怖則神奪。極才致則賞激名流,通俗情則娛快婦豎。斯其至乎!” 創作主體上,他強調戲曲創作者應有才,最好是 “通才” “傳奇一小技,不足以蓋才士,而非才士不辨,非通才不妙”[48]《棲真館集》卷十一《章臺柳玉合記敘》,第198頁。這是晚明時期的重要戲曲批評理論。
小說方面,汪道昆親為《水滸傳》作敘②明新安刻本《水滸全傳》卷首《水滸傳敘》末署曰: “萬歷己丑孟冬天都外臣撰。” (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王利器校注:《水滸全傳校 注》附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1頁。)萬歷己丑,即萬歷十八年(1589); “天都外臣” ,指汪道昆。沈德符釋之曰: “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郭勛)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9頁。,闡釋其文學主張。該序文比較系統地探析了通俗小說構思的虛實、章法的繁簡、藝術風格等問題,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如汪氏認為, “史又言淮南,不言山東。言三十六人,不言一百八人。此其虛實,不必深辨,要自可喜” , “紀載有章,煩簡有則。發凡起例,不難易于。如良史善論繪,濃淡遠近,點染盡工;又如百尺之綿,玄黃經緯,一線不紕。此可與雅士道,不可與俗士談也”[49]3939。胡應麟也給予《水滸傳》極高的評價,不僅稱其 “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 ,還高度評價了其人物塑造的個性鮮明、拿捏得體: “第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詠嘆之工,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者。”[50]卷四十一《莊岳委譚》下,第437頁
郎署文人關注通俗文學,從事戲曲、小說的創作、刊刻與傳播,不僅分散了其從事正統詩文寫作的時間與精力,也降低了其作品所謂 “品位” 。因為,在正統文人(包括一些郎署文人)看來,小說、戲曲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至多也不過有補于正史而已,其關注點多在于正人心、淳教化③(明)李贄:《焚書》卷三《忠義水滸傳序》,第110頁。(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九流緒論》下,第283頁。。這也從郎署內部,削弱了其所擁有的文學權力。
結 語
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晚明商賈游走于市井與文人士大夫之間,成為聯系士大夫與市井的重要紐帶。郎署文人與商賈互動,實際上也與市井產生了互動。再說,有些郎署文人本來就與市井有諸多接觸。士人逐利、商賈求名,名利互補,是奢靡世風之下儒、商互動的基礎與重要動力。儒、商互動,造成士商相混,模糊了士商間的界限,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覺不自覺地調整、改變著自家寫作風貌,先前多適用于上流社會的一些應用文體,很大程度上因之而走向商賈、市井之家,逐漸世俗化,降低了其應有的文化 “品位” 。另一方面,它還是新的文學觀念 “性靈” 說的催生劑;同時,又激發起一些郎署文人對通俗文學的興趣,使其主動參與到通俗文學的創作、刊刻、批評與傳播流程中。郎署文人與商賈的互動,從內外兩個維度,對郎署文學造成了很大沖撞。在山林文學沖擊下正在流失的郎署文學權力(已另撰文論之),又受創于商賈、市井文學,郎署文學權力因之大為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標志著晚明文學開始由以傳統詩文為主的雅文學,逐漸向以小說、戲曲為重心的通俗文學轉型。可以說,儒、商互動與晚明郎署文學權力之關系,為我們觀察晚明文學的發展演進,提供了一個相對別致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