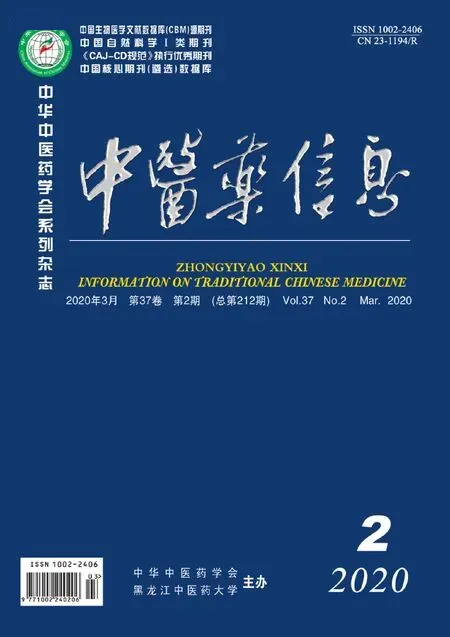基于“肺與大腸相表里”淺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夏衍婧,黃艷輝
(1.湖北中醫藥大學,湖北 武漢 430000;2.武漢市中醫醫院,湖北 武漢 430000)
2019年12月以來,從湖北省武漢市到我國其他地區及境外陸續發現了多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2020年1月30日,WHO已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針對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將其命名為“SARS-CoV-2”, 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正式命名為“COVID-19”。SARS-CoV-2屬于β屬冠狀病毒,其基因特征與SARSr-CoV和MERSr-CoV有明顯區別,人群普遍易感,主要經呼吸道飛沫和接觸傳播。患者以發熱、乏力、干咳為主要表現,少數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瀉等癥狀。重癥患者多在發病1周后出現呼吸困難或低氧血癥[1]。
“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是來源于《靈樞》,立足于整體觀的中醫經典理論,也是中醫臟腑表里學說的重要理論之一。其理論的重點就在于對肺系疾病的發生、發展及其治療、防控的闡釋,對指導臨床COVID-19防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筆者根據“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及公開的病例報道等相關資料,做出中醫理論指導下的理性的分析與推斷,以期為COVID-19的防治提供有益的參考。
1 “肺與大腸相表里”的理論闡述
《靈樞·經脈》曰:“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大腸手陽明之脈,……絡肺,下膈屬大腸”。 肺與大腸通過經脈間的相互絡屬,構成臟腑表里關系,二者在生理病理上關系密切。肺主氣,司呼吸,主宣發肅降、通調水道,朝百脈,主治節;“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大腸傳導糟粕,吸收津液。肺主宣發肅降、通調水道,與大腸主津的作用相互配合,參與了水液代謝的調節,使大腸既無水濕之患,又無津枯之害,保證了大便的排泄正常。肺氣以清肅下降為順;大腸以通為用,其氣以通降為貴。肺與大腸之氣化相通,故肺氣降則大腸之氣亦降,大腸通暢則肺氣亦宣通。《馮氏錦囊秘錄·雜癥大小合參》云:“大腸為肺之腑,大腸既有濕熱留滯,則肺家亦必有邪滯不清”。因此臨床治療肺系疾病時,常佐以調理腸腑,腑氣得通,肺氣亦調。
“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的現代研究主要從組織胚胎學、物質傳遞以及腸道微生態環境等方面闡述。肺、氣管與腸的結構來源是相同的,這是組織胚胎學理論的基礎[2]。部分學者發現肺臟和部分腸道在P物質(SP)、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指標中有關,說明肺與大腸可能是通過血管活性腸肽(VIP)、SP、CGRP等神經肽物質相互影響,說明肺和大腸相表里具有物質相關性[3]。目前研究表明肺和腸道菌群有著同步變化規律,這也可能是“肺與大腸相表里”的機制之一[4]。其中,腸道微生物學說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
2 基于“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分析COVID-19
2.1 正虛邪實是COVID-19的根本病因
《素問·刺法論》曰:“正氣存內, 邪不可干。” 《靈樞·百病始生》言:“風、雨、寒、熱, 不得虛, 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 蓋無虛, 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 與其身形, 兩虛相得, 乃客其形。”明確指出了正虛邪實是疾病發病的一般規律。
正虛是指免疫力低下,現代人工作繁忙、生活緊張、作息紊亂、基礎疾病多,飲食再不加節制,脾胃亦虛,胃腸功能紊亂,腸道菌群失調。脾胃為先天之本,脾胃虛弱,則氣血生化乏源,正氣不足,易感受客氣邪風。《柳葉刀》2020年1月29日刊載的對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的首批99例COVID-19患者的流行病學和臨床特征進行的回顧性分析證明了這點, 該研究發現患者的平均年齡為55.5歲,40歲以下患者僅占10%,50歲以上患者占比67%。其中51%患者患有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和腦血管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消化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惡性腫瘤和神經系統疾病。并且在11個死亡病例中有5例年齡大于60歲,8例淋巴減少,7例雙側肺炎,3例高血壓,3例吸煙者[5]。
邪實是指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即SARS-CoV-2,為人類首次發現,目前研究顯示與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bat-SL-CoVZC45)同源性達85%以上,體外分離培養96 h左右即可在人呼吸道上皮細胞內發現。武漢市屬北亞熱帶季風性氣候,常年雨量豐沛、熱量充足、雨熱同季,且江河縱橫,有大小湖泊166個,被稱為“百湖之市”。加之2019年末至2020年初武漢呈現暖冬,給病毒的滋生創造了合適的環境。
縱覽各個學者對COVID-19病因病機的認識,說法不一,矛盾大多集中在寒或熱以及是否存在“濕”。如鄭榕等認為此次COVID-19多屬寒濕疫毒為患[6],而馬家駒等認為濕熱內蘊為內在基礎[7]。如項瓊等以濕為關鍵病機,提出“濕毒疫”概念,認為濕毒郁于肺為總病機,提倡以宣肺利濕、芳香化濁法來治療[8]。 而李曉鳳等認為真正病機是感受風熱疫毒之氣,外風引動內風,木勝乘土,加重脾濕內阻,木火刑金而發病[9]。出現以上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難以做到三因制宜,每個人、地方、病情發展階段均可能出現不同的病機變化,但無論以何種病機為落腳點,正虛邪實都為根本矛盾點,并結合四診合參,辨證論治。
2.2 腸道微生物群紊亂是COVID-19發病的可能關鍵因素
在微生態平衡狀態下,正常腸道菌群起到生物拮抗、營養作用、免疫作用、抗衰老及抗腫瘤作用。在微生態失調狀態下,菌群則由生理性組合轉變為病理性組合,成為致病因素[10]。
基于“肺與大腸相表里”的理論,COVID-19病位在肺,腸道微生物紊亂病位在大腸,當SARS-CoV-2感染時,邪毒犯肺,肺氣宣發肅降失常,水液代謝失調,肺氣不降,則腑氣不通,糟粕傳導失常;當腸道微生物紊亂時,胃腸功能失調,脾胃運化失常,則肺氣虧虛,加之SARS-CoV-2侵襲,肺部感邪,肺氣宣降失常,出現干咳等呼吸系統癥狀。
全身炎癥反應過度激活是重癥肺炎的基本病理特征, 也是造成多器官功能障礙發生的重要病理因素。陳曦等通過比較重癥肺炎與健康患兒的腸道菌群變化和外周血和血清中的炎癥因子、應激因子,發現重癥肺炎患兒存在腸道菌群紊亂, 益生菌雙歧桿菌減少、致病菌大腸桿菌增多且紊亂的腸道菌群能夠加重病程中全身炎癥反應及應激反應的程度[11]。當腸道微生物群失調時,一方面, 腸道內的潛在致病菌如SARS-CoV-2因此乘機移位到口咽部, 再下行致呼吸道深部導致下呼吸道感染,另一方面, 腸源性的內毒素被增多的革蘭陰性桿菌大量釋放并進入血液, 通過體循環和肺循環進行肺臟, 造成肺部感染和肺組織損傷,同時在免疫方面, 腸道微生物群失調導致T淋巴細胞數量和比例減少以及體液免疫衰退[12]也增加了SARS-CoV-2的感染可能。
2.3 臨床佐證
COVID-19患者除呼吸系統癥狀外,可伴有腹瀉等消化系統癥狀,存在部分患者首發癥狀僅為腹瀉的情況[13]。目前已有研究表明,SARS-CoV-2通過細胞受體-血管緊張素轉換酶Ⅱ(ACE2)進入宿主細胞,ACE2不僅在肺AT2細胞、食管上段和分層上皮細胞中高表達,而且在回腸和結腸的吸收腸細胞中高表達,表明消化系統是SARS-CoV-2的潛在途徑[14]。李萍等報道有2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糞便SARS-CoV-2核酸陽性,且其中1例病例咽拭子標本SARS-CoV-2核酸檢測呈陰性[15]。因此,SARS-CoV-2除經呼吸道飛沫和接觸傳播外,消化道傳播是有可能的。
針對COVID-19的治療,李蘭娟院士團隊的人工肝血液凈化系統及“四抗二平衡”救治模式初現成效,同時采取微生態平衡的治療方法,做好腸內營養,補充微生態調節劑[16]。李蘭娟院士團隊救治模式的初現成效證明了從腸道微生物出發治療COVID-19的可能性及有效性。
3 基于“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提出COVID-19的診療策略
3.1 將腸道微生物作為COVID-19的判斷指標
現有多例報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咽拭子標本SARS-CoV-2核酸檢測存在假陰性[17],建議將糞便SARS-CoV-2核酸檢測作為COVID-19的診斷指標并常規檢測。但現有臨床報道病例較少,期望更多病例發現用于研究。建議同時送檢口鼻咽拭子標本和糞便標本進行SARS-CoV-2核酸檢測,以期提高核酸檢測的陽性率。
有研究比較了40例不同預后的重度顱腦損傷手術后患者的腸道菌群變化,結果顯示腸道微生物分布與接受腸內營養的重度顱腦損傷手術后患者預后相關,有益菌的存在對其愈后有促進作用[18]。為此,建議以腸道微生物作為判斷COVID-19預后轉歸的指標之一,并以此指導臨床用藥。
3.2 健脾益氣中藥輔助糾正腸道微生物紊亂防治COVID-19
從脾胃論治是糾正腸道微生物穩態的關鍵。大腸與脾胃皆與消化系統有關,是以治療上應當健運脾胃為主。脾胃得運,一方面,氣血生化正常,機體得以濡養,稍佐益氣之品,肺氣得養,衛氣則盛,邪不可干;另一方面,脾主升清,胃主降濁,腸腑得通。因此干咳、發熱、乏力、腹瀉等COVID-19癥狀得以緩解,特別是對于伴有腹瀉或便秘等消化系統癥狀者,建議在針對呼吸系統疾病用藥時輔助調脾胃,通腸腑,以加快COVID-19癥狀改善以及預后。
現已有部分健脾中藥被證實可以改善腸道微生物紊亂,如參苓白術散、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等[19]。如滕晉等觀察了參苓白術顆粒聯合美羅培南對老年重癥肺炎住院患者腸道菌群失調的影響,發現參苓白術散與抗生素聯用比單純應用美羅培南更加有利于平衡腸道微生態, 從而改善重癥肺炎的感染情況[20]。
3.3 維持腸道微生物穩態以減少COVID-19繼發感染
趙健等對30篇文獻報道的3 904例ICU重癥患者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早期進行腸內營養有助于降低肺炎發生率和住院時間。而腸內營養對腸道微生物影響很大,可以改變腸道微生物群的功能代謝[21]。重癥患者大多存在腸道菌群失調,因此建議在對癥治療同時做好腸內營養,維持腸道微生物穩態以減少激發感染。
3.4 從修復腸道微生物平衡出發改善COVID-19患者預后
COVID-19重癥患者治愈后會遺留一定的肺纖維化,勞動耐力和肺功能可能會有一定的下降,雖然體內會產生抗體,但抗體保護時間尚無法明確,不排除有再感染風險[22]。因此,促進機體恢復和避免再感染是治愈患者防護的重點。Biagi E等認為,益生菌可能有助于預防和治療與年齡有關的病理生理狀況,例如恢復和促進免疫功能,參與各種抗炎機制[23]。因此,建議從修復腸道微生物平衡出發,使用健脾益氣類中藥或益生菌等調節腸道微生物的藥物促進患者機體恢復,預防再感染。
4 結語
綜上所述,基于“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從脾胃論治,健脾益氣中藥可能有助于改善COVID-19患者病情及預后,并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變、愈后防復。建議將腸道微生物作為COVID-19病情的判斷指標。但目前專門針對COVID-19患者腸道微生物群改變的報道甚少, 本研究僅僅是從理論上初步探究其發病和發展規律, 提供更多的思路,供臨床一線醫生參考借鑒,期待進一步的研究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