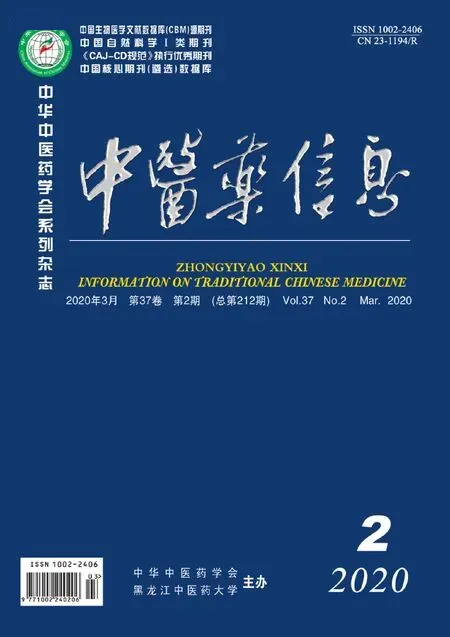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單純性肥胖的研究進展
杜立杰,杜麗坤,周海麗
(1.北京仁和醫院,北京 102600;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單純性肥胖是指全身脂肪過量堆積僅是因為攝入過多或能量消耗過少,無其他明顯病因引起的肥胖癥。其發病病因尚不明確,是一組異質性疾病,在肥胖癥中約占95%[1],可能與遺傳、環境、心理等若干致病因素相關。現代醫學對于單純性肥胖的治療主要以藥物和手術治療為主,不良反應及副作用較多。中醫藥在治療單純性肥胖方面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療效。古人雖未將肥胖定義為一種疾病,但很早就有關于肥胖的描述。《靈樞》中描述土形之人的體貌特征酷似今日之肥胖患者。肥胖的發生與過食肥甘厚味、某些特殊疾病如痰飲、脾腎功能不足等有關。中醫治療多以湯劑、針灸及中醫其他療法如穴位埋線、推拿點穴、循經刮痧等為主,療效顯著。本文對近年來中醫藥對于單純性肥胖的治療方法綜述如下。
1 病因病機
1.1 中醫學
眾多醫家根據古代的傳統理論,認為肥胖者本虛標實,本為脾虛,標為痰濕。吳小慧[2]認為,單純性肥胖主要因為是脾失健運、痰濁內聚,由此可分為脾虛濕阻、脾虛痰瘀、濕熱困脾、脾腎陽虛4型。李超德等[3]認為,大多肥胖患者為痰濕體質,痰濕是肥胖的基本病因,該理論對肥胖的臨床診治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段娟等[4]指出,基于患者的個體差異以及臨床證候的不同表現,從機體的氣化功能方向考慮,用“虛、實、虛實相間”來辨證。羅守濱[5]認為,肥胖是以氣虛痰濕偏勝為主要病機,病因較多,臨床辨為胃熱滯脾型、脾虛不運型、痰濕內盛型、脾腎陽虛型4型。黃蕙莉[6]亦贊同病機為氣虛痰濕壅盛的理論,主要歸因于脾,辨證為脾虛濕阻證、痰濕內盛證、脾腎陽虛證3型。王東[7]認為,肥胖的病機分虛實,虛為氣虛兼夾痰濕,實者為胃熱濕阻,依據病機辨為脾虛濕阻和胃熱濕阻2型。脾胃功能減弱致運化失司,飲食、水液均運化障礙,久之可轉變為體內的痰濁,內聚而致肥胖;同時指出了肥人痰濕內盛,日久則血濁而成瘀血,血為氣之母,瘀血可阻礙氣的功能,致氣輸布津液的能力減弱,最終形成氣虛痰濕兼血瘀的證候。
1.2 現代醫學
單純性肥胖作為一種異質性疾病,其發病病因尚不明確,可能與遺傳、環境、心理等若干致病因素相關。最新研究表明其與腸道的菌群紊亂、脂肪組織慢性炎癥或某些激素水平等也有一定的關系。總體講能量的攝入大于消耗,多食或消耗減少,或兩者兼有都可導致肥胖,也就是機體能量攝耗失衡。研究表明[8],FTO(Fat Mass Obesity Associated)是與肥胖關聯最強且最確切的基因,其主要致病因素是單核苷酸多態性變異。Turnbaugh等[9]研究也發現,肥胖患者腸道中厚壁菌門明顯增高,擬桿菌門相應減少。有學者[10]發現,在肥胖小鼠脂肪組織內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過表達,為肥胖和慢性炎癥提供了最先的聯系紐帶,首次提出肥胖是一種全身性的慢性低度炎癥狀態,由不同炎癥因子誘導產生。瘦素可以抑制人體對食物的攝入、調節體內能量代謝,是一種調節能量使之平衡的激素,可以反映高血脂癥的病程進展[11]。GLP-1是一種腦腸肽,由回腸內分泌細胞分泌,因為其可抑制胃排空,減少腸蠕動,因此可減少攝食,降低體質量。范可軍[12]將180例T2DM患者,根據是否肥胖分為肥胖組(100例)與非肥胖組(80例),采用ELISA法測定血清GLP-1水平,發現肥胖組患者的GLP-1水平低于非肥胖組患者(P<0.05)。
2 治療
2.1 中藥復方治療
中藥復方可以調節人體氣血陰陽、祛邪扶正,還可以通過患者病情改變而隨之加減[13],在治療單純性肥胖方面廣泛應用。段陽泉[14]采用二陳湯加減治療痰濕中阻型和濕熱內蘊型2例肥胖患者,痰濕中阻型患者加入厚樸、枳實、川芎、夏枯草、石菖蒲等,濕熱內蘊型患者加入黃芩、黃連、澤瀉、車前子、大黃等,均持續服藥3個月,體質量分別由90.5 kg、103 kg下降到73 kg、87 kg,且肥胖的諸多癥狀如頭暈頭重、咳嗽痰多、胸悶等均得到明顯緩解,療效顯著。
王洪源[15]隨機納入56例單純性肥胖患者,將其分為對照組(28例)和治療組(28例),對照組給予桔紅丸治療,治療組組給予中藥湯劑導痰湯加減(組方:茯苓15 g、陳皮12 g、枳實10 g、半夏10 g、甘草6 g、膽南星12 g),治療1周后,治療組臨床療效顯著,對照組臨床療效較治療組欠佳。治療組與對照組總有效率分別是85.71%和60.72%。
2.2 針灸治療
針灸可以對人體經絡腧穴起直接作用,有調精養精、調節陰陽的作用,最終達到增強人體抵抗力的目的,用于單純性肥胖患者可以改善其臨床癥狀體征。金宇[16]選取門診治療的36例患者,給予針刺治療,主穴:腹部任脈、足陽明胃經腹部及大腿部的循行線穴位,配穴:豐隆、足三里。采用排針法沿任脈腹部、足陽明胃經大腿部循行線進針,深度1~1.2寸,對足陽明胃經腹部經穴梁門、太乙門、天樞、水道采用合谷刺,足三里、豐隆行瀉法。隨機選腹部穴位進行疏密波、連續波交替進行的電針刺激。1天進行1次,1個療程為6次,2個療程后,與治療前比較,體質量、腰圍、臀圍、 BMI、脂肪含量、基礎代謝率均顯著下降(P<0.01),大腿圍、手臂圍均下降(P<0.05),治療前后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
李思康等[17]納入80例單純性肥胖患者,使用常規針刺法針刺雙側滑肉門、大橫、梁丘、足三里、中脘和氣海等穴位。記錄患者治療前后的體質量、BMI、體圍(腰、圍、上臂及大腿的圍度)以評定療效。經統計學分析,結果顯示患者的體質量、 BMI及各部位圍度均有顯著下降,總有效率為76.3%,其中患者肥胖前期、Ⅰ度肥胖、Ⅱ度肥胖患者的效率分別為58.3%,83.3%,85.7%。可見針刺治療該疾病可顯著降低體質量,達到改善體型的效用,且對Ⅰ度和Ⅱ度肥胖效果顯著。
2.3 其他療法
中醫藥治療疾病手段多樣,還包括穴位埋線、推拿點穴、循經刮痧等,直接作用于患者肥胖部位,對于改善患者的肥胖體征療效顯著。段云慶等[18]將50例單純性肥胖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25例)和對照組(25例),治療組給予穴位埋線治療,取雙側滑肉門、足三里、豐隆,中脘、天樞、氣海、關元為主穴。取合谷、四滿、曲池、脾俞、胃俞、大腸俞、三焦俞為配穴,間隔15天治療1次,4次為1個療程;對照組穴位選擇同治療組,采用常規針刺方法,每日1次,留針30 min,10次為1個療程,間隔3~5天,繼續下一個療程,觀察治療3個療程。治療后觀察組總有效率(96%)明顯高于對照組總有效率(80%)(P<0.05)。
李慧梅等[19]采用推拿點穴的治療方法觀察對脾虛濕阻型單純性肥胖患者的療效,研究方法為給予治療組(33例)以推拿點穴加平衡飲食及運動的方法,每周治療3次,包括背部、胸腹部和四肢部經脈循行部位,每次為40 min,治療12次為1個療程,共計2個療程。對照組(34例)僅采取平衡飲食和運動相結合的方法。每周測量1次各項數據,包括體質量、BMI、腰圍、臀圍等。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78.8%)明顯好于對照組總有效率(29.4%)。
毛丹旦等[20]采用隨機數表法將80例單純性肥胖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各40例,對照組給予飲食、運動管理,觀察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循經刮痧,以平補平泄、補刮為主,包括背部兩側夾脊穴、腹部任脈、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和手太陰肺經的循行路線,每周1次,連續4周為1個周期,共治療3個周期。治療后治療組與對照組相比,體質量、腰圍、BMI三者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對于肥胖的痰濕體質評分也有明顯的改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 結語
目前,現代醫學對于肥胖的治療以運動、飲食及行為治療為主要方式,必要時采用藥物或手術治療。降低熱量攝入,増加熱量的消耗是核心治療環節[21]。另外需要根據患者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目標及方案,使體質量平穩下降并能長期保持。藥物治療多采用脂肪酶抑制劑(奧利司他)、擬兒茶酚胺類制劑(苯丁胺)、擬血清素制劑(氟西汀)等為主,雖有一定療效,但因其易引起嚴重的不良反應如胃腸脹氣、大便次數增多、失眠、乏力等,故不推薦單純性肥胖患者使用[22]。現今臨床常用的手術治療為吸脂術、切脂術、空腸回腸分流術、胃氣囊術及小胃手術等。此方案的治療雖可使患者獲得長期療效,減少并發癥的發生,但卻有一定的風險,并可能引發貧血或管道狹窄等嚴重后果[23]。重度肥胖或減重失敗且伴嚴重并發癥者可選擇此法。單純性肥胖患者臨床日益多見,對其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接受度不高。中醫學對單純性肥胖的臨床研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進展,通過辨證論治、分期論治、綜合辨治從整體上、根本上調理疾病,針對病情的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藥物治療,做到“扶正補虛、標本兼治”,在強化人體正氣的同時,加強祛除外邪的藥力[24]。但是中醫藥在治療單純性肥胖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各個醫家各執己見,缺乏統一的辨證和用藥,且缺乏大樣本的研究,研究周期也較短,今后研究應立足于經方或經驗方,開展大樣本研究,同時開展中藥作用機制的微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