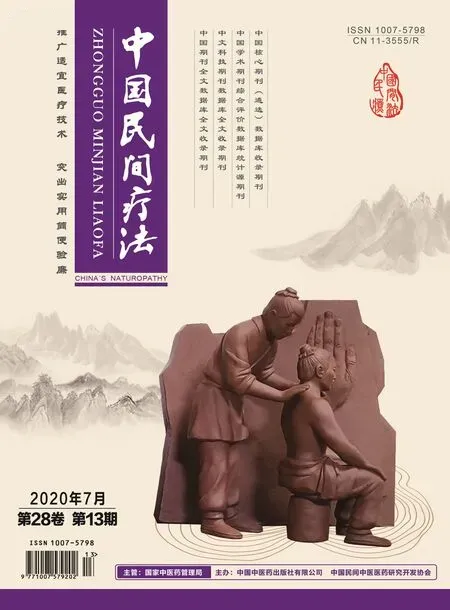清肺排毒湯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淺析
李長輝
(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遼寧 沈陽110032)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屬中醫“疫病”“瘟疫”“寒濕疫”范疇,多因感受寒濕之邪,寒濕邪氣裹夾疫毒侵襲人體而致病,臨床主要表現為發熱、乏力、干咳等。新冠肺炎具有傳染性、人群易感性、流行性等特點,可受氣候、飲食、地理等因素影響,中醫治療該病具有獨特優勢。清肺排毒湯是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帶領下,由中醫專家擬定的治療新冠肺炎的通用方、基礎方。本文從中醫理論角度探討清肺排毒湯防治新冠肺炎的優勢。
1 新冠肺炎的中醫觀
1.1 疫病的認識 疫病首見于《黃帝內經》,其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疫病具有傳染性強、傳染范圍廣等特點。《傷寒雜病論》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提示疫病的致死性高,病因以“傷寒”為主。《諸病源候論》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明確指出疫病具有強傳染性和致死性。明·吳又可所著《溫疫論》對疫病的病因、病機、診療思路進行了詳細闡述,其中“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闡明疫病的來源有別于六淫邪氣。隨著溫病學的進一步發展,疫病的辨證思路及診療方案逐漸完善[1]。新冠肺炎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導致的肺炎,屬疫毒之邪侵襲人體導致的病證,具有傳染性、人群易感性。根據其病因、病性、病證特點,故將新冠肺炎歸屬于“疫病”“瘟疫”范疇。
1.2 疫病辨證思想 我國醫家在與疫病的不斷斗爭中,總結創立的多種辨證方法在疫病的診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漢·張仲景創立了六經辨證法,將外感病分為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病(又稱六經病、三陰三陽病),并在“麻杏石甘湯”“小柴胡湯”等經典方劑中具體體現。六經辨證的方法及原理仍是治療疫病的基礎[2]。金·張元素根據人體五臟六腑的生理功能及特點,創立了臟腑辨證法,利用四診合參以辨識疫病的病因、病位及臟腑受損后的變化,調節臟腑氣機、功能以達到治療作用。因此,臟腑辨證也是疫病辨證不可或缺的理論觀。清·葉天士創立衛氣營血辨證法,將溫病分為衛分、氣分、營分、血分病,針對溫病起病急、進展快的特點,制定了溫病各個時期的治則治法,發展了溫病學。清·吳鞠通創立三焦辨證法,將疾病分為上焦、中焦及下焦,將病機與臟腑相聯系,且對于快速傳變的疫病有指導意義。三焦辨證及衛氣營血辨證均是溫病學派的杰出成就,為針對溫病所設。而溫、瘟相通,因此可以利用其辨證治療疫病[1]。中醫理論思想蘊含著證候及病勢的轉變規律,以及病機傳變相互影響的思想。六經辨證以陰陽為經,經絡為緯,反映了病邪侵入人體后六經、臟腑的變化;臟腑辨證闡明了病位及臟腑的功能變化;衛氣營血辨證反映了病情的發展階段;三焦辨證反映了病程階段、病情傳變及病位。
1.3 疫病診療方法 《溫熱論》提出衛氣營血理論,提示溫病的病理變化主要是衛氣營血的病機變化,并提出清透風熱、清熱泄濁、涼血和營、散瘀等治法,提示新冠肺炎可從三焦、衛氣營血傳變規律入手。仝小林院士[3]認為疫病“皆相染易”,病證多相似,但病毒有強弱之分,體質有寒熱、虛實偏頗,雖感同一疾病,但病情有輕重之別,傳變、轉歸亦有不同,故新冠肺炎防治時須針對疾病不同分期、不同證型及機體不同體質等合理辨證、處方用藥。
據統計,新冠肺炎證型主要為內閉外脫、疫毒閉肺、肺脾氣虛、寒濕郁肺、氣陰兩虛、濕毒郁肺等;治療方劑主要為麻杏石甘湯(出現頻次最高)、銀翹散、藿樸夏苓湯、升降散、達原飲、宣白承氣湯、安宮牛黃丸、麻杏苡甘湯、黃連解毒湯、千金葦莖湯等;涉及中藥主要為甘草、杏仁、麻黃、藿香、石膏、陳皮、茯苓、蒼術、半夏、厚樸等[4]。針對傷寒、溫病、瘟疫等疾病,歷代醫家總結出諸多經典方劑,如麻杏石甘湯、涼膈散、達原飲、銀翹散、桑菊飲等。麻杏石甘湯,原名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出自《傷寒雜病論》,主治風熱襲肺,或風寒郁而化熱,壅遏于肺的邪熱壅肺證;涼膈散,出自《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主治上中焦邪郁生熱證。達原飲出自《溫疫論》,主治瘟疫穢濁毒邪伏于膜原;《溫病條辨》言:“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銀翹散、桑菊飲出自《溫病條辨》,是吳鞠通論治溫病的第一方。
1.4 新冠肺炎病因病機 疫毒易裹夾六淫邪氣侵襲人體,新冠肺炎初期病理因素主要為濕、毒、寒、熱、溫,病機主要為溫邪犯肺,或疫毒(邪毒)襲肺,或濕邪(毒)郁肺,或寒濕襲肺,或濕熱犯肺等,病位主要在肺、脾,臨床表現以發熱、咳嗽、咳痰、納差、惡心、嘔吐等為主;中期病理因素主要為濕、熱、毒,病機為濕毒化熱、熱毒郁肺;重癥期病理因素為濕、熱、毒、閉,病機主要為邪毒內陷,內閉外脫;恢復期病理因素主要以虛為核心,病機主要為肺脾氣虛、氣陰兩虛[5]。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省武漢市暴發,仝小林院士[3]認為新冠肺炎歸屬“寒濕疫”,由寒濕裹夾戾氣侵襲人群導致,病位在肺、脾,可波及心、肝、腎;證型以寒濕傷陽為主,兼有化熱、變燥、傷陰、致瘀、閉脫等變證。
2 清肺排毒湯方藥解析
方藥組成:麻黃9 g,炙甘草6 g,桂枝9 g,紫菀9 g,款冬花9 g,澤瀉9 g,苦杏仁9 g,生石膏15~30 g(先煎),豬苓9 g,白術9 g,茯苓15 g,柴胡16 g,黃芩片6 g,姜半夏9 g,生姜9 g,射干9 g,細辛6 g,山藥12 g,枳實6 g,陳皮6 g,藿香9 g。清肺排毒湯由麻杏石甘湯、五苓散、射干麻黃湯、小柴胡湯等加減化裁而成[6],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可散寒邪、利水濕;小柴胡湯祛皮里膜外之邪;五苓散合藿香、陳皮、枳實增祛濕之功;山藥溫補脾、胃、肺、腎,扶正氣。全方共奏散寒祛濕、宣肺健脾、扶正祛邪之功。①麻杏石甘湯。該方出自《傷寒雜病論》,主治寒邪化熱、熱邪壅盛證,治以清透壅熱、宣降肺氣,為辛涼解表重劑。麻杏石甘湯為麻黃湯去辛溫之桂枝,重用辛涼清透之石膏而成。方中麻黃配伍杏仁可宣肺降氣,麻黃配伍石膏宣透壅熱。筆者認為,該方適用于以發熱、汗出、喘促等癥狀為主的濕毒化熱、熱毒閉肺證新冠肺炎。若患者熱象較輕,可減少石膏用量。②五苓散。該方出自《傷寒雜病論》,主治水濕困脾、陽不化氣、津液內停證,治以溫陽化氣、利濕行水。方中豬苓、茯苓、澤瀉共利水濕;白術健脾益氣,助脾散精,輸布津液;桂枝溫陽化氣,助津液、氣血運行。筆者認為,該方適用于以納差、小便不利、水腫等癥狀為主的寒濕證新冠肺炎。③射干麻黃湯。該方出自《傷寒雜病論》,主治寒痰郁結,氣逆喘促證,治以溫肺化飲,止咳平喘。方中射干、半夏消痰利咽;麻黃、細辛、生姜溫散解表;款冬花、紫菀、生姜化痰止咳;五味子斂肺降氣。筆者認為,該方適用于以咳嗽、咳痰、喘氣(氣促)等癥狀為主的寒濕郁肺證新冠肺炎。④小柴胡湯。該方出自《傷寒雜病論》,主治邪在半表半里的傷寒少陽病證,治以和解少陽。方中柴胡苦寒,疏散少陽氣郁及邪氣,黃芩苦寒味重,祛膽腑郁火,二藥相合,經腑同治,樞機得利;半夏配伍生姜可助柴胡行氣,又可化痰降逆;人參、甘草、大棗可扶正祛邪。疫毒侵襲入里,傷及少陽經,易出現頭暈、胸悶、心煩、咽干、咳嗽等循經病證;少陽病生郁化火,易出現反復發熱癥狀;少陽膽腑郁熱、樞機不利,影響脾胃升降,可見口苦、納差、多食易饑、大便失調等癥狀。筆者認為,該方適用于以反復低熱、咳嗽、咽干、口苦、納差等癥狀為主的少陽證新冠肺炎。
3 清肺排毒湯防治新冠肺炎的中醫作用機制
3.1 化疫毒之“寒濕” 濕性重濁,阻礙氣機升降,若侵襲機體胸脅,則出現胸悶、呼吸憋悶癥狀;侵襲頭部,則出現頭重如裹癥狀;侵襲周身,則出現身體困倦、乏力癥狀;侵襲腸道,則出現下利清谷、大便溏薄癥狀。濕性黏滯,易聚液成痰飲,進一步阻礙氣機、津液運行,導致病情纏綿難愈。清肺排毒湯中涉及化痰、祛濕類中藥15味,具有解表化濕、健脾燥濕、行氣化痰、燥濕化痰等功效,可祛全身之痰、濕、飲邪。寒邪具有寒冷、凝滯、收引的特性,易導致氣滯血瘀、水飲內停。清肺排毒湯中麻黃、桂枝、細辛、生姜等溫性中藥可祛寒散寒、溫陽化飲。
3.2 解疫毒之“毒” 疫毒性烈,傳染性強,一般分為寒、熱及濕性。新冠肺炎屬寒濕疫,初期運用清肺排毒湯可辛溫散寒、化痰祛濕,療效確切。劉菁菁等[7]探究小柴胡湯及其拆方對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的影響,發現小柴胡湯具有抗病毒作用,可能與柴胡、黃芩有關。吳昊等[8]通過網絡藥理學及分子對接技術探究“清肺排毒湯”抗新冠肺炎的作用機制,發現清肺排毒湯中部分中藥核心化合物對新型冠狀病毒的3C類似蛋白酶和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具有一定的親和力。這些研究均為進一步研究清肺排毒湯防治新冠肺炎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機制提供了參考。
4 清肺排毒湯防治新冠肺炎的療效觀察
2020年1月27日,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山西、河北、黑龍江、陜西省開展了清肺排毒湯救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臨床療效觀察。截至2020年2月5日0時,4個試點省份運用清肺排毒湯救治確診病例214例,3 d為1個療程,總有效率達90%[9]。2020年2月7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聯合發布通知,推薦“清肺排毒湯”作為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冠肺炎的通用方。王饒瓊等[10]采用清肺排毒湯治療新冠肺炎,3 d為1個療程,共治療3個療程,治療總有效率為92.09%,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癥狀改善明顯。李曠宇等[11]回顧性評價加減清肺排毒湯的療效,發現常規治療聯合加減清肺排毒湯組比單純常規治療組的退熱時間、咳嗽好轉時間、肺CT好轉時間均顯著縮短。
5 小結
麻杏石甘湯、五苓散、射干麻黃湯、小柴胡湯等中醫經典方劑,具有組方合理、藥味少、功效專的特點,是古代醫家綜合病因、病機、證候等要素認真思辨及臨床實踐的產物,體現了中醫以人為本、整體觀念、辨證論治的思想,為現代中醫藥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清肺排毒湯是以中醫經典理論為基礎,根據新冠肺炎病因病機及主要臨床癥狀總結出的通用方,是對古代經典醫方的傳承與創新。但清肺排毒湯治療新冠肺炎的具體機制研究尚顯不足,需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