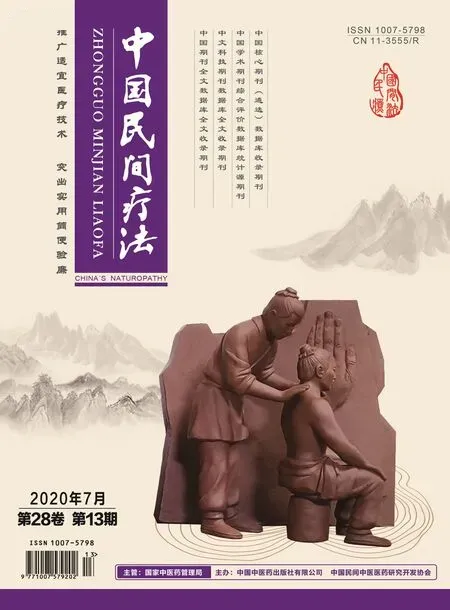《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藿香正氣散解析※
周歲鋒,陳華瓊,繆英年
(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廣東 中山528400)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以下簡稱《局方》),是我國著名的方書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第1部由政府頒布的成方藥典。該書共10卷,載方788首,最初是宋官方和劑局所使用的成藥處方范本,該書以病證對應方劑進行分類,便于檢索及學習,詳細論述藥物的制作方法和服藥法,配伍合理,療效卓著。藿香正氣散出自宋代《局方》,可適用于濕邪為患的多種病證,被尊為“祛濕圣藥”。近年來臨床上使用的丸、散、膠囊劑,也都是在原書散劑基礎上發展而來。本文主要闡釋藿香正氣散的原文含義、方藥特點及治療范圍。
1 原文解析
原文出自《局方》卷二:“治傷寒頭痛,憎寒壯熱,上喘咳嗽,五勞七傷,八般風痰,五般膈氣,心腹冷痛,反胃嘔惡,氣瀉霍亂,臟腑虛鳴,山嵐瘴瘧,遍身虛腫;婦人產前、產后,血氣刺痛;小兒疳傷,并宜治之。”[1]根據原文分析藿香正氣散主治證的病機。
1.1 外感寒邪 傷寒頭痛,憎寒壯熱,上喘咳嗽為外感癥狀。《傷寒雜病論》言:“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又言:“病有發熱惡寒者,發于陽也;無熱惡寒者,發于陰也。”發熱惡寒病位在太陽。太陽者,巨陽,統攝營衛,主一身之表,為人體之藩籬,外邪侵犯,太陽首當其沖。太陽病因六淫之邪,由皮毛肌腠而入,先滯絡脈,由表而里,傳至臟腑,發為熱病。人體正氣與之相搏,正邪交爭于體內,或熱、毒充斥于人體而發熱,即所謂“陽勝則熱”。發生陽氣偏盛的熱性表證表現,以發熱為主,伴有惡寒、口干等。頭為諸陽之會,清陽之府,位于身體之最高處,凡六淫之邪外襲,上犯顛頂,阻遏清陽,導致陰陽失調、腦失所養而致頭痛。《黃帝內經》認為外感邪氣是引起頭痛的重要因素。《素問·骨空論》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風氣從外而入,客于肌膚之間。風為陽邪,容易傷及人體陽氣,兩陽相合,正邪交爭,故見惡寒,頭痛,身重。寒邪可從肌膚侵入,或從足太陽膀胱經侵犯骨髓,上逆于腦,發頭痛。《素問·奇病論》云:“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為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為厥逆。”此為下受之寒,上逆至顛頂,成厥逆之病。
1.2 虛損體質 五勞七傷是全身虛損證候病因。《素問·宣明五氣》云:“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認為五勞可傷五體。《諸病源候論》言:“五勞者,一曰志勞,二曰思勞,三曰心勞,四曰憂勞,五曰瘦勞。又肺勞者,短氣而面腫,鼻不聞香臭。肝勞者,面目干黑,口苦,精神不守,恐畏不能獨臥,目視不明。心勞者,忽忽喜忘,大便苦難,或時鴨溏,口內生瘡。脾勞者,舌本苦直,不得咽唾。腎勞者,背難以俯仰,小便不利,色赤黃而有余瀝,莖內痛,陰濕,囊生瘡,小腹滿急。”五勞,一是傷及五志,二是傷及五臟。七傷一種說法是7種病因,《諸病源候論》認為七傷是“大飽傷脾,大怒氣傷肝,強力舉重、久坐濕地傷腎,形寒飲冷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恐懼不節傷志”,包括了因起居、飲食失節、六淫、七情、勞作所傷引起的臟腑病變。《金匱要略》認為七傷為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榮衛氣傷。《諸病源候論》言:“一曰陰寒,二曰陰萎,三曰里急,四曰精連連,五曰精少、陰下濕,六曰精清,七曰小便苦數,臨事不卒。”提及男子腎虛有七傷。五勞七傷從不同層次、不同病因解釋人體虛損,雖不能完全概括疾病的本質,但從養生角度仍不失借鑒意義。
1.3 風痰內擾 風痰首見于《肘后備急方·卷四》,其言:“治膈壅風痰,半夏不計多少……好茶或薄荷湯下。”風痰是一個病因病機概念,風邪和痰飲之邪,二者互兼互生,共同致病。風為百病之長,如風與寒、風與濕、風與熱、風與燥等,形成復合的致病因素,致病表現則兼有兩種外邪的特點。風為陽邪,風性揚散,容易侵襲人體的肌表及上部。痰飲有兩種成因,風夾外感六淫侵襲人體,肺失宣降,不能通調水道,水液失布,聚而為痰;飲食不節,傷損脾胃,脾失健運,痰濁內生,攜風陽之邪竄擾經脈,引起風痰病證。《丹溪心法·論中風》言:“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風痰互結,阻滯經絡脈絡,出現眩暈、胸悶、嘔吐等癥。
1.4 膈氣 《傷寒雜病論》言:“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谷,以胃中虛冷,故吐也。”“膈氣”等同于脾胃功能虛弱,胃氣上逆之癥。《諸病源候論·五膈氣候》明確提出“膈氣”是作為一種疾病而單獨存在的。《外臺秘要》言:“謂憂膈、恚膈、氣膈、寒膈、熱膈也。”將膈氣病分為5種。《肘后備急方》言:“膈中之病,名曰膏肓,湯丸經過。針灸不及,所以作丸含之。令氣勢得相熏染,有五膈丸方。”可見,膈氣是由于情志內傷,或者外邪入里,導致中焦運化失常,脾氣不升,胃氣不降的諸多閉塞不通之癥。
1.5 脾虛濕滯,水濕內停 水液的生成和輸布涉及多臟器及部位。胃、小腸和大腸是化生津液的場所。脾、肺、腎、肝、心、三焦為津液輸布的動力臟腑。《素問·經脈別論》言:“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黃帝內經》高度概括了津液從生成到排泄的過程。寒邪客于中焦,寒凝氣滯,臟腑失其溫煦,心腹冷痛。脾胃升降失司,胃氣上逆,反胃嘔惡,脾喜燥惡濕,脾虛濕滯,氣瀉霍亂。臟腑虛鳴、山嵐瘴瘧亦為脾胃虛弱、濕邪內阻之癥。鐘學文等[2]用藿香正氣散治療特發性水腫療效良好,認為病機為濕濁內蘊,三焦水道不暢。
1.6 婦人產前、產后血氣刺痛及小兒疳傷 從藿香正氣散主治的證候可以看出,一方面可以解外表之邪,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祛除中焦濕邪,恢復人體正氣。吳崑在《醫方考》中講到“疏表則能正氣于外矣;若使表無風寒,二物亦能發越脾氣,故曰正氣”。用藿香正氣散治療從病機上解釋不通,臨床亦不為治療此類病證之主方藥。
2 方義分析
原方藥物組成為大腹皮、白芷、紫蘇葉、茯苓(去皮)各一兩,半夏曲、白術、陳皮(去白)、厚樸(去粗皮,姜汁炙)、苦桔梗各二兩,藿香(去土)三兩,甘草(炙)二兩半(上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姜錢三片,棗一枚,同煎至七分,熱服。如欲出汗,衣被蓋,再煎并服)。原方為研磨散水煮熱服。中醫方劑用法較為講究,“湯者蕩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不能速去病舒緩而治之”。劉菊妍等[3]較為全面而完整地闡述藿香正氣散的特點,認為有以下4個方面的特點:雙效奏表里同治之功;升清降濁以斡旋中州運化;化濕未忘行氣,氣化則濕亦化;祛邪扶正,正不正之氣。藿香正氣散的組方和立法是以六淫之邪侵襲和水液的代謝紊亂為依據。方證的病機特點為外感風寒,濕邪中阻,表里同病為主要致病因素。
3 治療范圍
3.1 表里同治 本方主治外感風寒,內傷濕滯證。從用藥的特點看,外感之邪不是從口鼻而入,而是因四時不正之氣引起,直接祛邪易損傷正氣,可用辛散風寒、芳香化濕藥,如藿香、白芷、紫蘇葉。藿香辛散風寒,芳化濕濁,悅脾和中,為君藥。《本草正義》載:“藿香芳香而不嫌其猛烈,溫煦而不偏于燥烈,能祛除陰霾濕邪,而助脾胃正氣,為濕困脾陽,倦怠無力,飲食不甘,舌苔濁垢者最捷之藥。”白芷辛溫解表散寒,祛風止痛,通鼻竅,燥濕。《本草匯言》載:“白芷,上行頭目,下抵腸胃,中達肢體,遍通肌膚以至毛竅,而利泄邪氣。”紫蘇葉能散表寒,發汗力較強,亦可行氣寬中。《名醫別錄》言:“主下氣,除寒中。”《本草綱目》言:“行氣寬中,消痰利肺,和血,溫中,止痛,定喘,安胎。”三藥合用,既能辛溫發散于表,又能芳香化濕于里,達到表里同治的目的。
3.2 升清降濁,化濕和中 脾胃居中焦,中焦運化正常,才能保持正常的升清降濁功能。桔梗宣肺利咽,祛痰排膿。《珍珠囊藥性賦》言其“止咽痛,兼除鼻塞;利膈氣,仍治肺癰;一為諸藥之舟楫;一為肺部之引經”。藿香、紫蘇葉辛香化濕,發散脾胃陽氣;桔梗引清陽之氣上升;半夏辛溫降逆,《醫學啟源》言半夏“治寒痰及形寒飲冷傷肺而咳,大和胃氣,除胃寒,進飲食”。陳皮、厚樸苦溫而燥濕,又下氣除脹滿。
3.3 健脾扶正祛邪 脾主運化,因脾氣不足,運化失健,往往水濕內生。《本草通玄》言:“土旺則能勝濕,故患痰飲者,腫滿者,濕痹者,皆賴之也。土旺則清氣善升,而精微上奉,濁氣善降,而糟粕下輸,故吐瀉者,不可闕也。”白術、茯苓、甘草、大棗同用可健脾燥濕,恢復脾胃正常運化功能,水濕自除。
4 小結
藿香正氣散主治表寒里濕證。隨著臨床深入研究,發現藿香正氣散可治療多種內科雜病,臨床應用超出原有治療范疇,臨證時抓住濕邪內盛、偏寒濕或熱證不明顯的病證特點,就能起到很好的臨床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