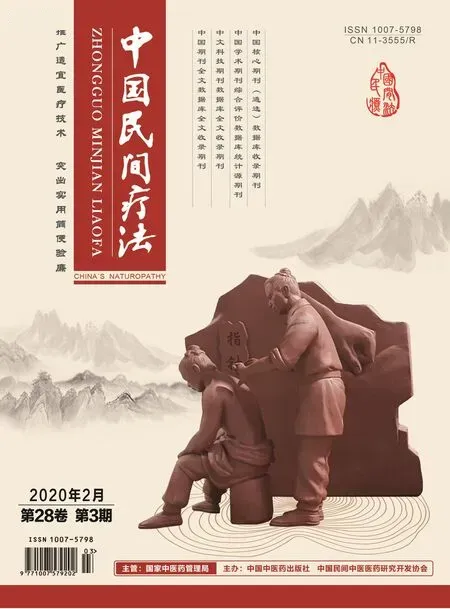謝麗萍運用通陽法辨治尿道綜合征經驗※
江志雄,謝麗萍,史 偉,齊殿偉,曹 響,周翠萍,張天彬
(1.廣西中醫藥大學,廣西 南寧530001;2.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廣西 南寧530023)
尿道綜合征是指有尿頻、尿急、尿痛或小便排出不利的癥狀表現[1],歸于中醫“淋證”范疇。該病纏綿反復,難以速愈。《黃帝內經》首載“淋證”之名,《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記載:“小便黃赤,甚則淋。”認為小便黃赤者乃熱郁于內,陽氣不通,甚者即為小便淋瀝不暢。《金匱要略方論》曰:“淋之為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諸病源候論》云:“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宿病淋,今得熱而發者。”可見淋證發病與腎虛、膀胱熱相關,有易復發的特點。曹穎甫《金匱發微》認為:“吾謂治淋之法,病之初起,以疏達瘀滯為急,是猶濕熱下利中有宿食而宜大承氣者也,病之既久,宜溫中通陽,佐以泄水,是猶下利虛寒而宜四逆理中者也。”[2]《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化氣,陰成形。”陽氣者貴乎溫通[3],臨證治則當以通陽為法。
謝麗萍,教授,主任醫師,碩士研究生導師,師承廣西名老中醫史偉教授,為史偉廣西名中醫傳承工作室學術繼承人,從事中醫臨床及教學、科研工作20年。在長期臨床工作中運用中醫藥治療慢性腎臟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臨證效如桴鼓。筆者有幸跟師臨診抄方,總結謝麗萍教授運用通陽法辨治尿道綜合征的臨證經驗,并附2例醫案解析,以饗同道。
1 病因病機
尿道綜合征的病因雖有不同,但其根本病因可歸結于陽氣郁結或下焦陽氣不足,而致陽氣不通。惱、怒、憂、愁等情志不暢,則令陽氣郁結不通;飲食、作息多不節制,以致陽氣損耗難以恢復,皆可致陽氣失于通達,膀胱氣化失常而發病,可見尿頻、尿急、尿痛或小便排出不暢等癥狀。謝麗萍等[4]總結發現葉天士治淋五法中有運用通陽法治療淋證之案析。現代醫家朱光有“溫陽、通陽各有所適,同中有異,吃透其中意理才能恰當運用”之論述[5]。劉寧[6]認為通陽法即針對導致陽氣不通的原因進行對癥治療,以達到疏通氣機、通達陽氣的治療目的。通陽法可分為利水通陽、理氣通陽、補氣通陽、溫中通陽、溫腎通陽等治法。
2 通陽法的運用
2.1 水濕泛溢,宜予利水通陽 陽氣與水濕之邪密切相關,一陰一陽不可分離。當水濕停滯,寒濕中生,會阻遏陽氣周流,損傷人體陽氣,而陽氣具有推動作用,可運化水濕。故當先祛水濕之邪,使陽氣得以通達,則小便自利,治則應遵“水濕者,利而通之”的治法。臨證常見小便不利,渴而不欲飲,舌苔白膩,脈滑等癥。此類病證可予以五苓散加減。《傷寒雜病論》曰:“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該方由豬苓、澤瀉、白術、茯苓、桂枝組成。方中重用澤瀉以利水滲濕;豬苓、茯苓助君藥利水滲濕;白術健脾運濕;桂枝溫陽化氣。諸藥合用,達到利水通陽的功效。
2.2 氣郁難解,應尋理氣通陽 臨床中尿道綜合征多與情志相關。在論述該病病機時應強調疏肝解郁,調理情志。理氣通陽法則起到行氣通陽解郁之功。臨證常見小便不利或尿頻、尿急,情志抑郁或焦慮,四肢不溫,舌淡暗,苔薄白,脈弦等癥。治當以理氣通陽為法,方選四逆散加減。《傷寒雜病論》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四逆散組成藥物為炙甘草、枳實、柴胡、芍藥。方中柴胡升陽解郁,白芍柔肝斂陰,二者合用可疏肝理氣;枳實理氣解郁,與柴胡為伍,可增加通陽解郁之功;甘草為使,調和諸藥;隨癥酌加烏藥、萆薢以溫陽理氣。諸藥共奏通達陽氣利尿之功,從而達到陽通厥回的目的。
2.3 氣虛下陷,治當補氣通陽 陽氣不足者,當補氣通陽。脾主升,主運化,脾虛氣陷,則濕濁下停,而致膀胱氣化不利。臨證常見小便不利或尿頻、尿急,納食欠佳,神疲乏力,小腹墜脹不舒,舌質淡,苔薄白,脈沉等癥。治當給予補中益氣湯加減。本方出自《脾胃論》,方藥組成為黃芪、人參、白術、炙甘草、當歸、陳皮、升麻、柴胡、白術。方中以黃芪為君,可補中升陽,益氣固表;人參、白術、炙甘草為臣,助君藥補氣健脾。氣虛日久,營血易虧,加當歸以養血和營;陳皮理氣,除滋膩礙味,共為佐藥。升麻、柴胡引陽明、少陽清氣上升,為脾胃引經藥。炙甘草可安中調和諸藥。諸藥合用,以達補氣通陽、化氣通調之功。
2.4 中寒內生,理須溫中通陽 臨證若見中焦陽氣不足、寒邪內生者,其脾失運化,胃失受納,氣化不利,可見小便不利或尿頻、尿急,腹痛不適,四肢不溫,或伴嘔吐、腹瀉,舌質淡,苔白膩,脈沉緩等癥。治當給予理中丸加減。《傷寒雜病論》曰:“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該方由干姜、人參、炙甘草、白術組成。方中以干姜為君藥,性味辛熱,可溫中焦,散寒邪;人參為臣藥,甘溫補氣。二者相配以達溫中通陽之功。脾喜燥惡濕,以白術苦燥之性除濕健脾;佐使炙甘草,既合君臣補氣溫中,又兼調和諸藥。上藥合方,共奏溫中通陽、氣化流通之功。
2.5 久病傷陽,法取溫腎通陽 患者常因病程日久,正氣漸傷,或體質本虛,受邪未盡,由實轉虛,最終可致腎陽虛衰,虛寒內生,而發為該病。臨證常見小便不利或尿頻、尿急,小腹拘急,腰膝酸軟,畏寒肢冷,舌質淡,苔薄白,脈沉無力等癥。《金匱要略方論》曰:“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治當以溫腎通陽為法,給予腎氣丸加減治療。該方由地黃、山藥、山茱萸、澤瀉、茯苓、牡丹皮、桂枝、附子組成。方中附子大辛大熱以溫里;桂枝溫補腎陽,助陽行水。腎陽虛乃疾病遷延已久,陰陽互根互用,給予地黃滋補腎陰;山茱萸、山藥補肝脾以養精血;澤瀉、茯苓滲水利濕;牡丹皮可調血分瘀滯。諸藥共用,陽復得以主水,陰滋得以生氣,腎氣復常,則病邪盡祛。
3 醫案舉隅
3.1 氣虛不通案 患者,女,49歲。因“反復尿頻、尿急3年余”于2018年1月15日就診。患者訴3年前因外感后出現尿頻、尿急、淋瀝不暢,夜尿每晚2~3次,無肉眼血尿,尿量不多,喝涼水后急需排尿,伴有小腹墜脹感。于外院行尿常規、腎功能等檢查未見異常,曾長時間服用中草煎劑(具體不詳),病情未見好轉。患者近1個月來尿頻、尿急、小腹墜脹感較前明顯加重,夜尿每晚5~6次,神疲乏力,納食欠佳,大便溏稀,平素易外感,面色萎黃。舌質淡,苔薄白膩,脈沉細。四診合參,辨證為脾胃氣虛、氣化不利,治當補氣通陽,給予補中益氣湯化裁。藥物組成:黃芪30 g,黨參片15 g,白術15 g,炙甘草10 g,柴胡10 g,升麻10 g,當歸10 g,陳皮10 g,桂枝15 g,烏藥15 g,小茴香6 g。7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2018年1月23日二診:患者尿頻、尿急、小腹墜脹等癥較前明顯改善,守上方續服7劑。2018年1月31日三診:患者夜尿每晚1~2次,無明顯尿頻、尿急,納寐轉佳,大便成形。守法鞏固治療月余,隨訪患者排尿、納寐等皆如常。
按語:該患者平素體虛,病久反復,脾虛氣陷,氣化不利,而出現尿頻、尿急等癥。補中益氣湯可補中通陽,氣化周流,諸癥皆消。《長沙藥解》言:“桂枝……升清陽之脫陷,降濁陰之沖逆。”《藥品化義》曰:“烏藥,氣雄性溫,故快氣宣通,疏散凝滯。”小茴香有行氣止痛、健胃散寒之功[7]。該例患者可酌加桂枝溫通陽氣,烏藥溫里通陽,小茴香行氣散寒。諸藥合用,可起到溫陽補氣、通達下焦陽氣之功。
3.2 氣郁不通案 患者,女,57歲。因“排尿不暢1周”于2017年11月16日就診。患者訴1周前因生氣后突發排尿不暢,郁怒時排尿點滴難出,伴少腹憋脹,檢查尿常規、腎功能等未見異常。刻下癥:排尿點滴難出,伴少腹憋脹,時胸脅脹悶,納寐欠佳,大便時干時稀,日行2~3次。舌暗淡,苔薄白,脈弦。四診合參,辨證為陽氣郁結、氣化不利,治當理氣通陽,方選四逆散化裁。藥物組成:柴胡15 g,白芍15 g,枳實12 g,炙甘草10 g,川芎15 g,香附15 g,郁金15 g,烏藥15 g,粉萆薢15 g。3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2017年11月10日二診:癥狀較前改善,小便排出較為順暢,少腹憋脹減輕,效不更方,續服上方7劑。三診:排尿如常,情志舒暢,納寐轉佳,身輕體泰。
按語:肝主疏泄,調達氣血,舒暢情志,通利三焦[8]。該例患者因郁怒傷肝,以致陽氣郁結,膀胱氣化不利,而致尿液點滴難出。四診合參,辨為陽氣郁結之證,給予四逆散化裁,可疏解氣郁,暢達瘀滯,以恢復膀胱氣化之功。氣滯則血行不暢,可見暗淡舌、弦脈,故加香附、郁金、佛手調理氣機,川芎行氣活血,烏藥溫陽理氣。諸藥合用,可理氣通陽,使陽氣周流無礙,膀胱氣化恢復如常。
4 小結
中醫臨床遣方用藥如同派兵遣將,須理法方藥俱全。謝麗萍教授認為陽氣不通、膀胱氣化失常所致的尿道綜合征,可運用通陽法之利水通陽、理氣通陽、補氣通陽、溫中通陽、溫腎通陽等法施治,理法清晰,辨證得當,臨床用方則效如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