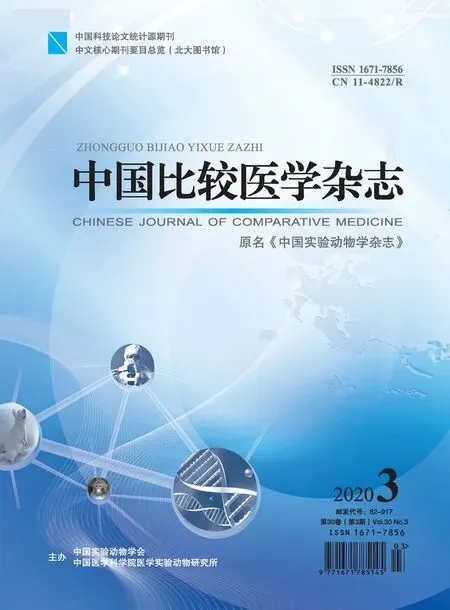Keap1/Nrf2/p62和NLRP3炎性小體與自噬調(diào)節(jié)作用的研究進展
楊根夢,洪仕君,王一航,沈?qū)氂瘢?浩,曾曉鋒,李利華
(昆明醫(yī)科大學法醫(yī)學院, 昆明 650500)
細胞自噬 (autophagy)分為3種不同的形式:小自噬 (microautophagy)、分子伴侶介導的自噬 (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和大自噬 (macroautophagy)。通常所說的自噬是指大自噬,其發(fā)生過程可分為4個階段:分隔膜的形成;自噬體的形成;自噬體的運輸、融合;自噬體的降解。自噬由自噬相關基因(autophagy related gene,Atg)進行調(diào)控,截至目前為止,可作為自噬標志物的基因有LC3、Beclin1、Atg5及Atg7等[1-3]。細胞自噬參與機體多種疾病如腫瘤,炎癥,神經(jīng)退行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的調(diào)節(jié)。但自噬的調(diào)控機制非常復雜,至今尚未完全闡明。
核因子NF-E2相關因子 (nuclear factor-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是機體抗氧化應答反應的核心途徑之一,Nrf2的缺失或激活障礙,會加重機體氧化應激狀態(tài)、破壞細胞內(nèi)正常的氧化還原平衡的穩(wěn)態(tài),導致細胞功能障礙,引起細胞毒性,甚至死亡。在正常生理狀態(tài)下,Nrf2的激活依賴于Keap1,Nrf2和Keap1 在細胞質(zhì)內(nèi)形成復合體處于抑制狀態(tài),并通過Keap1介導的泛素化對Nrf2 持續(xù)進行降解以維持轉(zhuǎn)錄形成的Nrf2 之間的平衡[4]。p62,也稱SQSTM-1,是一種多面銜接蛋白,其主要功能是將泛素化的蛋白質(zhì)帶到蛋白酶體中進行降解,p62對Keap1具有調(diào)節(jié)作用。研究表明,Keap1/Nrf2/p62可參與中毒、腫瘤、凋亡和自噬等的調(diào)節(jié)[5-7]。NLRP3炎性小體是一種多聚體蛋白復合物,由NLRP3,ASC和pro-caspase-1組成。NLRP3炎性小體作為一種重要的促炎性細胞內(nèi)受體,在炎癥反應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研究表明,NLRP3炎性小體可參與自噬的調(diào)節(jié)[8]。因此,本文主要從Keap1/Nrf2/p62和NLRP3炎性小體與自噬的調(diào)節(jié)方面進行綜述。
1 細胞自噬的雙重作用
在生理情況下,自噬主要是一種應激適應機制,促進細胞的生存。但過度應激時,細胞自噬可看成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死亡。近年來,尤其是用Atg基因敲除研究,證實了細胞自噬與細胞死亡之間的相互關系。但到目前為止還不能斷定究竟是何種因素決定細胞自噬過程是保護作用還是毒性作用。細胞自噬與細胞生死之間具有復雜的關系,這種復雜性反映了細胞自噬在疾病調(diào)節(jié)中具有復雜多變的作用。激活自噬可作為抗氧化途徑,通過清除受損或功能失調(diào)的蛋白質(zhì)和細胞器,對神經(jīng)退行性疾病和癌癥等具有保護作用[9-10]。在毒品濫用機制研究中發(fā)現(xiàn),抑制自噬可使大鼠多巴胺能細胞通過激活caspase-3促進甲基苯丙胺誘導的細胞凋亡,說明自噬對甲基苯丙胺誘導的神經(jīng)毒性作用具有保護作用[11]。然而,有研究表明,甲基苯丙胺誘導自噬對神經(jīng)細胞具有明顯的毒性作用[12-13]。說明自噬對機體的調(diào)節(jié)是一把“雙刃劍”,自噬一旦激活,必須在渡過危機后適時停止,否則自噬過度激活將導致細胞發(fā)生不可逆的損傷。
2 Keap1/Nrf2/p62的結構及相互調(diào)節(jié)作用
Keap1是Cul3-泛素E3連接酶復合物的銜接子,由 624個氨基酸組成,包括5個區(qū),即NTR、BTB/POZ、IVR、DGR/Kelch 和CTR。Nrf2是機體較為重要的抗氧化防御體系,其發(fā)揮作用需要與抗氧化反應元件(ARE)相結合,調(diào)控下游抗氧化酶和II相解毒酶基因的轉(zhuǎn)錄活性,增強細胞清除活性氧自由基的能力,從而降低氧化應激對細胞、組織及器官造成的損傷[14]。Keap1對Nrf2具有負調(diào)控作用,正常情況下Keap1/Nrf2形成復合物定位于細胞質(zhì)中,Nrf2被Keap1-Cul3-E3泛素連接酶復合物泛素化并被26S蛋白酶降解以維持其穩(wěn)態(tài)水平,而處于抑制狀態(tài)。在應激條件下,Keap1中的半胱氨酸殘基可發(fā)生修飾而使Keap1構象發(fā)生改變,從而使Nrf2從Keap1/Nrf2復合物中分離出來,同時半胱氨酸殘基可抑制E3泛素連接酶的活性,使Nrf2不能泛素化和降解,最終激活Nrf2,激活的Nrf2從胞質(zhì)進入核內(nèi),與小Maf蛋白形成二聚體,該二聚體可與ARE結合,激活抗氧化基因和蛋白的表達,從而發(fā)揮抗氧化應激和細胞保護的作用[5,15-16]。p62主要功能是將泛素化的蛋白質(zhì)帶到蛋白酶體中進行降解,此外,p62可通過LC3相互作用區(qū)與自噬標志性蛋白LC3直接相互作用。因此,p62被認為是泛素化蛋白和自噬之間的聯(lián)系[16],同時,p62已廣泛作為自噬流的標志。Keap1/Nrf2是抗氧化應激的關鍵調(diào)控因子。p62也可調(diào)節(jié)Nrf2的活性,p62結構中含有STGE序列可與Keap1中kelch結構域相結合,從而破壞Keap1/Nrf2復合物的穩(wěn)定性,使Nrf2從復合物中解離出來而激活Nrf2。由于p62可與LC3相互作用,因此Keap1/Nrf2/p62與自噬的調(diào)節(jié)具有相互作用。若p62異位表達或自噬缺陷,使p62與Keap1結合形成聚集體,使Nrf2泛素化和降解減少,而激活Nrf2,該過程稱為Nrf2激活的非經(jīng)典機制[5-7]。
3 NLRP3炎性小體的結構
Nod樣受體(nod-like receptor,NLRs)是一種細胞質(zhì)識別受體,主要負責IL-1β和IL-18的加工和釋放。截至目前為止,在人類中已發(fā)現(xiàn)22個NLR成員,小鼠中有34個,而根據(jù)它們N末端區(qū)域的不同分為NLRA,NLRB,NLRC和NLRP四個亞家族。其中NLRP3是研究最多且研究較為透徹的亞基[17-18]。NLRP3炎性小體作為一種重要的促炎性細胞內(nèi)受體,在應激狀態(tài)下,NLRP3將募集ASC蛋白并作為激活pro-caspase-1的支架,無活性的pro-caspase-1將寡聚化并自動水解切割形成具有活性形式的caspase-1,激活的caspase-1直接誘導IL-1β和IL-18前體的加工,促進IL-1β和IL-18的成熟和釋放[19-20]。研究表明,氧化應激釋放的ROS可激活NF-κB,NF-κB又激活NLRP3炎癥小體,促進IL-1β和IL-18分泌增多,IL-1β是一種正反饋式促炎因子,可放大炎癥反應。由于NLRP3炎癥小體的激活可釋放大量IL-1β,IL-18和其他炎性因子,從而激活程序性的炎癥壞死,此過程稱為細胞焦亡(pyroptosis)[15,21]。然而,在應激狀態(tài)下,針對NLRP3炎癥小體的激活對細胞命運走向的影響,目前仍然是一個沒有明確且存在眾多爭論的論題。
4 Keap1/Nrf2/p62和NLRP3炎性小體與自噬的關系
4.1 Keap1/Nrf2/p62與自噬的調(diào)控作用
大量研究證實,Nrf2通過Nrf2-Keap1-p62反饋環(huán)參與氧化應激誘導自噬的調(diào)節(jié)[22-23]。Tang等人[6]對椎間盤退化研究中發(fā)現(xiàn),在衰老過程中,缺乏Nrf2可加重椎間盤的退化,同時自噬相關基因 (LC3,p62,Atg5,Atg7)的表達減少。并且椎間盤退化過程中髓核細胞發(fā)生明顯氧化應激,同時自噬水平明顯上調(diào),而缺乏自噬的細胞發(fā)生氧化應激毒性作用較為明顯,說明自噬可通過Keap1/Nrf2/p62通路被激活而發(fā)揮抗氧化作用。此外,氧化應激狀態(tài)下,聽覺細胞的死亡取決于自噬與ATP耗盡所致壞死之間的平衡,而自噬通過p62與Keap1/Nrf2相互作用而對氧化應激誘導細胞壞死發(fā)揮保護作用[23]。總之,自噬依靠p62與Keap1-Nrf2-ARE信號通路相互作用[24],p62的磷酸化在選擇性自噬期間可激活Keap1-Nrf2通路而發(fā)揮相應的作用[7]。當機體發(fā)生氧化應激時可激活自噬和p62介導的Keap1-Nrf2系統(tǒng)。自噬和Keap1/Nrf2/p62系統(tǒng)之間相互作用,對控制氧化還原穩(wěn)態(tài)和保護細胞完成適應性應激反應至關重要[25]。
4.2 NLRP3炎性小體與自噬的調(diào)控作用
研究表明,通過自噬可誘導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NLRP3發(fā)生磷酸化后可減少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從而減少IL-1β和IL-18的分泌[26]。大量ROS可激活NLRP3炎性小體而破壞腸屏障功能,同時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可誘導自噬,NLRP3炎癥小體的激活和自噬對腸屏障功能的破壞具有相互協(xié)同作用[27]。急性腎損傷時,線粒體可釋放大量ROS并激活NLRP3炎性小體,同時可激活自噬,該選擇性自噬可通過PINK1-parkin途徑降解受損的線粒體和減少ROS的釋放來抑制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從而對腎具有保護作用[28]。此外,錳可使小鼠海馬和BV2細胞自噬功能障礙而激活NLRP3炎性小體,使大量促炎因子IL-1β和IL-18在體內(nèi)聚集引起神經(jīng)炎癥反應而損害海馬神經(jīng)細胞,從而導致海馬依賴的學習和記憶障礙,這可能與阿爾茨海默病的發(fā)病機制有關[29]。總之,NLRP3炎性小體和自噬之間具有密切聯(lián)系。NLRP3炎性小體可激活自噬,自噬也可激活NLRP3炎性小體,兩者之間的調(diào)節(jié)具有雙重[8]和雙向作用[8,30]。
4.3 Keap1/Nrf2/p62和NLRP3炎性小體與自噬之間的相互作用
Nrf2系統(tǒng)和NLRP3炎性小體之間可相互作用,Nrf2系統(tǒng)可調(diào)節(jié)NLRP3炎性小體下游基因的表達,而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又可調(diào)節(jié)Nrf2系統(tǒng),兩者的相互作用與許多急性和慢性炎癥,氧化應激以及自噬有關[31-32]。急性腎損傷過程中,機體Nrf2/ARE/HO-1通路的抗氧化防御體系明顯減弱,大量ROS聚集可激活NLRP3炎性小體,從而使腎損傷[15]和腎毒性[33]更加明顯。而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后,機體可激活Nrf2/ARE信號通路來抑制ROS誘導NLRP3炎性小體的激活,從而對腦損傷具有保護作用[34]。上述研究說明機體存在危險信號時,Nrf2系統(tǒng)與NLRP3炎性小體之間可相互調(diào)節(jié)。然而Nrf2體系和NLRP3炎癥小體對自噬的調(diào)節(jié)存在復雜的關系,激活Nrf2誘導的自噬可激活NLRP3炎癥小體,但在某些情況下,自噬的激活可抑制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同時也說明自噬對機體的調(diào)控具有雙重作用。研究表明,自噬激動劑雷帕霉素可通過p62/SQSTM1依賴的方式激活自噬,通過自噬清除線粒體ROS和pro-IL1β,從而減少IL-1β和IL-18的產(chǎn)生。同時雷帕霉素上調(diào)p62/SQSTM1激活Nrf2通路,更進一步清除mtROS,使IL-1β明顯減少[35]。此外,Nrf2激動劑蘿卜硫素可激活Nrf2通路而抑制NLRP3炎癥小體,從而對糖尿病患者視網(wǎng)膜病變起保護作用。總之,上述研究均表明,Keap1/Nrf2/p62和NLRP3炎性小體與自噬之間相輔相成,在炎癥和損傷性疾病中相互調(diào)節(jié),相互作用。
5 藥物的開發(fā)和治療
Nrf2通路和NLRP3炎性小體以及自噬均參與了許多病理生理過程,和許多疾病的發(fā)展及治療緊密相關。針對關鍵蛋白和重要信號通路設計和尋找藥物,可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研究表明,菊苣酸[15]和阿魏酸[33]可通過激活Nrf2/ARE/HO-1通路抑制NF-κB /NLRP3炎性小體來預防甲氨蝶呤誘導的腎毒性。短鏈脂肪酸可通過抑制NLRP3炎性小體和自噬對腸屏障功能障礙具有治療作用[27]。冬凌草甲素可通過調(diào)節(jié)Nrf2介導的氧化應激和Nrf2非依賴性NLRP3炎性小體/ NF-κB通路對脂多糖誘導的急性肺損傷具有保護作用[36]。蘿卜硫素可通過激活Nrf2和抑制NLRP3炎性小體對糖尿病患者視網(wǎng)膜病變具有治療作用[37]。
6 小結與展望
自噬在NLRP3炎性小體激活和炎性因子分泌調(diào)節(jié)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作用是復雜的。此外,自噬在Nrf2系統(tǒng)調(diào)節(jié)細胞穩(wěn)態(tài),細胞死亡和存活等方面中也發(fā)揮著關鍵作用。Keap1/Nrf2/p62和NLRP3炎性小體通路對自噬均具有雙向調(diào)節(jié)作用,因此揭示上述兩個通路對自噬的調(diào)控機制及其作用將有助于于人們開發(fā)和治療與自噬相關疾病的藥物和策略,可為藥物的發(fā)現(xiàn)和臨床治療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