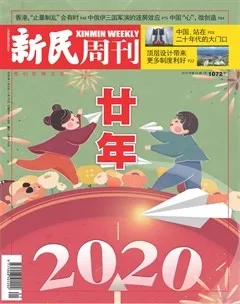恐怖主義全球陰影揮之不去
劉朝暉
2018年12月19日,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宣布,隨著在敘利亞打擊極端組織的戰(zhàn)事“取得成果”,美軍已經(jīng)打敗了臭名昭著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然而,美軍撤離敘利亞,并沒有讓世界獲得太平,2019年這一年里,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爆炸聲和絡繹不絕的槍擊事件中,國際社會面臨的暴恐威脅變得更為嚴峻。在國際反恐斗爭進入治亂新周期,如何反恐、靖亂和治亂,成為擺在世界面前的全球安全治理難題。

2019年12月24日,敘政府軍與伊德利卜省南部和東南部地區(qū)的武裝組織頻繁交火,當?shù)卮笈用裣驍⑼吝吘程油觥?/p>
中東地區(qū)亂局依舊
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2019年10月28日宣布,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最高頭目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已在美國特種部隊在敘利亞西北部地區(qū)采取的一次襲擊行動中死亡。特朗普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在視頻上目睹巴格達迪臨死前的表現(xiàn)多么不堪入目,而且最后不忘得意地加上一句“我找了他三年了……”
從2014年起,“伊斯蘭國”陸續(xù)占據(jù)敘利亞東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大片區(qū)域,成為繼“基地”組織之后危害最嚴重的恐怖組織。經(jīng)過國際社會幾年的共同打擊,“伊斯蘭國”2019年3月失去最后一個據(jù)點,呈窮途末路之勢。而巴格達迪的死亡,表面上是美軍在敘利亞采取襲擊行動的戰(zhàn)果,實際上,這可以被視為國際反恐合作的一個重大標志性勝利。
然而,不少國家也對美方宣布的巴格達迪死訊持“謹慎”樂觀態(tài)度。雖然巴格達迪的死訊對“伊斯蘭國”無疑是個沉重打擊,有利于提振國際社會反恐信心,但就整體而言,中東地區(qū)反恐形勢仍然任重而道遠。國際社會有識之士也一再指出,恐怖組織在包括伊德利卜省在內(nèi)的敘西北部地區(qū)不斷擴大自身勢力范圍,是導致當?shù)爻霈F(xiàn)人道主義危機的根源,也是該地區(qū)安全穩(wěn)定的重大隱患。
2011年,美軍擊斃拉登,而后“基地”組織出現(xiàn)了分裂。“伊斯蘭國”就是2014年從“基地”組織的伊拉克分部自立門戶演變而來的,其興起與快速擴張主要是利用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內(nèi)戰(zhàn)沖突等混亂局勢。結(jié)果趁著敘利亞內(nèi)戰(zhàn)的機會,后來鬧得比“基地”組織還囂張。
“伊斯蘭國”崛起的原因是治理不力和教派紛爭,而這種局面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并未得到改善,特別是庫爾德人問題日益突出。此外,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使得巴以局勢急轉(zhuǎn)直下,加沙地帶暴力事件明顯升級。也門胡塞武裝與沙特支持哈迪政權(quán)之間的戰(zhàn)爭持續(xù)不斷,也成為中東地區(qū)矛盾的另一個爆發(fā)點。這一切,使得中東地區(qū)滋生蔓延恐怖主義的土壤不僅未被鏟除,反而更加肥沃,中東地區(qū)的社會動蕩仍在繼續(xù)。
除社會動蕩、教派沖突,大國干涉也是導致恐怖主義在中東肆虐的重要因素。美國在2003年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使“基地”組織在伊拉克有了可乘之機;敘利亞內(nèi)戰(zhàn)又使“伊斯蘭國”迅速崛起。而在軍事打擊“伊斯蘭國”問題上,美國、俄羅斯,甚至土耳其和伊朗各自建立“反恐陣營”,尋找代理人。在打擊“伊斯蘭國”之外,代理人之間的相互廝殺不斷,新的矛盾沖突再起。這種將反恐作為“工具”而不是“目的”的做法,很難真正遏制恐怖主義發(fā)展蔓延的勢頭。
拉登和巴格達迪死了,但是“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化整為零,作為恐怖組織仍然存在,其極端主義思想將繼續(xù)在全球產(chǎn)生影響。
歐洲反恐難言樂觀
歐洲多國在2015年至2017年間遭遇一系列重大恐怖主義襲擊,刀光劍影,至今令人記憶猶新。2019年歐洲安全形勢總體平穩(wěn),沒有什么重大恐怖襲擊事件,但去年底斯特拉斯堡恐襲和2019年11月倫敦橋上的持刀殺人事件,都提醒著人們,恐怖襲擊并沒有遠離歐洲。
2019年11月29日,英國倫敦橋上發(fā)生一起持刀傷人事件,襲擊造成2名市民死亡,3人受傷。而倫敦橋在2017年6月3日曾發(fā)生恐怖攻擊事件,3名“伊斯蘭國”支持者駕車沖撞橋上行人,造成2人遇害,然后到附近的南端的波羅市場持刀刺殺6名民眾。這起慘劇另造成48人受傷,3名恐怖分子均遭警方擊斃。
引起媒體關(guān)注的是,2019年底的這次英國倫敦橋持刀傷人案的兇手奧斯曼·汗曾因?qū)嵤┛植婪缸锶氇z,2018年12月有條件獲釋。多家媒體報道說,類似奧斯曼·汗這樣的極端恐怖分子不應該提前被釋放出獄,危害公共安全。英國政府官員也表示,提前釋放恐怖分子是一種錯誤,英國應該加強對恐怖分子的懲罰力度。2012年被判刑的9名奧斯曼·汗的同伙中,目前還有5人和奧斯曼·汗一樣,被有條件釋放,其中還包括當年團伙的頭目。
盡管“伊斯蘭國”日漸式微,但隨著大批極端分子返回歐洲以及極端分子從監(jiān)獄釋放,歐洲遭遇恐怖襲擊的風險在不斷增加。國際刑警組織秘書長斯托克在去年初就說過,大批極端分子在未來幾年將從歐洲的監(jiān)獄釋放,他們在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接受過專業(yè)訓練,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思悔改,一旦釋放很有可能發(fā)動“獨狼式”恐怖襲擊,這些“危險分子”是歐洲未來的重大安全隱患。
聯(lián)合國負責反恐事務的副秘書長沃龍科夫2019年2月11日向安理會匯報的有關(guān)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恐怖威脅的第八份報告中指出,目前“伊斯蘭國”及其分支組織活動比較隱蔽,但其領(lǐng)導層仍保持著影響力,且具有發(fā)動國際恐怖襲擊的意圖。其中,該組織中的外國武裝分子的存在加劇了這種情況,他們中一部分正離開沖突地區(qū),一部分已返回原籍,還有的即將從監(jiān)獄中被釋放。
“歐洲面臨的另一重要安全威脅是來自本土的極端分子。”歐盟反恐總協(xié)調(diào)員科赫夫說,這些人在思想上受到恐怖組織的蠱惑。2019年12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fā)生的恐怖襲擊實施者謝卡特就屬于這類人。謝卡特是一名北非裔,出生在法國,曾在法國、德國、瑞士多國入獄,罪名涉及盜竊、使用暴力等,警方推測他在服刑期間接觸到極端主義思想。案發(fā)前,法國警方已將他列入“極端人員監(jiān)視名單”。科赫夫說:“相比有組織的大規(guī)模恐怖襲擊,無組織、隨機的‘獨狼式恐怖襲擊更加防不勝防。”
在歐洲遭遇多次重大恐怖襲擊之后,歐盟成員國都建立了應對大規(guī)模恐襲機制,在最近兩年中都發(fā)揮了應有的作用。比如法國就對內(nèi)加強移民管理和反恐計劃,對外加大與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反恐軍事合作。
“最近幾年,在日益猖獗的恐怖威脅下,歐盟成員國在情報共享等方面取得一定進展,但由于安全事關(guān)各成員國主權(quán),各國在反恐領(lǐng)域的合作仍待加強,直到目前,歐盟還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反恐政策。”科赫夫說,恐怖主義是歐洲各國面臨的共同敵人,只有聯(lián)合起來形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才能有效打擊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
恐襲向更多國家蔓延
2019年4月21日,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等地的4家酒店、3處教堂和一處住宅區(qū)發(fā)生連環(huán)爆炸,造成至少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中國人在內(nèi)的30多名外國人。案發(fā)時正值西方基督教復活節(jié),眾多信徒集聚教堂參加隆重的儀式活動,這是一起精心策劃的、追求廣泛國際影響的大規(guī)模恐怖襲擊,也是2001年“9·11事件”以來發(fā)生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之一。
斯里蘭卡2009年內(nèi)戰(zhàn)結(jié)束后,給外界樹立了和平國度的良好形象,誰都沒想到會發(fā)生震驚世界的慘案。而在此前一個多月,被視為世界最安全國家之一的新西蘭也發(fā)生震驚全球的恐怖襲擊,50人在針對清真寺的槍擊中喪生。而2019年1月,在菲律賓蘇祿省的天主教堂也發(fā)生了炸彈襲擊案,造成至少27人死亡,77人受傷。針對教堂和清真寺發(fā)動襲擊,隱約顯現(xiàn)“文明沖突”的魅影,但更確切地說是“野蠻的沖突”。
偏安一隅,但仍未能免于恐怖主義侵襲。菲律賓、新西蘭和斯里蘭卡連環(huán)恐怖襲擊事件警醒國際社會,恐怖主義正向更多的國家傳播和蔓延,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確保百分百的安全。

2019年12月28日,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處公路檢查站清晨遭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已造成79人死亡。
在非洲,形勢也不容樂觀,遭受恐怖主義滲透的風險日益升高,非洲反恐形勢再次敲響了警鐘。布基納法索、尼日爾、索馬里等非洲國家前不久接連發(fā)生恐襲事件,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根據(jù)統(tǒng)計,去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qū)因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位居全球第二,首次超過中東北非地區(qū)。
世界反恐局勢處于“伊斯蘭國”崩潰之后的威脅外溢嬗變期,隨著美國逐步減少反恐投入和從主要反恐戰(zhàn)場抽身,國際反恐面臨大國牽引力下降和國際反恐難以合力聚焦的難題。
據(jù)經(jīng)濟與和平研究所的統(tǒng)計,在全球13個曾制造恐怖襲擊,并造成超過100人死亡的極端組織中,有6個主要活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分析認為,由于一些非洲國家政局動蕩,加上經(jīng)濟落后、部族矛盾交織,導致極端勢力乘虛而入。
分析認為,受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jīng)濟落后、部族矛盾交織等因素的影響,極端勢力加大了對非洲的滲透力度。非洲國家亟待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
在2019年7月舉辦的第八屆世界和平論壇“國際反恐形勢的新發(fā)展與新特點”分論壇上,中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陸忠偉認為,在伊斯蘭國氣數(shù)已盡后,現(xiàn)在的恐情新動向、新特點,尤其值得關(guān)注,并將其歸納為七點:后伊斯蘭國時代的反恐格局和戰(zhàn)爭軸線發(fā)生了變化;后伊斯蘭國時代的恐情特殊性和復雜性,表現(xiàn)在恐怖組織從死守城池向游擊圣戰(zhàn)的恐怖形態(tài)轉(zhuǎn)變;伊斯蘭國建政立國向基地網(wǎng)絡型蛻變,他們在化整為零潛入地下,還鄉(xiāng)蜇伏,這種隱蔽性以及分散性導致恐怖襲擊的威脅呈多維性;伊斯蘭國的技術(shù)隊伍在不斷提高;伊斯蘭國覆滅之后,正在按照他們的B方案,它的殘部向北非、東南亞、南亞以及中亞流竄,并且向非洲布基納法索、尼日爾以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滲透;本土恐怖勢力與伊斯蘭國重新整合,互傳伎倆;遠洋航行形勢嚴峻,在非洲除了索馬里、亞丁灣之外,近幾年出沒于幾內(nèi)亞灣和莫山比克海峽的海盜越來越多,成為社會熱點話題。
美國給世界反恐添亂
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2019年4月8日宣布,美國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列為恐怖組織。美方稱將采取必要手段威懾和破壞伊朗革命衛(wèi)隊的組織和活動,并制裁同伊朗革命衛(wèi)隊有經(jīng)濟往來的個人和實體。這是自特朗普退出伊核協(xié)議以來,美國對伊朗的又一次大規(guī)模制裁。這也是美國首次將一國的國家武裝力量列為恐怖組織,這一危險政策舉動給本已孱弱的國際反恐又一記重擊。
將伊朗與恐怖主義掛鉤只是美國制裁借口,行的是遏制之實。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guān)系學院院長王京武少將就曾指出:一些國家把打擊恐怖主義作為政策工具,謀求利益,使當前一段時間的國際反恐合作前景更加艱難。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在中東國家翻云覆雨,給一些國家經(jīng)濟上造成困難、政治上顛覆原有政權(quán),甚至直接出兵去攫取自己利益,埋下了中東等地區(qū)恐怖主義滋生的禍根。在敘利亞內(nèi)戰(zhàn)中,美國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縱容“伊斯蘭國”去打擊巴沙爾政權(quán),結(jié)果導致其掉頭反噬。
這些教訓并沒有讓美國有一絲反省,反恐政策的工具性色彩反而更趨濃厚,以反恐為幌子打壓他國。當前,在中東地區(qū),美國的首要目標是遏制伊朗進一步擴張地區(qū)影響,而打擊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反恐行動已不再是重點任務,對國際反恐的重視程度和資源投入明顯減少。與此同時,美國大幅調(diào)整安全戰(zhàn)略,將主要精力和資源用于遏制中國、俄羅斯等國。當國際反恐讓位于大國競爭,動能明顯不足。
此外,美國官員披露,美國國防部正考慮調(diào)整全球軍事部署,擬從西非地區(qū)大幅撤軍。在西非反恐形勢惡化之際,這一動向在美國政府內(nèi)部以及西方盟友間引起非議。
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guān)系研究院軍控與安全研究所所長、反恐研究中心主任傅小強指出,國際暴恐威脅仍然處于近40年來的大周期。2019年國際反恐形勢發(fā)生微妙變化:一方面國際恐怖和極端主義威脅并未因美國選擇性忽視而削弱,另一方面國際反恐的力度和節(jié)奏卻被美國任性打亂。他認為,世界反恐局勢處于“伊斯蘭國”崩潰之后的威脅外溢嬗變期,隨著美國逐步減少反恐投入和從主要反恐戰(zhàn)場抽身,國際反恐面臨大國牽引力下降和國際反恐難以合力聚焦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