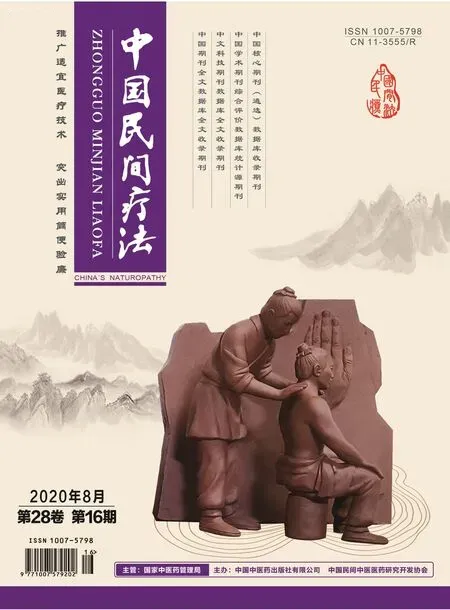芻議“針方”之臨證要略※
黃劍浩,陳嬌鳳
(1.福建中醫藥大學,福建 福州350122;2.福建省福州市中醫院,福建 福州350001)
針刺手法簡稱針法,是指醫者使用不同針具產生機械刺激以激發、調控、誘發經氣,氣至病所進而產生療效的技法。清代針灸學家李守先提到“針灸之難,難不在穴,在手法耳。明于穴而手法不明,終生不醫一疾;明于手法而因癥尋穴,難者多而顯而易知者亦不少矣。”研究表明,針法優勢組合治療疾病的療效明顯優于針法單獨使用,但也不乏針刺組合增效不明顯的案例[1-3]。鑒于此,臨床亟待解決針法如何有效組合的問題。針方是在中醫基礎理論的指導下選擇合適的針刺手法,以生物力學原理為依據酌定刺激量,借鑒中藥方劑組方結構框架,形成的以提高臨床療效為宗旨的超越復式針法的針刺手法優勢組合方案。筆者基于長期臨床實踐并結合文獻解讀,初步探討運用針方理論指導針法的有效組合方法,以期為臨床提供借鑒。
1 針方之理——方由結立,結由證出
《靈樞·經脈》言:“凡刺之理,經脈為始。”著重強調針刺之理是以經脈為本源,而經脈之氣輸注出入于腧穴,故探討針方之理需進一步落實到腧穴。《靈樞·九針十二原》言:“神乎,神客在門。”《靈樞·小針解》言:“神客者,正邪共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指出人體一旦內藏神氣不足,邪氣可隨正氣游行出入。《傷寒論考注》言:“凡云結者,謂邪氣與物相結聚也。”《傷寒貫珠集》言“蓋邪氣入里,必挾身中所有,以為依附之地。”提示邪氣可依附、客居于身體有形物質中。六淫、戾氣等邪氣可依附瘀血、痰、水飲等有形實邪,結聚成形聚于腧穴,形成穴結。結節、斑疹、條索、激痛點、敏化點、橫絡等病證反應點均屬于“穴結”范疇,是中醫學“證”在經絡系統的具體表現形式,可反映疾病發展的病程階段。臨床可將“有是結,用是方”的辨證方法,即方結辨證,作為針刺手法配伍選穴的依據。
《靈樞·九針十二原》言:“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五體是《黃帝內經》中人體解剖結構軀體部分的主體框架,其內合五臟,外應五行,反映了人體由淺入深的5個不同層次[4]。以病邪結聚的五體解剖位置為準則的分類方法稱為五體穴結。病邪結聚于毛發、腠理等皮部系統,為皮結;結聚于分肉、肌腠、溪谷等肉部系統,為肉結;結聚于經隧、經脈、絡脈、孫絡、浮絡,為脈結;結聚于經筋、宗筋、維筋、緩筋,為筋結;結聚于各部骨及骨結構相關的關節、骨屬、骨空,為骨結。五體穴結的治則為“病在脈,調之血;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調之骨”。治療遵循《靈樞·官針》中五刺、九刺和十二刺的論述。皮結應選取半刺、毛刺、直針刺;脈結選取豹文刺、絡刺、贊刺;肉結選取合谷刺、分刺、浮刺;筋結選取關刺、恢刺;骨結選取輸刺、短刺。如皮脂腺囊腫、痤瘡等屬于“皮結”范疇,宜配伍半刺、毛刺、直針刺。
2 針方之道——君、臣、佐、使
《神農本草經》言:“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君、臣、佐、使的概念來源于邦國制度,方劑與邦國是一對隱喻的概念匹配[5],針刺手法之間或藥物與針刺手法之間通過合理的配伍,也能發揮相輔相成的綜合作用。如通痹開結調氣針法是在提插法、捻轉法及搖擺法的基礎上,重視手法間君、臣、佐、使的配伍關系,形成以蒼龜探結(君法)、搗法和恢刺法(臣法)、青龍擺尾和白虎搖頭(佐法)等治療痹證和其他病證的特色組合針法[6]。君的隱喻概念是發號施令的尊者,在方劑結構中是針對主癥或主病起主要治療作用的部分[7]。通痹開結調氣針法的君法為蒼龜探結,來源于《針灸大全·金針賦》,其言:“蒼龜探穴,如入土之象,一退三進,鉆剔四方。”《刺法灸法學》言:“將針刺入穴位后,先退至淺層,然后更換針刺方向,上下左右多向透刺,淺、中、深三層逐層加深,并以拇指或食指抵住針體,做上下撥動(剔)的動作,‘鉆’指擴大針法的刺激面積,兩種操作配合運用。”通痹開結調氣針法著重發揮“鉆”的探察作用,而將“剔”的動作進一步簡化。具體操作步驟:醫者用押手觸診,進針后緩慢行針,依次穿透皮、脈、肉、筋達至骨面,上、下、左、右不同方向反復操作以尋找穴結。該法彌補了審循切按難以診察深部反應點的不足,豐富了臨床切診的應用。臣的隱喻概念是地位和社會權利次于君,并為君做事的人。搗刺法來源于《金針梅花詩鈔》,其言:“搗,捏持針柄不進不退,但又如進如退,在原處輕出重入,不斷提搗,有如杵臼,亦如雀之啄食。”[8]恢刺法來源于《靈樞·官針》,其言:“恢刺者,直刺,傍之,舉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其針感較強,解結力量較大,作用僅次于探結尋結的蒼龜探穴,故為臣法。佐隱喻概念是輔助臣行事,發揮更為次要的作用。五刺、九刺和十二刺等可根據穴結的不同靈活配伍,故為佐法。使乃“史”“吏”“事”的后起字,其本意為奉君王之命使于四方的使者,后引申出派遣、命令等含義[9]。使法多取調和之義,如赤鳳迎源法可激發經氣,調和諸法。
3 針方之屬——生物力學
《靈樞·終始》言:“凡刺之屬,三刺至谷氣。”張景岳注“谷氣”為“神氣”,淺刺祛陽邪,中層刺祛陰邪,深刺“分肉間”可使神氣正常地游行出入,起到調氣的作用[10]。三刺何以至谷氣?考慮到當時針具鍛造技術水平,能否直接刺至“分肉間”尚未可知[11]。《靈樞·官針》言:“合谷刺者,左右雞足于分肉之間,以取肌痹。”《醫學綱目》言:“雞足取之者,正入一針,左右斜入二針如雞之足之爪也。”《刺法灸法學》提到“多在肌肉豐厚處針刺,當進針后,退至淺層,又依次向兩旁斜刺,形如雞爪的分叉”。操作術式上雖存在“一針三向刺”和“三針刺法”兩種爭論[12],但不難發現無論哪種操作術式,其共性都是3次針刺提插形成“雞足”,所形成的合力必然大于任意一針的分力,從而滲透至更深的解剖層面。合谷刺實際上蘊藏著的合力效應才是其刺至神氣的關鍵。通痹開結調氣針法中的蒼龜探結也利用了“力的分解”的原理,傍針刺、齊刺、揚刺等在不同程度上均利用了合力效應,其結果就是增加疏通的力量和作用。如恢刺、青龍擺尾等撬撥法利用了“杠桿原理”,以巧勁一針帶多針,增加了疏通之力,即治點又治面,所施加的刺激量大。筆者認為,生物力學可為臨證酌定針刺刺激量的依據。
4 典型病例
患者,女,35歲,2018年12月25日就診于福州市中醫院。主訴:雙下肢間歇性酸麻10余年,加重10 d。現病史:患者10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雙下肢酸麻,以酸感為主,偶有蟻行感,發作具有明顯節律性,多于固定體位或入睡后加劇,坐臥不寧、煩躁不安,每于抖腿、行走或用力擊打后減輕,與氣候無明顯相關性。曾于當地三級甲等綜合醫院就診,查類風濕因子、腰椎核磁共振成像、雙下肢動靜脈彩超未見異常,診斷為不安腿綜合征,予電刺激、經顱磁刺激治療后,發作頻率有所減少。近10 d雙下肢酸麻加重,嚴重影響生活作息,遂來就診。查體:步態正常,肌力、肌張力正常,局部無紅腫和明顯壓痛點,無靜脈瘀滯,“4”字試驗陰性,神經系統檢查無陽性體征。刻下癥:患者精神焦慮,伴雙下肢酸麻,偶有脹痛,坐臥不寧,呈蟻行感,納可,寐差,二便調,舌淡,苔微黃膩,脈濡。西醫診斷:不安腿綜合征。中醫診斷:痹證(濁痹)。治則:開結通痹化濕。取穴:風池、風府、翳風、完骨。針方:君法蒼龜探結,臣法搗法,佐法恢刺法,使法赤鳳迎源。具體操作:患者取俯臥位,醫者用壓手切診枕骨下緣,選取0.4 mm×25 mm的無菌針灸針,針尖對準腧穴向上方呈45°~50°刺入,透刺至針尖觸及枕骨面,反復向左、右兩側從天部針至地部,以指下針感探尋病結;探至“筋層”穴結進行不斷地提搗,如雞雀之啄食;再配合數次向左、右方向的搖擺、撬撥,使手下的緊感、堅硬感、砂樣感或針尖被禁錮感消失,直至出現徐和感,最后刺手拇、食指捏持針柄呈交互狀,細細捻搓數次,然后張開兩指,一搓一放,狀如飛鳥展翅,搓摩約呈720°,使針感向四周及深部放射,刺激量以患者耐受為度,留針30 min。治療1次后,患者訴發作頻率減少,治療7次后基本控制,隨訪半年未再發作。
按語:不安腿綜合征以一側或雙側下肢具有不能名狀或難以忍受的酸、麻、脹等不適感為臨床特征的一種綜合征,在中醫學中雖無確切的病名,但與《黃帝內經》中記載的“脛酸”“痹證”等相似,多因風寒濕邪客于經脈,經脈痹阻所致。《針灸聚英》言:“腿腳有疾風府尋。”表明風府對下肢痹證的作用顯著。《玉龍歌》言:“若然痰飲風池刺。”風池功擅祛風利濕,輔以翳風、完骨,共奏祛風利濕、通痹止痛之功。針方的處方思路:蒼龜探結針法探結尋結,為君法。以搗法為核心的開結針法,為臣法。風府的解剖層次依次為皮膚→皮下組織→左、右斜方肌肌腱之間→項韌帶。進針過程中在項韌帶處探至穴結,即筋結。《靈樞·官針》載:“恢刺者,直刺傍之,舉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故以恢刺法為佐法。赤鳳迎源以激發經氣,調和諸法,為使法。結開痹通而氣調,通則諸癥皆消。
5 小結
針方處方的模式是以穴結為立足點,借鑒中藥方劑君、臣、佐、使的配伍規律,并融入現代生物力學理論以酌定刺激量,倡導“有是結,用是方”的辨證方法,可明顯提高針法優勢組合效率。但還需加強對針刺手法客觀量化和標準化的研究,以進一步揭示針刺手法間量效作用規律,從而將針刺的治療效應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