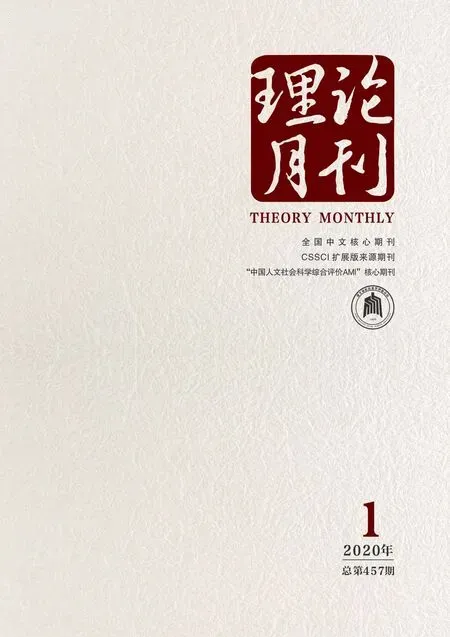農業文明的螺旋演化與原生國家的形成
□王志琛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長期以來,國家起源始終是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和政治學關注的熱門話題,莫頓·弗里德(Morton H.Fried)把最早出現的或者不受其他國家影響獨立演化生成的國家定義為原生國家(Pristine State),其他所有后出現的國家都叫作次生國家(Secondary State),國家起源其實考察的是原生國家的形成過程。1970年,著名人類學家羅伯特·卡內羅(Robert L.Carneiro)提出環境限制理論,他用封閉性的秘魯沿海山谷和開放性的亞馬遜盆地做對比,說明受限的地理環境在國家起源中的重要意義[1](p733-738)。秘魯沿海山谷的耕地被農業村莊(village)占滿時,不斷增加的人口因為有限的土地而爆發戰爭,由于地理環境的封閉,失敗的村莊無法搬走,只能向勝利者臣服,繳納貢品或稅收,政治由此實現了升級,產生了酋邦(chiefdom),酋邦再通過戰爭不斷相互兼并,產生了王國(kingdom),與之相反,亞馬遜盆地的開放性導致競爭失敗的村莊可以搬到其他地方重新開辟定居點,不必向勝利者臣服,政治始終得不到進化。環境限制理論憑借高度簡潔性和較強邏輯性,成為接受度極高的國家起源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卡內羅在收獲贊美的同時,也遭到一些學者的批評。
大衛·韋伯斯特(David Webster)是戰爭起源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承認生態壓力在文明演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強調多數原生國家形成的地方并不符合如卡內羅所說的環境受限的區域,合適的環境條件應該是核心—邊緣這種生產和人口潛力顯著不同且面積足夠大的相鄰地區。核心—邊緣的地理條件允許不同復雜程度的政治自治社會共存,關鍵是邊緣地區有小塊土地可供核心區域(人口密度較高)的酋邦擴張,酋邦的高級管理集團可以獨享這些土地,從而擁有了除威望以外的財富資源[2](p464-470)。羅伯特·沙赫特(Robert M.Schacht)逐一辨析環境限制理論的四個要素之后——受限的農業耕地、人口壓力、戰爭和國家,認為環境的催化劑效應是復雜的,雖然封閉的地理可以讓演化的動力集中,但應該增加其他環境變量,如不同的農業生產潛力,來提高模型的精確度[3](p438-448)。針對質疑,卡內羅指出,區域面積和地理封閉性共同影響政治進化的速度,最有利于國家形成的環境包含三個特征:地理足夠封閉以阻止人們通過遷移來緩解人口壓力;面積足夠小以便相對快速和容易地聯合;面積還必須足夠大以確保聯合后的政體龐大且復雜,從而能夠形成國家[4](p498-500)。可見,卡內羅把自己的環境限制理論帶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從上述的爭論中我們不禁要問,到底什么樣的地理環境有利于原生國家的形成呢,是卡內羅受限的地理環境,還是韋伯斯特核心—邊緣開放式的地理環境?沙赫特提及的農業發展潛力又在原生國家形成過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呢?
二、國家起源的既有研究
國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高級形式,社會演化論認為人類社會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無論通過單線演化、多線平行演化,還是非線性演化,存在普遍適用的演變規律,根據階級斗爭和戰爭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大小,社會演化論分為兩大派別:沖突論和整合論。沖突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會》一書,他依據技術進步將人類社會從低到高分為三種狀態:蒙昧社會、野蠻社會和文明社會,蒙昧社會和野蠻社會又各自細分為初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摩爾根認為高級野蠻社會始于鐵器的制造,終于標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獻記載的出現,這是文明社會的開端;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聯盟是古代社會自從氏族出現以后長期保持的組織形式,希臘人和羅馬人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創立了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政治組織,即國家[5](p3-35)。摩爾根直接跳過了青銅時代,把文明社會的起始時間設定得非常晚,不過他以地域取代血緣、財產私有制取代財產公有制作為國家和前國家社會區分標準的思想,被后來的學者廣泛接受,尤其被馬克思主義學者發揚光大。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該領域的經典著作,恩格斯認為,隨著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剩余產品的出現導致了復雜的勞動分工,少數人通過控制生產手段,掌握大量經濟財富,不斷剝削廣大窮人。國家正是這種階級斗爭的產物,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一切場合本質上都是鎮壓被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工具[6](p183)。莫頓·弗里德繼承了恩格斯的思想,將社會分為四種類型:平等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階等社會(Rank Society)、分層社會(Stratified Society)和國家(State)。弗里德認為生態所能承受的人口規模和再分配的出現是平等社會進化成階等社會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在人口壓力增大、婚后居住習俗改變等條件作用下,階等社會逐漸向分層社會轉變,相同性別和年齡的成員獲取基本生存資料的使用權不同是分層社會的主要特征[7](p182-196)。但弗里德認為分層社會中不存在國家級別的政治機構,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也導致弗里德政治社會演化理論給人的印象是,階等社會的權力太弱,而國家社會的權力太強,對農業定居社會來說,土地是最重要的基本生存資料,包括土地所有權在內的經濟基礎發生如此重大的變革,政治上層建筑應該會有所體現。
整合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代表人物霍布斯、亞當·弗格森、洛克、休謨、孟德斯鳩、盧梭等。誠如弗格森所言,人類最初是平等的,他們實則天然地享有平等地保護自己、使用自己才華的權利,社會的利益和成員的利益容易達成妥協,政府的締結應該旨在解決人類的快樂或痛苦,很明顯存在一些統治形式對于人類和對于社會本身都同樣必要,這不僅是為了實現政府的目標,也是為了順從自然形成的秩序[8](p55-60)。實際上,工業革命之前國家這種統治形式至少已經存在了四千年,社會契約論思想主要是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誕生鋪路,與原生國家的形成并無太大關系。20世紀50年代以后,作為新演化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埃爾曼·瑟維斯(Elman R.Service)認為,國家由“隊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國家(state)”的路徑進化而成,政治機構產生于服務某一預定目標,但后來被用于服務眾多更重要的整合性功能,這些新功能最開始并沒有被考慮到;在所有早期文明和歷史上已知的酋邦和最初的國家中,權威官僚的產生與擴張也是統治階層和貴族的產生與擴張,因此,最早的分層主要是政治分層——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而不是所有制集團的分層[9](p277-285)。瑟維斯強烈反對階級斗爭是國家起源的原因,反復強調再分配系統是官僚權力的來源,酋邦首領通過提供安全保護、維護長距離貿易、裁決內部糾紛等措施不斷加強和鞏固自己的地位。正如喬納森·哈斯(Jonathan Haas)所言,瑟維斯的整合理論依賴于對沖突論的駁斥,建立在最初的國家和文明與前國家社會沒有差別的基礎之上,但他本人卻不承認當一個政府有能力向民眾提供物品和服務時,它便同時具備了強有力的制裁工具[10](p64-65)。
整合論的精髓在于統治階層提供某種公共物品,以換取被統治階層的服從,至于這種公共物品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學者擁有不同的觀點。魏特夫(Karl A.Wittfogel)認為在諸多農業生產要素中,如有用的農作物、可耕種的土壤、充足的水源、適宜的溫度(光照與季節)和適當的地貌等,只有水源,前工業社會的農民可以通過修建灌溉設施進行調節,水利農業(hydraulic agriculture)導致了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和水利經濟(hydraulic economy),促進了勞動分工、農業集約化和大規模勞動合作的產生,農業管理人員(agromanagerial)的職能從農業領域不斷擴展到非農業領域,如修建防衛設施和道路、制定歷法等,他們逐漸演變成農業官僚(agrobureaucratic),成為統治階層,水利國家(hydraulic state)由此形成[11](p11-48)。魏特夫的農業灌溉理論由于過度追求普適性,案例選擇的范圍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都極其龐雜,招致了大量批評,損害了其理論的有效性,即便如此,魏特夫的理論抓住了農業——雖然并不一定是農業的灌溉方面——是國家起源的關鍵變量,總體上依然優于接下來將要介紹的貿易和城市理論。
貿易和城市理論擁有眾多追隨者,這些學者普遍認為長距離的商業貿易網絡需要開發和維護,城市人口的規模和密度較大需要組織協調管理,這些都要求權力集中的管理階層,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和政治的復雜性日益增大,最早的國家必然產生于城邦(city-state)。如琳達·曼薩尼利亞(Linda Manzanilla)所言,神廟組織作為復雜再分配循環的中心,是“城市革命”的基礎,隨后,宮殿成為收納貢品的軸心和階等社會的頂端,國家由此誕生[12](p27)。作為該理論的極端支持者,彼得·泰勒(Peter L.Taylor)已經把城市的重要性提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不凡,以至于它們擁有創造農業和國家的能力[13](p442)。但是,這些學說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實:早期文明大多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人口中絕大部分是農業人口,祭司、工匠、軍事首領等非農業人口所占比率低于10%,例如阿卡德帝國統治精英的直接依附者——仆人、家務奴隸、雇傭工匠、管理者和士兵只占總人口的5%—7%;長距離貿易交換的是奢侈品、祭祀葬禮用品等威望物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它們是統治階層(指階等和分層社會的統治者們,下同)的需要,而不是被統治階層的需要,與其說長距離貿易產生威望,不如說它是威望的產物。城市化本質上是生產力達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工業革命以后的事情,用工業革命以后的情況來解釋史前時期,不符合歷史的客觀實際,考察原生國家的形成,應該從農業發展的角度入手。
三、農業文明的發展潛力
農業是絕大多數早期文明最主要的經濟部門,少數情況是農業和畜牧業的混合經濟[14](p637)。農業定居社會想要保持穩定可持續發展,至少需要滿足下面三個條件:(1)非農業人口的消耗量應該小于或等于糧食總產量減去農業人口自身消耗之后的剩余糧食產量,即統治階層(如果存在的話)所消耗的社會財富必須在被統治階層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2)農業人口的數量應該小于或等于耕種全部耕地(考慮到休耕因素)所需要的農民數量,即農業社會擁有足夠的土地以吸納它的農業人口;(3)單位農業人口的消耗量小于或等于他所能生產的糧食,即糧食產量應該出現剩余,這是抵御災荒和供養非農業人口的前提。用數學公式將這三個條件表達如下:

n:非農業人口數量;m:農業人口數量;
i:單位非農業人口消耗量;i0:單位農業人口消耗量;
P:農業定居社會的勞動生產力,以單位農業人口能夠耕種的土地面積計;
A:農業定居社會耕地總面積;q:農業定居社會耕地的綜合質量;
u(q):單位耕地面積的糧食產量,u(q)>0;
v(q):農業定居社會耕地的使用率,0<v(q)≤100%。
由不等式③可以推導出不等式④,如下所示:

關于動植物的馴化和農業發源地問題,賈雷德·戴蒙德作了極為精彩和詳細的論述,不僅令人信服地解釋了新月沃地、中國、安第斯山區和美索美洲能夠成為農業獨立發源地的原因,還指明了農作物品種和農業技術在歐亞大陸沿緯線比在美洲大陸沿經線傳播速度更快的事實[15](p55-188)。有意或無意,戴蒙德主要圍繞上述不等式④中單位耕地面積的糧食產量u(q)探索農業起源問題,如最高產的農作物品種、最肥沃的土壤、最適宜的氣候水源條件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糧食產量u(q),根據不等式④,單位農業人口消耗量i0不變的情況下,單位耕地面積的糧食產量u(q)越大,所需要的起始勞動生產力P越小,即從事農業生產的門檻(Threshold)越低,這是新月沃地和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生產力非常低的時候,就能最早實現農業定居的根本原因。烏爾王朝初期,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大麥收獲率高達76.1倍,同一地區現代的收獲率不超過7到8倍,可見當時的新月沃地多么肥沃[16](p77)!影響糧食產量u(q)的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土壤的肥沃程度。在化肥被投入農業生產以前,糧食產量最大的制約因素是土壤的肥力,為解決肥力短缺問題,工業文明之前的農業社會普遍使用人畜的糞便作為肥料。另外,土壤的肥力也影響耕地的休耕年限,肥力越差,休耕年限越長,某些較差的耕地,甚至需要休耕二十多年才能恢復肥力,從而降低了農業定居社會耕地的使用率v(q)。
不等式①×②2可以推導出不等式⑤,如下所示:


圖1 農業文明發展潛力C關于農業定居社會勞動生產力P的函數圖
如圖1所示,是農業文明發展的生產力門檻,只有當勞動生產力P大于它時,農業定居社會才開始具備供養非農業人口的能力;當勞動生產力P等于時,農業文明發展潛力達到最大值;當勞動生產力P大于時,農業文明發展潛力C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出現下降。這一點符合約瑟夫·泰恩特關于社會復雜化邊際收益遞減的解釋,本文的圖1也與他著作中復雜化增加狀態下的邊際產量函數圖相似[17](p167)。在農業文明初期,一個極小的農業技術進步,都將帶來巨大的社會收益,該收益不僅有利于統治階層,也有利于被統治階層,在此階段,統治階層鼓勵新技術的研發和使用。但是,隨著技術進步帶來的邊際收益越來越低,當農業文明發展潛力達到最大值以后,農業技術的提高已經不符合統治階層的利益,于是在政治實踐中統治階層會抑制技術的進步。
在農業文明早期,先發農業社會的生產力停滯時間,為后發農業社會、甚至是游牧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和時間上的保障,從而使后者超越前者成為可能。如前文所述,最早的農業定居社會出現在最適宜耕種且土壤最肥沃的地區,一般都是沿河分布的肥沃易耕種土地,隨著農業定居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從發源地逐漸向臨近區域擴散,土地耕種的難度不斷上升,而肥沃程度卻在不斷下降,即耕地的綜合質量q逐層降低,對于耕地綜合質量q的評分定級,可以借鑒美國土地評價和立地分析系統(LESA)的做法,不過在農業文明早期,耕地的自然條件(LE)比社會經濟條件(SA)更重要。假設后發農業社會耕地的綜合質量q?是先發農業社會的1/2,即,參照既有的研究數據,后發農業社會單位耕地面積的糧食產量u(q?)變為原來的1/2①劉瑞平等將LE:SA的比值設定為3:2,這更符合農業文明早期情況,根據他們文章中耕地質量綜合分值與標準糧產量相互關系公式y=114.89x+464.96,分值x從最高值100分下降到50分時,產量y降為原來的1/2左右,參見劉瑞平、王洪波、全芳悅:《自然因素與社會經濟因素對耕地質量貢獻率研究》,載《土壤通報》2005年第3期。,耕地使用率也變為原來的1/2,即v(q?)變為原來的70.7%②關于耕地的休耕和使用率參考的是:(1)哥倫比亞安第斯山區經過長期耕種,土地貧瘠,休耕率穩定在25%—30%以保證土壤肥力的恢復,耕地的使用率則為70%—75%(參見Edmundo Barrios,Juan G.Cobo,et al,“Fallow Management for Soil Fertility Recovery in Tropical Andean Agroecosystems in Colombia”,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Vol.110,2005,pp.29—42);(2)津巴布韋奇維區的耕地在肥力下降、畜力不足等多種因素作用下,休耕率從1984年的0上升到2010年的51.5%,土地的使用率變為原來的49.5%(參見Emmanuel Manzungu and Linda Mtali,“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Fallow Land and the Underlying Causes in Southcentral Zimbabwe,”Journal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Vol.4,No.4,2012,pp.62—72)。以上數據都來自農業落后的偏遠地區(不使用化肥和機械,只用人力和畜力耕種),但即便是這樣的地區,它們的勞動生產力可能也高于農業文明早期的情況,本文中“后發農業社會耕地使用率v(q?)變為原來的70.7%”,只是為方便理論描述而進行的估算。,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作出后發農業社會文明發展潛力的函數圖如下。

圖2 不同耕地質量的農業社會文明發展潛力函數圖
如圖2所示,當耕地綜合質量從q下降到q?時,后發農業社會文明發展的生產力門檻變為,是先發農業社會的2倍,實際上,它也是先發農業社會文明發展潛力達到最大值時的生產力,先發農業社會為后發農業社會的文明發展準備了生產力基礎。農業文明早期,增大勞動投入和加快耕作效率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主要途徑,前者依賴于統治階層的強制,因為民族學研究發現,在沒有外界的壓力下,農民更傾向于享受休閑的余暇而非努力生產超出自己所需要的剩余產品[18](p229);后者依賴于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畜力的使用。農業生產工具從新石器時代,經過銅石并用時代的過渡,一直到青銅時代不斷發展演化,其間伴隨著大型哺乳動物的馴化,擁有大型牲畜的社會具有無與倫比的發展優勢,這些動物不僅為人類提供了肉食、奶制品、皮革、毛絨和肥料,更重要的是能被用于犁具牽引、軍事突擊和陸上運輸。相對于單純依靠人力的社會,使用動物運輸技術的社會,可以讓不同地區之間的交往更有效率,從而使更大地理范圍內的社會整合成為可能[19](23)。農業生產從人力向畜力的轉變,是早期農業文明生產力水平質的飛躍,七種對生產力有巨大提升的牲畜(馬、黃牛、水牛、中亞雙峰駝、阿拉伯單峰駝、驢和羊駝),歐亞大陸占據六種,美洲僅有的羊駝,不僅運輸能力差,無法供人騎乘和拖拉戰車,最致命的是它不能牽引犁具用于耕田,這是美洲早期文明農業生產力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
四、社會形態的演化軌跡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引言中提出的問題,利于國家形成的地理環境,如韋伯斯特和沙赫特所判斷的,是核心—邊緣這種農業生產潛力不同且面積足夠大的相鄰區域,它符合間斷平衡理論的思想。1972年,古生物學家奈爾斯·埃爾德雷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 Gould)提出間斷平衡理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該理論認為新物種的誕生是一件稀少且困難的事件,它形成于核心區的邊緣,打斷了原先的自我平衡系統,相較于長期穩定,大多數變異發生在極短時間[21](p82-115)。生產力的增長符合漸進累積的傳統社會演化論思想,而政治體制的演化更符合間斷平衡理論,即長期的穩定和短期的巨變交替出現。卡內羅的環境限制理論,其實是核心—邊緣的一種特殊情況,即邊緣區的耕地綜合質量無限趨近于零,導致單位耕地面積的糧食產量也無限趨近于零,而此時生產力門檻變得無限高,核心區的農業社會根本無法為邊緣區提供滿足開發所需的起始生產力,當核心區的土壤肥力耗盡或者遇到突然災害,該農業社會只能衰落崩潰,難以得到傳承,受限的地理環境不利于社會演化。
W如圖3所示,豎直方向代表時間因素,水平方向代表空間因素,在核心—邊緣的地理環境下,農業定居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從農業發源地逐漸向外圍傳播,耕地的綜合質量q環繞農業發源地逐層遞減,在每衰減1/2處畫一道圈,可以得到如圖3所示不斷增大的、螺旋上升的喇叭形,它就是農業文明演化的軌跡,伴隨這個軌跡上升的是社會的復雜化程度,農業定居部落、酋邦、原生國家分別形成于q1層、q2層和q3層。由前文的推導可知,每一個橢圓的圈都代表進入下一層的生產力門檻,前一層農業社會文明發展潛力達到最大值時的生產力,剛好成為后一層農業社會越過該門檻的起始生產力。

圖3 農業定居社會螺旋演化圖
農業定居部落形成于農業發源地q1層,處于從狩獵—采集的攫取型經濟向生產型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不同于卡內羅所說的村莊(village),雖然兩者都是小型農業定居聚落,但農業定居部落繼承了原始群體以血緣作為社會連接紐帶的特點,是一種平等的公有制社會,村莊純粹只是地理行政區劃的概念,即使偶爾整個村莊可能都屬于相同姓氏。農業定居部落無需繳納貢品,也不存在統治階層,傾向于把所有糧食全部轉化為生育沖動,反復進行生殖—分裂模式的簡單增長,當人口太多超出容納范圍后(一般在幾百到一兩千人不等),農業定居部落就會分裂成兩個或多個,一個留在原地,其余遷移到與母體部落耕地綜合質量相同的地方定居,繼續重復生殖—分裂模式。總之,經過漫長的農業技術積累,包括油料、果蔬、纖維等作物的培育,尤其是在兩河流域的綿羊、山羊、牛以及中國的豬、水牛這些大型哺乳動物馴化以后,農業定居部落對野生動植物資源的需求迅速下降,生產型經濟獲得了對攫取型經濟的重要優勢,農業定居部落在q1層不斷擴張,擠占狩獵—采集群體的生存空間。
當q1層農業定居部落的生產力發展達到q2層的生產力門檻時,q2層開始出現農業定居社會。相較于q1層異常肥沃且容易耕種的土地,q2層耕地的綜合質量次之,導致其對攫取型經濟的優勢下降,q2層農業社會需要更高的農業生產力;另外,面對q1層人口密度和規模更大的農業定居部落的競爭壓力(早期情況),q2層農業社會需要更大范圍的地理整合。變異是無目的、無順序、無規律的,巨變期的社會能夠涌現各種不同的政治思想,但選擇是有目的、有順序、有規律的,q2層農業社會雖然存在各種不同變異的可能性,但被選擇的形態一定符合上述兩項要求,即增大勞動生產力和耕地總面積,至少成功實現發展的社會是這么選擇的。q2層農業社會無法選擇農業定居部落這種社會形態,因為部落僅有的性別和年齡分工機制近乎生物本能,對生產力的刺激作用低效而且緩慢,當q1層土地被占滿,即生殖擴張的動力減弱后,農業定居部落缺乏發展生產力的熱情;除此之外,由于農業定居部落的社會連接紐帶依賴于血緣,當生殖—分裂經過兩三代以后,新生部落與最初母體部落的親緣性就已經很微弱了,血緣作為連接紐帶不利于更大地理范圍的社會整合。
在q2層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意識形態的物質化”獲得了對其他變異行為的競爭優勢。“意識形態的物質化”指用具體的、有形的方式將意識形態表現出來,這些方式包括:儀式性活動、象征性物品、公共紀念建筑和書寫系統,它們分別有助于聯合或召集各個群體、獎勵擁護者、永久化全體或領袖的權力、傳遞信息或進行宣傳[22](p15-31)。文明程度較低的社會一般只具備前三種方式,q2層農業社會盛行的意識形態是對神的信仰,這并不是為了打破血緣紐帶,因為q2層農業社會所信仰的神,來源于對祖先的崇拜,對同一個神的信仰,其實是對共同祖先的身份認同,q2層農業社會只是把農業定居部落直接的血緣聯系異化成了間接的血緣認同。意識形態并不是社會的消極反應,恰恰相反,作為積極因素被個人和集團用以建立和合法化他們的統治[23](p77)。那些持續不斷地把大量珍貴資源(人力、物力)投入到信仰事業中的農業社會,如舉辦大型飲宴慶祝活動、修建宏偉的神廟等,能夠召集生活在不同地區的群體,實現更大地理范圍的社會整合,而負責活動主持策劃、神廟維護等任務的人則成了最初的神職人員,他們是身份尊貴的祭司,壟斷了對神的旨意進行解讀的權力,獲得了高于普通民眾的地位,這樣的社會符合階等社會的特征,一般被稱作酋邦。修建神廟、制作象征性物品等行為促進了勞動分工和專職工匠(視酋邦的大小和復雜程度而定)的產生,他們是祭司的附屬,建筑和制造所需的稀缺材料,如黑曜石、原木、金屬礦石、青金石、玉石等,早期可能以相鄰酋邦之間互惠性禮品交換的方式獲得,后期則主要依賴遠距離貿易,這提高了酋邦的組織和運輸能力。由于需要繳納貢品以進行意識形態的物質化,酋邦的農民通過加大勞動投入來增加糧食產量,起初可能是自愿,作為神裔的優越感或許能夠鼓舞他們的勞動熱情,但祭司的神權權威確立以后,不排除強制的可能,尤其是在酋邦時代的后期,祭司作為酋邦的統治階層,可以協調不同區域內的勞動分工和資源分配,促進集約化農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業生產力。
隨著“意識形態的物質化”這一變異行為在q2層農業社會間不斷傳播,信仰不同神明的酋邦紛紛崛起,神明之間的親屬、朋友或仇敵關系,反映了酋邦之間復雜的互動。芭芭拉·普賴斯(Barbara J.Price)為研究國家起源問題構建了簇生互動模型(Cluster-Interaction Model),簇生個體的大小、制度結構、相對力量和生產方式都是類似的,它們的互動行為包括經濟性交換(廣義的貿易)、競爭和戰爭,整個簇生系統并不呈現等級化,也沒有確定的權力中心,長期來看,簇生系統內部的競爭不會趨向顯著的或持久的不平等[24](p209-233)。與普賴斯相似,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認為,同等政體互動(Peer Polity Interaction)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競爭(包括戰爭)和競爭性模仿;符號的借用和創新的傳播;日益增長的貨物交換。這些社會政治實體之間的聯系非常緊密,遠超與地區外的聯系,構成相互關聯的、但政治上又彼此獨立的互動集團,類似于他曾經論述過的早期國家模塊(Early State Module)[25](p1-10)。兩位學者都認為國家形成于一組互動政治實體的內部,某個實體通過吸收、擴張等方式合并其他實體,從而形成國家,但這種觀點存在邏輯錯誤——既然都是制度和力量相似的個體,又怎么能實現吸收或擴張呢?簇生互動和同等政體互動兩種互動類型適合描述酋邦之間的關系,但不適合描述酋邦與原生國家之間的關系。正如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26](p3)。當q2層酋邦的生產力發展達到q3層的生產力門檻時,q3層開始出現農業定居社會,q3層耕地的綜合質量較差,比q2層更加迫切地希望提高農業生產力和擴大耕地面積。同樣,q3層農業社會無法選擇酋邦這種社會形態:酋邦是地緣和血緣的混合組織方式,地理整合的力度有限,不能滿足q3層農業社會對更大耕地面積的需要;q2層被酋邦占滿形成酋邦體系之后,發展生產力的熱情消退,而此時q3層農業社會才剛剛起步,文明發展潛力遠沒有達到最大值,酋邦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無法滿足q3層農業社會對更高生產力的需要。
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土地私有成為q3層農業社會的優勢選擇。恩格斯把私有制作為國家起源的標志性事件,財產私有也是弗里德分層社會區別于階等社會的標準。蒂莫西·厄爾(Timothy Earle)甚至認為早在酋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土地私有的情況,酋長控制主要產品的財產權是復雜分層社會演化的基礎,意識形態控制和經濟控制是相互依賴不可分離的,經濟基礎給予意識形態控制穩定性,意識形態控制給予經濟基礎合法性[27](p71-99)。相對于厄爾的激進,布萊爾·吉布森(D.Blair Gibson)的論述可能更符合酋邦的實際情況,土地財產私有的概念是一種鑲嵌式的漸進過程,在平民部分土地仍是公有的,而在上層集團土地呈現出私有財產的特點[28](p46-62)。q3層農業社會土地綜合質量一般,開墾和維護的成本較高,在平民部分也實行土地私有,這可以極大提高農民耕種的積極性,鼓勵社會把更多人力和技術資源投入到農業生產當中,而不像q2層酋邦那樣把過多資源用于信仰事業,盡管它是酋邦社會的組織基礎。q3層農業社會實行土地私有后,因為與q2層酋邦的集體或神廟所有制存在本質區別,需要一種新的權力保護這種制度不受酋邦的損害,于是,世俗權力在q3層農業社會獲得了發展壯大的土壤。蘇美爾阿卡德時期,存在大量土地買賣文書,證明當時在王室、神廟土地之外,還存在著自由民私人所有的土地,從所有權關系上來說,都表明國王承認賣主的私人所有權[29]。與弗里德不同的是,筆者認為分層社會就已經出現了國家級別的政治機構,雖然它不太成熟,帶有嚴重的神權思想殘留,甚至都不算非常強大,但它卻是合乎邏輯的存在,用原生國家描述這種不成熟的國家形態是比較合適的,因此,我們把q3層以地緣方式組合,存在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和世俗權力的政治社會實體,稱為原生國家。
五、結語
農業是絕大多數早期文明最主要的經濟部門,本文通過研究農業社會的發展規律,來思考國家起源問題。隨著農業定居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從農業發源地逐漸向臨近區域擴散,土地的肥沃程度不斷下降,而耕種的難度卻在不斷上升,即耕地的綜合質量逐層降低,后發農業社會需要不斷提高農業生產力和擴大耕地總面積,才能維持農業文明發展潛力不降低,否則很可能被先發農業社會消滅。由于耕地綜合質量的下降,每一層農業社會之間都存在生產力門檻,后者的起始生產力由前者提供,但此時后發農業社會的發展才剛剛起步,文明發展潛力遠沒有達到最大值,所以有意識地選擇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和擴大耕地總面積的新社會形態和政治體制,生產力的增長符合漸進累積的傳統社會演化論思想,而政治體制的演化更符合間斷平衡理論,即長期的穩定和短期的巨變交替出現。在核心—邊緣的地理環境下,隨著農業定居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從農業發源地逐漸向外圍傳播,耕地的綜合質量q逐層遞減,即耕地綜合質量q1層>q2層>q3層,而農業定居社會的政治社會形態卻依次從內向外螺旋上升分布,農業定居部落、酋邦、原生國家分別形成于q1層、q2層、q3層,“意識形態的物質化”成為被酋邦社會選擇的變異,而土地私有成為被原生國家社會選擇的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