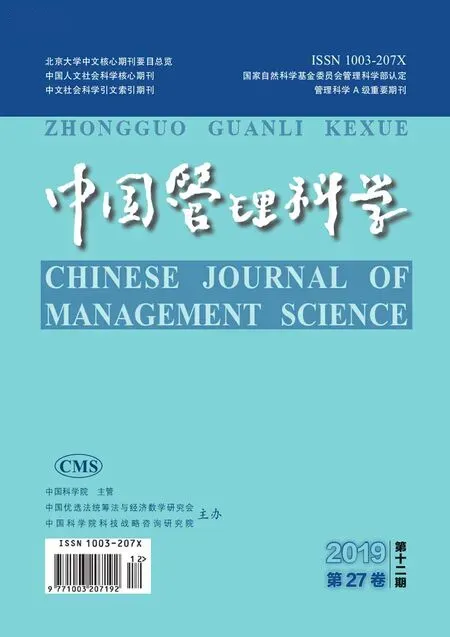經濟利益驅動下食品企業安全風險演化動態研究
王冀寧,張宇昊,王雨桐,陳庭強
(1.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6;2.南京工業大學大數據決策與社會績效評估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1816)
1 引言
近年來,隨著“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和“公安部食品藥品犯罪偵查局”等部門的相繼設立,以及“四個最嚴”指示和“嚴防嚴管嚴控食品安全風險”指示的陸續提出,我國的食品安全形式持續好轉,高發的食品安全事件態勢得以有效遏制。《中國食品安全發展報告(2018)》顯示:2017年我國食品質量安全監督抽檢總體合格率為97.6%,比2016年同期增長了0.8個百分點。截至2019年5月,全國上半年共偵破食品安全犯罪案件4500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500余名,有力震懾了犯罪活動,鞏固了食品安全持續穩定向好的態勢。2019年315晚會上所曝光的湖北蓮田農家鮮土雞蛋事件,再一次將食品安全中的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與政府的管理缺位推上了風口浪尖。
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EMA)指的是食品生產企業為獲取經濟利益,以欺騙性的手段故意在食品中加入替代成分或增加某種物質,從而達到降低成本或增加售價的目的[1-2]。2005年所爆發的蘇丹紅事件、2008年所爆發的三聚氰胺事件以及2013年所爆發的歐洲馬肉事件,都可以被歸類于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而引發的食品安全事件。相比于其他的食品安全事件,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而引發的食品安全事件在蓄意性[3-4]、隱蔽性[5]和技術性[6]等方面顯得尤其突出。當前,針對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學者們主要圍繞事件特征、檢測手段和政府規制三個角度進行研究。首先,在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的事件特征方面,Zhang Wenjing和Xue Jianhong[7]結合1553篇媒體報道,對發生在我國境內的由經濟利益驅動的食品摻假事件進行特征分析,并就事件的區域分布、摻假類型、食品種類進行了詳細描述。Everstine等[8]收集了自1980年起的關于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的代表性事件,并就這類事件的共同特征與現有食品檢測技術相比較,呼吁采用新的手段和方法確保食品品質安全。除了就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事件的特征進行直接探討以外,Marvin等[9]還借助貝葉斯網絡,對從RASFF(歐盟)和EMA(美國)數據庫中檢索到的食品欺詐案件進行數據記錄,據以識別和預測已知和新興的食品安全風險。而Bouzembrak等[10]則基于文本挖掘的方法,借助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的事件特征建立起一種專門用于食品欺詐的過濾器,對來自媒體報告中的公共衛生危險進行快速識別。其次,在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的檢測手段方面,隨著檢測技術的不斷發展完善,現有的食品摻假檢測技術已經實現了從原料到加工再到成品的全過程覆蓋,能夠有效地對檢測產品進行真偽鑒別和摻假物檢測等一系列操作。當前,常用的食品摻假檢測方法有色譜法[11-12]、光譜法[13-15]、指紋圖譜法[16-17]以及同位素檢測法[18-19]。如為了避免三聚氰胺事件的再次上演,Bergana等[15]借助1HNMR光譜法實現了對三聚氰胺、雙氰胺、蔗糖、大豆蛋白等八種可能的奶粉摻假劑的有效鑒別。而為有效檢測市場中的摻假芝麻油以及香精芝麻油,Zhang等[16]研發了一種快速簡單的IMS指紋圖,借助遞歸支持向量機建立的判別模型以及隨機森林分類模型實現了對芝麻油的快速現場檢測。第三,2017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首次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研討會后,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成為一項全球性的議題,學者們開始將目光聚焦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行為,從政策制定[20-24]、風險應對[25-31]以及經濟后果[32-34]等角度探討政府的規制策略。如Spink等[25]為解決摻假事件中的復雜性問題,提出應以跨學科、重預防、抓風險的方式綜合治理。考慮到近年來我國農村食品涌現的“劣幣驅逐良幣”特點,李慶江等[26]在提煉農村食品安全治理重點的同時,提出了從源頭監管到宣傳科普的五大建議舉措。
然而,現有針對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的研究,多數忽略了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的技術性特征,沒有考慮到食品企業摻假行為背后生產技術、產量水平以及企業得益的交錯關系。同時,不少學者在運用演化博弈對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的分析過程中,過度聚焦于結果中的穩定演化狀態,忽略了對持續振蕩的中性穩定狀態的考察與解釋。另外,多數研究假設區域內政府和企業的距離無限接近,忽略了地理位置對監管成效的影響。因此,本文綜合了借鑒Salom?o和Rocha[35]的研究框架,在經典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的基礎上,創新性地吸納元胞自動機理論,對食品企業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演化過程進行了空間上的拓展。同時,引入了食品企業策略轉變意愿和政府策略轉換意愿,探析食品企業和政府的策略轉變意愿對最終演化結果的影響。本文在提升模型的真實性、普適性的同時,也為振蕩狀態下的政府監管方式進行了有益探索,對提升我國食品安全監管效率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
2 食品摻假行為演化博弈模型構建
本文主要通過博弈模型探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食品企業的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意愿與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監管力度的相互作用及其影響因素。模型中的兩個博弈方分別為食品企業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兩者均為有限理性,其行為隨預期收益的變化而進行相應調整。
2.1 模型基本假設
(1)面對激烈的市場環境,食品企業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存在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以謀求非法利益的可能。因此,食品企業的策略空間為(合規生產,違法摻假),簡記為(L,IL)。相對應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負責地方食品安全的日常巡查工作。在實際工作中,受職業道德及監管成本的影響,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存在玩忽職守,消極監管的可能性。因此,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策略空間為(嚴格監管,消極監管),簡記為(D,FD)。

(3)食品企業F的收益πF由食品企業經營收入、企業殘次品損失以及企業技術成本共同組成,表示為πF(b,s,α,k,d)=bs-αskd-s2k-d。其中,bs表示食品企業經營收入,它是食品企業生產規模s(s>1)與食品企業盈利水平b(b>1)的線性函數;α代表食品企業策略類型,當食品企業選擇違法摻假時,α=0,此時食品企業選擇以次充好,將殘次品同正常產品一道賣入市場。而當食品企業選擇合規生產時,α=1,此時食品企業出于職業道德的考量,選擇將生產中的殘次品予以銷毀。
(4)基層食品監管機構P負責地方食品安全的隱患排查、信息收集報送工作,其收益πP表示為πP(b,s,α,k,d,β,c)=πF-βc。其中,πF代表食品企業收益,βc代表受監管機構策略類型影響的監管成本。當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嚴格監管時,β=1。而當基層食品監管機構消極監管時,β=0。
(5)對于違法摻假的食品企業,其摻假行為會產生相應的社會負面效益s2kd。當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選擇嚴格監管時,這種社會負面效益會轉化為對食品企業的罰款,從食品企業的經濟收益中扣除。此時食品企業的收益為πF=bs-s2k-d-s2kd,低于合規生產時的企業收益。而當基層監管機構選擇消極監管時,食品企業的摻假行為就不會被發現。此時食品企業的收益就高于合規生產時的企業收益,同時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還需承擔所有的社會負面效益。另外,對于合規生產的食品企業,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嚴格監管與否并不影響食品企業的收益水平。
(6)考慮到有限理性的存在以及食品企業內部各部門協同作用的缺乏,假設食品企業所采用的技術風險水平k與其生產規模s相互獨立。即對于食品企業而言,其長期的技術風險水平k由食品企業的規劃部門率先確定,確定時不考慮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而其各期的產量水平s則在食品企業技術風險水平確定后,由業務部門在各時期分別控制,此時政府的監管水平予以考慮。
2.2 演化模型構建
根據2.1節的假設,對于合規生產的食品企業,其企業收益為:
πF(b,s,α,k,d)=bs-s2k-d-skd
(1)
式(1)對技術風險水平k的偏導函數為:
(2)

(3)
同理,對于違法摻假的食品企業,其企業收益為:
πF(b,s,k,d)=bs-s2k-d
(4)
式(4)對技術風險水平k的偏導函數為:
(5)

(6)

πF=bs-2s3/2
(7)
式(7)對產量水平s求偏導及二階偏導分析,可得選擇合規生產行為的食品企業最佳產量為:
(8)
由式(7)和式(8)可知,選擇合規生產行為的食品企業收益為b3/27。相對應地,選擇嚴格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收益為b3/27-c,而選擇消極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收益為b3/27。
同理,當違法摻假的食品企業未接受嚴格監管時,其企業收益及其最佳產量為:
(9)
(10)

而當選擇違法摻假行為的食品企業面臨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嚴格監管時,其企業收益及其最佳產量為:
(11)
(12)

結合上述分析,食品企業與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博弈支付矩陣如下表所示:

表1 食品企業與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支付矩陣
2.3 模型演化分析
針對表1構建的支付矩陣,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選擇嚴格監管的動機需滿足如下條件:
(13)

(14)
基層食品監管機構P選擇消極監管FD的期望收益為:
(15)
同理,可以得到食品企業F選擇合規生產L和違法摻假IL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16)
(17)
根據Malthusian方程,結合條件(14)、(15)、(16)、(17),可得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以及食品企業群體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18)
(19)
根據條件(18)和條件(19),可以得到食品企業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所組成的二維動力系統,即:
(20)
(21)
(22)
由于上述局部均衡點不一定是食品企業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所組成的二維動力系統的演化穩定策略(ESS),根據Friedman提出的方法,該二維動力系統對應的雅可比矩陣如下:
(23)
其中:
復制動態方程的局部均衡點是演化穩定策略的充分條件為:
trJ=a11+a22<0
(24)
(25)
容易得到,各局部均衡點處Jacobian矩陣的元素值如下表所示:

表2 局部均衡點處a11、a12、a21、a22具體取值
其中,A和B的具體表達式分別為:
(26)
(27)
命題1:在條件(24)和(25)的約束下,食品企業群體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所組成的二維動力系統沒有穩定演化策略,但存在一個中性穩定狀態。
證明:若食品企業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所組成的二維動力系統的演化穩定均衡點是E1(0,0),E2(0,1),E3(1,0),E4(1,1)中的一種,則該演化穩定均衡點需同時滿足條件(24)和(25)。然而,由于在這四個局部均衡點處a12=a21=0,且a11a22<0。因此,E1(0,0),E2(0,1),E3(1,0),E4(1,1)都不是該系統的演化穩定均衡點。而在局部均衡點E5(x1,y1)處,a11+a22=0。因此局部均衡點E5(x1,y1)也不是復制動態方程的演化穩定均衡點。根據中性穩定定義可知,在食品企業群體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所組成的二維動力系統中,兩博弈方的群體策略選擇(x1,y1)屬于中性穩定狀態,如圖1所示:

圖1 食品企業群體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的策略演化路徑圖
由圖1中可以看出,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和食品企業群體一直處于周期振蕩狀態,不存在一個穩定的演化策略。對于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而言,由于受監管成本的控制,其共同構建的監管高壓并不能在長時間內延續。而對于食品企業而言,政府罰金總能在一定程度上督促企業向合規生產轉變。每當與之對立的博弈方策略改變時,另一方總能通過改變策略來使得自身收益最大化。這樣的中性穩定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食品摻假問題的監管困境,比如每當食品消費的旺季來臨或大型食品安全事件爆發時,政府監管部門往往會采取重點專項行動,對轄區內的食品企業進行重點排查,此時轄區內的監管高壓促使摻假企業向合規生產轉變。而當專項行動結束后,違規行為往往死灰復燃,重新采取違規摻假行為謀求非法收益。
3 食品摻假行為的空間博弈模型
為了更好地研究現實中兩類博弈方的真實情況,破解命題1中所呈現的監管困局。本節基于元胞自動機理論,從空間地理位置、信息傳遞方式以及博弈方主觀意愿等角度對先前模型進行優化,運用空間博弈模型對各博弈方的策略演化狀態進行深入分析。
3.1 元胞自動機理論
元胞自動機是一種由馮·諾伊曼提出的,在時間、空間和狀態上都離散,空間相互作用和時間因果關系皆局部的網格動力學模型[39-41]。其基本組成部分包括元胞(d)、元胞空間(L2)、鄰居(N)、元胞狀態集(S)和演化規則(R)五個部分,表示為A=(d,L2,N,S,R)。沿用2.1中模型的基本假設以及2.2中構建的博弈矩陣,本部分元胞自動機的具體設定如下:
(1)在元胞與元胞狀態集的設定方面,本文令d={F,P},即在元胞空間的每個網格上,都包含著一個食品企業和一個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兩個元胞。對于類型為食品企業的元胞而言,其狀態集為SF={L,IL},而對于類型為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元胞而言,其狀態集為SP={D,FD}。
(2)在元胞的空間與鄰居設定方面,本文使用二維元胞空間進行模擬,并假定元胞空間為具有周期性邊界條件的邊長L=50的正方形網格。同時,假定元胞鄰居形式為VonNeumann型鄰居。
(3)在元胞的演化規則方面,本文設定元胞在t+1時刻的狀態受t時刻其自身的元胞狀態和鄰居的元胞狀態影響,表示為:
(28)

1)在t=0時,假設食品企業元胞群體中狀態為L的元胞比例為0.3,狀態為IL的元胞比例為0.7,兩種狀態的元胞隨機分布于網格中的各個位置。在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元胞群體中,狀態為D的元胞比例為0.2,狀態為FD的元胞比例為0.8。令所有狀態為D的元胞呈條帶狀集聚在網格下部,狀態為FD的元胞集聚在網格上部。


3.2 食品企業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空間博弈分析

3.2.1食品企業策略轉變意愿λF對博弈演化結果的影響
令λF={0.01;0.3;0.5;0.7;1;5;50;80},針對每類食品企業策略轉變意愿,本文進行50次模擬,除λF=0.01情況下的迭代步數T=14000外,每次模擬的迭代步數T=2000。與2.3中所展現的中性穩定狀態不同,在其他條件不變,λF∈[0.01,0.7]或更低時,隨著迭代次數的增加,消極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以及違法摻假的食品企業群體逐漸減少,并直至滅絕。該范圍內兩類博弈方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如圖2所示:
由圖2可知,當λF處在一個較低水平時,隨著迭代步數的增加,盡管達到穩定的速度有所區別,但所有的食品企業都轉為了合規生產,所有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都選擇認真監管。當λF較低時,食品企業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相鄰食品企業進行收益對比,因此實現內部策略統一的時間較長。而隨著λF的逐漸升高,食品企業的反應速度加快,其策略統一的時間也隨之縮小。

圖2 較低水平下不同λF中兩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
為了進一步分析λF在較低水平時兩博弈方策略演化的運作機理,以λF=0.3為例,對其演化過程進行細致剖析。在λF=0.3水平下,兩博弈方群體策略的變化過程如圖3所示:如圖3所示,在T=0時,所有的食品企業按照初始的群體比例隨機散布在網格的各個位置,而所有嚴格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則集中于網格下方的條帶內。在迭代開始時,受基層食品監管機構位置的影響,食品企業的分布逐漸呈現出合規企業聚集在下方,違規摻假企業聚集在上方的現象。此時,對于條帶內部選擇合規生產的食品企業而言,盡管外部采用違法摻假策略的企業收益更高,但在較低的λF以及嚴格監管環境的影響下,選擇合規生產的食品企業難以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向違規摻假類型的策略轉變。因而條帶內部食品企業的策略漸趨穩定,逐漸穩定于合規生產的策略選擇。對于條帶邊緣,選擇消極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而言,由于同一位置上的食品企業策略為違法摻假,因此其收益低于相鄰的采用嚴格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存在改變自身策略的動機。故而隨著迭代次數的不斷增加,選擇嚴格監管策略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元胞由空間兩端向中間聚攏,逐步實現空間內部的策略統一。而違法摻假企業也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策略選擇,以合規生產的方式保證自身利益,并最終全部穩定于合規生產的策略選擇上。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圖3 λF=0.3水平下兩博弈方群體策略的變化過程(圖中第一列和第三列為食品企業元胞分布,第二列和第四列為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元胞分布)
命題2:當λF處在一個較低水平時,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演化均衡(嚴格監管,合規生產)。
在其他條件不變,λP∈[1,80]或更高時,隨著迭代次數的增加,不論是食品企業還是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都無法實現內部群體策略的統一。兩類博弈方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如圖4所示:

圖4 較高水平下不同λF中兩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
由圖4可知,在λF超出先前的較低水平時,隨著迭代步數的增加,兩博弈方的策略選擇都進入持續的振蕩狀態。在λF=5水平下,兩博弈方群體策略的變化過程如圖5所示:

圖5 λF=5水平下兩博弈方群體策略的變化過程(圖中第一列和第三列為食品企業元胞分布,第二列和第四列為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元胞分布)
如圖5所示,隨著迭代次數的逐漸增加,較高λF水平所帶來的食品企業行動特性逐漸顯現。然而,過快的行動特性給予了基層食品監管機構消極監管的機會。T=10中呈現的條帶內部的灰色區域,正是消極監管的策略在基層食品監管機構中不斷擴散的體現。而隨著迭代步數的進一步增加,食品生產企業逐漸發現了條帶內部監管力度不一的現象,于是越來越多的食品企業也開始轉變自身的策略,由合規生產轉為違法摻假。并最終造成兩博弈方內部各類群體數量的此消彼長,類似T=100時的混雜狀態。在群體比例上,這種此消彼長的混雜狀態就顯示為圖4中各群體策略比例圍繞某個區間的來回振蕩。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3:當λP超越上面的較低水平時,食品企業與政府監管機構,都進入了一個群體策略比例相對穩定的持續振蕩狀態。
3.2.2 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策略轉變意愿λP對博弈演化結果的影響
令λP={0.001;0.005;0.008;0.012;0.015;0.018;0.02;0.1;5},針對每類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策略轉變意愿,本文進行50次模擬,每次模擬的迭代步數為2000。在其他條件不變,λP∈[0.001,0.008]或更低時,隨著迭代次數的增加,所有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選擇了嚴格監管,同時所有的食品企業選擇了合規生產。兩類博弈方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較低水平時不同λP下兩博弈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
在圖6中,根據λP∈[0.001,0.01]的三種群體變化軌跡來看,λP的改變不僅影響了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策略改變速度,還間接對食品企業的策略改變速度產生了影響。圖7顯示了λP=0.008下兩種群體的變化狀態:

圖7 λP=0.008水平下兩博弈方群體策略的變化過程(圖中第一列和第三列為食品企業元胞分布,第二列和第四列為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元胞分布)
從圖7中可以看出,當λP處在一個相對較低水平時,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策略改變速度相對緩慢,而食品企業此時顯得更為活躍。由于λP較低,采用嚴格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能夠擁有足夠漫長的時間糾正條帶內部違法摻假的食品企業,在保證內部食品企業策略統一的同時,穩步地向外部推進,逐漸轉化周圍消極監管策略的同類主體。每當一個網格內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將其策略由消極監管轉化為嚴格監管時,處于相同位置的食品企業就會緊隨其后,將其策略迅速轉為合規生產以保障收益。隨著演化時間的不斷推進,兩博弈方的策略最終穩定于(嚴格監管,合規生產)。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4:當λP處在一個相對較低水平時,隨著迭代次數的增加,所有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選擇了嚴格監管,同時所有的食品企業選擇了合規生產。
在其他條件不變,λP∈[0.02,5]或更高時,隨著λP的升高,不論是食品企業還是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都無法實現其群體內部的策略統一。兩類博弈方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如圖8所示:
由圖8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在λP處在一個較高水平時,由于存在較高的策略轉換意愿,因此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對收益水平更加敏感,更愿意通過模仿的行為去實現更大的自我收益,故而兩博弈方的策略選擇都逐漸偏離原有的(嚴格監管,合規生產)的穩定狀態,進入無休止的持續振蕩。
圖9顯示了λP=5下不同時刻兩種群體的變化狀態,其變化過程與λF在較高水平時兩種群的變化過程相類似。都是由于在較高的策略轉換意愿下,采取嚴格監管策略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無法抵御周圍消極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所帶來的利益誘惑,致使策略轉變行為由條帶邊緣向其內部蔓延,并后續引發了相同位置食品企業的策略轉變。最終導致兩個博弈方內部各類群體比例同步變動,呈現出持續振蕩的演化結果。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圖8 較高水平下不同λP中兩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

圖9 λP=5水平下兩博弈方群體策略的變化過程(圖中第一列和第三列為食品企業元胞分布,第二列和第四列為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元胞分布)
命題5:當λP處在一個較高水平時,食品企業與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都進入了一個策略比例相對穩定的持續振蕩狀態。
在其他條件不變,λP∈[0.012,0.018]時,該策略轉變意愿水平下兩類博弈方的演化狀態存在三種不同的情況。分別是1)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全部選擇嚴格監管,食品企業全部選擇合規生產;2)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全部選擇消極監管,食品企業全部選擇合規生產;3)基層食品監管機構中選擇嚴格監管的比例和食品企業中選擇合規生產的比例同步振蕩,后文分別用演化狀態1、2、3來進行描述。具體的三種演化過程如圖10所示:
盡管在λP處在中等水平時,上述的三種演化狀態都會有所顯現。但是隨著λP的變化,不同演化狀態出現的頻率不盡相同。表3是在50次模擬中,不同λP下各類演化狀態的統計情況。由表3可以看出,在λP=0.012時,演化狀態1出現的頻次更高。而隨著λP的不斷增加,演化狀態3出現的頻次不斷增加。
而之所以會出現演化狀態2的情況,本文認為,演化狀態2不僅受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策略轉變意愿λP控制,還與最初的食品企業種群分布情況有關,更與演化過程中的隨機性密切相關。圖11記錄了λP=0.012條件下,出現演化狀態2的兩博弈方群體變化過程。
由圖11可以清晰的看出,在迭代過程中,嚴格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內部涌現出了一部分呈現消極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由于這些消極監管策略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處于條帶底部,既不會影響食品企業群體策略的轉換進程,也不會影響中間地帶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向嚴格監管策略的轉化。因此隨著迭代過程的不斷增加,消極監管的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的數量不斷擴大,逐漸由空間底部向外圍拓展,最終在不改變食品企業狀態的同時,實現了對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內部的策略統一。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命題:
命題6:當λP處在中等水平時,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和食品企業群體內部的策略變化情況處于命題4和命題5之間。此時,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群體和食品企業群體既存在全部選擇嚴格監管和合規生產的演化情況,也存在所有食品企業群體選擇合規生產、所有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選擇消極監管的演化結果,還存在兩博弈群體比例同步性振蕩的狀態。
4 結語
隨著食品產業的不斷升級和社會需求的不斷提升,食品安全的監管也隨之產生了全新的問題。針對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的長效治理,本文構建了食品生產企業和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的演化博弈模型,解析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監管困局。在此基礎上,本文創新性地借助元胞自動機理論,將上述的基準模型擴展到帶有空間位置的網格中,并引入食品企業策略轉變意愿與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策略轉變意愿,從空間的角度探索食品企業經濟利益摻假與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監管的相互作用機制,破解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監管困局。研究結果表明:

圖10 中等水平下不同λP中兩群體比例隨時間變化的結果

表3 不同λP水平下三種演化狀態出現頻次統計表
(1)通過將企業策略轉變意愿與基層食品監管機構策略轉變意愿維持在較低水平,可以實現結果為(嚴格監管,合規生產)的演化均衡。對于食品企業而言,較低的企業策略轉換水平表明企業更重視長期利益。在長期利益的引導下,食品企業的摻假動機能夠得到有效抑制。對于基層食品監管機構而言,較低的政府策略轉變意愿代表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具有擁有長期的政策規劃和執行能力。當基層食品監管機構不執著于短期的政績,穩步推進區域內的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時,轄區內的違法摻假的不正之風就會得到糾正,逐漸形成合規生產的企業風氣。
(2)在實現穩定演化均衡的過程中,相比于基層食品監管機構,食品企業的策略轉變意愿空間更加寬泛,更容易實現兩博弈方在空間上的策略穩定。由命題2和命題4可知,盡管將兩博弈方的策略轉變意愿維持在較低水平均可實現結果為(嚴格監管,合規生產)的演化均衡,但兩者實現穩定的策略轉變意愿空間不盡相同,顯然食品企業的意愿轉變空間更為充裕。因此,相較于提升基層食品監管機構在長期政策方面的執行能力,借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食品安全,能夠切實有效的將食品企業的摻假意愿降至最低,從而實現區域內食品安全的長治久安。
本文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僅從政府規制的角度探索解決食品企業經濟利益摻假的解決思路,后續研究可以不斷引入新聞媒體、消費者協會等第三方監督機構,實現對食品企業經濟利益驅動型摻假監管的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