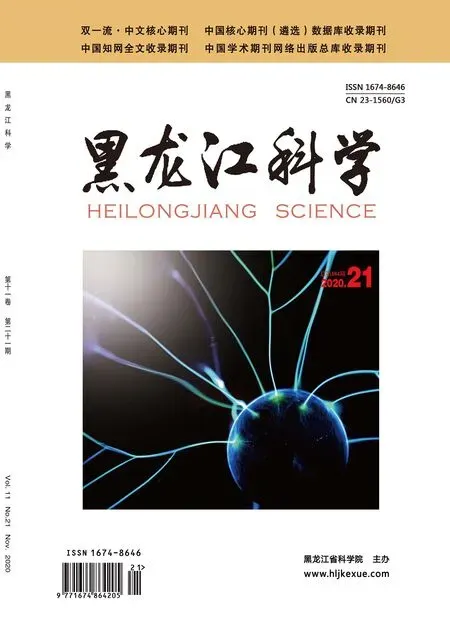我國隨遷子女教育政策發展狀況分析
——基于吉爾伯特和特雷爾的社會福利政策分析框架
謝春艷,王立紅
(長春理工大學,長春 130022)
1 文獻綜述
1.1 研究背景
21世紀以來,二代農民工的遷移模式區別于一代農民工,開始由個體遷移向家庭遷移轉變[1],更多的農民工選擇舉家遷移到流入地,于是隨遷子女的數量也在逐年攀升。2015年,相關調查顯示,全國外出農民工共計1.69億人,同期,義務教育階段的隨遷子女數量1 367萬人。2017年,相關調查顯示,全國外出農民工達1.72億人,較2015年增長了兩百多萬人,近半數以上的農民工向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如浙江、上海、廣東、北京等地[2]。廣東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學生的數量占廣東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總量的1/3。
農民工數量的增多助推了城市化進程,同時也對城市的公共服務提出了挑戰。農民工舉家遷移的新模式意味著政府不單需要考慮到農民工自身的福利和需求,還需要考慮到隨遷子女的福利和需求。近年來,政府針對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力求能夠滿足隨遷子女的教育需求。
1.2 概念界定
1.2.1 隨遷子女
隨遷子女是指戶籍登記在外省(市、區/縣)、本省外縣(區)的鄉村且隨務工父母到輸入地的城區、鎮區(同住)并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少年[3]。在這一定義中可以看出,隨遷子女是農村戶口。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有較大區別,隨遷子女可能會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但我國戶籍管理制度較為嚴格,隨遷子女在流入地獲得教育的機會也會更加困難。
1.2.2 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界關于教育政策的概念主要有三類,一是關注意義,突出政策在教育方面對社會問題和社會關系的調整[4]。二是關注制定者和對象。政策制定者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對象主要是針對學校行為[5]。三是關注組成內容,闡明教育政策是以教育為中心的權利和利益的呈現[6]。目前,有關隨遷子女的教育政策主要集中在義務教育和異地升學上。
2 吉爾伯特和特雷爾的社會福利政策分析框架
社會福利政策分析框架是吉爾伯特和特雷爾在對社會福利政策各個要素進行整合后提出的一個四個部分和三個維度的政策分析框架[7]。四個部分包括分配基礎、分配內容、提供策略和資金籌措。分配基礎就是向誰提供,是遵循普遍性原則還是選擇性原則。分配內容即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服務形式是實物還是現金,其中還包括機會、服務、物品、代金券等形式。提供策略即如何提供福利,它是一種輸送系統。資金籌措則是指資金來源于哪兒,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民間都有可能。每個部分下面都會包括三個維度:①有怎樣的方案可以選擇。②有哪些價值觀支持這些方案。③有哪些理論和假設支持這些方案[8]。
3 隨遷子女教育政策的發展概況
3.1 分配基礎演變:逐步推開普遍性義務教育
1986年,我國規定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并逐步推行開來。頒布義務教育制度時,我國的農民工數量還不多,那時的遷移模式以個體遷移為主,當時并沒有考慮到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一代農民工時期由于嚴格的戶籍管理及繁瑣的異地就學程序,絕大部分農民工并沒有攜子女一同外出務工。攜同子女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安排子女就學也十分困難,尤其是升學階段,如六年級、九年級。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多是借讀,或者就讀在工農子弟學校,存在學費比較高昂,師資力量參差不齊,轉回流出地時容易留級,輟學率較高等問題。
21世紀初,一代農民工和二代農民工更替存在,舉家遷移成為一種新趨勢。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的“兩為主”政策,隨遷子女普遍性的義務教育自此推廣開來。自2001年《決定》頒布之后,中央和地方也陸續出臺了更多政策來推廣隨遷子女的普遍性義務教育。這個《決定》的推行進一步推動了九年義務教育的普惠性發展,確保隨遷子女落實普惠性九年義務教育。2016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九年義務教育的鞏固率達到95%。《意見》的出臺使隨遷子女的異地就學和異地升學更加方便容易。
隨遷子女教育政策是普遍性分配,這一分配基礎堅持以公平為價值導向,強調政府在社會福利事業中起主導作用,要求限制市場機制的調節范圍[9],讓人們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果實。隨遷子女教育普遍性分配遵循了發展性社會福利理論。發展性社會福利認為社會福利可以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教育是一種有回報和可持續的人力資本投資。
3.2 分配內容演變:不斷深化實物分配,持續擴大現金分配和代金券分配
21世紀以來,針對隨遷子女就學難的問題,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其中“兩為主”政策的頒布推進了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發展,保障了隨遷子女教育公平的機會,確定了我國隨遷子女就學以“兩為主”政策為基礎。2016年,《意見》要求隨遷子女入學的主要依據為居住證,簡化優化他們的入學流程,讓他們少跑路,少辦證。這些確保隨遷子女有學可上的政策是最基礎的隨遷子女教育政策。此外,《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通知也使得流入地隨遷子女參加高考更為方便,使異地高考政策得到了進一步落實。這些政策以實物形式來分配教育福利,有利于實現教育公平。
為進一步提高隨遷子女入學率,讓隨遷子女都能上得起學,做到不輟學,2008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意見的通知》出臺,要求流入地政府通過“兩免一補”的形式來幫助家庭經濟困難的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就學。2008,《國務院關于做好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工作的通知》頒布,將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納入公共教育體系,對入讀公辦學校的隨遷子女免除學雜費,不收借讀費。2016年,《意見》要求利用全國中小學生經濟信息管理系統的數據來切實推進“兩免一補”資金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能夠隨學生的流動而轉到流入地政府。政府正不斷擴大現金分配和代金券分配,確保隨遷子女都能上得起學。現金分配和代金券分配基本能夠滿足隨遷子女更多元化的教育需求。
通過對以上政策的歸納可以看出,自21世紀以來,政府通過程序減免、降低準入門檻、促進和保證就讀、平等對待等方式來實現教育福利的實物分配,并通過“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定額攜帶的方式來提供現金分配,在分配內容上不斷深化實物分配,同時擴大現金和代金券分配,此舉依舊遵循公平原則,實物形式的分配能確保隨遷子女有學可上。“兩免一補”中“一補”的現金分配遵循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將社會資源傾向于弱勢一方。
3.3 提供策略演變:強化中央統籌
1986年,我國開始實行義務教育,當時的義務教育制度是區縣級及以下的責任。2008年,“兩免一補”政策被提出和推行,中央對于隨遷子女教育政策的統籌開始逐步顯現和落到實處。“兩免一補”政策中,中央通過財政支持的方式對隨遷子女教育政策進行統籌規劃。2016年,以全國中小學信息管理系統為平臺,創造性提出“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資金隨學生而流動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流入地的教育經濟壓力,中央通過統籌兩地促進了隨遷子女教育的發展。另外,2012年發布的關于隨遷子女異地升學的政策也在考驗著中央的統籌能力。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中央統籌隨遷子女教育政策的提供起于2008年,興于2012年的異地升學政策,深化于2016年的教育資金隨學生而流動。
3.4 資金籌措演變:持續擴大中央撥款力度
我國教育資源主要的資金來源是以國家財政和地方各級政府財政為主。2003年,《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規定了流入地地方政府對隨遷子女的財政責任。2008年3月,流入地政府財政部門要對接收進城務工就業的農民子女給予較多的補助,城市教育費附加中也要安排一部分經費,用于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的義務教育工作。2008年8月,中央財政將對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解決較好的省份給予適當獎勵。最開始,中央下達了多份文件來保證隨遷子女的教育需求,特別指出了地方政府對流入隨遷子女的財政責任。用于隨遷子女教育的支出基本全是地方財政支出。2008年,中央以獎勵的形式開始對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進行撥款。
2015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中提到了“兩免一補”政策,中央負責國家規定課程的教科書資金,并承擔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生一半的生活費用,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資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擔。2016年,《意見》提出“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可隨學生的流動而攜帶,更進一步緩解了流入地的教育財政壓力。“兩免一補”政策提出后,隨遷子女教育政策的資金投入迎來了中央撥款,而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的規定更是將中央撥款的數額提到了一個新高度。
4 結論與討論
隨著分配內容的多元化及中央和地方財政支持力度的不斷加大,在中央統籌和兩地配合的操作下,隨遷子女普惠性的教育政策不斷發展,為隨遷子女的教育公平創造了更多有利條件。
隨遷子女教育政策的出臺最主要的目的是維護我國的教育公平,在目前一路向好的態勢下,依舊有幾個問題需要考慮:其一,農民工的遷移方向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有超過半數的農民工流動到了北上廣深四地,還有絕大部分流動到了其他沿海城市,接受大量農民工流入也就意味著要接受更多的隨遷子女。這些流入地對于隨遷子女的教育投入會非常大,流入地在面對財政的巨大挑戰時,也能獲得中央的財政支持,這對于流入地的教育發展也是一個機會。其二,流入地更多的教育投入有可能導致流出地生源減少,教育投入相對也會減少,會限制流出地的教育發展。其三,隨遷子女教育政策一直在不斷發展,但依舊停留在宏觀層面。2016年,《意見》要求實現混合編班和統一管理,以促進隨遷子女融入學校和社區。這種混合編班是否真的有利于促進隨遷子女的社會融合還有待繼續考察,這也可以成為社會整合的研究內容。其四,隨遷子女教育政策發展有可能導致教育不公平的現象發生,一方面是隨遷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更好的教育,然后在流出地參加高考,享受一些農村的扶持政策;另一方面是異地高考放開帶來的高考移民,即從教育A區流入到B區(云藏疆等地),享受更多的特殊地區優待。
隨遷子女的教育政策發展正向著教育公平的方向出發,但目前政策上還有一些地方需要完善,這不是僅通過隨遷子女教育政策就能解決的,還需要全面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同時也需要東西部經濟均衡發展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