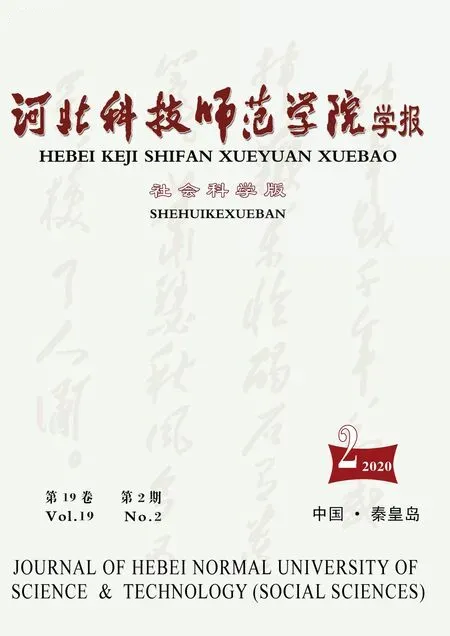《傷逝》作為悲劇藝術的張力書寫
李夢瑩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傷逝》是魯迅唯一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自問世以來一直受到學界的關注。在《傷逝》的解讀中,研究者多從愛情悲劇的角度入手,探究其愛情失敗的原因;或者從文章的敘事角度進行分析,探討涓生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而引發的關于兩性關系的思考;亦或聯系作者的生平,將其視作兄弟之情或與其伴侶關系的隱喻描寫,以上的論文觀點卻忽略了文章作為悲劇藝術本身所具有的美學意義。 “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在黑格爾看來,矛盾不僅使事物充滿生機,而且還是其前進發展的動力,在悲劇中,正是由于不同倫理力量之間的較量和沖突,其情節才得以展開。而悲劇人物之所以具有悲劇性,不在于他被惡統治著,而在于他們各自堅持自己所代表的具有片面性的倫理力量時,一方為了實現自己所代表的倫理力量而要毀滅另外一方。《傷逝》中借涓生愛情的幻滅過程來書寫特定時代下知識分子建構理想世界所面臨的來自外部以及內部倫理力量的矛盾沖突,在表現新一代知識分子為實現自己的欲求遭致來自社會、文化傳統以及主體精神世界的壓抑而惆悵痛苦時,又彰顯了人的生命意志在進退維谷的矛盾沖突中所迸發的生命欲求和進取精神。正因為如此,《傷逝》作為悲劇藝術在內涵與外延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
一、永不破滅的希望:在現實中的求存
在《傷逝》中,造成新一代知識分子精神困境的首先來自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矛盾。魯迅在《傷逝》中以涓生愛情的發展軌跡來訴說時代困境下知識分子的掙扎和彷徨,在理想與現實不斷交疊下,他們成了兩難處境中的悲劇式人物,一方面是新思想滋養下不斷涌現的美好理想,一方面是來自現實的嚴酷打擊。
從涓生的精神世界來看,他反對家庭專制、倡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是當時時代影響下先進思想的代表,然而他的悲劇性也源于此。具體來說,要實現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的悲劇沖突之間構成了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生活其中的“涓生”們作為時代的先鋒者,一方面受到來自現實環境的重重阻礙,薩特的存在主義觀點就將“他人”與環境當成各種各樣的“異化”,其是對個人的壓抑性力量,一種令人討厭的“粘液”,并處處限制人的自由的“他者”……想要擺脫它、卻又無法脫身[1]。涓生與他所生活的現實環境便處于這樣一種境況,即他與現實已融為一體,但目標的理想性卻又要求他擺脫現實環境,而現實又時時纏繞著自己,阻饒著自己,最終成為實現理想的一種壓抑性力量;另一方面,以涓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企圖改變現狀的理想本身就帶有悲劇性。“在黑格爾看來,真正悲劇的災難,卻完全作為本人行動的后果,落在積極參與者的頭上,他們本身既是悲哀的制造者。”[2]112黑格爾將社會性的普遍意義寓于個體體驗當中,以具體的人的體驗來揭示抽象的悲劇命題,而涓生的藝術形象則是當時普遍狀態下知識分子悲劇的縮影,從“涓生”作為個體的生存悲劇中窺探人類悲劇性的根源。他們是時代的先覺者,雖看到了未來新希望的曙光,但通過一番掙扎后,卻發現無力改變現狀的殘酷事實,由此造成了知識分子苦悶的精神困境。
在涓生的會館處所里掛著雪萊最美的一張半身像,代表浪漫主義思想的雪萊形象是涓生對新生活充滿無限希望的化身,而渴望實現自由浪漫的愛情成為新一代知識分子理想世界中一個象征性存在。涓生的手記中,我們看到的是知識青年涓生在失去愛情后的內心獨白,他在手記的開頭講到:“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3]109涓生在追求愛情失敗后只剩下寂靜和空虛,而為愛情出走的子君則走進了“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這是雙方在憧憬美好愛情時所不曾料到的,然而卻不能由于當事人的主觀意愿而避免這種悲劇性的結局。在恩格斯看來,任何悲劇都是社會的、歷史的,只有從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和社會生活出發,才能予以說明。
涓生的愛情理想遭到失敗,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和個體主體兩部分,即外部沖突和內部沖突兩方面造成的。一方面,新思想的傳入并未給國人帶來思想上的大變革,而接受者多為在新環境成長下的知識分子、留學生,而文中出現的“雪花膏”、子君的叔父等都是舊思想的代表,這也說明構成實現理想的現實阻力之大;另一方面,悲劇人物在實現理想過程中所暴露的個人局限性形成了人物悲劇命運的內因,涓生雖受新思想的洗禮,然而對于愛情卻難以有清醒的認識,從而暴露出其思想上的片面性。在浪漫主義知識分子那里,“他們往往只是按照他們對愛情和生活的單方面期待及幻想來面對他人,要求他人,成為自我欲望的滿足,從而失去了與他人之間的相互性關系”[4],思想上的片面性使得涓生的愛情理想在與現實發生沖突時,形成兩人悲劇性的結局。“而較之單純地由他人所給予的災難,由于自身原因而引起的重大的不幸才是更深刻的悲劇”[2]114,涓生在手記的末尾寫道:“卻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涓生雖然逃離了“吉兆胡同”,卻陷入了更大的悲哀當中。在叔本華看來,任何人都無法逃脫由自身編織的羅網,而破壞幸福和生命的力量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每個人隨時都可能同時充當悲劇的制造者和悲劇的承擔者,涓生的逃離以及逃離之后的空虛便帶有這種叔本華式的悲劇色彩。
《傷逝》作為悲劇藝術作品,一方面,作者借涓生與子君的愛情幻滅揭示了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下,由于現實與理想間難以調和的矛盾所造成的人物悲劇;另一方面,作者通過矛盾沖突為文本意義的解讀創造了更大的闡釋空間。在艾倫·退特《論詩的張力》中指出:“我所說的詩的意義就是指它的張力,即我們在詩中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展和內包的有機整體”[5],而《傷逝》則透過兩人的愛情揭示出在故事深層一場理想與現實矛盾的雙重交疊。在嚴酷的現實中,涓生帶著知識分子對未來的希望,帶著子君,逃離會館,逃離寂寞和空虛;在與子君組建新的家庭時后,當知識分子涓生為奔向新生活而扇動翅子時,每一次都以失敗告終,但是作為悲劇的主人公,卻依舊向往著新的希望,涓生在手記中寫道:“我活著,我總得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3]130在現實與理想這對矛盾因素中,“我”沒有就此向殘酷的現實低頭,而是在經過現實的洗禮后,重新整裝出發,繼續前行。
二、 兩種聲音的對抗:傳統與現代
在易卜生的《娜拉》被翻譯到中國之后,魯迅等人關于“娜拉出走之后”進行了大范圍的討論,魯迅認為接受了新思想而出走的女性“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來自外部世界的壓力以及自身思想的局限性成為新一代女性難以擺脫悲劇命運的重要因素。可以說,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境況是帶有悲劇色彩的。五四運動后新思想隨之在中國掀起熱潮,中國傳統文化面臨著挑戰,幾千年來處于正統地位的儒家文化成為新一代知識分子批評的對象,而這時魯迅卻在新思想熱潮中進行了“冷”思考:即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遺留物是否要一味舍棄,對待新思想是否要全盤接受,在《傷逝》這篇愛情題材的小說中,子君和涓生的愛情悲劇便是魯迅對于那個時代思考的縮影。
《傷逝》中子君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所誕生的悲劇人物。子君在遭到涓生的遺棄后走向了死亡,構成子君悲劇性的源于現代與傳統兩種力量在子君思想中的沖突所構成的張力。“在黑格爾看來,這種沖突中對立的雙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辯護的理由,而同時每一方拿來作為自己所堅持的那種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內容的卻只能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6]子君是深受傳統與現代兩種思想影響的人,一方面她生長在有著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思想的土地上,另一方面,她又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強烈要求擺脫現實生存環境,因此子君身上體現出傳統與現代兩種思想的對抗和沖突。
首先,子君作為不徹底的思想革命者和不徹底的傳統擁護者本身就是悲劇。在子君的性格形成中她始終被現代性和傳統性這兩種聲音所支配,在與涓生聊男女平等、家庭專制時,她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涓生作為浪漫主義知識分子自然是欣喜的,因為他看到了中國女性在接受新思想、反專制方面是極有希望的,解放封建下的中國是“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這正與他們在五四時期進行思想啟蒙的愿望相契合。然而,同居后的涓生并沒有如他所愿逃離寂靜和空虛,而是陷入了更加異樣的寂寞和空虛。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回歸家庭的子君與涓生在生活中出現了分歧,涓生喜歡帶有浪漫氣息的花花草草,而子君更鐘意于有生活氣息的油雞和叭兒狗;子君為叭兒狗取名“阿隨”,其中這個“隨”字有跟隨、依附的意思,表明她并沒未從依賴他人的思想中獨立出來,暴露出思想革命的不徹底性。正是由于子君思想上的不徹底性,造成了她在從私人的家庭空間走向社會公眾空間時,自我身份轉變的失敗,即靠著旁人走出“父權”之家的子君,憑著自己卻難以走出“夫權”的家。
其次,涓生所導向的思想啟蒙與子君所導向的生活啟蒙之間的矛盾沖突形成了兩人之間真正的隔膜,并最終導致了子君的死亡。與文章《娜拉走后怎樣》相同的是,魯迅在《傷逝》中所關注的并非是愛情如何發生,而是愛情發生后會如何的問題,出走后的子君也如娜拉一樣,等待她的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悲劇命運。 “劃分一個社會制度、一個階級、一個事變或一個人物是悲劇階段,還是喜劇階段,最根本的標志是歷史存在的‘合理性’。”[2] 110-111顯然,在新舊交替的特定歷史下,無論是傳統思想還是受西方影響的新思想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當兩者交織在一起時,企圖改變對方而單方面服從自我意愿的嘗試注定是失敗的。一方面要認識到涓生所導向的思想啟蒙者試圖將子君改造為新歷史時期下的“新人”的進步性,即“從傳統的禮法道德、風俗習慣等層層束縛解放出來,成為西方現代文化標準下所定義的‘人’”[7];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子君身體力行用生活啟蒙的方式追尋愛情的合理性。與涓生完全受西方思想影響而展現出的過度理想主義、自私、缺乏責任感相比,子君身上則呈現出帶有傳統色彩的一面。她專注于對生活的營造,更加務實和關注眼前,她辛勤操持家務,雖沒有為家庭帶來直接的經濟補貼,但她卻力所能及地為家庭付出,甚至在即將離開時仍在努力維持對方較長的生活。涓生的不理解使子君的死亡成了必然,子君用生活啟蒙來維持兩人較長愛情的努力在涓生這里卻形成了兩人真正的隔膜:“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3]118
子君的悲劇是五四新思潮退潮后魯迅對關于現代與傳統思想沖突的反思。在去往“新的生路”上,涓生所代表的處于西方文化視野下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企圖用思想啟蒙的方式解放國人,但在他們呼吁男女平等、女性獨立時,并未能認清社會發展的特殊性所在,一方面中國傳統思想在新的歷史環境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傳入中國后,應對中國傳統持相互融合、取長補短的態度;另一方面他們忽略了人所賴以生存的實際社會狀況,即對于女性解放而言,她們是否具備獨立的條件和地位、出走后的女性如何重新確立身份等。子君自身性格上兩面性以及與涓生所代表的新思想的悲劇沖突構成了一種張力效果,即子君的悲劇命運所喚起的國人對傳統與現代的深刻反思以及關于傳統的時代意義和價值的思考。
三、未來之路的抉擇:埋葬真實
是否要告知民眾沖破鐵屋子的問題常常使魯迅陷于真實與謊言的矛盾之中,因此,是將殘酷而沒有希望的現實告知民眾還是繼續讓其在沉睡中死亡成為魯迅小說探討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在《藥》《祝福》《孤獨者》等小說中展現了魯迅內心的艱難選擇,彷徨和猶疑構成了知識分子精神上的困境,對于那個特定時代而言如何選擇都將構成一出悲劇,正如在《死火》中所說,被驚醒的死火倘若繼續留在冰谷必將凍死,而要將其帶出,則會燃盡。
面對種種矛盾的對立與沖突,黑格爾提出,當矛盾的雙方由于陷入片面性而各執一端時,唯有通過他們的毀滅才能否定各自的片面性,使沖突得以解除,從而體現出普遍意義的倫理力量的勝利。在涓生與子君的愛情幻滅過程中,子君的結局宣告了在兩人所代表的不同的思想觀念相互碰撞時,一方以死亡的形式暫時緩解了矛盾沖突,但對于涓生來說并卻未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矛盾和解,真正的和解則來源于自我思想層面上。具體來說,再次回到會館時的涓生其時并未擺脫靜寂與空虛,反而由此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危機之中,子君的死使得涓生看到深層的矛盾來自于自身精神世界中對未來的猶疑和彷徨。在《傷逝》中,這種矛盾的化解體現在知識分子涓生對“真實”的認識上以及在得到“真實”后卻選擇用“謊言”來繼續負重前行的思想升華。
首先是在對“真實”本身的理解上。伴隨著愛情的幻滅,涓生對“真實”的理解逐漸清晰,兩人剛交往時涓生雖處在寂靜和空虛中,然而卻是常含期待的,涓生在子君身上看到了在不遠的將來中新希望的曙光,然而他逐漸意識到兩人同居并非想象中那么完美,不過三星期,涓生在手記中寫道:“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3]119,子君從偶像的位置中跌落,成了涓生眼中真實的凡人,子君不停地做著家務,操持著飯食,同涓生心中的反家庭專制、雪萊、易卜生等浪漫主義理想背道而馳。此時,他的精神世界是痛苦的,在理想遭到外部因素的破壞后,他寫道:“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在遭遇偶像破滅后,他的思想逐漸成熟。被浪漫主義驅動的知識分子在這里遭到了現實打擊,隨著對現實的不斷認識,他開始理性對待與子君的愛情。從另一方面來看,涓生在意識到必須將真實說給子君后,卻沒有對眼前的困境指出一條明確的出路,從而直接導致了子君負著空虛的重擔走向死亡,這也暴露出新的革命力量在誕生之初思想上不成熟、不理智的特點。
其次是在對“真實”態度的轉變上。涓生在生的路上,卻選擇以遺忘和說謊為向導,繼續前行,這與魯迅之前在小說中對真實的態度形成了反差。總的來說,魯迅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堅定真實到徘徊于真實與謊言之中再到選擇帶著謊言“走”出去的變化過程。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曾說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8],此時的魯迅堅定地站在了真實的一面。在《藥》中魯迅通過烏鴉“鐵鑄一般站著”的姿態表達了對謊言的否定,而在面對祥林嫂是否有靈魂與地獄的疑問時,“我”卻選擇了用“說不清”來回答她,他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9]顯然在經歷了“沖破”鐵屋子的吶喊之后,魯迅在未來之路的選擇中陷入了彷徨和猶疑。
面對“真實”與“謊言”的兩難之境,魯迅最終在尋找自由之路中選擇了虛無。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認為,真正自由的人,在他所能實現的個人存在中,必須盡可能尋求一切機會使自身的意識“虛無化”,因為意識的虛無意味著它不受任何限制,它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與之前的文章相比,魯迅對于真實的理解更加趨向理性和復雜,他既看到了真實的必要性,同時又意識到其存在的局限性,在理想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真實與謊言等種種矛盾交織中,魯迅并未在客體環境中尋找到真正的解藥,而是通過以主體思想上的虛無來擺脫困境、尋求自由。與薩特所不同的是,魯迅的虛無之路是被動的、別無他法的。在《傷逝》的結尾處,魯迅借涓生之口堅定了人活著必須跨出去的目標,而跨出去的第一步卻要將真實埋葬,將謊言作為前導。
結 語
《傷逝》雖是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但其主旨并沒有局限于描寫知識分子的愛情幻滅,第一人稱下的懺悔性自述,揭示了涓生等知識分子從幼稚逐漸走向成熟的思想歷程,在理想與現實、現代與傳統、真實與謊言等矛盾的交織下,彰顯了其作為悲劇藝術的張力之美。在理想遭到幻滅后,以涓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選擇向著空虛和寂靜的前方繼續前行;當現代知識分子決定與傳統徹底訣別時,卻發現在傳統中仍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與謊言不斷的抗爭中,魯迅看到人活著就必須向前邁進的殘酷事實,而謊言卻是通向前路的向導。在時代與理想不可調和的矛盾中,首先覺醒的人必是痛苦的,他們生活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下,其精神上的痛苦和彷徨不僅展現出個體主體的悲劇性,更顯示出人在悲劇面前頑強向上的斗爭精神,而悲劇的美學意義也在于此,它既包含著人受到歷史環境而感受到的痛苦的精神體驗,同時又顯示出人在困境的迷霧中所迸發出的積極向上的進取意識,能夠在充滿張力的內外矛盾中彰顯出悲劇藝術本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