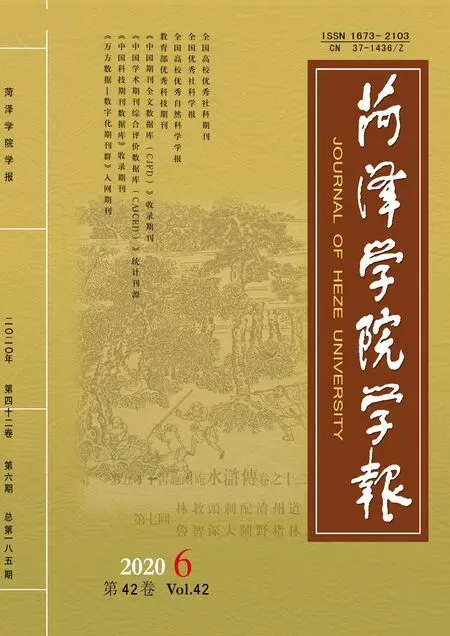從大學職能的歷史演變談高校為社會服務*
劉美丹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福建 廈門 361005)
“職能”一詞指的是人、事物或機構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對于大學來說,作為社會或教育大系統之下的一個子系統,它的職能就是高等教育系統內部及它在與社會各個子系統的聯系中表現出來的作用。如同大學從中世紀古典形態逐漸過渡到現代多元形態一樣,大學職能的演變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最初單一的教學職能發展到現在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職能之間的緊密滲透,其演變的實質就是大學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起源于19世紀60年代美國贈地學院運動的社會服務職能,經歷數十年的發展已成為現代大學的重要職能,越來越發揮出促進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科技繁榮的重要作用。但大學在走向社會中心的過程中,也不斷面臨著應該固守“學術象牙塔”還是成為“社會服務站”的爭議與沖突。與此同時,飛速發展的現代信息社會也會對大學服務社會的能力、水平提出新的要求。大學各個職能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大學究竟應當怎樣做才能有力消除各種爭議?大學又要如何回應與現代社會關系的新變化?這一系列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探討。因此,梳理大學職能的演變歷程,在此基礎上弄清楚社會服務與其他職能之間的關系,把握社會職能的發展趨向和原則,具有重要意義。
一、大學職能的演變歷程
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職能并非是大學與生俱來的,其產生到發展、單一到多元的漸進式演變過程充分體現了大學時代使命的變化,是大學根據當時社會發展需求的變化不斷調整、適應的結果。
(一)中世紀大學:單一的教學職能
雖然在中西方古代,如太學、國子監、柏拉圖學園一類具有高等教育性質的教育機構早已存在,但一般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誕生于12、13世紀的歐洲,以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法國巴黎大學、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等一批中世紀大學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是具有行會性質的學者自治組織,堅持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原則,貫徹精英教育的理念,注重古典神、法、醫學知識的傳授,以培養有教養、有趣味、符合本國或本民族基本價值規范的專門人才,如官吏、牧師、律師、法官等為主要目的[1]。
作為高度自治的學術機構,中世紀大學獨立于社會之外,將教學視為自己唯一的職能。比如紅衣主教紐曼就在《大學的理想》一書中,開門見山指出“大學是一個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2],大學應當以傳授知識和培養理性為己任;并在對大學的功能定位上,他明確提出了科學研究與教學相分離的主張。由此可見,受宗教思想和經院哲學的影響,中世紀大學表現出強烈的與世隔絕的特點,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象牙塔”。
(二)近代大學:教學與科研職能相結合
經歷了14~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之后,高等教育受宗教神學的影響和控制逐漸減弱,教育世俗化日益成為歐美近代教育的重要特征[3]。與此同時,以牛頓、達爾文、伽利略為首的科學家們在科學領域的重大發現推動了近代自然科學的進步,大學的職能也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不再只局限于人才培養,漸漸也在大學開展一些科學研究工作。
特別作為近代大學發源地的德國的大學,在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1694年,弗雷德里克創辦的哈勒大學是當時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第一所近代意義的大學,其辦學思想、課程設置均嚴格恪守專業學習和科學研究的標準;1810年,洪堡創辦了柏林大學(即洪堡大學),將自己一力倡導的“教學自由”、“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原則引入到柏林大學的辦學理念之中,并主張實行講座制和習明納(即研討班)制,大力發展研究生教育,使得科學研究職能同人才培養職能一起,成為近代大學并列的兩大職能,共同致力于科學人才的培養。自此,近代大學借助科學研究職能的發揮,開始與社會建立一定的聯系,并逐漸走出與世隔絕的“鄉村形態”,走向城市的中心。
(三)現代大學:社會服務職能誕生
在早期殖民地時期,美國主要移植和沿襲了英國和德國的高等教育模式,既實行精英教育,也發展科研事業。到了19世紀南北戰爭結束之后,美國的農業墾殖、工業生產進入迅速發展的新時期,迫切需求懂得工廠機械操作、農業種植技術的實用型人才,這時的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模仿歐洲模式,而是自主地開展了一些創新,在原有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職能基礎上,又發展出新的為社會服務的職能。
而這一職能的興起直接緣于美國的贈地學院運動,確立的標志是1862年美國政府頒布的《莫雷爾法案》,該法案規定要根據各州在兩院的人數分配相應的土地,并用土地出售或投資所得資金在本州建立一所以農業、機械知識為主的農工學院[4]。農工學院的出現,使得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后來這一實用主義的觀念被范·海斯運用到威斯康星大學的辦學理念中,明確指出“大學要為自己所在州、社區服務”[5],并發展成為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即“大學要走出校園,把大學的知識和技術優勢推向社會,通過大學中的專家和學生直接參與當地的工農業生產,實現大學與社會、社區的一體化”[6]。大學為社會服務職能的確立,使得其完全突破了傳統的“象牙塔”模式,與社會之間建立起愈加密切的聯系和互動。自此,大學終于實現了由中世紀的單一教學職能向現代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多元職能的巨大轉變,大學的功用也在培養人才、創新研究與服務社會的過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二、大學社會服務職能與教學、科研職能的關系
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職能,三者之間并非是同等重要、不分先后的關系,而是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的;同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大學對三大職能的履行具有不同的側重點。
(一)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是社會服務的前提和基礎
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創始人潘懋元先生在談到高校三大職能的關系時,明確指出“高等學校三個職能的產生與發展,是有規律的。先有培養人才,再有發展科學,再有直接為社會服務。它的重要性也跟產生的順序一致,產生的順序也就是它重要性的順序”[7]。作為大學最早產生的職能,人才培養同時也是大學的基本職能,其他職能的發揮必須以這一職能的實現為重要前提。而且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必須以教學、科研職能為依托,通過創造和傳播新知識、研發和轉化新成果、為社會各行各業培育所需的專門人才才能實現。如果脫離教學、科研職能來空談大學為社會服務,就會破壞大學最為寶貴的學術傳統,違背大學自身的內在邏輯,還極有可能使其由紐曼筆下的“國民追求真理的中心”淪為蔡元培先生所批判的那種“職業資格養成所”。
(二)社會服務對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職能的發揮起能動作用
社會服務職能的發揮既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職能的制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大學為社會服務有自己特定的條件和范圍,并非所有的社會服務活動都是由大學來提供,大學為社會服務必須堅持學術性、專業性的活動原則,遵循自身內在的學術邏輯。而且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與教學、科研職能相比,更加突出其直接性的特點。即“教學職能”是通過傳授知識、培養人才的方式實現大學的間接服務的,“科研職能”是通過創新知識、研發技術的方式來實現其間接服務的,但“社會服務職能”的發揮是大學依托自身知識、技術和人才方面的優勢,將這些智力資源直接轉化成能夠服務社會的活動,其實踐性更強,服務社會的方式和途徑也更加直接。
第二,社會服務職能會對大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職能的發揮起能動作用。這種能動作用既可能是積極的,也有可能是消極的。積極的促進作用表現在:一方面,大學在為社會提供服務的過程中,能夠加強自身與社會的聯系,提高自身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和知名度,從而幫助高校獲得更多的資源、信息和資金支持,進而改善大學培養人才與科學研究所需的設施、條件,實現辦學水平與辦學實力的整體提升;另一方面,大學在與社會接觸的過程中,能夠更加清楚社會需求的變動情況,并據此主動調整自己的辦學規模、專業設置及人才培養目標,使得培養出來的人才更符合社會需求、更具有針對性,無形中也提升了學校自身的競爭力。而消極的阻礙作用則主要表現在如果大學過于強調自身的社會服務職能,將所有的智力資源都直接用于社會服務,而忽視了更為重要和基礎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職能的發揮,就極有可能使得教師也出現重社會服務、輕教學與科研的偏差,課不好好上,更不好好做研究,從而導致學校整體辦學水平與教學質量的嚴重下滑,甚至使大學異化成為“服務工廠”。
總之,從大學職能的歷史演變來看,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職能的出現是有先后順序的,后一職能是在繼承和發展前一職能的基礎上產生的,三大職能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相互滲透和融合。因此,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不能游離于教學、科研職能之外,更不能沖擊到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的核心地位,以犧牲自己固有的精神傳統為代價,大學也不能因為過于強調教學和科研職能的核心地位,而忽視其社會服務職能的實現,把自己束縛在“學術象牙塔”之內。
三、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發展趨勢
從大學三大職能的演變歷程可以看出,大學職能經歷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社會生產力變革、社會與大學關系變化推動的結果。特別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不斷實現的今天,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教育的作用[8],知識日益成為校與校之間、國與國之間競爭力水平的決定性因素。而大學作為知識生產、知識創新的原始動力中心,其社會服務職能的發揮必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社會需求的持續更新,也必將對大學服務社會的能力、水平提出新的要求。
現代大學既不是紐曼時代居住著一批教士的“村莊”;也不是弗萊克斯納時代擁有一批知識寡頭的“單一工業的城鎮”;而是克爾時代豐富多彩、“充滿了無窮變化的城市”。與村莊和城鎮相比,“城市”更像文明的總和,并且越來越多地成為文明的內在部分,也越來越快地與周圍的社會發生互動[9]。作為時代標桿的現代大學,不能像原來那樣只能被動地適應社會的各種需求,一味迎合公眾的各種期望,而是要像一面旗幟、一座燈塔那樣,指引社會前進的道路,更要扮演社會的良心,站在公正、客觀的角度上對諸多社會現象與價值觀念采取獨立、質疑的態度[10],引領社會文明進步的風尚。同時,為迎接知識社會的新挑戰,大學的社會服務職能也要由被動適應社會需求向主動引領社會發展的方向轉變,堅持豐富自身內涵,積極拓展和發揮文化、創新引領的作用。
第一,大學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要發揮文化引領的作用。大學作為一種功能獨特的文化機構,自誕生之日起就承擔著傳承人類文化精華、啟發人類心智文明的作用,無論是教學、科研還是管理,諸多的校園活動都具有鮮明的文化屬性和文化特征。如果說文化是一所大學的精髓,那么大學就是以知識為載體進行文化傳播的學術組織[11]。在現代社會,隨著文化的政治、經濟功能的強化,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職能的地位不斷凸顯,現在已經上升到了國家文化戰略的高度。大學要服務社會,首先就要發揮文化引領的重要功能。一方面,大學要加強大學精神和大學理念的塑造,組織傳播優秀文化的活動,抵制不良社會文化的侵擾,不媚俗、不盲從,以理性、科學、民主之風化解現時社會的戾氣、浮躁、愚昧之狀。另一方面,大學的文化引領作用與學生個人的發展并不沖突,現代社會需求具有全球視野、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因此大學要發揮“文化育人”的作用,培養學生的道德責任感與社會服務意識,形成全面的文化科學素養,使之完善人格、涵養心靈,服務社會。
第二,大學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要發揮創新引領的作用。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靈魂,在科學技術水平日趨進步、大學與社會關系日益密切 的當代社會,大學要服務社會,就必須充分發揮創新引領的作用。首先,大學要引領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培養創新型人才現已成為國家的重要發展戰略,而大學作為人才培養的主陣地,必須把人才培養目標轉變到創新人才的培養上來,在課程內容上重視問題情境的創設,注重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提升;在培養環節上鼓勵企業參與,強化實踐教學。其次,大學要引領科學技術創新。從歷史經驗看,科技革命對國家前途具有機遇作用,比如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機的發明就幫助英國確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第二次科技革命,電氣技術的熱潮使德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前,以智能、泛在為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競爭格局,為我國這樣的后發國家提供了趕超的契機,所以提升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就顯得尤為迫切。大學作為知識轉化成生產力的孵化器和動力源[12],要充分利用自身強大的科研、信息、人才、資源優勢,瞄準科技前沿,為國家、社會科技創新提供有力支撐。
四、大學發展社會服務職能應當堅持的原則
作為社會的“智力領袖”,大學在履行和發展社會服務職能時,必須堅持以下四條基本原則。
(一)以人才培養職能的發揮為前提
自中世紀至今,大學已存在900多年的歷史,雖然其內部課程專業的設置、外部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大學一直以來都是以人才培養為根本使命的學術性組織,為社會所需的各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無論社會怎樣變化、大學怎樣發展、其職能如何演變,人才培養都應當是大學首要的、也是最為重要的職能。大學只有通過教學和科研培育好專門人才、發展好科學事業,才能更好地服務國家、社會,實現文化和創新引領。正如張楚廷先生所言,“大學拿什么去服務?它或提供科學技術,或提供人才(培養或培訓),然而,人才是通過教學來培養或培訓的,科學技術成果是靠科研來提供的。所以,社會服務的職能是由基本職能衍生出來的”[13]。因此,大學的社會服務必須在教學、科研的質量有所保證的前提下進行。特別在國家統籌推進“雙一流”大學建設的今天,重新平衡社會服務與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之間的關系,培養國家發展所需的一流人才,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遵循大學自身的內在邏輯
阿什比指出,大學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14]。前者指的是高等教育應該遵循的信條,即大學發展的“內在邏輯”,這里主要指19世紀德國洪堡時代的大學理想;后者是指“本國的社會背景”,即每個大學所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諸多因素的總和。在日益強調大學要為社會服務、走向社會中心的今天,大學已然不可能蜷縮在“學術象牙塔”內,對外界需求不聞不問。大學要肩負起社會發展“動力源”的責任,對外界需求做出適當的反應,但并非是盲目地滿足社會的任何要求,大學要遵循自身的內在邏輯,堅守自身作為學術堡壘的本質屬性,捍衛自身不懈追求真理的學術立場,永葆“學術象牙塔”之精神,其服務社會之路才能越走越遠。正如弗萊克斯納所言,“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斷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5]。
(三)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則
大學為社會服務職能的履行,必須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則。特別在從事涉及政治、戰爭、軍事等敏感性問題的研究時,學者們不能推卸自己對研究可能造成的意外或不良社會后果的責任,必須恪守學術道德的基本原則,履行好學術責任。并且教師在對學生進行科學教育的過程中,要積極融入人文素養的內容。正如阿什比所言,“大學不能只教學生如何制造炸彈或建筑教堂,更應教他們對于制造炸彈或建筑教堂兩者之間如何進行選擇”[16]。又如博克所言,“大學必然要走出象牙塔,但大學必須受到某些道德倫理標準的約束”[17]。因此,作為大學來說,必須關注自身滿足了社會某方面的需求之后,在倫理道德和社會生活上可能產生的諸種后果。
(四)不斷引領社會發展
大學引領社會的發展是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應有之義,是大學價值的最高體現[18]。美國知名的高等教育學者赫欽斯教授就強調了大學負有引領社會發展的重要責任,他明確指出,現代大學要應對社會的需求,就必須成為一座指明社會前進方向的“燈塔”,而不應是社會需求什么、大學就反映或提供什么的“鏡子”;大學應積極地引導社會,而不是一味去迎合大眾的淺近需求。與傳統的社會服務職能相比,前者更突出主動服務的重要性,即大學自己掌握社會服務的主動權,對社會前進的道路有預見和指引的能力,能夠智慧引領社會發展;后者仍停留在被動適應的狀態,往往是社會需求變化了之后,大學才有所察覺,再作調整,此時就已經滯后了。因此,大學服務社會應不止于簡單、低層次地滿足社會各種需求,維持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現時狀況,而是要充分利用學術性的本質屬性,發揮其“智慧領袖”的作用,以理性批判、前瞻規劃的態度和意識積極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人性價值的完善。
結語
從歷史演變的過程來看,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作為現代大學的三大職能,從產生到發展都擁有非常深厚的歷史淵源,每一種新職能的出現都見證著大學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變化。在大學已然置身于社會中心的今天,再去討論大學究竟是“學術象牙塔”還是“社會服務站”失去了意義。未來大學要在著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大力開展科研創新的同時,更加重視和發揮大學為社會服務的重要職能,不斷豐富和拓展其內涵,引領和推動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