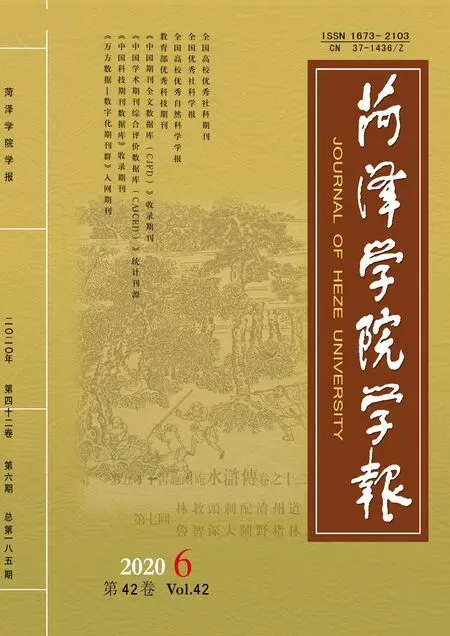文學倫理學批評視角下苔絲的倫理傾向研究*
曹 南
(遼寧對外經(jīng)貿(mào)學院公共外語教研部,遼寧 大連116052)
《德伯家的苔絲》是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所創(chuàng)作的重要作品,同時也是一部飽受爭議的小說。此作品不僅展示了哈代高超的寫作技巧和文學素養(yǎng),而且對后世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影響也極為深遠。從文藝批評的角度來看,該小說最重要的是深藏于小說布局謀篇技巧之下的對女性愛情與倫理傾向的道德關懷。女主人公苔絲身上具有豐富的隱喻符號和象征特質(zhì),以致于在作品發(fā)表之初就被評論為“不道德、消極”,但在當代文學評論中,《苔絲》還是受到了較高的評價。比如Boumelha,P說“正是苔絲奠定了哈代在英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地位”[1]。除去作品本身在文學領域的建樹之外,大多數(shù)評論者仍未改變對苔絲形象的固有看法,比如仍有人認為她是一個通奸者、一個地地道道的殺人兇手。傳統(tǒng)批評論者多聚焦于苔絲悲劇的外部因素,側(cè)重于將其作為一個悲劇的承受者懸置于特定的社會關系網(wǎng)中,從而忽視了苔絲作為主體的悲劇命運來源。本文擬依據(jù)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對苔絲的倫理傾向加以分析,探討其悲劇的內(nèi)在原因。
一、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及應用價值
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一種批評方法最早出現(xiàn)于西方文藝評論界,直到2004年才被學者引入我國,目前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倫理學批評體系。與西方倫理批評不同,中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將倫理批評與特定文學作品結(jié)合,以解決實際的文學問題為目標,同時基于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方法論體系建構(gòu)了全新的倫理批評概念,重點通過范例分析研究特定問題。對于本文研究的對象而言,其倫理環(huán)境較為簡單,整部小說圍繞美麗善良的農(nóng)村姑娘苔絲和貴胄后代亞力克以及擁有開明思想的知識分子安吉爾之間錯綜復雜的情感糾葛展開,小說中,因家庭變故而不得不選擇去遠親家打工謀生的苔絲被垂涎其美色的少爺亞力克誘惑并發(fā)生關系,經(jīng)歷懷孕及孩子夭折的苔絲遠走他鄉(xiāng)遇到了善良的牧師的兒子——安吉爾,但由于安吉爾無法接受苔絲的荒唐往事,因此遠走巴西。經(jīng)歷人生與愛情困境的苔絲被迫再度成為亞力克的情婦,直到故事最后以苔絲殘殺亞力克并被處以死刑結(jié)束。整部小說在具體事件的變化發(fā)展中表現(xiàn)出相應的倫理選擇和道德秩序體系的矛盾與沖突。為了貫徹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要旨,本文在研究作品及人物的同時也涉及到作家和當時整個英國社會的倫理傳統(tǒng),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學性和倫理批評性的多維結(jié)構(gòu)。
二、苔絲倫理傾向研究
(一)傳統(tǒng)的倫理選擇——進化論傾向
19世紀末,伴隨著啟蒙運動思想的擴散,以赫胥黎和達爾文等為代表的生物學家傾向于將自然選擇的觀點納入倫理和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人們基于對物質(zhì)世界的探索而考察精神倫理世界的實際可能性日益提升。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信仰開始由宗教轉(zhuǎn)向科學,理性認知逐漸取代宗教神學,適者生存、自然選擇等生物學概念被運用到社會學研究層面,助推人們在精神層面實現(xiàn)對社會發(fā)展的全新認知。但對于女性而言,傳統(tǒng)的倫理枷鎖并未減輕,正如Boumelha寫道:“歷史和圣經(jīng)對女人的定義僅僅是變成了生物和科學術(shù)語”[1]。
在《德伯家的苔絲》中,哈代使用標志性的“環(huán)境—人物性格”描寫方法將苔絲化身為“純潔”的代表,這不僅體現(xiàn)在外表的純潔,還包涵有性格及道德品質(zhì)的純潔。比如少女時期苔絲的出場,作者使用“寧靜的布蕾山谷、美麗的河流和草地”加以襯托,暗示了苔絲在恪守女性貞操底線和心靈底線方面的意愿與能力。純潔的苔絲讓亞力克垂涎三尺,小說寫“她站在那兒,光艷照人……使他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于是亞力克開始不斷地嘗試接觸苔絲,但都沒有獲得成功,直到苔絲在亞力克家工作幾個月后,和她的伙伴去鎮(zhèn)上參加星期六的狂歡舞會回程的途中,亞力克得到了苔絲的身體,其時苔絲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一切都包裹在濃密的黑暗中”,兩人就在無比自然、原始的環(huán)境下暴露了性本能。苔絲雖被人侵犯,可是由于她內(nèi)心對純潔的堅持使她“把自己想象成這個環(huán)境中一個不倫不類的人”。由于受到維多利亞時期社會傳統(tǒng)的影響,苔絲絲毫沒有認識到她的行為的自然屬性,因此也導致在失貞之后,對象征秩序的敬畏使她一直難以擺脫精神分裂的狀態(tài)。
這反映出在傳統(tǒng)倫理傾向下苔絲精神和行為選擇的局限性,想要沖破自然倫理的束縛使她更加看重與安吉爾之間的關系,安吉爾和苔絲的融合是受到苔絲身體和心靈純潔的吸引。因為在維多利亞時期,社會倫理道德體系更愿意將女人所受的“非自然的性”等同于軍事、經(jīng)濟方面的沉淪(Lawrence,2008)。因此,男性意志對女性的支配和定義相比女性自身的認知更加具有決定性,如果女人是不純潔的就會被視為倫理道德層面的徹底淪喪。因此當安吉爾在新婚之夜聽聞自己視作純潔的象征的妻子苔絲曾被人奸污,他當即表示無法忍受。在潛意識里,安吉爾對苔絲的遭遇予以同情,但他又無法擺脫當時的倫理道德束縛。
可以看出,作為達爾文式倫理立場的忠實擁躉,作者片面地將自然放在現(xiàn)存的社會結(jié)構(gòu)語境中加以理解,從而導致了苔絲的悲慘命運和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苔絲作為個體的悲慘命運與傳統(tǒng)社會的倫理態(tài)度息息相關,個體是難以真正突破傳統(tǒng)的桎梏直面內(nèi)心自由的。
(二)傳統(tǒng)與自我間的倫理選擇——功利主義傾向
功利主義倫理學說在邊沁等人的推動下成為社會倫理的主流,功利主義倫理學說認為“自然被人類置于兩位公主——快樂和幸福——的主宰之下”[3]。即,人的快樂與痛苦決定著自身的行為動機和目的,追求快樂與避免痛苦二者必居其一,因此實現(xiàn)個人的最大幸福是每個人的行為準則。受此影響,苔絲的倫理選擇還具有向傳統(tǒng)世俗功利主義價值觀妥協(xié)的傾向。苔絲在情感方面的選擇無一不與男性的家庭、地位等外在條件有關,對于亞力克是如此,對于安吉爾同樣如此。家中突遭變故,苔絲面對有錢有勢的富家公子亞力克的追求時想到的更多的是他能夠為自己和家人帶來良好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但作為交換的是其美貌以及勤勞的品質(zhì)。亞力克指望她在結(jié)婚后能做個好管家,給他帶來“方便”與“幸福”。在這樣的世俗道德下,苔絲自然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欲望,縱使作者仍有意地表現(xiàn)她作為女性追求平等幸福情愛的主體地位,但卻只是為將她拋入更大的傳統(tǒng)倫理泥沼中。小說在描寫苔絲的女性自我認同覺醒時寫道:“在她今天走路的時候,她的胸部上下震顫,女人味十足”。苔絲雖然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但又不得不面對社會現(xiàn)實,這表明苔絲是一個在傳統(tǒng)與自我間不斷掙扎的角色。但故事的發(fā)展以及諸多巧合與命運的轉(zhuǎn)折仍不可避免地使苔絲滑向功利主義倫理那一面。比如陷入悲觀絕望境地的苔絲試圖從道德上尋找出路,亞力克在苔絲的父親病死且住房租約到期的窘迫時期強迫苔絲與他同居,于是苔絲在抱有美好愛情幻想及對家庭利益的現(xiàn)實考量下答應了亞力克。“他待我很好,待我母親也很好,我父親死后,他待我們?nèi)叶己芎谩保z無法在現(xiàn)實的利誘面前強調(diào)自己的獨立主體地位,其內(nèi)心的倫理態(tài)度仍然被現(xiàn)實境遇裹挾,這正符合功利主義倫理觀中強調(diào)以自我犧牲換取最大幸福的觀點。
在有關苔絲是否是真正的道德墮落抑或只是以低矮的姿態(tài)尋求妥協(xié)并進行反抗的觀點論爭中,一些學者堅持苔絲與傳統(tǒng)抗爭的觀點,摩根認為苔絲處事果斷而不怯懦,擁有面對困難毫不退縮的性格,因而她絕不是一個消極的犧牲品。這表現(xiàn)在苔絲個人的疏忽導致全家唯一的一匹馬被意外撞死,她連連自責“全是我的錯——全是我的!我沒有理由”[2]97,她由于對此感到由衷地內(nèi)疚而答應父母去德伯家做工并直接導致了之后故事的發(fā)生。命運的巧合使得作為窮人家孩子的苔絲遇事無法選擇逃避只能轉(zhuǎn)向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尋求突破,筆者認為一連串的命運變化也致使苔絲不斷地認清了渺小的自己相對于巨大的命運之輪而言微不足道,因而她轉(zhuǎn)向新的人生際遇,尋求新的歡樂。作者也進行了類似的描寫“天地萬物都有尋求歡樂的本能,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這一思想暗合邊沁等功利主義思想家的思想體系,但即使是追求功利主義的幸福安樂而言,苔絲的自我幸福也全然受到傳統(tǒng)男性思維的影響,在她生活十分拮據(jù)時無奈只能尋求安吉爾的父母幫助,但她碰巧聽到安吉爾的哥哥詆毀她的一系列言論,她完全被這些意外之事影響了良好的心情,認為自己“不可能再考慮回到牧師家里去了”[2]。此后,她回去的過程中遇到了亞力克,并再一次重新成為他的情婦。
可以看出,苔絲在突破傳統(tǒng)與尋求自我的道路上仍然需要屈服于現(xiàn)實,而現(xiàn)實環(huán)境對苔絲自身的性格和追求造成了多方限制,縱使苔絲會給自己的私生子施洗禮、會勇于把自己的真實情況告訴情夫,但事實證明結(jié)局還是難以逃脫功利主義倫理世界的巨網(wǎng)。因此,在傳統(tǒng)與自我之間,苔絲僅代表了一種抗爭的意志,但同時這意志在現(xiàn)實世界的強壓下顯得弱不禁風,最終還是淪為“大眾的凝視下一個沉默的客體”。在這一層面,苔絲的自我意識崛起更多地是表現(xiàn)出強烈的悲劇性,而這一悲劇性也正來源于其時發(fā)達工業(yè)資本主義社會倫理觀對底層女性的壓迫。
(三)自由與責任間的倫理選擇
薩特認為“自由不可回避,同時責任亦不可推卸”[4]。自由與責任二者之間紛繁復雜的關系影響著苔絲作為獨立主體的命運,因此苔絲是背負著沉重的家庭與社會責任在艱難地找尋自由的救贖之路,同時進行著痛苦的倫理選擇。
首先是家庭責任。苔絲出生于貧窮小販家庭,父親家庭責任的缺失使得家庭重擔不免落到苔絲身上,偏偏母親生育能力較強,眾多弟弟妹妹需要作為長姐的苔絲承擔起撫養(yǎng)責任。因此,苔絲更加清楚自身地位,在家中唯一的生產(chǎn)工具——馬死后,出于無奈的苔絲只能選擇去亞力克家做工,這也有了亞力克用金錢和階級地位交換苔絲身體和情感的故事,從自由與責任對立的角度來看,苔絲犧牲了自我層面的自由選擇了家庭責任,但從自由與責任于差異中融合的角度來看,苔絲無法放棄責任,因而只能在責任的重壓下企盼自由,因此苔絲的悲劇形象顯露無疑。在小說的描寫中,苔絲與亞力克住在一起并完成了對家庭的照顧責任,但她的精神已脫離了肉體。安吉爾從巴西回來找她時,發(fā)現(xiàn)她的精神已經(jīng)與其生存意志無甚關聯(lián),完全像是“一具順水漂浮的尸體”。可以看出,在傳統(tǒng)家庭責任的重壓下,苔絲對于找尋自由已無能為力。
其次是社會責任。19世紀后期英國后工業(yè)時期的社會倫理伴隨著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階級關系和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而有了新的發(fā)展,但家庭倫理方面改觀甚小,妻子要對丈夫溫柔并百依百順的社會現(xiàn)象十分普遍。對于苔絲而言,她也曾為了情愛而甘愿扮演安吉爾順從、溫柔的妻子。但對于亞力克而言,縱使他瘋狂的追求于己,苔絲還是堅守對安吉爾的婚姻倫理,她對亞力克大喊:“懲罰我吧!……用鞭子抽我……一旦成為犧牲品就永遠是犧牲品了!”這體現(xiàn)出苔絲對于倫理與法則的執(zhí)著追求。與此同時,苔絲的痛苦亦是根深蒂固的,在保持對安吉爾忠誠的同時也由于家庭的困境和愛人的出走而愈發(fā)加重了自己內(nèi)心的孤獨無助。在面臨絕境時,苔絲選擇殺死亞力克尋求精神解脫并奔向真正愛人的懷抱時,整個社會均視她為敵人,警察們馬上改變冷漠的姿態(tài)抓捕她并處以死刑,至此苔絲在精神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尋求自我的道路徹底坍塌,社會的無情和倫理秩序的潰敗進一步導致了苔絲的痛苦。
筆者認為,苔絲的凄苦命運雖不無意外地與其出身和家庭有關,但更多地則是社會的不公、傳統(tǒng)倫理體系對女性的嚴防死守等外部原因的推動。正如Miller指出的那樣,“苔絲的人生旅程具有不可逆性,但我們找不到足夠的理由來解釋這些變故,她更多的是工業(yè)文明、男性社會欲望的犧牲品”[6]。盡管她在叛逆地追尋自我的過程中也未嘗有一刻卸下重壓在肩的家庭及社會責任,但她的死仍令人感覺十分遺憾。就整部小說中腐朽落后的階級思想、僵化的社會格局而言,苔絲是唯一具有自由倫理意識的人,在她認知到自己擁有更多的可能追尋公平、自由和愛時,她義無反顧地加以實踐,結(jié)局的遺憾并不能抹殺過程的精彩,相比那個奄奄一息的社會,苔絲更像是一根努力跳動的神經(jīng),是全體的希望。
結(jié)語
哈代塑造的苔絲是一個靈與肉交融的、活生生的人物,她內(nèi)心深處對抗著社會傳統(tǒng)倫理價值觀,有追求自由的意識。在哈代看來,人文的倫理環(huán)境需要符合自然界“物競天擇”的倫理規(guī)律,人無法勝過天,但人同樣具有追求快樂、趨利避害的選擇權(quán)利。人作為社會性動物,自由與責任相互依存,不可分離,人的道德行為的選擇與倫理傾向既有符合自然主義進化論的一面,同時也具有功利主義的相應特征。本文采用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對苔絲的倫理傾向加以分析,苔絲在適應傳統(tǒng)倫理框架約束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尋求自身的倫理選擇,然而在當時的社會,女性探索符合自身角色定位的倫理價值體系并不可行,她的死表明,社會倫理與個人倫理沖突時個人將無法更好地保存自身倫理的完整。這也啟示我們需要正視社會存在的相應問題從而完成對傳統(tǒng)倫理秩序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