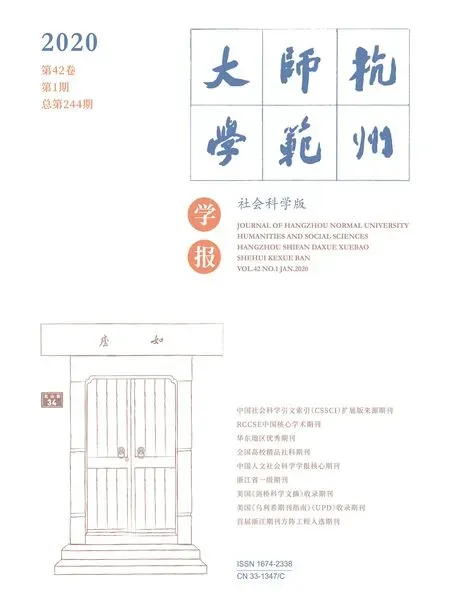民族國家視角下的帝國
——約翰·西利的國家觀念及其英帝國史研究
施華輝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帝國是歷史上延續時間最久且形式最多樣的政治形態。它邊界模糊,強調普遍主義的統治原則,以因地制宜、差異政治為治理策略,因而內部結構呈現多元性與不平等性。(1)參見赫爾弗里德·明克勒《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閻振江、孟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4-8頁;簡·伯班克、弗里德里克·庫珀《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柴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克里尚·庫馬爾《千年帝國史》,石煒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19世紀的英帝國是典型的“海洋帝國”,其疆域遼闊且遠隔重洋,治下環境千差萬別,(2)以人口結構、民族構成、治理模式等因素為標準,19世紀的英帝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部分:白人定居殖民地、印度和殖民帝國。參見克里尚·庫馬爾《千年帝國史》,第301-302頁。所以治理模式多種多樣。(3)根據不同殖民地的情況,英帝國大致行使三種統治方式:建立責任政府、直接統治與間接統治,參見John Darwin,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4, pp.189-222。同時又因大國競爭使然,英帝國邊疆并不穩定。可見它難以與注重民族一致性,并且邊界清晰可辨、民眾政治身份平等的民族國家框架相兼容。但在19世紀后期,透過民族國家的視角來思考英帝國的做法開始出現。相關討論旨在劃清英帝國邊界,加強各成員的團結,以鍛造出具有相同民族認同的統一國家。簡而言之,論者希望將英帝國打造為民族國家。約翰·西利(John R. Seeley, 1834-1895)的論述為以上思考提供了理論資源。
約翰·西利是19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1869年成為了劍橋大學欽定現代史教授(Regius Professors of Modern History)。他長于政治史與外交史,奉德國史學為典范,視蘭克為榜樣,著作甚多。1883年,西利發表了《英格蘭的擴張》,(4)西利生平參見Deborah Wormell, 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該書被視為專業英帝國史研究的開端[1](P.8)。其充分介入了當時圍繞英帝國治理經驗及未來命運的論爭。(5)例如曾任殖民地事務大臣的約瑟夫·張伯倫就認同西利的觀點,相關言論參見Joseph Chamberlain, “The Ture Conception of Empire”, in Joseph Chamberlain, Foreign & Colonial Speeche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97, pp.242-243。在該書的歷史敘事中,英帝國的擴張被書寫為國家的成長,并指明未來的英帝國將是統一的民族國家。而上述敘事之所以成型則有賴于背后的國家觀念,特別是“有機國家”(organic state)的理論。西利為何在此時提出以上觀點,他又是如何將國家觀念融入英帝國史書寫當中,并據此塑造出民族國家式的英帝國形象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以往學者對西利的英帝國史研究多有關注。他們將《英格蘭的擴張》置于19世紀末帝國主義擴張熱潮的歷史語境中,認為西利是熱情的帝國主義者,但并不信奉“天定命運”觀念,而以現實主義態度梳理英帝國的歷史。(6)相關討論參見Peter Burroughs, “John Robert Seeley and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1, no.2, 1973, pp.191-211; Luke Trainor, “Historians as Imperialists: Some Roots of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1880-1900”,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vol.15, no.1, 1981, pp.35-48; J. G. Greenlee, “ ‘A Succession of Seeley’: The ‘Old School’ Re-examined”,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3, no.3, 1976, pp.266-268。相比之下,關于西利國家觀念的討論并不多,有關學者主要就西利的國家觀念是民族主義的還是普世主義的,(7)參見Daniel Deudney, “Greater Britain or Greater Synthesis? Seeley, Mackinder, and Wells on Britain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Er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2, 2001, pp.187-203; Duncan Bell, “Unity and Difference: John Robert Seeley and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1, no.3, 2005, pp.559-579; H. S. Jones, “The Idea of the National in Victorian Political Though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5, no.1, 2006, pp.12-21; Georgios Varouxakis, “ ‘Patriotism’,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ity’ in Victorian Political Though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vol.5, no.1, 2006, pp.100-118。其理論淵源是歷史主義還是實證主義等問題展開論辯。(8)參見John burrow, “Historicism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Benedikt Stuchtey and Peter Wende, eds., 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 1750-19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55-258; James Meadowcroft, Conceptualizing the State: Innovation and Dispute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880-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46-47。可見西利的國家觀念與其英帝國史研究之間具體的思想聯系有待闡明。本文以國家觀念為中心,闡述西利如何以此為主軸,編織英帝國的歷史敘事,并討論由此建構出來的地緣政治構想及實踐,以深入理解帝國與民族國家間的復雜關系。
一、英帝國國家形態的論辯
19世紀中后期,英國學者、文人就英帝國的結構形式及未來前景展開了熱烈討論。其中有相當多的意見可以歸納為一點:英帝國不能或難以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它實際或可行的結構形式是松散的聯盟體系或經濟網絡。北美獨立運動與英屬加拿大地區叛亂的歷史為以上意見提供了事實支撐。在論者看來,殖民地終將脫離母國,因此耗費大量物資來搭建龐大的統一帝國是得不償失的行為。合理的追求或可行的方案是英國減少對殖民地的干預,將防衛任務及責任下放至地方,以盡可能小的成本維系經濟網絡的運作。該認識根植于豐富的理論淵源,它處在由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及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等人構筑的思想脈絡當中。(9)參見George Burton Adams, The Origin and the Results of the 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899, pp.95-98; Michael David Burgess, “The 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1869-1893”, Ph.d Dissertation, Leicester University, 1976, pp.15-17。相關議論與19世紀早期開始形成的“小英格蘭主義”(Little Englandism)關系密切,參見王本濤《簡析19世紀中期英國的“小英格蘭主義”》,《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第28-32頁。至19世紀中后期,葛德文·史密斯(Goldwin Smith, 1823-1910)接續了前人的思考。他反對英帝國的統一化,鼓吹分離論和負擔論,闡明殖民地自治和帝國權力下放的事實理據及倫理基礎。同時期,約翰·莫利(John Morley, 1838-1923)也持相近觀點。他認為在經濟因素外,整合英帝國多種政治架構的錯綜復雜,以及殖民地民眾獨立意識的萌生是兩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所以帝國統一化并非合理目標。(10)葛德文·史密斯與約翰·莫利的相關議論散見多處,參見Goldwin Smith, “Imperialism”, Fraser`s Magazine, vol.55, 1857, pp.493-505; Goldwin Smith,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45, 1884, pp.524-539; John Mor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in John Morley, Critical Miscellanies, vol. Ⅲ, London: Macmillan, 1888, pp.291-335。在上述作者的觀念中,未來的英帝國將是一個缺乏中央權力,僅由情感及利益維系的同盟體系,其間缺乏強韌的制度紐帶。
負擔論和分離論質疑了英帝國的統一化,但未否定團結的價值。諸多關心英帝國團結的學者、文人參與到討論當中,在懷疑統一計劃的同時強調團結的意義。查爾斯·迪爾克(Charles W. Dilke, 1843-1911)游歷了英國人的海外社區,于1868年發表《更大的不列顛》一書。(11)關于“Greater Britain”的譯名,中文世界中有兩種,即“更大的不列顛”及“大大不列顛”,參見陳志宏《帝國愿景與歷史變遷——維多利亞時代“更大的不列顛”思想探析》,洪慶明、陳恒主編《世界歷史評論(04):觀念發明與思想形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1-129頁;顧鵬程《作為歷史撰述、治國方略與思想傳承的“大大不列顛”:約翰·西利筆下的大英帝國》,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本文采用“更大的不列顛”。他認為英語民族同文同種,由無形紐帶維系彼此情感,但這并不意味著英帝國會走向統一,松散的“邦聯”才是合理的形式。[2](PP.155-157)愛德華·弗里曼(Edward A. Freeman, 1823-1892)在1884年成為牛津大學欽定現代史教授,他從歷史的角度指明英國的自由傳統與帝國統一的設想相矛盾,但其無意質疑帝國本身,而只是為了闡明母國并非殖民地的統治者,文化與血緣的一致性預示著兩者間應保持松散的同盟關系。[3](PP.430-445)接替弗里曼牛津大學教席的詹姆斯·安東尼·弗勞德(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奉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為精神導師,秉持種族主義觀點。他曾以殖民地事務大臣特使的身份于1874年至1875年出訪南非。[4](P.105)基于海外訪問體驗,弗勞德警惕英帝國統一化,但并未號召放棄帝國,而是將希望寄托于建立在移民網絡基礎上的種族情感,及其培育而成的“家庭氛圍”之上。[5](PP.1-16)總而言之,以上論者均認為未來的英帝國并非統一的民族國家,而是松散的“邦聯”,維系其存在的基礎是文化與血緣的親緣關系。(12)相關討論參見Amanda Behm, Imperial History an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Exclusion: Britain, 1880-194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66-68。
前述觀點在19世紀中后期的相關討論中有較大市場,但相反觀點也在成長中,并有后來居上的勢頭。約翰·西利不把英帝國視為同盟體系、經濟網絡或邦聯,而是將其視為民族國家。
19世紀后期理論與現實的變化是西利的觀點得以產生的歷史語境。在理論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的經濟學民族主義進入了英國經濟學論辯當中。[6](P.42)李斯特學說的英國支持者試圖將英帝國的經濟體系從奉自由貿易論為準則的開放網絡轉變為保護性的統一市場。旨在構筑貿易壁壘的設想既加強了英帝國統一化的勢頭,又有利于明確帝國的邊界。與此同時,種族優越論及等級論日漸興盛,擠占了啟蒙普遍主義的思想空間。受其影響,營造民族一致性的共同體的想法逐漸抬頭。[7](PP.206-211)在以上思潮、情緒導引下,英帝國被想象成排他性的種族帝國,(13)殷之光認為19世紀后期以來,種族中心論在英帝國政治想象中扮演關鍵角色,參見殷之光《敘述世界:英國早期帝國史脈絡中的世界秩序觀》,《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第113-128頁。進而易于從中推演出將英帝國打造為民族國家的計劃。實際上,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大國崛起及帝國競爭成為國際局勢的潮流之一,并被冠以“新帝國主義”之名。[8](PP.220-224)內戰后的美國在民族國家建設上成就顯著;俄國與日本的崛起威脅著英帝國在東方的利益;歐陸上德國與意大利的統一改變了大陸地緣政治格局。以上變動極大催生了將英帝國打造成統一國家的呼聲。在許多輿論看來,英帝國唯有加強團結,甚至發展為統一的民族國家,才能應對日益嚴峻的挑戰。另外,在相關議論中,帝國的統一以及民族國家建構不僅必須,而且可行。這是因為聯邦制的實踐、代議制政治的成熟、電報與蒸汽機的發明克服了大國統一的制度及技術阻礙。[9](PP.63-90, 235-237)這使時人意識到廣土眾民與民主自由兩種因素能共存于一個國家之中,糾正了帝國統一必然導致專制的看法,從而祛除了原先籠罩在統一計劃上的情感障礙。
西利的觀點在英帝國統一及民族國家建構設想中扮演關鍵角色,他憑著1883年發表的《英格蘭的擴張》為以上設想提供了歷史論據。西利之所以認為英帝國理應統一為民族國家,除了歷史語境使然外,更重要的是他所持國家觀念的作用。換言之,西利將其秉持的國家觀念貫徹于英帝國歷史書寫當中,強調英帝國應該且能夠成為民族國家。
二、西利的“有機國家論”與英帝國史研究
西利的學術思考圍繞著國家議題展開。他認為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是國家,而非英雄人物的行動,所以“歷史學可以被定義為國家的傳記”[10](P.298),其最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演變的規律。西利對國家問題的關注是英國學者對國家理論興趣提升的表現之一。該現象一方面得益于英國學者對歐洲大陸思想的吸收和轉化;另一方面也與生活方式驟變以及社會改革訴求迫切相關。在此情形下,國家建設的問題得到了時人的重視,國家成為了學者們熱議的對象。[11](PP.10-24)西利在此思想潮流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西利的國家觀念是英德學術交織下的產物。首先,西利在倫敦求學時加入過多個有“廣教會”(Board Church)背景的組織,接受了“自由派圣公會主義”(Liberal Anglicanism),尤為服膺該派別精神導師托馬斯·阿諾德(Thomas Arnold, 1795-1842)和弗里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 D.Maurice, 1805-1872)的學說。(14)西利與“廣教會”接觸頻繁,曾加入過奉莫里斯學說為指南的“劍橋阿瑞納斯協會”(Cambridge Eranus Society),也曾在莫里斯主辦的學校中講課,其史學觀念則深受阿諾德學說的影響。特別在強調現代史研究的價值時,西利把阿諾德的言論視為至理。相關情況參見J. Llewelyn Davies, ed., The Working Men`s College, 1854-1904, London: Macmillan, 1904, p.116; Deborah Wormell, 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 of History, p.18; Reba N. Soffer, “History and Religion: J. R. Seeley and the burden of the past”, in R. W. Davis and R. J. Helmstadter, ed., Religion and Irreligion in Victorian Society: Essays in Honor of R. W. Webb,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36; Duncan Bell, “Unity and Difference: John Robert Seeley and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569。關于19世紀英國的“自由派圣公會主義”,參見Mark D. Chapman, “Liberal Anglica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Rowan Strong,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glicanism, Volume III: Partisan Anglicanism and its Global Expansion 1829-c.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13-231。在“自由派圣公會主義”的觀念里,國家應當是具有倫理道德的生命體。例如,阿諾德認為“國家就像人一樣”[12](P.81),歷史學最主要的任務是追蹤由種族、語言、制度和宗教組成的民族性因素在國家中的構成。在他看來,“一旦四個因素黏合起來,那民族性就會變得完整”[13](P.44)。同樣,莫里斯認為教會將個體與國家相整合,自此國家不再意味著“冰冷”的制度,而會成為具有鮮活生命力的道德倫理共同體。受此影響,西利習慣將信仰、民族與國家結合起來思考。(15)西利在《作為道德教師的教會》一文里說明了國家是倫理道德的共同體,民族性的教會是其紐帶。相關內容參見J. R. Seeley, “The Church as a Teacher of Morality”, in J. R. Seeley, Lectures and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870, pp.245-289。其次,正如鄧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 1922-1994)所言,“自由派圣公會主義”之所以在英國的國家理論討論中產生革命性影響,是因為它吸收了德國的思想資源[14](P.10)。同樣,西利作為“自由派圣公會主義”的支持者,德國思想也為其國家觀念提供了滋養。(16)西利在1859年前往德國留學,此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多次提及西利的學術貢獻離不開德國思想的影響,相關情況可參見G. W. Prothero, “Memory”, in J. R. Seeley, The Growth of British Policy,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 ix; Oscar Browning, “Personal Recollection of Sir John Seeley and Lord Acton”, The Albany Review, vol.2, 1908, p.549。西利也曾幾次強調自己深受德國學術思想的影響,參見J. R. Seeley, ed., Livy Books I- X,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0, p.9。學界對于西利接受德國思想的情況進行過深入討論,參見John L. Herkless, “Seeley and Ranke”, The Historian, vol.3, no.1, 1980, pp.1-22。特別在撰寫普魯士政治家施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 1757-1831)的傳記時,西利集中論述了費希特(Fichte, 1762-1814)的國家觀念。借助后者的言論,西利在“日耳曼有機浪漫主義”(Germanic organic romanticism)的啟發下,指出國家不能僅僅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者,而應當是民族意識的載體和鮮活的道德共同體。(17)西利對費希特國家觀念的關注可參見J. R. Seeley, Life and Times of Stein, or, Germany and Prussia in the Napoleonic Age,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78, pp.28-36, 79-82。費希特關于民族和國家的看法詳見費希特《對德意志民族的講演》,梁志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鄧肯·貝爾以“日耳曼有機浪漫主義”來串聯施泰因男爵、費希特和西利的思考路徑,參見Duncan Bell, “Unity and Difference: John Robert Seeley and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573-574。總而言之,在以上兩種脈絡的交匯下,民族、倫理等關鍵詞,以及生命體的隱喻進入了西利的國家觀念中,并集中體現在由課堂講稿修訂而成的《政治科學導論》里。(18)該書于西利去世后出版,所收集的內容為1885至1893年間相關課程的講演錄,相關情況參見Henry Sidgwick, “Preface”, in J. R. Seele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Two Seri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896. vi。該書可被視為西利國家觀念的總結,他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始自19世紀60年代,尤其體現在其寫作的涉及宗教問題的論著中,參見J. R. Seeley, Ecce Homo: A Survey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esus Christ, London: Macmillan, 1866; J. R. Seeley, Natural Religion,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82, pp.172-202。
西利指出有機(organic)與無機(inorganic)是區分國家類型的標準。關于什么樣的共同體可以被視為國家的問題,與當時國家理論論辯中的關鍵人物托馬斯·格林(Thomas H. Green, 1836-1882)與大衛·喬治·里奇(David George Ritchie, 1853-1903)不同,西利秉持“非亞里士多德意義上”(not in the Aristotelian sense)的觀點[11](P.47),不贊成將文明和野蠻之間的界限當作分析國家的出發點,而是認為人類所有組織性的共同體都能成為國家理論思考的對象。此外,西利也不喜歡用君主或者共和的概念來定義國家的統治形式。在反駁了各種既有劃分標準后,慣于將國家比作生命體的西利借用動植物學的術語,把所有國家置于有機與無機兩個范疇中,并表露出對待兩者的不同態度,有機國家更有活力,更善待治下的民眾,無機國家(inorganic state)則是暴力的代表。[15](pp.43-44, 72-74)
西利認為在種族、信仰與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的政治共同體就是有機國家。具體而言,在他看來,原始部落、宗教社團與現代觀念里的國家是國家的三大類別。粗略來說,將三者結合在一起的紐帶分別是種族、信仰與利益。以上三條紐帶并無等級高下之分,由其中任意一條紐帶結合而成的國家都可能是堅實的共同體。同時,西利指出三條紐帶可以對應人類歷史前后相繼的三個階段。換言之,國家一旦演化到最高階段,那么利益就是最主要的紐帶。但他并未遵循嚴格的進化論。西利指出當現代國家最終形成后,前兩條紐帶并未在國家結構里消失,而是依舊發揮重要作用。[15](P.69)由此他認為:共同的種族、信仰與利益是現代國家三個最主要的特征,凡具有以上三個特征的政治共同體就是有機國家。“它的組成部分各盡其用、各司其職,或多或少像是生活工具或器官。”[15](P.43)通過以上簡述可知,有機國家不能是多民族混居的共同體,其中的民眾應具有一致的血緣、文化與生活習慣。由此“國家由眾人有機結合而成,而非僅僅是擁擠或聚攏于一處的產物”[15](P.44)。
至于什么樣的國家是無機國家的問題。西利指出在以上三種紐帶外,尚有第四種紐帶,即力量。他認為如果由共同的種族、信仰與利益連結而成的國家是有機國家的話,那將力量作為團結工具的國家即為無機國家,它們由征服戰爭塑造。因此在西利看來,盡管無機國家也有政府機構存在,表面上與有機國家無異,但它只能算是“準國家”(quasi-state)。[15](PP.72-75)也正是由于不成熟的狀態,“準國家”的統治基礎無疑是不穩定的。西利曾將上述觀點首先運用于思考古羅馬史。他認為基于軍事征服的羅馬帝國以力量為紐帶,它的擴張需要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因此“帶來了不間斷且無法避免的蠻族移民浪潮”[16](P.50)。羅馬帝國的瓦解與道德的墮落無關,其治下多民族的混居才是衰亡的重要原因。[16](P.48)
有機國家是以種族、信仰與利益為紐帶的國家,它不靠強制力來維系,因此其統一化的進程更順利,體制也更為穩定和諧。進而言之,有機國家的成長依托著本民族的擴散,而非基于對異民族的宰制。在西利看來,英帝國就是有機國家。他通過《英格蘭的擴張》,為國家的成長提供了一套歷史敘事。西利認為正因為英帝國基于種族、信仰和利益的共同性,所以不列顛島與海外殖民地在等級上并無二致,兩者是同一國家內平等的兩部分,英帝國與其說是帝國,還不如說是“世界國家”(world-state)。[17](PP.63-64)與此同時,西利指出英帝國的建設并不依靠強制力,而是借助移民擴散。他說道:
更大的不列顛不單單是英語民族的延伸,也是英國這個國家的擴張。但是對于更大的不列顛來說,一個同樣驚人的特點是,它仍然可以說是英語民族的延伸。以希臘殖民地為例,當民族的延伸與國家的擴張相分離時,那么它可能在道德和思想上增進了影響,但是它不會就此增強政治實力。另一方面,當國家超越了民族的界限,那么它的權力就會變得岌岌可危而且虛假了。……英格蘭在擴張自身時遠離了以上所有危險,因而對于它來說是一筆財富。而之所以遠離危險,是因為英格蘭在世界上占領的地方是如此的空曠,以至于能夠為新定居點提供無限的空間。那里有每一個選擇來到此地的移民所需要的土地,對于移民們來說,當地的種族遠未達到具有與之進行和平競爭的條件,更不用說能有力量來對抗移民了。[17](PP.45-46)
所以,西利認為英帝國的歷史展現了國家擴張與種族擴散相結合的過程。換言之,帝國建立并非基于對廣大異民族的暴力壓迫。相反,海外殖民地里的民眾多為生性熱愛自由的同胞。在此基礎上,西利才會認為由種族、信仰與利益三條紐帶結成的英帝國是具有“有機”性質的“更大不列顛”。[17](P.72)相對于用“無機的”人為力量塑造出來的帝國,英帝國擁有更文明的倫理道德和更堅韌的團結紐帶,因而也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有機國家強調民族一致性,所以西利在《英格蘭的擴張》中將現實的英帝國一分為二,把印度歸入另類。他認為印度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不同,它并非移民定居地,而只是帝國軍事征服的占有物。在種族、信仰及利益上,母國與英屬印度之間毫無共同性可言,之間的紐帶也并非“有機”。西利說道:
在那里,英國政府的力量是強大的,但是在亞洲人口的海洋中,不列顛民族就像微不足道的水滴。當一個民族將其自身擴展至其他領土時,就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遇,但即使你成功地征服了他們,你也難以摧毀或是驅除這些人的民族性。當這一切發生時,我們與之抗衡的便是一個巨大且永恒的困境。當他們的主體或是民族性不能被完全地同化時,便會留下造成政權虛弱和危險的永恒原因。[17](P.46)
在他看來,無機國家充滿危機,羅馬帝國、西班牙帝國、葡萄牙帝國的瓦解即是明證,因此英屬印度不僅難以成為“更大的不列顛”一部分,而且其未來的命運也不太樂觀。西利認為原本各自為政的印度次大陸終究會在英國人的統治下生成共同意識,結成統一聯盟。與此同時,在俄國崛起后,來自北方的威脅變得更為緊迫,再加上歐洲政治格局日趨不明朗,英帝國的注意力與資源勢必向西轉移。那么雖然從目前來看,維系英屬印度仍有希望,但在內外局勢惡化的情形之下,英帝國在當地的權勢必將瓦解。(19)西利將《英格蘭的擴張》一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更大的不列顛”;第二部分討論“印度”。從這樣的編排上能夠看出西利對兩者的不同態度。他對印度的討論可參見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883, pp.163- 292。另外,為了吸引更多讀者,強調建設“更大的不列顛”的重要性,之后西利推出了《英格蘭的擴張》的節選本。節選本刪去了印度部分。參見J. R. Seeley, Our Colonial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1887。在他看來,英帝國的未來命運系于白人移居殖民地與母國的統一,印度因終將失去而不再重要。
總之,基于英格蘭國家成長史的敘述,英帝國的邊界與內涵得以明晰。西利認為未來的英帝國將主要由不列顛島、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白人移居殖民地組成,印度及其他依附殖民地(dependent colony)終將脫離帝國。在此視角下,英帝國被塑造成了統一的、由盎格魯-薩克遜人組成的民族國家。
三、西利的英帝國史研究與聯邦制設想
西利的國家觀念貫徹在英帝國史研究中。他從有機國家的論斷出發,建構出統一的、民族性的“世界國家”圖景。同時,他認為這一“世界國家”也能夠實踐民主的治理原則。在傳統政治理論中,國家規模與自由、民主相關,廣土眾民的大國與專制統治間有著“天然”的親和關系。(20)參見羅伯特·A·達爾、羅伯特·R·塔夫特《規模與民主》,唐皇鳳、劉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如前述愛德華·弗里曼所言,統一的帝國與英國人珍視的自由民主傳統相抵牾,原因就在于國家規模擴大后,專制成為了必然選擇。但是西利認為時下制度實踐的創新使得小國民主、大國專制的對應關系不再理所當然。有機的英帝國或“更大的不列顛”自然也能是民主大國。而該制度創新便是代議制及聯邦制的運用。
在《英格蘭的擴張》中,美國始終扮演關鍵性角色,一方面它是不列顛第一帝國與第二帝國的交界,是整條歷史敘事的轉折;另一方面它是英帝國統一構想的榜樣。在西利看來,代議制及聯邦制在美國卓有成效的實踐預示著英帝國也將在此架構下建設自由和民主的國家。(21)關于美國的形象對于19世紀后期英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參見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32-258。在論述當中,他頻頻提及美國得以自由、繁榮的原因,并號召熱衷帝國問題的人士多學習美國的成功經驗。[17](PP.155-159)如其所言,“在本世紀末,美國巨大的人口數量將廣布于四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而這預示著“自由的體制能夠與領土的無限擴張相結合”。[17](P.300)因此,龐大的英帝國是有機國家,其合理的政治架構應當是聯邦制與代議制。這一觀點同樣是西利國家觀念中的重要部分。
在《政治科學導論》中,西利除了闡釋有機與無機國家的概念和發展規律外,還對國家結構形式做出了解釋,點明了聯邦制是適合時下大型有機國家的制度。首先,他認為古典政治理論是從古代國家的歷史中得出,其突顯了小國與大國間的根本性分別。例如亞里士多德認為凡符合政治原理及組織良善的國家皆為小國,大國必然專制,并且是不正常國家。但是古代的城邦并不會遇到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問題,而現代國家則必須要處理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分配。在此基礎上,西利與定義國家概念時的態度一樣,拋棄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論,認為他在處理現代國家問題時已不合時宜。其次,西利認為現代國家跨越城邦限制,從“城市國家”(city-state)邁向了“地域國家”(country-state),所以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皆是整合的產物,它們必然會遇到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難題。分權,抑或集權關乎政治共同體的命運。[15](PP.89-100)進而言之,西利認為城市國家的結構形式應被淘汰,而過于松散的邦聯又很難成為正常國家,不符合有機國家的生存需求。所以最后西利提出,唯有聯邦制才能在廣土眾民的情形下,較好地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不至于使英帝國走向專制。
西利指出美國的歷史為聯邦制的成功實踐提供了絕好范例,但這不意味著“共和制度與我所定義的聯邦主義之間有著必要聯系”[15](P.99),聯邦制同樣可以在帝國中實踐。由于帝國權力具有多重性,所以聯邦制一方面能夠賦予中央統合政治體的能力,使其不至于變為邦聯,失去整合地方權力的機會,另一方面又能兼顧地方自治權,避免了像中央集權制國家一樣扼殺地方活力。盡管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曾認為遠隔重洋的境況扼殺了英帝國實行聯邦制的可能,但該觀點建立在18世紀歷史境況的基礎上,隨著時代發展與技術進步,類似的擔憂已不合時宜。西利已經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英格蘭的擴張》最后一講里寫道: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國家建設的進程受到了空間條件的嚴格制約。在很長一段時期中,除非是小國,否則國家很難具有高效的組織形式。……如今我們能夠看到一些國家統轄著二十萬平方英里的土地,有著三千萬人口,并且在政治意識上還極富活力。進一步的發展如今正在開始。聯邦制被添加到了代議制系統當中,同時蒸汽機與電力技術也被引入其中。這些改進使得規模巨大的國家能夠高度有機的整合。[17](PP.299-300)
總之,通過他的歷史書寫,未來的英帝國被賦予了一個聯邦制民族國家的形象。他認為英格蘭擴張至英帝國的過程不僅僅是領土的擴大,而且也是民族的擴散,所以說英帝國是一個民族國家,符合有機國家的標準。同時,英帝國的聯邦制建設不僅可行,而且必須。
西利對聯邦制的思考早于《英格蘭的擴張》一書的發表。19世紀70年代中,在思考歐洲前途命運時,西利就認為美國的聯邦制是締造和平的模范,而如果要使歐洲成為聯邦,首要的條件是制度、文化、語言、宗教認同的統一化。(22)西利認為歐洲和平有賴于聯邦制,但現如今的歐洲尚不具備條件,種種制度文化間的抵牾阻礙了歐洲聯邦的建立。對此西利并不悲觀,而是寄希望于隨后政治家和民眾的努力。參見J. R. Seeley,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Macmillan’s Magazine, vol.23, 1871, pp.436-448。以此來對照《英格蘭的擴張》就可知,在西利心目中,“更大的不列顛”有著“共同的民族、共同的宗教與共同的利益”[17](P.50),它無疑適用聯邦制。憑借著以上論斷,西利的英帝國史研究與現實政治間產生了密切關聯。
西利始終不是深居象牙塔的學者,而是有著豐富現實關懷的知識分子。他總是強調歷史學與政治相輔相成的關系,比如曾提到“離開政治科學的歷史學難以結出果實,離開歷史學的政治科學則缺失根基”[15](P.4)。同時,他還認為科學的歷史學是引導政治家做出合理決策的關鍵。[15](P.6)西利的英帝國史研究包含了政治意圖,他撰寫英帝國歷史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思考過去,還為了謀劃未來。[17](PP.166-174)“帝國聯邦運動”(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為西利透過英帝國史書寫來彰顯的聯邦制設想提供了施展的機會。
“帝國聯邦”設想的現實指向是鞏固英帝國的措施,而非謀求擴張的戰略。作為術語的“帝國聯邦”于1853年首次出現于威廉·阿瑟(Rev. William Arthur, 1796-1875)的言論中。19世紀70年代后,時人開始醞釀實際計劃。[18](PP.23-25)愛德華·詹金斯(Edward Jenkins, 1838-1910)、威廉·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 1818-1886)、朱利葉斯·福格爾(Julius Vogel, 1835-1899)、弗朗西斯·拉比利爾(Francis Peter Labilliere, 1840-1895)是其中的代表。在支持者的運作下,“帝國聯邦協會”(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在1884年成立,福斯特·羅斯伯里勛爵(Lord Rosebery, 1847-1929)、愛德華·斯坦霍普(Edward Stanhope, 1840-1893)相繼出任過主席[19](PP.155, 298)。
西利的《英格蘭的擴張》突顯了國家統一的愿景與聯邦制的設想,這不僅呼應了這場運動的主旨,也為運動的發展提供了思想資源。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不滿足于渲染帝國成員間的情感聯系,而認為英帝國應將原先松散的形式改為聯邦制,故而專注于聯邦制架構的設計。例如福斯特認為在現代科技發展下,大國建設將會克服時空阻礙,同時殖民地與母國又共享著諸多傳統,且民族構成一致,所以用聯邦制來打造統一的英帝國不僅可行而且必要。[20](PP.21-23)另外,福格爾指出英帝國應該效仿美國、法國,設立一個帝國議會(Imperial Parliament),以作為最高立法機構。[21](P.830)此外,拉比利爾強調在英帝國統一化中,民族情感很重要,但面對現實時,它還遠遠不夠,因此建設有形的聯邦制度是必然的出路。[22](PP.190-191)
西利的英帝國史研究滋養了“帝國聯邦運動”,他本人也親身參與其中。1884年“帝國聯邦協會”成立。同年11月18日,協會召開了首次大會。西利被選為協會委員會的委員,并且還兼任協會劍橋分會的主席職務。[23](PP.31-32)劍橋分會得到了劍橋大學的大力支持,分會參與者來自三一學院、岡維爾與凱斯學院、西德尼·蘇塞克斯學院等,其中包括了13名教授與81名學院議事會(academic senate)成員。西利雖然身為主席,但由于身體欠佳,其組織者的身份并不突出。(23)參見David Kerstein, “Greater Brita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Victorian Idea, 1865-1939”,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pp.167-168。 關于西利晚年身體欠佳的情況參見G. W. Prothero, “Memory”, in J. R. Seeley, The Growth of British Policy Vol.Ⅰ, p.xvii。盡管如此,西利仍參與了多次活動,1885年10月6日,西利主持召開劍橋分會第一次會議,喬治·普羅瑟羅(George W. Prothero, 1837-1923)和弗里德里克·揚(Frederick Young, 1817-1913)出席了會議,討論的主題是殖民地的認同感。另外,普羅瑟羅等人也談及建立聯邦制的具體舉措。隨后,1887年3月10日、1888年2月1日及5月21日、1889年11月18日、1892年5月5日及5月19日,以及倫敦“帝國聯邦協會”解體后的1894年4月26日及5月3日,西利都以主持者的身份召集劍橋分會成員討論聯邦制建設中的問題。(24)西利的相關行跡參見Imperial Federation,vol.2, p.81; Imperial Federation, vol.3, 1888, pp.56, 118; Imperial Federation, vol.5, 1890, p.28. 又可見The Cambridge Review, vol.6, 1885, pp.379-380; The Cambridge Review, vol.13, 1892, pp.283, 312; The Cambridge Review, vol.15, 1894, pp.283, 299。除了主持劍橋分會外,西利還涉足“帝國聯邦協會”的其他事務,比如曾致信協會,闡述自身對建設英帝國聯邦的看法。他認為協會應當專門成立一個委員會,用以普及聯邦制的理念。[24](P.19)同時,他也在協會官方雜志《帝國聯邦》(ImperialFederation)上刊發文章。(25)在文章中,西利指出當下建立協會、創辦雜志的行動都是為了下一步的制度實踐做準備,唯有在理智上做好充分準備,未來的帝國聯邦才能是好的聯邦。另外,他還談及了帝國防衛與移民事宜,具體內容參見J. R. Seeley, “The Journal of the League”, Imperial Federation, vol.1, 1886, p.5; J. R. Seeley, “The Objects to be gained by the Federation of Empire”, Imperial Federation, vol.1, pp.205-206。另外,1887年3月31日,西利參加了協會第二次年度會議(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會上,西利表達了自己的看法,發言內容涉及協會雜志的發展,以及籌集資金等事項。[19](P.198)
總之,西利將國家觀念貫徹于英帝國史研究當中,認為英帝國是具有“世界國家”規模的民族國家。這一前所未有的國家適合實行聯邦制,也唯有以聯邦制來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英帝國才能維持有機國家的形態。由此,西利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投入到19世紀末加強英帝國團結的運動當中。他所提供的英帝國史敘事也溢出學界,成為了政治行動的資源。然而,不久以后,政治行動的受挫反過來也限制了西利的歷史書寫在帝國史研究領域中的活力。簡而言之,西利的后學并未在英帝國史研究領域中完全貫徹西利的國家觀念。
19世紀的最后幾年,在組織內部路線不一、財政困難、殖民地意愿不強與政策落實難度太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國本土的“帝國聯邦協會”最終解散,“帝國聯邦運動”終告瓦解。[19](PP.312-324)在失去政治行動的支撐后,西利的英帝國史敘事也迅速遭到質疑,批駁的對象即是統一民族國家的構想。作為英國第一位正式的帝國史教授,(26)1905年“拜特殖民史教授席位”(Beit Professorship of Colonial History)在牛津大學設立,這是全英國首個專供殖民帝國史教學與研究的教席,艾格頓是該教席首任教授。相關情況參見Amanda Behm, Imperial History an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Exclusion: Britain, 1880-1940, pp.117-123。休·愛德華·艾格頓(Hugh Edward Egerton, 1855-1927)在他的成名作《英國殖民政策簡史》里寫道:
在時間充裕的情況下,帝國內各散亂部分被整合為一個更加統一的聯合體是很有可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這絕不意味著,該聯合體要像原先所強調的那樣,采用聯邦制的形式。[25](PP.511-512)
隨后,其他致力于英帝國史研究的學者,例如查爾斯·盧卡斯(Charles P. Lucas, 1853-1931)和阿瑟·牛頓(Arthur P. Newton, 1873-1942)同樣懷疑聯邦制的可行性。(27)盧卡斯原為殖民部官員,卸任后以英帝國史研究作為工作重心,撰寫并主編了多部英帝國史論著,1929年他為《劍橋英帝國史》撰寫了“導言”。相關情況參見Ashley Jackson, “Sir Charles Lucas and The Empire at War”, The Round Table, vol.103, no.2, 2014, pp.166-168; C. P. Lucas, “Introduction”, in J. Holland Rose, A. P. Newton and E. A. Benian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Ⅰ,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p.1-21。1919年,“羅德斯帝國史教席”(Rhodes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History)在倫敦國王學院設立,牛頓是該教席首任教授,參見Richard Drayton, “Imperial History and the Human Futur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74, no.1, 2012, pp.164-165。可以說,盡管他們表示自己是沿著西利開辟的道路前進,(28)艾格頓在牛津大學里講授英帝國史時指出,自己的研究建立在西利的工作基礎上;牛頓在就任倫敦大學羅德斯帝國史教授的就職演講里也提到了西利的貢獻。參見H. E. Egerton, On some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of Imperial History, London: Sifton, Pread & Co., 1911, p.4; A. P. Newt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lonial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19, p.13。在其英帝國史敘事中,西利所強調的民族性因素得到了保留,但其聯邦制民族國家的政治想象則被放棄。(29)相關言論可參見C. P. Lucas, 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2, p.173; Arthur Percival Newton, The Old Empire and the New, New York: Macmillan, 1919, pp.139-140。兩人均不認為變動帝國憲政體制,例如建設帝國聯邦的方案具有可行性,相關討論參見J. G. Greenlee, “Imperial Studies and the Unity of the Empire”,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7, no.3, 1979, p.322。面對現實局勢的變化,這些學者不再像西利那樣,透過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看待英帝國,而這也恰好體現了與英帝國政治密切互動的英帝國史研究所具有的多變性。(30)阿西娜·賽利亞圖指出自英帝國史研究成為一個專門領域開始,英國及英帝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化就是它發展的重要語境,因此英帝國史研究不斷地改變著敘事模式、主題和政治內涵。詳見阿西娜·賽利亞圖《民族的、帝國的、殖民的和政治的:英帝國史及其流裔》,徐波譯,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10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4-50頁。
四、余論
在“有機國家論”的影響下,西利透過民族國家的視角重新思考了英帝國,同時借助聯邦制的設想,未來的英帝國被想象為統一的民族國家。在歷史敘事中,西利把英帝國的疆域一分為二,再三強調血緣、語言、制度、信仰等因素的共同性,因而將國家未來的希望寄托于母國與幾個移民殖民地的緊密團結上。西利的論述與時代氛圍相呼應,在大國崛起與帝國競爭的時代里,英帝國向何處去,怎樣調整自身來應對時局是時人關注的問題,因此西利的思考引發了眾人熱議,(31)西利的《英格蘭的擴張》在1919年賣出了11000本,在1931年賣出了3000本,相關情況參見A. P.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London: Macmillan, 1985, p.51。并鼓勵了以聯邦制來強化帝國團結的行動與構想。
西利將英帝國塑造為民族國家,其前提是承認美國與俄國的崛起,以及它們對英帝國權勢地位的挑戰,[17](P.16)可見這一做法是危機時代的反映。具體而言,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動促使西利重新定義英帝國,廓清帝國邊界。在論述中,英帝國雖然仍舊占據領導者地位,但已只是大國之一,以民族性為標準勾畫出來的清晰帝國版圖抑制了普遍主義的帝國理念。《英格蘭的擴張》內“天定命運”與“文明教化”不是編織歷史敘事的主軸,取而代之的是現實主義的國家競爭歷程。克里尚·庫馬爾(Krishan Kumar, 1942- )認為對帝國來說,抑制或超越民族性,而非強調民族性,才是生命力的表現。“在統治者開始強化自身民族身份的同時,無論作為土耳其人、奧地利人、俄羅斯人、英格蘭人還是法蘭西人,都是帝國衰亡的開端。”[26](P.Ⅷ)
帝國與民族國家是不同的政治實體,具有不同的治理方式與原則。西利的英帝國史研究將帝國置于民族國家的框架當中,試圖為兩者的結合尋求歷史根據。但其在回應危機挑戰時,自身也陷入了矛盾當中。他輕視英屬印度及其他依附殖民地,并在歷史書寫中扼制普遍主義意識形態的做法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熱潮中的進取精神并非若合符節。(32)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帝國競爭除了體現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外,還體現在文化領域。歐洲帝國間的爭霸推進了文化宣傳戰。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借助各種輿論工具來闡述英帝國之于人類命運的價值,強調自身的普遍主義理想。在此基礎上,更被廣泛傳播的英帝國形象不是民族國家,而是文明本身。參見John M. Mackenzie, Propaganda and Empi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在英帝國史研究領域,20世紀初的學者也以“十字軍精神”代替西利式的現實主義觀念,將“福音主義”色彩的文明觀融入歷史書寫當中,參見J. G. Greenlee, “ ‘A Succession of Seeley’: The ‘Old School’ Re-examined”, pp.270-273。同時,西利從民族國家視角出發的思考也恰好與殖民地內民族主義活動的迭起相沖突。(33)理查德·吉布(Richard Jebb, 1874-1953)較早地關注到殖民地民族主義,并在此基礎上構思加強英帝國團結的方案。他不認同帝國聯邦制的設想,對約瑟夫·張伯倫多有批評,參見Richard Jebb, Studies in Colonial Nation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5, pp.7-10。這都是受其影響的“帝國聯邦運動”未能收獲成果的重要原因。總之,西利以民族國家視角看待英帝國的做法,在英帝國史的學理層面和英帝國建設的現實層面都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因而體現了整合帝國與民族國家的困難。但這并不意味著西利的英帝國史研究不再有討論的必要。
在歷經世界大戰、非殖民化運動后,西利打造民族國家式英帝國的設想早已不合時宜,其英帝國史研究也逐漸被冷落。(34)比如閱讀西利論著的興趣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后難以為繼。參見Duncan Bell, Reordering the World: Essays on Liberalism and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65。但是它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始終潛藏在隨后的思想運動和政策方針中。雖然建構統一帝國的話語不再為人提及,但《英格蘭的擴張》中涉及帝國成員間種種紐帶的論述,自該書問世以來即被諸多地緣政治構想頻繁利用,比如阿爾弗雷德·米爾納(Alfred Milner, 1854-1925)及其追隨者的“圓桌運動”(The Round Table Movement);溫斯頓·丘吉爾的“英語民族”的概念;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 1912-1998)的演說中皆或明或暗地浮現出西利言論的影子。在他們看來,英語民族及其國家的友好、同盟理所當然,意義具有自明性。另外,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頗具市場的“盎格魯文化圈”(Anglosphere)構想也在重溫著西利的思考。這一構想指出英語國家,尤其是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美國同文同種,共享著自由市場經濟、普通法、議會民主制、清教主義等因素,因此能團結一致。在此影響下,撒切爾設想著加強英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美國的聯系,以組成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西方集團;歷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guest, 1917-2015)則提議建立 “盎格魯-大洋政治聯盟”(Anglos-Oceanic Political Association);而“五眼情報共享體系”(Five Eyes Intelligence Sharing System)及“CANZUK”(加、澳、英、新四國組織)的計劃則試圖將“盎格魯文化圈”實體化。(35)關于“盎格魯文化圈”的理論脈絡與實踐參見Michael Kenny and Nick Pearce, Shadows of Empire: The Anglosphere in British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2018。可見西利的國家觀念及其英帝國史研究被選擇性利用,并依舊存活在輿論空間當中。在思考現今世界格局時,我們仍需回顧西利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