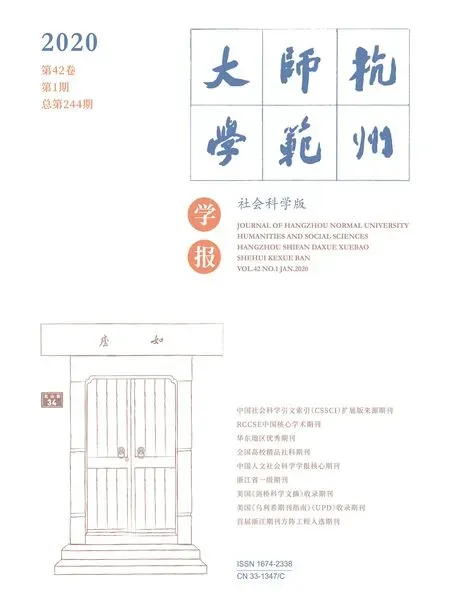杜威的浙江之行及其教育影響
仲玉英,顏士鵬
(杭州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約翰·杜威(John Dewey)是美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教育家,他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不僅深深地影響了美國本土教育的變革和發展,而且對世界各國特別是中國的教育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1919年4月,杜威在其學生陶行知、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倡議下,接受了中國數個教育團體的集體邀請訪問中國,歷時兩年零兩個月。期間,杜威應浙江教育會的邀請先后兩次到訪浙江,并在浙江杭州和嘉興進行了數場講演,對浙江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目前學術界對杜威的中國之行及其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關注較多,對杜威在中國某個地區的旅行、講演及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擬參照當時報刊的報導,結合杜威浙江演講錄以及《經亨頤日記》《陳范予日記》等著作的原始記錄,對杜威兩次浙江之行的過程進行梳理和考訂,并從區域研究的視角探討其教育影響。
一、杜威的第一次浙江之行(1919年5月5日至5月11日)
杜威第一次浙江之行的時間是1919年5月5日,是杜威到上海后的第6天。杜威之所以在赴南京和北京之前先到浙江杭州,與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對新教育的推崇、浙籍杜威學生蔣夢麟的牽線以及江蘇省教育會的帶動相關,同時又得臨近上海的地域便利,占了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一)浙江教育會是杜威來華的邀請團體之一
杜威在訪日期間收到了來自中國的邀請,但究竟有哪些團體邀請杜威訪華,文獻記載不一。據1919年5月29日的《晨報》和1919年6月《教育潮》的報道,浙江教育會就是邀請團體之一。《教育潮》的報道稱,“我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暨江浙兩省教育會,特電請其來華講演”。[1](P.75)
浙江教育會是從江蘇教育會處得到杜威出訪消息的。杜威來華前夕,江蘇教育會特致函浙江教育會,提議兩會聯合邀請杜威。對此,浙江教育會“深所贊同,愿行附驥”,并擬派時任浙江教育會會長的經亨頤為代表赴滬歡迎。[2](P.106) 早在杜威訪華之前,江浙兩省教育會就已經展開了合作,并計劃成立江浙教育會協進會,“共同研究教育之問題,交換教育之意見” [3](P.10)。 杜威來華期間兩省教育會聯系緊密。
1919年4月30日下午,杜威一行抵達上海。北京大學代表胡適、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代表陶行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蔣夢麟到碼頭迎接,浙江省教育會代表經亨頤因為杜威一行到上海的日期不定未能及時趕赴上海,故未出現在迎接人群中。[4](第3版) 5月1日,經亨頤通過閱讀《申報》得知杜威一行已經抵達上海,便于次日一早乘早車赴滬,先到西門江蘇省教育會會晤胡適,后同往蔣夢麟處,與杜威及其夫人握手相見。5月3日,經亨頤前往江蘇省教育會聆聽杜威的演講。嗣后,先行返回杭州。[5](PP.162-163)
(二)杜威來浙由蔣夢麟陪同
1919年5月5日,杜威及其夫人由蔣夢麟陪同來到杭州,經亨頤約同美國傳教士鮑乃德(1)鮑乃德(1888-1970),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清宣統二年(1910年)來華創辦杭州基督教青年會,居杭州岳王路8號。杜威來華期間鮑在杭州傳教。一起前往城站迎接,帶其入住新新飯店。杜威此次來浙與蔣夢麟頗有關系。蔣夢麟本是浙江余姚縣人,曾先后就讀于紹興中西學堂、浙江高等學堂、上海南洋公學。他1908年暑期赴美留學,1912年從加州大學教育學系畢業,后前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繼續自己的學業,與胡適一起,成為杜威的受業弟子。1917年,蔣夢麟學成回國,由時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的黃炎培介紹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同時兼任江蘇教育會理事。1918年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專職總書記職務,后出任由“中華新教育共進社”創辦的《新教育》雜志的主編。在杜威訪華前夕,蔣夢麟在《新教育》雜志第1卷第3期上專設“杜威號”,專門刊登杜威的文章,為杜威來華造勢。他自己則從倫理道德問題出發闡釋杜威的實用主義,發表了《杜威之人生哲學》《杜威之倫理道德》《杜威之道德教育》等文章。作為江蘇省教育會理事,同時又是浙江籍的杜威學生,蔣夢麟為杜威來浙做了許多前期聯絡工作,后又一路陪同,充當翻譯。5月5日和5月6日,蔣夢麟居住在經亨頤處,協同浙江教育會接待杜威,7日上午因北京大學的事趕回上海。
(三)演講的聽眾“不下二千人”
杜威的演講排在5月7日。5月6日晚,經亨頤在浙江教育會宴請杜威及其夫人,后一起前往鳳舞臺(今延安路南段)觀劇。5月7日下午3時,杜威在浙江省教育會(今平海路)發表演講。前來聆聽演講的人數非常多,據《經亨頤日記》記載,“到者不下二千人”。[5](P.164)另據《新聞報》報道,各學校教職員學生有千數百人,“樓上樓下幾無隙地”,由安定中學童子軍植立會場門口及四周維持秩序,省會警察二區也派警察2名在門口幫助維持秩序。[6](第2版)杜威本次演講由鄭宗海擔任口譯,朱毓魁記錄。鄭宗海又名鄭曉滄,浙江海寧人。1914年赴美留學,1918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教育碩士學位,杜威訪華時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科任教。杜威在蘇、杭一帶演講,鄭曉滄都以學生身份陪侍左右并充當翻譯。朱毓魁(朱文叔)則是浙江嘉興人,1912年就讀于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17年畢業后服務于浙江省立女子師范學校附屬小學,兼任浙江省教育會臨時干事。他在1930年回憶當年做記錄的情形時說:“杜威到杭州來演講的時候,由鄭曉滄先生做翻譯,我坐在講壇旁邊,一手拿著筆寫。寫了一段,演講間歇的時候,抬頭望著他們倆,一長一短,站在講壇上。這很有趣味的對照,到現在還深深映在我的腦中呢。”[7](P.69)
(四)演講主題為《平民教育之真諦》
杜威本次演講的題目是《平民教育之真諦》。杜威認為,歐美普及教育的發達,距今不過百年內之事,中國素有師道尊嚴的傳統,社會對教育界人士頗有信仰,中國應對普及教育有信心。他強調共和國家的教育必須破除門閥主義,注重平民教育。其教育宗旨“在使人人有被教育之機會,其方法則在尊重個性”。所以,“教育之良否,不因其學科之多寡,授課時間之久暫,教材分量之重輕以判,而視其能藉學科以養成生徒之判斷力,自覺力,應用力,使于未來能適應社會狀況,而善營其生活與否為斷”[8](PP.27-34)。短短的兩小時演講,表達了他平民教育的核心思想。
5月8日,杜威夫人在浙江省教育會講演了“女子教育之新義”,由張天祚翻譯,朱毓魁筆錄。杜威夫人著重闡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認為“社會國家之組織,必不能離女子而成立,無女子則無所謂種族,又安有社會國家。環球各地,不問其為都會,為市鎮,為村落,為荒僻之區,茍為人類所居,即不能屏棄女子,故吾人必不能舍女子而言教育”,“欲圖人群之進化,國家之強盛,必使國民皆得遂其發育,斷勿置女子于度外” 。同時強調欲振興女子教育“非女子自己努力不為功” 。[9](PP.35-37)杜威夫人的演講是杜威來華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題也屬于杜威平民教育思想的范疇。
5月9日,經亨頤在浙江教育會與各校職對杜威講演開談話會,討論聽講心得。5月10日,經亨頤于家中宴請杜威夫婦和鮑乃德夫婦,下午,同至清河坊等處游覽,并在西泠印社攝影留念。次日,經亨頤前往杭州城站送別杜威夫婦。[5](P.165)
從5月5日到5月11日,杜威第一次來浙雖然只有一次演講,但在浙江的影響面非常大。浙江教育會提前預備聽講券千余張,分送杭垣中等以上各學校教員學生,另由勸學所轉送各地方小學校教員,所以聽眾多且分布較廣。
二、杜威的第二次浙江之行(1920年6月10日至6月14日)
從1919年6月至1920年的4月,杜威作為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足跡主要在北京。1920年4月,由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暨南學校、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聯合成立的“中華新教育共進社”公請杜威南下講演,時間為4月1日至6月30日。浙江就是杜威此次南下行程中的一站。5月,浙江教育會致函中華新教育共進社,討論杜威來杭日期、旅費、食宿等問題,為杜威第二次來浙做準備。[10](第2版)
(一)在浙江嘉興的演講(6月10日)
根據行程,杜威南下巡回演講的第一站是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以及江蘇省內部分城市,第二站是上海,第三站是杭州,然后再回到江蘇。在從上海到杭州的途中,杜威還應嘉興、海寧兩縣教育會的邀請,在嘉興作了第二次浙江之行的首次演講。
1920年6月10日上午10時30分,杜威偕夫人及其女兒乘車到達嘉興,同來者還有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鄭宗海以及杭州派赴上海迎接杜威的兩位代表。嘉興秀州中學校長竇維斯(2)竇維斯,美國傳教士,也是杜威學生,教育理論上信奉杜威的從做中學和生活化教育。參見朱尚剛《詩侶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年,第18頁。、嘉興二中校長計宗型(計仰先)到車站迎接。下午一時杜威等人至公共運動場講演廳,“其時聽講者已有三千余人,杜氏入場全體鼓掌歡迎”。[11](第2版)隨后,杜氏講演“小學教育的新趨勢”,由鄭宗海口譯,奚銘癸記錄。杜威講到教育的新趨勢是注重普及教育,也就是擴充小學,培養有自主教育精神的小學教員,打破教育為少部分人服務的傾向,發展為大部分人服務的事業。同時,改變被動的教育理念,通過游戲、手工和自然應用的教學方式,發揮兒童的本能和個性,增進兒童的興趣,調動兒童的學習自動力,以培養兒童的創造力。[12](PP.1-4) 杜氏講演結束后休息了20分鐘,繼而由其夫人講演“女子教育問題”,仍有鄭宗海口譯,主題思想與前次在浙江省教育會的講演一致,即強調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她談到“有多數人之主張不愿女子受高等教育,其理由謂經濟不足,難以供給,殊不知人民所負捐稅,男女固同輸也;社會上種種事業,男女固同服務也,何以教育男女竟不能享同利之幸福,然徵諸社會之須要趨勢而觀,則此項主張已不適用,故今日女子有此機會不能不積極奮圖,以彌補缺陷。”[11](第2版)杜威夫人的講演持續了一個小時有余。隨后,杜威一行便動身前往火車站,乘坐下午五時二十分的特快火車赴杭。杜威在嘉興的演講,雖然聽眾多,但時間短,又發生在路途中,不易被今天研究者關注。
(二)在浙江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演講(6月11日)
6月10日下午晚時,杜威一行到杭。省教育會代表阮荀伯、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姜琦(姜伯韓)、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教師壽毅成等到站歡迎,并帶杜威一行寄寓清泰第二旅館。6月11日上午,杜威一行由楊俊夫帶領游葛嶺、玉泉、靈隱、紫云洞各景點。[13](第7版)下午六時,杜威在馬坡巷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大講堂做了“社會問題之研究”演講,由鄭宗海口譯,黃維時記錄,法政專門學校的校長張羽生、教務長周智荷等諸位教員、全體學生到會聽講。杜威談到,社會問題是當時世界各國極其關注的問題,但與西方在漫長的時間里解決了政治、經濟等問題,唯余社會問題不同,中國四千年來所積累的宗教、文學、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問題至為復雜,在短時間內一齊解決非常不易。他強調中國要研究解決社會問題當用重證據、重觀察、重事實的科學方法。[14](PP.1-5)
(三)在浙江教育會的演講(6月12日)
1920年6月12日上午,浙江教育會借律師公會歡迎杜威,出席歡迎會的各校校長及學務人員約有六十余人。先由阮荀伯致歡迎詞,而后由教職員聯合會提出四項問題與杜威討論,至十二時結束,并攝影留念。[15](第2版)下午四時,杜威在青年會屋頂花園講演“德謨克拉西真義”,由鄭曉滄翻譯,朱學鋤筆記。聽眾“至三時已坐滿難容,后至者竟無立足之地”[16](第8版)。杜威在講演中強調德謨克拉西主義真義,就如林肯所講的,是一種政治,是一種“為民的”“由民的”“被民的”政治。包含了三種要素,即德謨克拉西目的是專為人民的幸福,不是為私人的一部分的幸福;是“處處以民意為重”的;這個政治的組織是從人民中選出的代議士所組織的。[17](第1-2版)
(四)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演講(6月13日至14日)
1920年6月13日上午8點,杜威在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禮堂講演“德謨克拉西的社會分子應有的性質”。此演講主要談在德謨克拉西社會里所需要的態度,同時說明“怎樣才能實現學校生活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杜威提出要注意三件事。第一是虛心,在各方面有可以得到一種知識或技能的地方,總得想法子去學習。德謨克拉西反對成見、藐視和自是之見,注重相互了解和協力合作。第二是有目的,德謨克拉西的社會做事要有明確的目標、有秩序的計劃和標準。第三是責任心,在人格上養成一種堅定不拔的精神,不論前途有什么艱難困苦,都要竭力擔當社會責任。[18](第6-7版)
晚上7點,杜威在禮堂又作了題為“造就發動的性質的教育”的演講。他借用中國某位教育家的說法,中國的教育在道德和理知方面偏向忍耐刻苦等“被動的性行”,認為這種性行已“無足深取”,應倡導理知上的見解精明、有獨創力和道德行為上的協力合作,學習西方的創造精神和科學精神,即造就發動的性質的教育。針對師范學校的特點,杜威將演講的重心放在了怎樣去發動小學兒童“有精力的、有生氣的精神”。他認為其方法有三:第一種是注重游戲運動,因為游戲運動能夠使一個被動的、靜穆的、無生氣的人,一變而為活動的、有生氣的、有用于社會的人;第二種是注重手的活動,手工的最大功用是造就發動能力,給我們以表現思想的機會;第三種是打破被動性質的書本教授,注重天然物象的觀察和實驗。他主張如果能夠切實地奉行這幾種方法,變化社會,改造社會,都易如反掌。[19](PP.1-5)
1920年6月14日上午7時,杜威又應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友會所請,在西湖鳳舞臺講“科學與人生之關系”。前來聽講者者一千多人。[20](第7版)他認為科學可以改良人生,其方法是改良觀念,使人類自省能力勿使其處于被動力。強調科學非由物質而來,乃溯源于精神方法之狀態和理想方面之元素。科學者的求真實之心,求真理的勇氣、耐心和犧牲都是精神的元素。此次演講還涉及“社會”的主題,雖然杜威主張的是通過教育改良社會的方法,但還是希望學生能保持社會主義熱忱,同時實在地擔負起應用科學為民眾謀福利的責任。[21](PP.8-12)
杜威在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演講均由鄭宗海翻譯,“男女各校生齊集聽講,無容膝地”。14日午后,杜威再應女子職業學校邀請,到西湖昭慶寺演講,當日夜車返滬。[22](第7版)
從6月10日至6月14日,杜威的第二次浙江之行才4天,但是演講的場次卻多達7次。與一年前只有一場演講比較,杜威本次來浙演講內容更豐富,更有針對性,聽眾的互動和反饋也更強。杜威第一次來浙,浙江聽眾對這位“白發短須,氣色勝人”的“大哲學家、大教育家”很感興趣,但由于對杜威思想事先知之不深,又是第一次面對面地聆聽杜威的講演,師生聽后不免來不及消化和思考,所以曾出現各校職討論杜威講演心得時,“未有如何誠得(心)”的情況[5](P.165),學生聽后也覺“至于理之奧處則未能達矣”[23](P.86)。但是,杜威第二次浙江之行情況就不同了。一方面,經過一年的宣傳,浙江聽眾對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已經較為熟悉;另一方面,杜威本人也是有備而來。杜威在嘉興演講的開頭談到,浙江是文化運動有名的地方,小學教育很擴充,很進步。他的演講贏得了嘉興三千多聽眾的熱烈掌聲。他在浙江教育會與各校校長及學務人員討論教育問題時,雙方“討論良久至十二時”,可見互動的成效。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面對青年學生演講時,直言欽仰浙江青年學生的一腔熱血和愛國憂時精神,非常羨慕學生界改造社會的志愿。他選擇“德謨克拉西真義”“德謨克拉西的社會分子應有的性質”“科學與人生之關系”等主題進行演講也都是切合學生需要的,說明他對浙江的新文化運動比較了解。
三、杜威來浙對浙江教育的影響
杜威來浙講學引起了浙江教育界的高度關注,不僅在教育理論界掀起了“杜威熱”,更是在教育實踐上掀起了教育改革的熱潮。
(一)浙江教育媒體的杜威熱
在杜威來華期間,浙江的教育報刊對杜威及其教育思想進行了大力宣傳,其中最鼎力的是《教育潮》。《教育潮》是浙江省教育會的會刊,前身為《教育周報》。在1919年杜威來浙前后,《教育潮》對杜威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作了持續的宣傳,對杜威來浙來華的動向作了跟蹤的報道。1919年4月,《教育潮》第1卷第1期發布了浙江省教育會《為歡迎杜威博士致江蘇省教育會函》,贊同兩會聯合邀請杜威來華,同時轉載《時事新報》的文章《記杜威博士》,對杜威的生平、教育活動以及來華演講的活動日程做了介紹。杜威到浙江省教育會演講后,《教育潮》第1卷第2期及時刊登了杜威在浙江省教育會的演講錄《平民教育之真諦》以及杜威夫人的演講錄《女子教育之新義》,同時刊布《杜威博士來華講演紀聞》,對杜威5月至6月間在江蘇教育會、浙江教育會、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北京的講演一一作了介紹,還對杜威在江蘇省教育會的演講錄《平民主義的教育》作了轉載。之后的《教育潮》第1卷第3期和第4期,陸續轉載了《每周評論》上的杜威演講錄《現代教育的趨勢》和《國民公報》上的杜威演講錄《學問的新問題》,還刊布了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教師夏丏尊翻譯的《杜威哲學概要》,這是日本帆足理一郎氏為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在日本發行所作的序文。不僅《教育潮》,其他如浙江教育的官方報刊《浙江教育》,地方教育刊物《上虞教育雜志》等也都轉載了杜威的部分講演錄。
(二)對浙江教育界人士的思想影響
伴隨著杜威來華來浙演講以及相應的教育報刊宣傳,浙江教育界人士對杜威教育思想的興趣日益提高。杜威的講演也引發了教育界人士對美國教育的推崇,帶動了浙江教育界從向日本學習轉向向美國學習。以杜威來浙的接待人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經亨頤、姜琦以及嘉興二中校長計宗型為例,三人都是留日學生,與杜威本沒有直接的師承關系,但杜威的來浙對他們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有的甚至追隨到美國,直接拜師門下。
杜威來浙期間,經亨頤一直關注教育發展動向,對杜威的思想抱有積極熱情的態度。他在杜威來華前后發表的關于“動學觀”的文章間接地受惠于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1919年2月,經亨頤在《教育周報》上發表《最新教育之三大主張》一文,稱其“‘三大主張之要義’取自日本及川平治所著《動的教育法》”[24](《最新教育之三大主張》,P.77)。4月,又發表《動學觀與時代之理解》,進一步宣傳及川平治的動的教育學說,并發表自己的見解。[24](《動學觀與時代之理解》,P.91)經亨頤極力宣傳的及川平治(1875—1939)是日本大正、昭和前期的教育家,是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和實踐者,自稱讀了幾乎所有杜威的著作,思想得到了杜威的啟發。[25](PP.87-88)可以說,經亨頤的“動學觀”源頭就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1919年5月2日,經亨頤在上海迎接杜威時,曾經聽過胡適在江蘇教育會的有關實驗主義的演講,認為“實驗主義亦為動學說之一義,可助我心得”,聽了杜威的平民主義之教育的演講后,又感覺“詞意頗幽遠”。[5](PP.162-163)而且,經亨頤還在1920年1月發表的《教育的新禧和時間問題》一文中直接表達了對杜威實驗主義思想的認同,并從此出發,提出了新教育的關鍵不是教育的時間,而是被教育者的“自覺”。[24](《教育的新禧和時間問題》,PP.133-135)
杜威第二次浙江之行的主要接待人姜琦(浙江永嘉人),也曾留學日本明治大學和東京高等師范學堂,1915年回國,任浙江第十師范學校校長。1918年任暨南學校教務主任兼師范科主任,同時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史教授,兼任《新教育》雜志的編輯,1920年4月由蔣夢麟推薦任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姜琦與杜威的淵源與蔣夢麟相關。《新教育》雜志是中華新教育共進社出版,主編就是杜威的學生蔣夢麟。該雜志在“教學法上主張自發自動,強調兒童的需要,擁護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與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張”。[26](PP.117-118)姜琦對西洋教育史有研究,任《新教育》雜志編輯的時候,就曾發表了多篇介紹西洋教育家的文章,還撰寫過《教育史上杜威氏的地位》的文章,把杜威的教育觀點概括為“學校即是社會,功課即是生活”,對杜威教育思想比較熟悉。[27](第9版)。1920年,他還在永嘉新學會會刊《新學報》的“發刊詞”中說,永嘉學派的精義與美國實用主義頗相符合,建議“采取美國實用主義,以藥我永嘉學派之病”,以謀求適應今日的實際生活。[28](PP.20-21)杜威的第二次來浙,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訪問兩天,演講三場,與姜琦對杜威思想的熱衷不無關系。1922年姜琦由教育部選派赴美留學,追隨杜威的腳步,先在芝加哥大學教育學院研究教育,后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院攻讀教育行政和中等教育,投身杜威門下學習。他后來撰寫的《教育哲學》《德育原理》等著作都是繼承了杜威教育思想并有所發展。他在自己著的《現代西洋教育史》的“編者謹識”中說道,杜威和凱興斯坦納是他最敬仰的西洋教育家,是他曾經受教過的兩位先生。[29](插圖頁)
杜威嘉興講演的接待人計宗型(浙江嘉興人),曾留學東京物理學校,1910年回國任教嘉興府中學堂,杜威嘉興演講時任浙江省立第二中學校長。計宗型在杜威回國當年(1921)由浙江省教育廳委派赴美考察教育,在加利福尼亞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行政和教育測量,1923年回國復任二中校長。同年12月,擔任嘉興教育會會長,第二年12月,擔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30](PP.59-60)計宗型在擔任嘉興教育會會長期間,設立嘉興平民教育事務部,自任教育部主任,推廣平民夜校。后發起“新嘉興平民社”,以“喚醒民眾,改進地方事業”為宗旨,大力推進平民教育。[31](第3版)他在擔任浙江教育廳廳長期間,制定浙江省“新學制”試行計劃,積極響應以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為指導,以美國學制為模板的“新學制”改革;成立浙江全省小學基金會,支持地方興辦平民教育,切實實踐杜威的平民教育思想。[32](P.257)而且,計宗型在任廳長期間還對浙江省公派留學的留學國進行了調整,改變原來寬日本而緊歐美的狀況,增加留學歐美人數,特別是留美人數。根據“民國十年至十四年歐美留學生籍貫及所適國別表”,浙江省在此期間留學歐美人數為107人,特別是留學美國的人數為72,占留歐美總人數的67%。[33](P.147)這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浙江教育界從向日本學習轉向向美國學習。
(三)對平民教育的推動
平民教育是杜威在華宣傳的主要思想,也是來浙講演的重要主題。他第一次來浙演講,闡明了平民教育的真諦在于“使人人有被教育之機會”,第二次在嘉興的演講再次申明“教育的新趨勢就是打破了教育為少數人所享的權利”,倡導“謀多數人的福利”的平等教育。
隨著杜威平民主義教育思想的傳播,全國上下掀起了平民教育運動。從設立平民學校,開展平民識字運動,到1925年以后轉向鄉村,發起鄉村教育運動,平民教育風起云涌。浙江教育人士也積極投入到平民教育運動中,尤以杜威所到之處嘉興和杭州最為風行,也最有影響力。
嘉興的平民教育運動是從杜威到訪過的秀州中學開始的,后在計宗型等教育人士的推動下逐漸向全嘉興鋪開。1923年春,秀州中學試辦平民夜校,以《平民千字課本》做教材,用最新“幻燈”教授,使年長失學者入學,頗有成績。接著嘉興縣教育會、商會、農會舉辦平民教育大會,就地推廣秀中經驗。[34](第4版)嘉興的平民教育運動因“創造了新的教學工具——幻燈,新的教學法——群眾教學法”而聞名全國,得到了當時平民教育的發起者晏陽初、朱其慧、陶行知等人的贊賞,其方法也向全國推廣。[35](PP.336-340)
杭州的平民教育的主要方法是利用中學和小學附設平民學校 。1924年,杭縣開辦平民學校77所,教員97人,學生84個班,1668人,其規模位于全國前列。[36](P.167)杭州的平民教育在杜威學生蔣夢麟擔任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后改稱浙江大學)校長期間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主要體現在頒布了系列民眾學校暫行規程,推廣民眾教育事業;建立湘湖師范學校,助力鄉村教育運動。
湘湖師范學校是蔣夢麟在同為杜威學生的陶行知協助下建立的。與曉莊師范一樣,湘師的辦學宗旨是實施鄉村教育,改造鄉村生活,其指導思想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這是陶行知結合中國國情,對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改造。湘師在培養優秀青年教師,提高民眾的文化知識水平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浙江的改革試驗。
(四)對教學改革的助力
伴隨著杜威來華,以尊重個性為主旨的各種教學方法也被介紹到中國,出現了教育改革新氣象。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生楊賢江曾說,杜威來中國到處講本能、興趣、自動、自治,之后在教育上的確發生了許多新的現象,如學生自治、選科制、學分制、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都是發展個性的表現。[37](PP.76-77)1919年,經亨頤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開展的學生自治、改文言為白話、改學年制為學科制等教學改革實驗就是貫徹了當時倡導的“學生本位”思想。[24](《對教育廳查辦員的談話》,P.127)這也是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影響下的浙江教育改革的先聲。
隨后,新教學方法紛至沓來,浙江教育界出現了改革教學方法的熱潮。據1922年的《杭縣教育雜志》描述:“現在的教育,已經從教師方面轉移到兒童方面;從被動的變而為自動的;從抽象的進而為實際的了。從前一切劃一的、呆板的、有規律的……教育,統統像落葉似的向溪里吹去了,從事教育的人們,自己也覺得應該除舊布新,去適應這澎湃浩蕩的潮流,什么啟發呀,輔導呀,自動呀,兒童本位呀……種種的聲浪,應時而起了。”[38](PP.10-11)。
在這些教學方法中,設計教學法和道爾頓制是最為普及的。設計教學法是杜威的得意門生克伯屈創造的。它既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產物,又是普及杜威教育思想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杜威做中學思想的具體化。[39](PP.282-283)而道爾頓制的創始人柏克赫斯特也是“私淑杜威”。道爾頓制強調“給兒童以自由,在團體互動的可能范圍以內使學校成為社會”,與杜威的思想一脈相承。[40](PP.5-7)設計教學法和道爾頓制在浙江的實施面比較廣。據統計, 在1924年11所浙江省立中學的附屬小學中,有7所附屬小學的高級部采用了道爾頓制,有10所附屬小學的初級部采用了設計教學法。其他地方上的縣立小學也紛紛采用新的教學方法。[41](P.255)比如杭縣縣立第五小學校,高級部采用道爾頓制,“每天自八時四十分至十時二十分,系個別研究;十時四十分后是堂課,系團體教授”,“初級部行設計教學法,第一節是談話班,為一日功課的出發點”。[42](P.49)可見新教學方法的盛行。
五、結 語
綜觀杜威的浙江之行,除了間歇的游覽,主要的活動是演講。主題涉及平民教育、德謨克拉西主義、科學與人生、造就發動的性質的教育等。杜威演講的重心是教育問題,主要觀點是通過教育的普及、自動精神的培養及科學的應用,改善人生,改造社會,最終實現民主和共和。這是一種通過實施民主教育,改良社會的思想,整體上符合當時新文化運動倡導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的需要,所以受到了浙江師生的熱烈歡迎和熱切的期待,對浙江教育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也正因為杜威的浙江演講宣傳的是通過應用“科學”為民眾謀福利,通過“試驗法”解決社會問題,通過“造就發動性質的教育”改造中國社會的教育救國方法,因而也遭到了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的質疑和批評。在杜威第二次來浙后的姜琦校長的“修身”課上,學生陳范予向姜校長提出疑問,他說,如果像杜威所說,中國現在必須照西洋百年前的過程進行,那么,“豈不中國跟不上做二十世紀之一國嗎”?[23](P.209)同樣,一師學生曹聚仁在1931年回憶杜威講演時也說:“我們雖是為赫赫的聲望所懾,但大家都批評他,說他只懂得教育,不懂得社會。”[43](P.3)這些質疑也從另一角度說明了杜威的兩次浙江之行,給浙江青年學生帶來的不僅是教育的新理念,也直接促發了浙江青年學生對社會改革問題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