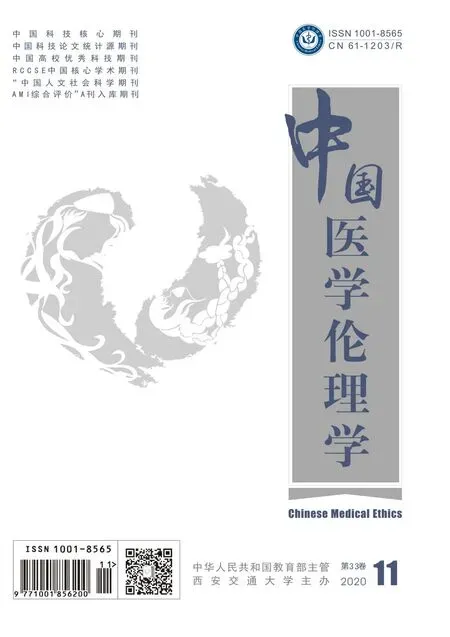傳統(tǒng)文化視域下的道德創(chuàng)傷及修復*
王璐穎,常運立
(海軍軍醫(yī)大學基礎醫(yī)學院,上海 200433,15800610624@163.com)
道德創(chuàng)傷是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下衍生的創(chuàng)傷新概念,是社會的道德現(xiàn)象尤其是反道德行為對個體道德良知造成的創(chuàng)傷。道德創(chuàng)傷雖源于軍事,但也有不可忽視的社會學意義。道德創(chuàng)傷的產(chǎn)生涉及心理、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尤其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文化孕育了道德和倫理準則,個體或集體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下,也許會作出符合該文化情境的倫理選擇,例如殺戮、背叛等,一旦脫離文化情境,回歸日常生活后,一些人可能會面臨難以適從的各種道德沖突和經(jīng)歷。美國近些年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道德創(chuàng)傷的發(fā)生和治愈,美國臨床精神病學家Jonathan Shay從文化學視角探討了道德創(chuàng)傷,提出道德創(chuàng)傷是作戰(zhàn)中“高危情境下法定權威人士對社會公正的背叛”[1]。將文化分析引入道德創(chuàng)傷研究中,進行哲學思辨,是有效認識和修復創(chuàng)傷的可行之道。
1 道德創(chuàng)傷是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
道德存在于一定的文化情境中,體現(xiàn)著文化的價值理想、精神追求和善惡依傍;而對美德的貶損、扭曲、壓抑或背叛往往被作為一種反文化現(xiàn)象為世人所詬病與指責。基于此,道德創(chuàng)傷無疑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
1.1 緣起:文化是道德發(fā)生的土壤
“‘文化’是由‘文’而‘化’構成,通過‘文’的過程,使人發(fā)生變化即提升,從而將人與動物區(qū)分開。而‘化’是一種狀態(tài),又是一個過程,文‘化’的終極目標就是使人從里到外變成一個完全的人;而所謂文‘化’程度,則代表人由‘文’而‘化’的階段和程度,從終極目標說,是接近完全的人的程度,從始點來說,是與動物相區(qū)別的程度。”[2]人自誕生之日起就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不同類型的文化以其獨有的價值觀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規(guī)范,進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說,有多少種文化就存在多少種生活方式。作為一種軟實力,文化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滲透在社會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規(guī)范乃至生活方式。道德以人的完善為根據(jù),規(guī)范著人們的倫理關系。而人是文化的人。由此,道德的發(fā)生不免帶有文化的印記。文化對道德來說,具有內在的、本源的、基礎性的影響。正如麥金泰爾在分析規(guī)范倫理學的弊端時指出,離開人類道德的文化背景去解釋道德,這種解釋就會成為無傳統(tǒng)、無根源的主觀解釋。
1.2 核心:道德創(chuàng)傷實質是對社會文化的背離
丹尼爾·貝爾認為:“文化本身是為人類生命過程提供解釋系統(tǒng),幫助他們對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3]文化的產(chǎn)生是為了人們能渡過生存困境,達到理想的生活狀態(tài)。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蘊幫助和引導人們建構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崇高而神圣的意義世界,使人明確生活、生命的意義,明確個體與社會整體之間的人文關系。文化給人構筑了意義和價值的世界。人們自然而然地運用文化所提供的是非善惡的價值評判標準從道德上判斷自我和他人,常常毫不自覺地按照所篤信的價值觀念為人處世。人的道德本性、價值意識的發(fā)生和建構的現(xiàn)實性全部來自于有意義的文化世界。道德主體的思想和行為更多包含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性和文化制約性,受到同一時代或同一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基于此,道德創(chuàng)傷發(fā)生的核心本質可以看作是個體或群體的道德價值體系與反道德現(xiàn)象所凸顯的價值觀的沖突,進一步來說,其實是外在不良文化對主流文化的背離給個體價值體系帶來的迷茫與困頓。文化是道德創(chuàng)傷發(fā)生的基本依據(jù)。
2 傳統(tǒng)文化視域下的道德認知與創(chuàng)傷
習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shù)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傳統(tǒng)文化以其歷代傳遞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思維方式等時刻在人們的頭腦中起作用,塑造了中國人的心靈和思維方式,給社會大眾提供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真與假等一系列價值評判標準,構成了社會大眾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的文化依據(jù)。當面對反道德行為和事件時,其所蘊含的價值指向在一定程度上與傳統(tǒng)文化所涵蓋的核心價值發(fā)生背離。在這種道德碰撞和沖突的現(xiàn)實境遇下,一切意義和價值所依附的文化根基遭到瓦解和傾覆,容易導致道德創(chuàng)傷的來襲。基于此,認清道德創(chuàng)傷發(fā)生背后的文化境遇是有效診斷和修復道德創(chuàng)傷的重要途徑。
2.1 重義輕利與盲目私利的矛盾造成道德創(chuàng)傷
義利之辨是傳統(tǒng)倫理的基本問題。義利即為道德和利益的問題,“義”指的就是人的立身之本,是非善惡價值判斷的標準。正所謂“君子以義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利”指的就是利益,好處。《尚書·泰誓》:“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義利關系即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它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道德與物質利益誰為第一性;二是社會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誰服從誰的問題。首先,義利關系是道德與人的利益與需要之間的關系。義與利即道德與利益是人們道德價值選擇的兩個根本取向。義利之辨中,義是最高的價值。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若得之有道,則執(zhí)鞭之士亦可為之。”衡量客體對人的價值大小的標準,即它滿足人的需要的程度。而在人的所有需要中,物質利益與需要是低層次的,道德才處于最高的層次。古代的哲人雖然重義輕利,但不完全反對利,認為利是人的生命活動所必需,提出利的獲取要考慮是否符合道義。當義和利相沖突時,要舍利取義;其次,義利問題實質是公私問題。這是從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上來討論以義為標準還是以利為標準。在儒家看來,道德是維護群體、發(fā)揮群體力量的根本保證。群體價值取向必然需要人們把群體的利益置于個人的利益之上。基于此,儒家把義規(guī)定為社會整體利益,把利規(guī)定為個人一己之私利,強調群體價值取向,主張個人利益服從社會利益。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發(fā)生沖突時,主張小我之私服從大我之公,不能為了個人利益不顧甚至危害社會整體利益。
當背離此“道”,就會發(fā)生道德創(chuàng)傷。當前,社會上盲目私利的現(xiàn)象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重義輕利的主流價值發(fā)生沖突,給人們內心蒙上道德創(chuàng)傷的陰影。市場經(jīng)濟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生產(chǎn)經(jīng)營者的直接出發(fā)點和目的,這是支配整個市場運行的根本機制。一般說來,求利是推動整個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根本動力。但這種求利的取向也給一些人助長了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思想和行為,給世人內心帶來了道德沖擊。在一定程度上挑戰(zhàn)了社會的道德底線,引發(fā)了公共信任危機。不可否認,他們的這些行為嚴重腐蝕了社會的核心價值準則,擾亂了基本的道德評價標準。
2.2 戰(zhàn)爭正義與戰(zhàn)爭非正義的沖突造成道德創(chuàng)傷
傳統(tǒng)文化中對于戰(zhàn)爭的性質,是從倫理道德,即正義性的層面上來作出是非善惡判斷的。夏商周時期,多以順天承命的“天授兵權”理念來申明戰(zhàn)爭的正義性。商湯伐夏桀時聲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書·甘誓》)至春秋時期,孔子倡仁戰(zhàn);孫武“仁戰(zhàn)觀”的最高價值理想是“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戰(zhàn)國時期,墨子反對侵略戰(zhàn)爭,吳起以“舉順天人”作為正義戰(zhàn)爭的標準;孫臏主張戰(zhàn)而有“義”;《呂氏春秋》認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秦漢之后,戰(zhàn)爭觀的主導傾向皆是反對外來侵略,以仁義戰(zhàn)爭為基本主張。由此,盡管各家學派對正義和非正義的解讀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崇尚正義戰(zhàn)爭,反對和制止非正義戰(zhàn)爭。正義戰(zhàn)爭包括兩方面內容,即戰(zhàn)爭開戰(zhàn)的正義性與戰(zhàn)爭行為的正義性。一方面,戰(zhàn)爭開戰(zhàn)的正義性問題。開戰(zhàn)的正義性來源于民意和民利,即是否是維護了構成政治實體民眾的根本利益,戰(zhàn)爭是否造成人員的巨大傷亡和物質財富的極大消耗。儒家主張興正義之師、仁人之兵,孫子將“勝敵而益強”作為戰(zhàn)爭正義性的必要維度;另一方面,戰(zhàn)爭行為正義性。戰(zhàn)爭行為正義性所關涉的是在交戰(zhàn)過程中將帥以及士兵的行為是否正當,這體現(xiàn)為:一是平民應該區(qū)別對待,不傷害無辜民眾;二是戰(zhàn)爭中禁止不合軍事目的的武力行為。先秦原典中,荀子有言:“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荀子·議兵》)平民應該區(qū)別對待,不傷害無辜民眾,軍事打擊的目標應是給百姓帶來暴亂的人。
現(xiàn)實中,當戰(zhàn)爭的非正義性行為與戰(zhàn)爭正義的傳統(tǒng)價值發(fā)生背離容易引發(fā)世人的道德創(chuàng)傷。放眼未來,在高技術戰(zhàn)爭的背景下,隨著器物因素的過分凸顯,容易使軍人在武德認知和道德評價上發(fā)生錯覺,如,認為擁有強大武器裝備就可以為所欲為,戰(zhàn)爭的倫理意義要服從狹隘的功利意義,正義要服從非正義……由此,軍人的價值規(guī)范體系和坐標產(chǎn)生非道德主義泛化態(tài)勢,容易引發(fā)道德創(chuàng)傷[4]。
2.3 公正不阿與社會不公的沖突造成道德創(chuàng)傷
傳統(tǒng)文化中對“公正”有著豐富的論述。“公正”首先是指社會資源分配的“均平”。儒家強調社會資源的分配要以禮義為原則,按照禮的等級差序來分配資源。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其次,“公正”是指天下為公的執(zhí)政理念和美德。這就是要求君主和為官者為政以德,秉公辦事,執(zhí)法公平,將天下公利放在第一位。早在西周時期,周公就提出“用中罰”的理論,“中”就是不偏不倚、公正公道。諸葛亮提出“刑不擇貴”“誅罰不避親戚”(《諸葛亮·賞罰》)。只有處理政務杜絕一己之偏私,才能形成公平正義的社會治理局面。最后,“公正”包含了公正的法律和制度。執(zhí)政者和當官者除了要有“公心”,社會的治理還需要以“公心”立“公法”。韓非指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理;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韓非子·有度第六》)。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公正則難以實現(xiàn)。
由此,深受傳統(tǒng)制度倫理影響的百姓在面對社會不公、貪污腐敗的現(xiàn)象時就會發(fā)生群體或個體的道德創(chuàng)傷。魏晉晚期的嵇康,因為對社會政治不公表示強烈不滿,拒絕了司馬昭想讓其在朝中為官的請求,被司馬昭誣陷入獄,行刑的當天,三千名太學生集體為嵇康求情,請求統(tǒng)治者放過嵇康但是最終以失敗告終。“嵇康事件”表現(xiàn)出百姓對當朝者執(zhí)政不公的憤慨。這種就是群體性的道德創(chuàng)傷,即政治黑暗、執(zhí)政偏私現(xiàn)象挑戰(zhàn)了百姓的道德底線,讓社會上的一些人產(chǎn)生顯性隱性的創(chuàng)傷。這種道德創(chuàng)傷就是制度倫理視域下的道德創(chuàng)傷。南宋時期奸臣秦檜對岳飛的誣陷,最終讓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在獄中被殺害。“岳飛冤獄”引起了南宋軍民的強烈義憤,許多百姓為之哭泣。無論皇室或朝廷官員,軍校或布衣,都為岳飛等人鳴不平。可以說,岳飛的冤案引發(fā)了當時的社會大眾群體的道德創(chuàng)傷,扭曲了公平公正的價值準繩。清末楊乃武被誣陷“謀夫奪妻”問成死罪,其胞姐與妻子屢屢上訴,歷時20年,依舊判定死罪。此案一出立刻傳遍街衢,輿論轟動,百姓紛紛控訴大清黑暗腐朽的吏治。可以說,清末腐化的政治生態(tài)使得百姓罹患道德創(chuàng)傷。
傳統(tǒng)文化中的道德價值與當下反道德事件或行為發(fā)生的異質沖突致使人們對自身或是他人行為歸因和評價發(fā)生了偏差,實施道德評判所依附的意義和依據(jù)受到?jīng)_擊甚至瓦解。由此,一些人不同程度地發(fā)生顯性或隱性道德創(chuàng)傷,道德認知體系崩塌,羞恥感、內疚感等負面情感奔襲而來。
3 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下的道德創(chuàng)傷康復療法
傳統(tǒng)文化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認知和道德行為,是道德創(chuàng)傷發(fā)生的文化依據(jù)。而要系統(tǒng)地修復道德創(chuàng)傷,從道德創(chuàng)傷的發(fā)生機理看,需要從道德認知、情感兩方面著手。道德認知是對道德意義的辨認,從而獲取新知的過程,完成“現(xiàn)有”向“應該”的轉化[5]。從發(fā)生機理來看,道德創(chuàng)傷的誘因來自于對他人、自身道德評價和歸因的偏差造成的道德失衡。正確道德認知,把準道德指向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情感是對道德活動所產(chǎn)生的內心體驗和主觀態(tài)度。個體對社會中道德現(xiàn)象和道德行為的好惡、愛憎等情感直接影響了道德原則和規(guī)范的自覺遵守。道德認知和道德情感統(tǒng)一于道德意識,決定個體的道德判定、道德評價及道德選擇。道德認知和情感既是道德創(chuàng)傷發(fā)生的誘因,同樣道德創(chuàng)傷發(fā)生后,在認知和情感上也會表現(xiàn)出相應的癥狀,比如信任危機、內疚感、羞恥感等。基于此,就上述三類道德創(chuàng)傷類型,需要以傳統(tǒng)文化為資源,從道德認知和道德情感兩方面探求可行之道。
3.1 以致知仁愛端正義利觀念
就義利沖突造成的道德創(chuàng)傷,需要借鑒古代的格物致知、仁者愛人的哲學智慧,從認知和情感著手進行修復。
首先,以格物致知端正道德認知。在儒家看來,“道德的力量不僅在于輿論、習俗等帶有某種強制性、范導性的外在行為規(guī)范,而且在于主體要通過教育、習慣等操作將外在規(guī)范內化為道德良心,變?yōu)榈赖滦袨榈膬闰屃Α盵6],這種內驅力就是內在的道德認識。因此,所謂知就是指道德的認識。程朱理學的朱熹說:“知之為先,行之為后,無可疑者。”(《朱子語類》卷九)由此可見,知與行方面,程朱理學主張“致知為先”,比較重視道德意識。王陽明認為“格物致知”是端正事業(yè)物境,達致自心良知本體。如何格物致知,儒家主張通過認識外物之理來明確內心之理,以至達到至善的人生境界。一方面,要反求諸己,先格自己。就是要反思自己的行事與動機,克服不道德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實踐中要探求社會的倫理綱常,即格萬物。關于格物良知的方法,王陽明提出要“靜坐”“事上磨煉”“悔咎”。
落實到治療道德創(chuàng)傷的實踐中,一是通過“靜坐”和“事上磨煉”來提升自身價值自覺。“靜坐”可以培養(yǎng)個體定力,掃除人欲,克服外來的紛擾,克制私欲。靜坐并非絕對靜止,而是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通過靜坐,反思自身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規(guī)矩。靜坐雖是一種修養(yǎng)的途徑,但并非人人都可以練好。所以,王陽明更看重實踐對于個人的磨煉,即“事上磨煉”。這就是要求個體在紛繁復雜的道德實踐中堅守自身良知,堅定道德準則。正所謂“徒知養(yǎng)靜,而不用克己功夫,如此臨事便會傾倒,須事上磨,逆境、困境中磨來,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7]事就是指“人情事變”。“人情事變”的范圍十分廣泛,喜怒哀樂、視聽言動、患難死生,都包含在內。只有經(jīng)歷了事事中的道德困頓,道德意識經(jīng)過磨煉,才能做到遇事能心合符理,時刻省察克治。現(xiàn)實中,要注重道德實踐的養(yǎng)成,要在實踐中堅守自身價值準則,強化定力,以正確的取向引導行為,此外,對于不良的道德行為要及時辨明和處理,扼制反道德行為。二是要通過“悔咎”查明自身,改過自新。“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無過之人在世上是不存在的,而圣人卻能虛懷若谷、改過自新。“悔咎”就是對已犯過失深刻反思并進行及時糾正。悔而能改,則能使人向善進步。這就啟示我們時常審視自身言行,對于不合道德的現(xiàn)象要痛徹心扉,知過能改。
其次,以仁者愛人修復道德情感。儒家講仁愛,注重人的價值,主張把別人也當作與自己同類的人看待,形成良好的道德關系。這種愛不是私愛、偏愛。而如何推行自己“心中之愛”,儒家提出的行為模式是推己及人,講求“忠恕”之道。關于忠恕,朱熹解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8]54就是說對人要奉獻自己全部愛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不苛求于人。在修復道德創(chuàng)傷方面,一方面要發(fā)揮社會組織、家庭的關愛力量,奉獻愛心。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已經(jīng)建立了社會互伴互助小組。其主要方法就是,陪伴于老兵的生活,干預、支持、鼓勵老兵從痛苦和持久的過去經(jīng)歷中解脫出來從而獲取新的意義和目的。治療的核心在于通過發(fā)揮社會力量,信任的重塑,建立團隊信仰[9]。另一方面,不能苛求他人,對道德創(chuàng)傷受創(chuàng)者而言要寬容和接受。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0]61這就啟示我們,無論從事任何職業(yè),要以一種自覺的倫理精神,充分考慮他人利益,講究信譽、樂于合作、互相幫助,使社會形成溫暖的大家庭,充滿向心力、凝聚力,有效防范道德創(chuàng)傷。
3.2 以武德文化塑造正義之師
所謂武德,即是從武、用武、尚武的德性,泛指在軍事活動中形成的倫理思想、價值觀念、道德傳統(tǒng)、行為品質的總和。“忠、智、信、仁、勇、嚴”是武德文化的基本規(guī)范體系。“忠”是歷代仁人志士立身之本、價值之石,忠指忠于國家、忠于職守,忠是一種行為準則,是對國家、民族的一份責任,也是對本職工作的履職盡責。“智”一方面指精武藝、中計謀,另一方面指辨利害。既包含練兵精武、計謀制勝,更具備“明大是大非、權利害得失、謀大勝全勝”的價值追求。“信”是治軍用戰(zhàn)的規(guī)律,對軍官而言,要對部下和士卒示之以信,禮信親愛,對于軍隊群體和領軍人物而言,要取信于民,深得民信。“仁”是武德文化的核心。武德因仁而立,仁因武德而興。武德之仁一是指利國愛民,“以成救國救民之仁”;二是指畜義豐功,就是為國家和人民利益建立功勛和榮譽;三是指珍愛生命,“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是最高的戰(zhàn)爭價值追求。為了多數(shù)人的安寧,殺戮少數(shù)人符合仁的原則;四是愛卒善俘。“視卒如愛子”,優(yōu)待尊重俘虜。“勇”就是敢于攻堅克難的勇氣、維護正義的責任和承擔風險的決心。孫子對于軍人勇德進行了闡述: “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shù)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孫子兵法·勢篇》)“嚴”一方面指人格威嚴,軍官要有至上的權威人格和嚴肅的作風,統(tǒng)帥要高度自律,具有鞠躬盡瘁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治軍善嚴,軍官要嚴格管理部隊,法紀嚴明。武德作為一種深層的價值觀念,具有良好的規(guī)范、激勵和教化作用,可以激發(fā)軍人的榮譽感、正義感,興正義之師。
具體落實到道德創(chuàng)傷的治療上,一方面,要以忠、仁的觀念正確認識戰(zhàn)爭的性質,正確處理人與武器的關系,樹立正確的國防觀。要以武德文化中“安不忘危”“和不忘戰(zhàn)”“安國保民”的忠告和“兵民一體”的樸素的軍事民本主義思想教育民眾和官兵,正確把握戰(zhàn)爭性質,明辨戰(zhàn)爭正義與正義戰(zhàn)爭,激發(fā)愛武、習武的國防文化自覺,激發(fā)官兵保家衛(wèi)國、捍衛(wèi)民族利益的責任擔當。吉林省檔案館公布的侵華日軍檔案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在日本侵華戰(zhàn)爭期間,部分日本軍人厭戰(zhàn)怕死情緒強烈,迫切“想回家”,甚至“想自殺”。與此相反,我國的抗日戰(zhàn)爭和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由于作戰(zhàn)目的和作戰(zhàn)手段鮮明的正義性,鮮有創(chuàng)傷事件的發(fā)生。
另一方面,要以忠、信、仁的武德優(yōu)良傳統(tǒng)正確把握軍人的價值。軍人的價值包含職業(yè)價值和人生價值。關于職業(yè)價值,主要是通過價值關系來認識和確定的。任何軍隊都是國家的軍隊、民族的軍隊,都是為保衛(wèi)本國家、本民族的利益而戰(zhàn)斗的。軍人的價值在于為保國、保民、保族作出應有的貢獻。如孫武所謂“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孫中山“捍族衛(wèi)民者,軍人之天職”等,道出了軍人價值的方向和目標。軍人的價值并非在血與火的戰(zhàn)爭沖突中實現(xiàn)的,孫武所謂“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命題,揭示了和平條件下軍人價值的真諦。關于軍人的人生價值,武德文化認為人格的完善是求發(fā)展的需要,建功立業(yè)是自我實現(xiàn)的一種形式,為國捐軀是軍人人生價值的升華。修德、強體和精武是軍人內在價值提升的有力途徑,因此立足軍旅實踐,勇于獻身是軍人內在價值轉化為外在價值的根本途徑。
3.3 以公正思想強化公共秩序
傳統(tǒng)文化中的公正思想直到今天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那些超越時空和階級局限的思想是建構社會公共秩序,促進社會公正的道德基礎。首先,“天下為公”的社會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在階級社會中成為治國安民的根本哲學,成為仁人志士的社會政治訴求,也是中國政治建設不可或缺的養(yǎng)料;其次,反對分配懸殊,追求社會均等的思想在推動歷史向前發(fā)展中具有時代價值。中國共產(chǎn)黨繼承并發(fā)展了“均貧富”的公正思想,以“共同富裕”為社會公正的價值意愿和價值選擇,是社會穩(wěn)定、長治久安的有力保障;最后,古代思想家主張的“行公法”,作為一種重要的道德規(guī)范,一定程度維護了統(tǒng)治階級的地位和尊嚴。社會的公平公正成了中國民眾心理持續(xù)性的內在訴求。
落實到道德創(chuàng)傷治療中,一方面要積極傳播主流意識形態(tài),以主流價值建構公正思想秩序。面對不同文化、思想意識的沖擊,要發(fā)揮主流價值的正向引導作用,堅持主流的道德價值體系的主導作用,將社會公正的價值觀傳播給社會大眾,增強認同接受度;另一方面,構建平等價值導向,創(chuàng)設平等的機會。社會要注重激發(fā)個體的潛能,消除個體發(fā)展不平等的因素,滿足個體發(fā)展的需求。比如平等、民主的公民教育,參與政治的機會等。同時要致力于社會普遍受益,協(xié)調利益分配機制。“當代中國,原有的不平等和不確定因素因轉型中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而擴散,其負面影響因網(wǎng)絡的不恰當宣傳而擴大。一旦社會無法有效應對,群體性社會沖突將不可避免。”[10]利益分配和協(xié)調機制不完善是群體性事件發(fā)生的主要原因。基于此,黨和政府要著力構建利益表達、利益協(xié)調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平等溝通、協(xié)調機制被確認,弱勢群體受到社會關注,利益能得到有效保障,公共秩序得以構建,社會不公正的負面影響就會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