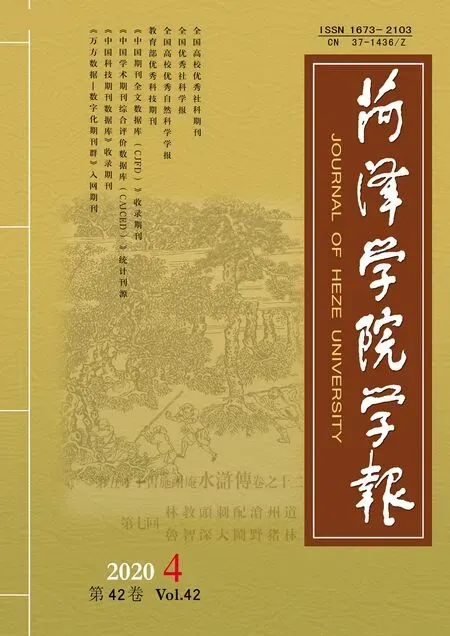《狂人日記》“吃人”問題再探
倪宏玲
(青島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山東青島,266071)
《狂人日記》發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作為五四新文學的肇始,歷經百年仍然煥發出強大的生機。借著狂人日記等創作,魯迅迅速確立了在新文壇上的地位,而《狂人日記》作為魯迅新文學作品的基始,亦對后來的創作有源發性影響。關于《狂人日記》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在學術史上經歷了“現實主義敘事”“啟蒙敘事”“病理學敘事”的脈絡演變[1]。《狂人日記》因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2]。而“吃人”更是這一奇異小說中的奇特之語。
一、“吃人問題”的四重含義
“吃人”,做為《狂人日記》的核心情節,不僅驚心動魄、創痛劇烈,而且是一個“具備深邃情思蘊涵和闡釋空間的意象”[3]。在傳統文學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中,“吃人”并不是問題,讓“吃人”成為問題,是在現代性情境之下發生的。只有在現代性視野之下,吃人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和文化政治問題才成為了一個被反復言說的話題[4]。
關于《狂人日記》“吃人”這一意象的來源,不少作者已經做了系統的探討和言說。比如以李冬木為代表的漢學界強調明治維新以來“吃人”言說對魯迅的影響,認為魯迅筆下的吃人事件是從日本明治時代“食人”言說當中獲得的一個母題[5],而國內學界則更注重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吃人”譜系[6]。有學者指出,“康梁學派”韓文舉所著的《人肉樓》,是吃人言說的現代肇始[7]。
《狂人日記》中“吃人”言說實則涉及了四個層面:生物學、倫理學、社會學、文化學。生物學意義上的吃人,是指人相食本身,例如小說中的陳老五吃人;倫理學意義上的吃人,則關涉到吃人的道德問題,如狼子村分吃“大惡人”,易子而食、割肉療親;社會學意義上的吃人,則是指“吃人”行為所映射的互害型人際關系;而文化學意義上的吃人,則涉及到象征意義上的吃人,也即禮教、文化吃人,四千年的吃人文化。因此,“吃人”成了一個復雜的聚合體。誰在吃人?為何吃人?在吃何人?吃人何果?要理解吃人這一中心事件,需要對吃人的具體發生作一細致探討。
《狂人日記》中的吃人者無處不在,整個鎮上的人互為仇敵,青面獠牙,磨刀霍霍。“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著的,這就是吃人的家伙”。首先出現的吃人者是打兒子的女人:“我要咬你幾口才出氣”。而“我”回到家,則像“一只雞鴨”樣被關了起來。吃人的序幕已經正式拉開。佃戶帶來了“大惡人”被吃的消息。“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壯壯膽子。”且不論被吃者是否真是大惡人(無疑是村人為了吃人而強加的惡名),也無論吃了油煎的心肝是否可以壯膽,僅僅這一帶有狂熱的轉述,便足以激發最野蠻的想象,吃人的快感想象刺激著吃人者的神經。隨后,陳老五也吃了幾塊“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的東西。隨后出現的醫生,顛覆了其治病救人的職業倫理,反而與大哥合謀要吃我,說“趕緊吃罷!”而大哥,亦是吃人的贊成者。“割骨療親”“易子而食”“食肉寢皮”都是為大哥所接受的,“不但唇邊還抹著人油,而且心里滿裝著吃人的意思。”而大哥卻在這種“從來如此”的習俗中,安然自處。
對“吃人主義”的批判,不僅是從民族文化生發出來的啟蒙關切,更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政治。“吃人”,是魯迅通過《狂人日記》系統地塑造出的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符號。“吃人”是實像與虛像的融合,吃人成為倫理禁忌,顯然是現代意義上的事情。有關Cannibalism這一文化禁忌的想象,關聯著人性最深處的幽暗秘境。《威尼斯商人》《三國演義》《水滸傳》《魯濱遜漂流記》《格蘭特船長》《福克》等中西小說中,都涉及到吃人情節。但對于吃人,卻未上升到文化批判的視野。甚至不少作品都帶有欣賞甚至沉醉的意味。這種對人性幽暗的不加辨別的賞玩,無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鋒芒與批判力度。這種傾向以《水滸傳》最為典型。“多餐人肉”的猊鄧飛,善飲“醒酒湯”(人心制成)的燕順、王英、鄭天壽,“吃人心肝”的周通,開人肉黑店的張青、孫二娘……將人“心肝來做下酒”正是梁山好漢的拿手法寶。以李逵生剮黃文炳最為血腥:“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8]而作者不加辨別地夸贊這種豪情,無疑也損傷了作品的思想力度。在法國啟蒙運動中,伏爾泰等人由批判吃人到批判信仰吃人、文化吃人,正是“吃人問題”中現代性的體現。而《狂人日記》正是在這一世界文學的“吃人”言說的譜系之中,發出了自己獨特的聲音。《狂人日記》中“我”對大哥的勸說,正是彰顯出這一現代倫理的作用:“……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后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野蠻的人是吃人的,而只有“變了人”“真的人”才不吃人,而只有被啟蒙了的人才是“真的人”,才不再吃人,不再互害。而從非人到人的跨越,“心思”的不同,正是人道主義的促成。狂人想憑一己之力,詛咒并勸轉吃人的人,于是做出“堅決”而“無用”的吶喊:“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只要立刻改了,也就是人人太平!”這一將來,正是由健全的個人所組成的真人的社會。就此,《狂人日記》也就成為魯迅“立人文學”的起始點,要立真人,首先就是要摒除非人狀態,擺脫吃人與被吃的悲慘境地。
二、“吃人”的情感軌跡:恐怖、恥辱、懺悔與贖罪
《狂人日記》關于吃人的書寫存在著兩條線索,一是四千年的吃人歷史,這條線索已經被諸多學者論及;第二條則常常被人忽略,也即“狂人”吃人的線索。丸尾常喜曾指出,狂人對于吃人的情感,包含了恐怖——嘔吐(他者之恥)——和恥辱(自我的恥辱)三個層次,頗有見地[9]。本文以為,狂人對于“吃人”,不僅經過了“恐怖”和恥辱的情感軌跡,最重要的是懺悔與贖罪的精神向度。從莫名的恐怖,到“恥辱”,再到“自己”的懺悔與贖罪,正是狂人“吃人”精神與情感的變遷軌跡。
恐怖,是狂人處于整體吃人氛圍之下的直觀感受。也是小說文本營造的整體情調。很好的月光下,上演的卻是一幕幕吃人的慘劇,無疑使小說具有了一種暗黑的哥特風格。以“狂人”的視點觀之,周圍沒有任何一個好人,只有吃人者橫行。這是多么恐怖的一幅地獄圖景!在“被迫害妄想癥”的狂人眼里,所有的人都是白牙森森,都想吃人,都想吃掉我。而每一次吃人,都如一場狂歡的盛宴。“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了!”這種恐懼是深入骨髓的,也正是由于這種深層的恐懼,使“我”感受到無處不在的惡意與傷害,甚至覺得連狗都多看我兩眼,有著“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的眼神。而連小孩子也都給“我”這樣恐怖的感覺,更讓“我”生發出徹底的悲觀。一代一代吃人的秘密被延續,小孩子置身于吃人氛圍之中,亦對“我”——闖入者抱以怪異的眼神。
吃人的恐怖,是由吃人群體、吃人社會所帶來的,而吃人的恥辱,則與“我”發生了關聯。原本置身于吃人之事外的狂人,猛然發現自己早已被深深卷入這一吃人活動中。“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此刻,狂人那種優越的啟蒙感開始蒙上了灰塵,因為他發現,自己與吃人者并沒有云泥之別,和大哥——吃人者的血親關系是無法擺脫的,即使死去也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承認這一點才是狂人難以接受的——發現大哥也吃人,使得“我”原本“恐怖”的情感轉向了“恥辱”。大哥淪陷于吃人世界,使“我”無法再以一種高高在上的睥睨態度來審視“吃人”,而是開始意識到,“吃人”與自己密切相關。恥辱感的發生,意味著狂人深層自我的覺醒,也是“我”由懦弱的順從者轉變為勇猛的行動者的契機。正如“幻燈片事件”給魯迅帶來了恥辱感。試想,如果幻燈上那些麻木無聊的看客并非中國人,或許不會對魯迅形成如此強烈的刺激。而正是因為同為中國人,具有同樣的種族歸屬,魯迅瞬間被日本同學同化為幻燈片中那麻木的中國看客,這就帶來了強烈的種群恥辱感。魯迅因之走上了啟蒙文學、改良人生的道路。同樣地,在《狂人日記》中,為了擺脫吃人的兄弟的這種恥辱感,狂人采取了啟蒙行動,開始勸轉大哥,“我詛咒吃人的人,先從他開始;要勸轉吃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不吃人者,才能從蟲子進化為魚鳥猴子,再進化為真人,“要好”的努力而向上。顯然,這是魯迅“進化論”視點的體現。狂人警示眾人、吁求眾人“從真心改起”——“你們可以改了”“你們立刻改起”,正是其啟蒙精神的強烈爆發。這種大聲疾呼,在五四熱潮中,也激動了不少青年的心,成為他們覺醒與反抗的利器。
然而,如果狂人僅僅從吃人中得到恐怖和恥辱的情感,如果魯迅僅僅刻繪出狂人恐怖和恥辱的情感,那么這篇小說當不起五四新文學的偉大開端。真正讓吃人事件發生反轉的,是狂人發現,自己也難免吃人,由此陷入無可逃遁的黑暗與深重的懺悔之中。“狂人”被徹底卷入這一吃人的閉環之中——吃人者終究被吃,我吃了小妹妹,我終究要被吃掉。“狂人”加入吃人的陣營,這無疑是自視為啟蒙者、光明者、真人的狂人最深重的悲哀與罪愆。這樣,四千年吃人的歷史與狂人“吃人”這兩條線索就形成了互動,也立體鉤織出吃人文化傳統的痼疾。因為“我”內在于社會,“我”和社會的罪惡形成同謀關系。“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痛恨詛咒吃人者的狂人,意識到這一黑暗深淵的深邃,將民族的恥辱與個人的恥辱相互勾連,并將民族罪愆等同于個人罪愆。“我”從小便接受了大哥關于“吃人”的教育,“我”置身于吃人的文化傳統之中,無可逃脫。最震悚的地方則在于,高呼要他人“改了”的“我”也吃過人——“我”也在吃人!我也吃了小妹妹的肉并且不自知:“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這一事實的發現,改寫了受害者狂人的形象——狂人亦是加害者。也即,在文化傳統中,無人幸免于難,也無人有資格置身事外。
至此,狂人形成了一種近似于“原罪”的意識。“狂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獨善其身的先覺者和審判者,而是有罪者和被審判的對象[10]。使其“民族的自我批評”的文學成為真正的“自我批評”的契機首先由此生出[11]。啟蒙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審判者,而首先是一種充分的自省者,這也是魯迅超出同代人的地方——后者往往忘記了,所謂啟蒙,首先是對自我的啟蒙,意味著對于自我創傷經驗的清理,意味著首先進行自我的贖罪與拯救。在《狂人日記》里,所謂覺醒,所謂自我的啟蒙,意味著最終對“恥辱”的自覺,也意味著深刻的懺悔、承擔與贖罪。在這一意義上,啟蒙文學,由此成為一種懺悔的文學與“贖罪的文學”[12]。正如竹內好“從《狂人日記》背后看到了魯迅的‘回心’ (類似于宗教信仰者宗教性自覺的文學性自覺) , 并以此為‘核心’確立了‘魯迅的文學可以稱為贖罪文學’這一體系”[13]。伊藤虎丸把狂人“我也吃過人”這一震悚的認知稱之為 “加害者有罪意識”的自覺。而吳曉東則認為,這種認知實則是狂人對自己的“原罪”意識的自覺——對于“我”與舊時代深層聯系的追認,是贖罪文學得以誕生的契機[14]。而魯迅的寫作也就成了一個曝露自己的罪責,以期獲得救贖的過程[15]。在懺悔意識與贖罪意識這點上,魯迅使他所提倡的啟蒙文學因之具備了世界文學的特質。懺悔之后又如何贖罪?讓黑暗止于自己這一代,為了后續的“新人”而自覺“犧牲”,這便是魯迅采取的態度。“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6]。面對殘酷的現實,將希冀寄托于孩子身上,亦是魯迅進化論視點的體現。孩子被看做是光明的可期許的未來,是進步的力量,是新生的要素,成人世界已無“真人”,而“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因此,為要破除這吃人文化,除了自省、悔罪、承擔,最重要的是“救救孩子”。由此,從“吃人”的恐怖、恥辱到懺悔與贖罪,這一情感變遷的軌跡背后,正是魯迅精神史的微觀再現。而只有通過文學的吶喊,才能反抗絕望、黑暗。而這種無聲、持久的吶喊,也正是魯迅希望通過文學之力量進行國民性啟蒙所進行的韌性持久的努力。
“吃人”是《狂人日記》的核心情節,它包含了生物學、倫理學、社會學和文化學的多重面向。而“吃人問題”所生發的文化隱喻,在現代文學史上得以延續,是作家們借“吃人”表現出對文化與人性的最激烈的批判。不管是《鄉村的教師》中吃掉同伴的吳錦翔,還是《酒國》中大啖嬰兒宴的諸人,抑或是《黑石頭》中真實的食人事件,都顯示出作為《狂人日記》中心情節的吃人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文化意義。由“吃人問題”所生發的文化批判與贖罪意識,顯示出魯迅作為文化啟蒙者的深刻的自省與沉重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