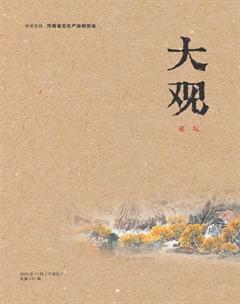大眾時尚與集體選擇
摘 要:趣味是時尚運作的核心要素。在一定意義上,時尚的發展邏輯決定了它對于趣味的更替與調適最為敏感,也最容易體現出與審美因素相關的諸多改變。同時,“趣味”這一概念既涉及個體的審美訴求,也關系到集體的審美選擇。而時尚正是將這兩種相反的力量結合起來的社會形態,它一方面基于對個人品味的私人主觀偏好,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具有社會約束力的行為標準。此外,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競爭模式導致了品味的不斷提煉以及分類的持續細化,這在催生了社會合法性趣味的同時,也導致了趣味標準的相對化。
關鍵詞:時尚;趣味;集體選擇;媚俗
注: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基于前沿交叉學科范式的藝術教育研究”(2020SCG182)研究成果。
科林·坎貝爾(Colin Campbell)曾指出:“時尚與趣味之間存在著重要的聯系。”[1]而時尚的中心議題恰恰是時尚與趣味、風格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風氣與趣味究竟誰帶動誰的問題。因此,關鍵在于如何對時尚中的審美因素展開探討,尤其是審美選擇與時尚的運作方式在現代社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審美因素在時尚中的著力點是否由此發生了改變。因此,審美在時尚中的定位是不斷變動的,它時刻處于個人的審美偏好以及集體的共同選擇之間,由此構成了審美感知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一、作為集體選擇的時尚
對于時尚工業的具體發展而言,社會學家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曾在其文章《時尚:從階級區分到集體選擇》中,根據對戰前女裝業和時尚之都巴黎的考察,分析了集體品味的形成過程。他認為,集體品味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共同構成了時尚領域的重要問題,而以下三個議題則為理解時尚提供了線索:首先,時尚的設定實際上是通過激烈的選擇過程進行的,這一過程體現為設計師代表、時裝公司管理團隊以及買方所共同構成的集體選擇的利益鏈條。其次,布魯默以此描述這些獨立選擇之間的驚人融合——“買家們沉浸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氛圍中”[2]。由于這種“強烈的沉浸感”,買家逐漸形成了共同的感知力和審美偏好,并以此表達了共同的品味。根據布魯默的說法,作為時尚領域的專家或內部人士,他們都積極參與了對女性時尚潮流的激烈討論,對時尚刊物的熱切閱讀,以及對于彼此產品線的密切關注。與此同時,這些買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充當了時尚“不知情的公共代理人”。
當代時尚史學家吉勒·利波維茨基(Gilles Lipovetsky)進一步闡釋了這一兩難問題,盡管他未能明確地提到這一討論,但卻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證明了布魯默和戴維斯立場的相對有效性。根據利波維茨基的說法,時尚以法國時裝公司所代表的經典高級時裝形式得以展現,并由此開創了一個將官僚制度與大眾民主相結合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時尚在一定程度上是這種社會過程的早期例證,它極為鮮明而普遍地表征了我們所處的社會。
二、從趣味的社會等級到大眾時尚
就現代大眾消費而言,社會競爭的模式導致了品味的不斷提煉以及分類的持續發展。由此,現代享樂主義的消費存在著狹義的社會基礎:新的享樂主義者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一員。同樣,新的趣味總是被理解為占據文化霸權的反傳統地位。正如齊美爾所指出的那樣,時尚被界定為一種新穎的、與傳統不同的東西,它更為突出地體現在“社會認同模式”及其消費影響之上,并鮮明地展現了現代消費的主要特征:對新穎的持續需求以及由此產生的消費和創新。對此,利波維茨基特別強調這一模式下的時尚:“是什么導致了奢侈消費的規則變成了一種珍貴的優雅?我們總是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超越奢華本身的變化和奢侈的升級?如果反對當下流行的理論,那么則有必要重申,這類競爭是時尚潛在的、不斷變化的原理。”
在理解現代消費和趣味的社會意義方面,還有另一種方法似乎更具啟發性,即,在齊美爾和科林·坎貝爾的理論框架之下,進一步分析消費的動力和時尚的社會機制,及其與趣味相關的發展過程,而并非假定任何層次鮮明的、有序的生活方式和品味。
三、時尚中的壞趣味:媚俗與品味的敗壞
關于奢侈或不必要的消費——超出必要性的消費——的討論在18世紀的英國尤為廣泛,特別是在分析社會問題及其起源的時候。奢侈的腐敗觀念可以追溯至古羅馬和基督教的道德哲學傳統,它一度被界定為從傳統限制中解放出的恐懼,因為人們的需求根本無法完全得以滿足。對此,戈夫曼(Goffman)就曾指出,如果所購買的商品明確地指示了特定群體成員的地位與資格,那么則可說此類商品具有展示地位象征的特性。這些符號只有在限制其“欺騙”效用的機制下才有效。在戈夫曼這里,“欺騙”意味著社會成員不能確定這些符號所具備的社會地位。在他對地位象征的分析中,有幾種不同的機制可以限制這些對象的不當使用。最明顯的是貨幣價格,但同時還有時間、社交技能以及家族史等,同時,對商品實施的禁奢法也是一種明顯的限制。
如果昂貴的東西確實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和美好的,那么,為什么它們并非真正的美呢?更重要的是,盡管我們天生有美感,但審美對象并沒有因此變得更美。根據凡勃倫(Veblen)的觀點,人有兩種美的感覺:金錢至上的美和所謂真實的或天生的美。物品越昂貴,就越被視作是美的。因此,任何手工制作的東西不僅比用機械制造的東西更昂貴,而且更漂亮。從凡勃倫對時尚機制的特定描述來看,這一點尤為重要。事實上,這同時也是兩種不同的美的法則相互作用的問題。如果時尚只遵循“金錢之上的美”的原則,那么我們所使用的物品就會變得越來越昂貴且不合時宜;如果僅僅遵循審美的原則,我們對美的自然追求,就會逐漸走向審美概念的完美化。顯然,這一理想情況從未發生過。時尚始終涉及這兩個原則之間的永久性變化,這也就是為什么自然的趣味不時地糾正了時尚過度性的原因,這在本質上是一種內在的排斥:“我們總是短暫地依附于最新的時尚,但這并非基于審美的理由,因為它伴隨并依賴我們持久的美感來維護自己,但同時又拒絕這個時刻更新的難以自洽的機制。”[3]
總而言之,凡勃倫對于炫耀性消費的批評似乎基于這樣一種觀念:金錢美的原則導致了過度和怪誕的表現,而這正是美感所要排斥之處。盡管凡勃倫的分析涉及與社會競爭以及趣味區分相關的各種研究,但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于,社會競爭如何與不同的生活方式相關,以及它們如何培養和提高了品味。在這一點上,質量和風格將重新塑造細微卻重要的差異。隨著社會等級中好的趣味標準的降低,口味也將隨之變得庸俗化,消費品則日漸成為重要的地位標志,并將個體從生活方式的原始聯系中分離出來。這也由此成為一種可以自由變動的生活方式,并同時作為社會價值的顯著標志而發揮作用。這正是凡勃倫所描述的膚淺和劣質趣味的突出特征,它同時也構成了媚俗時尚的核心議題。
綜上所述,時尚趣味與集體選擇的核心在于如何衡量時尚共同體與審美共通感之間的真正關聯,抑或如何厘清趣味合法性與審美的社會等級之間的本質關系。同時,就現代大眾消費而言,社會競爭的模式還導致了品味的不斷提煉以及分類的持續發展。在現代享樂主義消費的前提之下,時尚更為突出地體現為“社會認同模式”,并鮮明地展現了現代消費的主要特征:對新穎的持續需求以及由此產生的消費和創新。通過享樂主義的新生活方式,新興階級可以從社會競爭中脫穎而出,并將自己的道德和審美對立于統治階級,從而逐漸形成普遍的合法性趣味。此外,浪漫主義導致了趣味標準的相對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對于傳統審美準則的尊崇。通過對潮流、時尚、媚俗的劃分,時尚壞趣味的流行歷程得以進一步凸顯,并由此體現了時尚潮流如何受到媚俗藝術的裹挾與影響。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更為清晰地展現時尚的趣味生成機制。在一定意義上,時尚與先鋒存在著一定的邏輯相似性。先鋒派的目標是要創造出一種不可能被超越的絕對的“新”,而時尚本身也需要以不斷更替的創新風格作為自身發展的原動力,因此在這一點上,二者是重合的。但也正是在這種永不停歇的求新過程中,審美標準的傳統定位得以動搖,而社會流動性又導致了既定趣味結構的瓦解。在這一意義上,時尚在資本主義邏輯中最終與媚俗藝術形成了合謀。
參考文獻:
[1]CAMPBELL C.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M].New York:Basic Blackwell,1987:2.
[2]BLUMER H.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J].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69(1):279.
[3]VEBLEN T B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New York:Elibron Classics, 1961:132.
作者簡介:
熊亦冉,清華大學哲學系美學專業博士,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社會學系訪問學者。浙江財經大學藝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