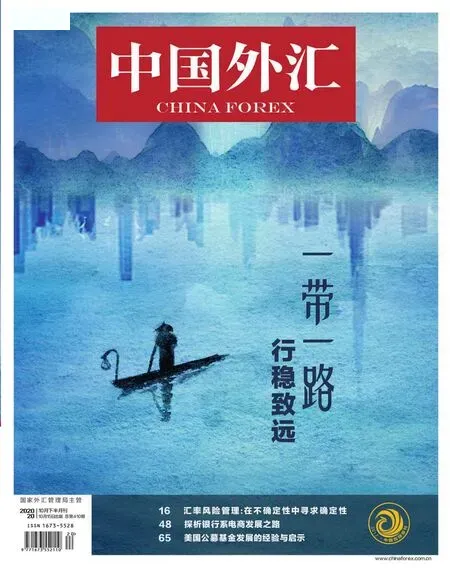匯率風險管理: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確定性
文/高銘 編輯/王亞亞
企業管理匯率風險,更重要的是平衡成本、風險與收益之間的關系。這需要企業以專注主業、穩健經營為目標,選擇適合自身的避險交易策略,將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變成確定性。
2020年5月美元兌離岸人民幣創年內新高后,人民幣一路升值超5.8%;但近一個月(8—9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超1.5%。如此大的波幅,大大影響了許多盈利能力較差的中小外貿出口企業的凈利潤。外匯市場較大幅度的波動給企業的經營管理帶來了挑戰,如何控制財務成本、加強匯率風險管理,是企業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
新形勢下企業匯率風險管理再自查
當前,歐美依然飽受疫情之苦,全球金融經濟環境也已生變。美元隨疫情發展開始了震蕩下跌的走勢。8月底美聯儲調整通脹目標后,美元愈加承壓;但9月后,隨著歐洲疫情再度復燃,美元開始弱復蘇。
作為新興市場貨幣代表的人民幣,得益于美元趨弱、中美利差擴大以及良好的疫情控制等因素而不斷走強,自2020年5月起,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進入下行通道。不過,在多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下,未來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波動將增大。總體而言,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具備升值基礎,但人民幣匯率仍處于雙向波動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外貿企業面臨的匯率波動風險也在加大。
目前,仍有部分企業匯率風險管理意識淡漠,主要是三種情形:一是完全未將匯率波動帶來的匯兌成本波動納入企業財務管理。這主要存在于多數小型外貿企業。這些小型企業本著“不做不錯”的原則,認為金融市場波動是天然存在的風險,無法規避。一旦金融經濟環境產生重大變革,這類企業就會面臨巨大虧損,甚至侵蝕主營利潤。二是部分企業過分套保甚至投機,寄希望于通過外匯交易來獲得額外收益,將精力過多用在判斷或投機匯率趨勢上,對賭匯率升跌,并為此故意擴大敞口、追逐風險,最終結果只能是得不償失。三是部分企業已經認識到了匯率風險的影響,并建立了相應的匯率風險管控機制,但面對復雜繁多的外匯衍生品,仍然存在認知偏差,本質上沒有形成正確的套期保值觀念。
在當前新冠疫情沖擊以及中美貿易爭端不確定性增強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不確定性也在提高,匯率波動的彈性空間在加大。在這一形勢下,外貿企業更應樹立風險中性理念,不要盲猜匯率走勢,更不要拿所謂的歷史經驗來判斷市場未來的變化。即使外匯市場的走勢有一定規律,周期性回歸會出現,但這個周期究竟多長?是多少企業能跟著耗下去的?因此,外貿企業在匯率避險操作中必須立足主營業務,嚴守套期保值原則,以降低實貨風險敞口為目的,與實貨的品種、規模、方向、期限相匹配,與企業資金實力、交易處理能力相適應,把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變成確定性。這才是企業進行實際匯率避險操作時應有的態度。
當前,外匯市場主流的匯率管理衍生工具是遠期、掉期和期權(組合),種類繁多。下文以具體案例說明對于不同經營狀況和市場預期的企業,有哪些不同的避險交易操作。企業可結合自身情況,根據自己匯率避險的需求,進一步明確交易策略。
“量身”選擇避險交易策略
案例一:某外貿企業A定期有美元收入,需要結匯成人民幣,對于未來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這種情況下,企業A可以選擇賣出USDCNY(美元兌人民幣)遠期鎖定匯價。假設目前USDCNY即期價格在6.82左右,一個月掉期點在170點左右,選擇期初或分批次進行遠期結匯,一方面可完全鎖定結匯價格,平抑市場波動的影響,且操作簡單;另一方面,還可以獲得因人民幣遠期升水而帶來的掉期點收益。

圖1 企業A遠期結匯損益

圖2 企業B賣出風險逆轉組合損益

圖3 企業C買入看跌期權損益

圖4 企業D買入看跌價差期權組合損益
遠期鎖匯的交易策略是直接鎖定匯價,與期權等其他衍生工具相比缺少靈活性。如圖1所示,如到期時人民幣不升反貶,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價格高于6.84的鎖匯價,則企業A無法享受這部分收益。但從企業風險管理的角度看,企業通過遠期鎖定匯價,完全規避了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
案例二:某出口商B定期有美元需結匯為人民幣,認為短期內美元兌人民幣更有可能呈區間震蕩,且希望能盡量降低風險管理成本。這種情況下,企業B可選擇賣出USDCNY風險逆轉組合,即買入較低執行匯率(6.7)的美元兌人民幣歐式看跌期權,同時賣出較高執行匯率(7.05)的美元兌人民幣歐式看漲期權,鎖定遠期匯價。到期時,如USDCNY市場價格在兩個執行價之間波動,企業B可自由地按照市場價結匯;如USDCNY市場價高于7.05,企業B對賣出的看漲期權行權,意味著企業B需以7.05的結匯價格結匯;如市場價格低于6.7,則企業B對購買的看跌期權行權,意味著企業B需要以6.7的價格結匯。
風險逆轉組合為企業提供了一種零成本或低成本的避險工具。通過賣出期權獲取權利金收入,還可以彌補買入期權的支出。同時企業還將結匯價格錨定在了一定的區間,在平抑匯率波動的同時不失靈活性,還回避了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尾部風險。如圖2所示,通過這種期權組合的方式,企業B可將結匯價格鎖定在6.7—7.05這個區間內,若一個月內人民幣大幅升值1.8%至6.7以下,企業B可以6.7的保底價結匯,因此完全鎖定了美元相對人民幣大幅下跌的尾部風險。該種策略的缺點在于,當人民幣大幅貶值時(本案例中大幅貶值3.3%至7.05以上),企業B需以低于市場價的執行價結匯。
從交易策略本身看,風險逆轉組合在價格大幅上漲時處于不利地位,交易者會面臨無限損失;但從企業匯率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由于企業B本來就有結匯需求,因此企業整體只是相當于放棄了人民幣大幅貶值后的部分潛在收益。而且在通常情況下,鎖定的上限結匯價格(本案例7.05)優于同期的遠期結匯價格(案例一的6.84)。

企業匯率避險操作情景模擬比較
案例三:某大型國有企業C出口商品,一直有結匯需求,預期人民幣會大幅波動。這種情況下,企業C可以選擇購買USDCNY歐式平價看跌期權,通過承擔一定成本來獲得相應的權利,從而鎖定USDCNY匯率下跌的風險。到期時,如果人民幣大幅貶值,USDCNY市場價格高于執行價,則企業C可以選擇不行權,直接按即期價格結匯,僅損失期初支付的期權費;如果到期時人民幣大幅升值,USDCNY即期價格低于執行價,則企業C可以按照期權執行價結匯,規避了價格大幅下行帶來的風險。
如圖3所示,相比于遠期鎖匯,購買看跌期權不僅可以使企業C獲得遠期保底結匯價格(6.84),規避了人民幣升值時的風險;同時還可以享受到人民幣貶值帶來的好處。這種對沖方式的缺點在于,目前人民幣雙向波動幅度加大,其隱含的波動率也處于高位,購買期權的成本較高(本案例中期權費為0.58%左右),因此,在扣除期權費成本后,企業實際鎖定的價格會比執行價低。
從交易策略的角度來看,購買看跌期權的成本較高,如果到期之前匯率點差波動小于支付的期權費的點差,其結果可能不如遠期結匯;但從企業匯率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企業通過支付一定費用而獲得了比遠期結匯更多的權利,既能得到人民幣升值時保底結匯價的保護,又能享受人民幣貶值時的潛在收益。若到期時美元兌人民幣大于6.84,雖然期權沒有行權,但因企業有看跌期權的保護,可以專注主營,安心以優于同期遠期價格的市場價結匯。
案例四:某大型國有企業D出口商品,定期結匯,預期未來美元兌人民不會大幅波動,人民幣溫和升值的可能性較大,同時其不愿承擔過高的風險對沖成本。這種情況下,企業D可以選擇購買USDCNY看跌期權價差組合,即購買較高行權價(6.84)的歐式美元兌人民幣看跌期權+賣出較低行權價(6.7)歐式美元兌人民幣看跌期權。通過賣出一個價外期權獲得的期權費來補貼買入期權所付的期權費,從而降低一部分對沖成本,同時也鎖定一部分人民幣升值后的匯率風險。如圖4所示,若到期時市場價高于6.84,則兩個期權都不行權,企業D享受人民幣貶值后的高價結匯;若到期時市場價低于6.7,則兩個期權可同時行權,企業賺取兩個行權價的差額,同時以低于6.7的市場價結匯;若到期時市場價格位于6.84和6.7之間,購買的看跌期權行權,企業按照6.84結匯。
不同于購買單一看跌期權,這種對沖策略的成本較低(本案例中期權費為0.44%,低于案例三中的0.58%),但需要對匯率的走勢方向有基本的判斷。如果人民幣小幅溫和升值(升值幅度不超過1.8%),美元兌人民幣在6.7以上波動時,企業的匯率風險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最多損失期權費;但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超過1.8%),企業則有面臨匯兌損失的風險。
從交易策略角度看,當美元兌人民幣價格下跌至6.7以下時,兩個看跌期權同時行權,交易者可以賺取行權后的差額收益;但從企業匯率風險管理的角度看,若到期時兩個期權同時行權,企業則喪失了保護,需按照市場價結匯,匯率風險暴露。
事實上,不同的衍生工具可以組合出幾十種適用于各種情景的對沖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種策略是完美適用于所有市場情形的,有得必有失,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這也提醒企業,在進行匯率風險操作時,要機動靈活,不要迷信某一種或幾種策略,更不要過分追求完美的結果。比如,通過情景模擬對比(見附表)可以看出:對于出口型企業來說,遠期鎖匯最考驗市場走勢,在當下人民幣升值的大趨勢下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然而,一旦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往相反方向發展,其面臨的匯兌損失風險也最大。購買看跌期權雖然支付的對沖成本最高,但企業結匯的靈活性也最高,既可以按人民幣貶值后的較高市場價結匯,也可以按人民幣升值后的保底價結匯。因此,企業管理匯率風險,更重要的是平衡成本、風險與收益之間的關系,要以企業專注主業、穩健經營為目標,而非簡單根據到期日的即期匯率來評判交易策略的好壞。不同的外貿企業有不同的市場預期和差異化的風險管理需求,外匯衍生品形式繁多且應用靈活。只要企業樹立理性的外匯風險管理意識、選擇好避險工具,就可以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有效防范外匯市場波動所帶來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