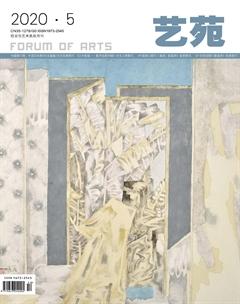由此及彼
【摘要】 孫志純的新作采用了與他慣用材料不同的丙烯,丙稀顏料給他帶來了全新的感覺。他的這批新作已不再是觀察后的作品,而是思索引導的創作之果。那些感覺似乎是偶然來到,但是那些偶然來到的、那些刮刀帶出來的跡象,卻是畫家內心里想要迸發出來的心聲。
【關鍵詞】 孫志純;“純屬偶然”;審美意向;人性
[中圖分類號]J22 [文獻標識碼]A
前兩天孫志純先生發給我28幅新作,打破了我對他的作品漸漸形成的固有感覺,假如不是他親自發給我,還真不敢相信是他的近期作品。緊接著,他又發來一張他的個展即將開幕的請柬,四個醒目的展覽主題“純屬偶然”。因無主語,亦沒賓語,“純屬偶然”就有了特別的理解空間。在他的審美路線上,出現純屬偶然的偶然之作,這些新作采用了與他慣用材料不同的丙烯,丙稀顏料給他帶來全新的感覺。也不完全是材料媒介引起的改變,說得嚴重點,應該是他對自己的創作路線作了審慎的思索,思索引導他的審美判斷。他的這一全新感覺是反著來的,與他一貫以來的審美趣味截然不同。以前他是通過觀察引導審美,讓內心情感與外在的感性感覺混為一體,這批作品與之前的語言風格截然不同甚至大相徑庭,那么這個全新感覺是其語言個性的一個延續還是否定?
不管是濃烈的色彩處理,還那些大刀闊斧的筆觸,都像是一陣強烈的臺風,將他之前所有作品的感覺一掃而空,即便全新的導航系統亦難找到他的審美家園。難道是他的盛年變法?這個念想閃過,再回首孫志純先生的每一幅新作,那種堅決果斷率性躍然畫上,我的眼前浮現一位朝氣蓬勃的畫家形象,這個形象釋放出某種超然物外的自信。審美是感性的現象,那種觀察得來的審美更多的是自然之存在,而思索引起的審美帶有更多的內在力量,超然物外的自信或許是內在力量的外顯。新作中有一幅作品用那么純粹的藍色,純粹到讓眼睛感覺炫目,似乎是群青,又比群青略微厚實沉著,使我想起他以前水彩作品的那種飄逸而簡約的風格,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每一幅新作的色彩遠比之前水彩作品濃郁,可能是丙烯引起的飽和度,但我想不能歸結于丙稀顏料帶來的結果,因為丙烯材料同樣可通過稀釋使其清淡。那么在創作前他想過這個問題嗎?他的創作動機可能與之前的作品沒關聯性,但任何一幅作品都是畫家內在性之外化,他不可能沒有意識到新作與之前自己求索的審美趣味之間的差異。假如現在的創作與過去還有聯系,那么其新作系列的審美趣味是對以往作品的一個否定。
否定的說法可能過于武斷,可能是之前審美趣味的發展,可以說是之前語言形式的反向變化。不管是變化還是發展,審美可以完成自我的循環,當它循環到相反的那一面,呈現出來的變化就包含部分的否定,也可能是對之前的肯定后之否定。這個否定或許不是審美層面上,而是對被描繪的物質性現象之否定,因為之前的美感包含更多的物質性,而這次新作是有一個從物質性回返心靈的跡象。感性的印象是一個物質性記憶,再怎么經過技術處理,那個記憶仍然是物質性幻相,當畫家意識到這個物質性幻相的時候,就很想從物質性那里走向精神,人都是精神動物,何況畫家!
從物質性那里走向內心,必然要經過一個懷疑環節。懷疑曾經的執著,懷疑那些好不容易得來的表現技術,懷疑這懷疑那,最終回到對自己的懷疑。懷疑自己遠比懷疑真理痛苦得多,只有自信的藝術家才敢于質疑自己。在這里用懷疑、質疑、否定這些字眼,好像越過了審美界限而到達那個思考的范疇,思考無時無刻不在跨界,也只有思想能夠走得很遠,當畫家走到很遠的那個點上,他仍然可以在那個點上面建立全新的感覺,所以他的這批新作已不再是觀察后的作品,而是思索引導的創作之果。那些感覺似乎是偶然來到,但是那些偶然來到的那些刮刀帶出來的跡象,卻是畫家內心里想要迸發出來的心聲。
這里出現一個反諷的現象,我們不妨稍作分析。那些來到刀下的色彩形塊,已不再是具象的感受,又怎么能被說成是畫家心里的情感流露呢,是不是畫家愛咋樣就咋樣,外人又怎么相信畫家的意向性選擇呢?越往精神去的作品越抽象,越走向自我的個性化作品越難被理解,超凡脫俗總是與流行的審美意識格格不入。偉大的藝術都有那種令人不悅的因素,因為那是一個召喚,將審美判斷從熟悉標準引導到陌生感覺,好像審美有一個否定式可能性。審美感覺順著自然去,還是源自自然又悖逆自然,畫家為什么不愿停在自然感覺那里,為什么不直接表現那些有形的自然而選擇那些無形的意向。當畫家想透一切之后,就想著從有形的約束那里逃向自由,就想著從物質性沉重那里釋放出輕松,當所有離個體而去時才能意識到什么是畫家自己真正的存在。這就是真正大家最終都走向精神性表現的原因,孫志純先生近期作品之蛻變是一個不易的掙脫。
從感性對象那里掙脫出來,因為被畫對象還是那些自然現象,作畫過程必有一個掙脫,使那些來到畫家內心里的激發已不再是自然的感覺,好像那個激發里多了一口氣,他要將氣吐納出來,好像要將那些自然對象經過一個刮垢磨光的過程,使之符合內心里那個審美意向,而這個審美意向只有經過心靈過濾之后,才能以陌生感突發出偶然的一剎那靈動,那些分不清是感覺還是悟得的形與色隨刮刀順勢而來。到底是刮刀帶動情緒,還是情緒推動刮刀,估計是一個懸案,即便畫家本人亦難細究。就像休謨弄不清楚是印象先于觀念還是觀念隨印象而來,果可能是因,因即是果。觀賞他的這批新作,可感受滾滾而來的情緒,作品已不再是自然的反映,而是畫家內心情緒的釋放,情緒使這批作品有溫度,那種感人的激情。情緒是偶然的現象,“純屬偶然”似可詮釋為偶然之情緒,唯有情緒是心靈最真。當然不能說之前的作品不真,那時候其作品的真是對自然的反映,而現在作品之真是發自內心,因此,在他的創作過程中發生了一個由此及彼的轉向,從物之描畫朝向心之呈現,心之所向不再是偶然,更是藝術之必然。
“純屬偶然”可能是一個偶然來到心里的念想,但作為一個創作個案來說,卻有一個不是偶然的創作問題,值得我們將它提出來。創作到底是一個先因后果還是先果究因的現象,因果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邏輯關系?首先要考察孫先生的審美意向如何產生的問題,我們可以懷疑在他的頭腦里存有那些形式化意向,那些意向形成很可能是丙烯材料在制作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換另一個畫家都會出現同樣的作品。這個說法全部否定了前文所有的分析,材料決定論肯定不等于藝術思考,藝術思考也不是材料媒介所能替代得了的。材料媒介再怎么神奇,終歸是物質,物質有其自身的變化規律,它不可能自身變為精神,它要有精神的活動。只有畫家的內心活動才能使材料媒介鮮活起來,于是就有畫家想畫畫到了那種不畫畫難受的程度,畫畫似乎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孫先生之前就做了這件很簡單的事。當他把很簡單的事做到很不簡單的時候,他發現那不是他的審美歸宿,于是有了這批蛻變的全新作品。這不是小說式的夸張語言,可能帶有點不經畫家認可的隨意揣測,還好,學術分析允許邏輯推理,我奉勸自己一定要合情合理看問題。
事實上,畫家作畫完全是一件求情求理的事,就是要在那幅作品里有自己的情又合自己的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孫先生之前的作品,恕我冒昧,情理之中有余,意料之外不足。這只是一個概觀式判斷,主要是為了文章分析之便,可能與真實情況不符。應該說孫先生最早那批簡約的水彩作品,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在他的心中有股濃厚的情,那些簡約的水彩形式感形成了他的審美之理,同時又有那種簡約處理帶來的驚奇。但藝術之悖論是一個畫家不可能重復一個感覺,他漸漸地回到感性世界,那個感性世界足夠他畫一陣子,他的處理技術與內在境界越來越純熟,也在這個過程中登上了情理之中的巔峰,到了不必看標簽即可辨識他的作品。發展到了這個程度,畫家是功成名就,等待不斷傳來的贊美之聲。他不是到此為止容易滿足的畫家,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對他感佩至深。
否定別人容易,否定外在事物不難,唯獨否定自己不易且難。何況是否定自己曾經獲得的成就,否定可能不是一個嚴謹的詞,質疑會更加確切一些。質疑早期作品里那些情與理,那些真情與那些越來越貼近自然的理,自然在他的手里變得順從。意料之外沒有了,之前的創作活動告一段落,這期新作使人耳目一新,意外的驚奇再次來到作品里。可以感覺到他在這批新作的創作狀態,肯定是那種一鼓作氣而浩然率真,一種深入到內心里的任性,好像要把慢慢在內心里形成的意向呈現出來,到了那種不如此不痛快之境。
分析到此,畫家內心里的那個審美意向源自哪里的問題,似乎有那么點清晰起來了,審美意向是源自自然又從于內心。從于內心的成分多了,意料之外的形式感更強,順乎自然的成分多了,看似合情合理也使人愉悅,缺少了一點使人不悅之感。藝術作品到底要使人愉悅還是令人不悅,這或許是一個無法論證的問題。但是,有一條律令是所有事都要符合人性,既要符合審美形式,又要發自畫家的心性。
孫先生心里開始有了質疑,可理解為心性不老,也是他的生命力旺盛之征兆,他已到了那種不順心不罷休的創作高度。一件好的作品肯定是要符合畫家的心性,至于個性語言要不要符合自然之理尚需要更多分析,假如藝術是精神產物,那么它要回到人性。而人性,只有人性,才是藝術最后的歸宿。
作者簡介: 黃永生,集美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福建省美協水彩畫會副會長,福建省美協水彩藝委會副主任,全國水彩高級研究專業認證委員會特聘導師,廈門水彩畫會會長,廈門桃源書畫院院長。